剧情介绍
在不久的将来:一股强大的全球恐怖势力袭击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基地,导致石油价格飞涨,进一步恶化了全球经济危机。这种动荡的局势引起了很多事端。汽油和食品的供应短缺以及持续减少的福利拨款激怒了老百姓。原本用来填补贫富差异的本就脆弱的社会凝聚力如今已趋于瓦解。与此同时,左翼与右翼集团中存在的极端政治势力急切的希望重新激起众怒——一部分原因是企图在政府选举的民意投票种夺取有利的地位。极端的右翼分子组建了一支由马克西米利安·施奈尔担任主席的新政党。他巧妙的运用巨额公共宣传投资得到了多方支持。施奈尔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人:权势——他唯一的兴趣所在——使他成功的从一个激进的左翼活动家转型为权利的追逐者。施奈尔承诺建立一个脱离其他国家的自由的政府。为了阻止这个可怕的事情发生并且控制住即将恶化为国内战争局势,政府秘密的支持处在优势地位的新成立的候选党派。他们必须在两个...陌陌影视陌陌影视重返青春期2018恋爱这件事儿窈窕美眉得到我 恋路篇幸福保卫战老九门(剧情解说)泡菜奶酪微笑黑暗球体等到烟暖雨收电影版我心永随桑德兰第二季乔老爷上轿尼罗河的新娘60岁小姐狄仁杰之异虫谜案荒野求生全明星 第六季整容季爹地的完美女孩德黑兰 第一季五岛医生诊疗所2004坎坷人生巨星总动员龙门金剑国语
长篇影评
1 ) 当一条鱼也比难民幸运多了
当电影片头出现“献给罗兴亚人”时,导演普蒂邦·阿朗潘的人道立场和政治隐喻昭然若揭,恰逢这个外交争端正在海牙国际法庭上激辩,昂山素季亲自为缅甸政府辩护,而身为泰国人的阿朗潘,显然站在了她的对面。
从这个角度入手来看《蝠鲼》,能体会到导演显然并不是要讲述一个“环保”的大而化故事,正如片中出现的军人、枪声和伤口,其内核是通过暴力来筛选人群,哪怕只是在最普通、贫穷的渔村里平静的生活,也不是人人都可以享受的。从蝠鲼变身而来的男子,其实具有明显的难民特征——不会说话,但又可以与当地的渔民作简单的肢体交流,穿上渔民的衣服,染成渔民的黄毛,几乎要融入当地文化,甚至还有黄毛前妻同居、生子的意向,这些都预示着他摆脱原有难民身份,鸠占鹊巢的趋势。影片前半程,两个男人之间似有若无的同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导演对东南亚民族“同源同种”的暗示,渔民给哑巴难民取了个歌星的名字,而后者也的确逐渐掌握了声带发声的方法,再下一步,自然就是开口说泰语了。
但这一切,都在黄毛死而复生后戛然而止了,难民最后的出路,依然是放逐,当然大海本身也寓意着生命,让他重新幻化为蝠鲼,而不是死在人类的枪口之下,多少还能看出导演的同情和寄望。除了政治上的隐喻和生命往复的哲思,《蝠鲼》最突出的地方还是在其营造的视听风格上,导演巧妙的因陋就简,用LED小灯珠和电子乐来打造出迷幻感,并不显得廉价,反而与当地的生活水平相得益彰。摄影师出身的阿朗潘,在色调和光线的渲染上得心应手,能够让观众陷入某种沉静的期待。而影片中的环境音效,也做得非常有立体感,虫鸣鸟叫,海浪涛涛,这几乎是阿彼察邦等东南亚导演的看家本领,烘托了当地特有的神秘主义,那种湿漉漉充满了生机和欲望的想象,同时也是寓言式的文明救赎。
Luc
2 ) 魔幻泰国!难民不是魔鬼,是受难的鱼
从威尼斯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到釜山电影节展映,再到平遥电影展藏龙单元提名,泰国电影《蝠鲼》可以说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这也是泰国新导演普蒂邦·阿朗潘从摄影师晋升为导演的第一次亮相。

影片以极简的自然主义手法,将严肃的移民议题用诗意的方式表现出高度融洽的个人风格,在奇幻之外展现出庞大的人文主义关怀。虽然阿朗潘现年已经是42岁“高龄”的新导演,但对于他的出现,电影界还是保持惊喜目光。

1. 献给罗兴亚人之诗
影片《蝠鲼》的片名原本并不叫“蝠鲼”(魔鬼鱼),影片最初的定名是《出发之日》,而在开拍之前,导演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潜水时遇见一只大魔鬼鱼,这种大鱼看似可怕,但其实极少去主动伤害其他的生物。在缅甸难民沉船的泰国海域遇到的这只大鱼,似乎是上天赋予我们这部影片的一个更为妥帖的名字。

影片的开场以极具阿彼察邦气息的镜头,静静凝视墨绿幽林中身上挂满彩灯的猎手。同样闪烁着五光十色宝石的丛林中弥漫着杀机。猎手与猎物之间的窥视和被窥视,在悠缓的气氛中交换着。当所有人都在等待枪响时,镜头却以上升姿态戛然而止,仿佛飘升的灵魂离开幽暗的陷阱。

三幕剧的常规形式,将影片整体切割成:渔夫救起将死的难民,并赋予其新生活和新名字“通猜”;渔夫在黑帮任务中失踪,替代其生活的通猜与渔夫前妻接续过往生活;死里逃生的渔夫回归,身份的交集与碰撞将影片推向高潮。

导演一开始用悬疑方式展开渔夫和通猜的关系,镜头切换和红色头套的细节似乎暗示渔夫就是枪杀难民的凶手。而后二人在相互救赎中,似乎发展出异于寻常的情感。
但从第二幕渔夫失踪开始,通猜开始接替渔夫原有的工作和家庭,甚至在渔夫的前妻回归时,也“接替”了丈夫的身份,将胡子和头发都变成和渔夫相同的样子,为第一幕频繁出现的二元对立、正反打镜头落下了实锤。

阿朗潘完全依靠镜头语言交代的叙事,在极简自然主义的叙事风格中,以奇妙迷幻的画面调出极其特别的迷幻莫吉托,将这个关于身份、流亡和生活的简单故事,包裹上层层象征主义气息。

得益于丰富的声音设计,导演和摄影师伦菲布·伊特创造出某种印象派氛围,利用浓重的黑暗和魔幻的色彩进行对比,在陆地和海洋之间编织出二元对应。移动的摄像机掠过森林底部,就好像它是一个深海海床。

导演在创作笔记中提到,《蝠鲼》是一部献给成千上万逃离缅甸涌向泰国寻觅生机的罗兴亚人。身披彩灯在密林中扫荡的武装人员,将死的难民全身泡在腐烂的沼泽中,沉到海底的难民渔船和岸边的万人坑,正是现实中种种的不可思议造就了《蝠鲼》不可思议的魔幻现实感。

所幸,影片并没有因此沉浸在现实政治的讨论中,而将焦点放到了难民的身份错位和经历上,使得影片《蝠鲼》既是一场奇幻视觉盛宴,也是一部细致入微的个人戏剧,在节制的诗语中体现难民与社会的地理复杂性。

阿朗潘用温和的方式传达着人文主义式的悲悯感,同时在魔幻现实主义语境中讲述了一个层层嵌套的故事。丰富的表达捆绑在一起,折射出一系列非同寻常又充满诗意的图像。影片临近结尾处,一组闪闪发光的宝石再次出现在森林,虽然是相同场景,但影片开头和结尾两处的气氛完全不同,恐怖和悲悯的转替,依旧是无能为力的宿命感。

从影片风格上可以明显看出,这并不是一部现实主义的电影,也并没有讨论移民问题,而是导演为罗兴亚难民所作的一首悲悯之诗。阿朗潘的剧作无疑靠近诗歌的本质,极其简洁的叙事让画面始终萦绕着介乎明暗之间的氛围。
得益于早年做摄影师的经验,阿朗潘导演在光线、色彩和音效上的得心应手,也让这部影片多了一份祭祀般的仪式感,大地、水、天、血、肉体,以及宏大自然下的“受难者”,勾勒出这场魔幻现实主义风景。

2. 完整的圆
影片以罗兴亚人为主题,虽然有一些微妙的暗示,但在创作上却让观众始终保持着一种不确定的疑惑,甚至让人怀疑这是否是一个悬疑倒叙剧本,抑或是一个周而复始的现代神话。直到影片发生概念逆转,在某种程度上为导演的叙事意图提供了象征性的澄清。

影片中大量的隐喻和象征让气氛更添诡秘,“失语”的通猜与”没有名字’的渔夫之间有个特别有意思的身份互换,从渔夫为受伤的难民起名字开始。渔夫以泰国著名歌手的名字,给难民一个新的名字、一个新的身份,而渔夫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海滩、海风和我俩》,对这首民谣的引用是两人关系的一个强有力的预兆。

除此之外,影片用蝠鲼(魔鬼鱼)隐喻难民们,同样为带着政治哀伤色调的主题增添不少奇幻色彩,失语的通猜有如深海中幻化成人的蝠鲼,好似既温柔又危险的潜在。他好奇地看着周围,跟着渔夫探寻宝石,学着吸气潜水,和渔夫前妻相爱,在这陌生的人间结结实实地走了一遭。

渔夫将其灵魂从他腐烂的身体中救出,教他游泳,骑摩托车,修拖网渔船,在树林里猎取宝石。在其中最迷幻的某个场景中,破败的木屋被挂上各式各样的彩灯和镭射,瞬间变成舞厅,两人在舞厅中央和闪闪发光的彩灯下闭着眼睛,面对面跳起舞。光影速度拉得极慢,正反打镜头的切换仿佛二人在轮舞之间将命运交换。

影片中,“借壳还魂”的通猜与其说有意取代,不如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没有社会认同的身份,就意味着无法继续生存;越来越像渔夫,则意味着越来越失去自己。在自我意识和社会身份之间的困境中,镜头始终对通猜保留着温柔的怜悯。

当通猜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真正拥有渔民的生活时,落魄的难民重新回到密林,在幽暗丛林中与闪闪发光、五颜六色的宝石融为一体,宛如丧命者的灵魂。在晨昏一线之间,从被埋在腐朽的腥土冉冉破土,利用电影波长,去感受这些环境中“居住”的罗兴亚人的灵魂、声音和记忆。

在影片最后一幕,哭泣的难民伤口依旧淌血,似乎离开故土之后更让他明白身体早已无处可栖。像海边的挽歌那般,密林中的宝石,闪烁着亮光漂浮在海上,喻示着难民的精神已经远去了,变回蝠鲼重新投入大海。

这种圆形循环结构,用容纳大量的形式主义元素和声音景象,这些元素和声景融合在电影的整体框架内,在电影进入象征和隐喻的过程中,将传统戏剧冲突和迷幻的视听语言进行饱和的透镜化处理,让建基在严肃命题上的电影情绪,得以借助奇幻的诗意语言吟唱出一首罗兴亚人之歌。

独家专访普蒂邦·阿朗潘导演
看死君:导演您好!这部电影的片名为何叫《蝠鲼》,有什么特别的寓意?
普蒂邦·阿朗潘:我个人特别喜欢潜水,回想2009年,我在泰缅边境的阿拉曼海潜水的时候恰好遇到了蝠鲼这种鱼。这么大的鱼冲着我游过来时,我感到挺害怕的。结果吓得我够呛以后,我就去做了一个研究,后来发现其实这是很友善的生物,而且它们在海里总是自由自在游动,并没有一个界限。我觉得它们这样的生活状态,跟我这部作品的主题比较切合。

看死君:这是您的第一部长片,便到威尼斯电影节荣获地平线单元的最佳影片,如今又来到平遥电影展参赛。自己的作品受到关注,您个人感受如何?
普蒂邦·阿朗潘:能入选威尼斯电影节,其实我自己都没想到,所以当我接到邮件得知入选了威尼斯的时候,已经是大喜过望了,没想到居然还能获奖,更是意外之喜。自从得奖之后,我们也受到了很多的反馈,不只是我自己,以及我整个拍摄团队,都能够借此去不断提高创作水平。这次能够有幸入选平遥国际电影展。我也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是贾樟柯导演忠实的影迷,既然他这边邀请我,我觉得必须要来参加的。

看死君:影片中被救的难民“通猜”这个角色,为何从始至终都保持沉默?
普蒂邦·阿朗潘:我们其实没有真正听到过难民的声音,虽然现实中也会有一些罗兴亚人或其他难民的这些声音,但是我们没有真正能够听到他们的呼声是什么。我也不希望说通猜(Thongchai)就是具像的代表罗兴亚人,我希望他能够作为难民这样一种人的代表。我写剧本的时候就在考虑,这个人物他应该讲什么语言呢?是讲泰语还是讲罗兴亚语?后来我一想就算了,干脆别说话了,反正咱们都没有听到过难民他真正的呼声是什么。

看死君:您让两个男主人公的身份发生互换,这个构想的灵感是如何产生的?
普蒂邦·阿朗潘:这个灵感其实就来自于我周围的人,因为我们泰国人自小在成长过程中都被教育去爱国,同样我们也会害怕外来的一些人,或者叫做陌生人,不管他们是缅甸人也好,穆斯林也好,会有这样一个恐惧的心理。
而且我们从教育当中了解到,泰国和缅甸历史上的矛盾很多,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这样一种历史是真是假,是不是政府编出来借此来教育我们要爱国,不得而知。在泰国的缅甸人也受到了一些压迫,觉得这也是一种不好的事情。
在整个泰国社会当中,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其实都很害怕罗兴亚人,怕他们来了以后会夺走我们的经济福利、工作机会,还有夺走我们的地盘,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存在,我希望能扭转它。

看死君:拍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普蒂邦·阿朗潘:我开始拍的时候是在2015年,那时泰国遇到一个问题,因为泰国传统上是向欧洲出口海产品,但因为有人口贩运的问题,所以欧洲那边就开始限制泰国海产的进口。一方面我们要解决人口贩运的问题,另外还要维持产品的质量和食品安全,所以那时候我拍这部电影必须要去报批。但泰国政府拒绝给我们拍摄许可,不让我们到出口海产品的地区去拍,因为他们不想解决问题,而只是想去掩盖问题。就希望我们不要跑到那边拍电影,只要沉默就好了。所以,我们当初最大的困难就是拿不到拍摄许可,但是反过来这部电影它又是一个渔村的故事,恰好就要发生在这样一个出口海产的地方。

看死君:您在影片中设置了很多彩色的光,并且一直贯穿着始终,这些超现实的构想从何而来?
普蒂邦·阿朗潘:我想,不管在中国还是泰国应该都有同样的情况,如果你有名胜古迹,你会用光线去进行装饰,然后通过光线能够诠释出来这样的名胜古迹。比如像平遥这样的古城,同样离不开人工装饰的光线,就会跟普通的日间的自然光区分开,能够赋予一个地方新的寓意。我在电影中运用各种颜色的光,也是为了赋予新的寓意。

看死君:为何在树林中会有死婴?
普蒂邦·阿朗潘:我刚才也讲到有这么一个新闻,就是在泰国南部发现了一百具罗兴亚人的死尸。发现这个事以后就应该调查的,但政府那边不声不响也没有去进行调查。所以我希望能够把这条新闻当中的某些元素融入到我的这部电影,树林中的死婴便是如此。

看死君:影片的声效做得很棒,可以具体聊聊声音方面的设计吗?
普蒂邦·阿朗潘:在我完成剪辑的时候,我就感到在这样天然的森林当中,可以用一些LED形成的光源做点缀。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我觉得应该能够让这样的天然林搭配上城市当中的电子音乐,形成奇幻森林的效果,就有一个不同的含义。我就跟法国的一个作曲家也进行了交流,之后他根据我跟他的交流进行下一步的创作,所以大家能听到的声效也好或者音乐也好,都是法方团队来做的。

看死君:很多影迷觉得影片的最后一场高潮戏很震撼,为何会以此作为结尾?
普蒂邦·阿朗潘:我在写本子的时候,故事还没有创作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想到结尾应该是什么样子了,也就是我希望能够让罗兴亚人的声音不再沉默。所以我就收集了很多罗兴亚人的声音素材,然后把他们录下来以后交给作曲家,然后作曲家去创作一个和声,那也就是最后您听到的他们和声出来的那个哼鸣的部分。所以说,我这个创作过程很有意思,是先有结尾再有这个故事,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意识到,我希望让这些罗兴亚人的声音不再沉默,而是能够在平常中可以体现。

看死君:在泰国,人们对艺术电影的关注度如何?比如像您这部《蝠鲼》这样的电影,一般会有多大的受众群?
普蒂邦·阿朗潘:艺术电影在泰国是非常小众的,观众其实非常少,所以说市场情况也很糟糕。
看死君:您有没有非常喜欢的导演,受谁的影响比较深?
普蒂邦·阿朗潘:我现在能想到的是三个人,第一个是美国的大卫·林奇导演,第二任是泰国的阿彼察邦导演,第三个是贾樟柯导演。我觉得,贾樟柯导演的电影中,有时候就会有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

看死君:您后续还有新的拍片计划吗?是什么样的题材?
普蒂邦·阿朗潘:我希望能够进一步来探索人性或者人的身份。那么这一部《蝠鲼》是关于难民的,下一部则希望是去了解城市当中的人,也当然会是一部泰国电影。
作者| 小飞侠;采访| 看死君
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转载请注明

3 ) 极简叙事令人疑窦丛生
自从泰国导演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在2010年摘下金棕榈大奖后,越来越多泰国新导演拍摄的作品似乎都摆脱不了阿彼察邦的美学影响,也许他们都认定了这是吸引西方人眼球,继而登上艺术殿堂最便捷的方式,所以看到这部处女作里的LED彩灯和丛林场景也就见怪不怪了。而事实上并不是在丛林里放几盏霓虹灯就可以拍出一部金棕榈作品来的,影片的美学风格要与主题契合才能够带给观众共鸣感。
这位新导演普蒂邦·阿朗潘(Phuttiphong Aroonpheng)此前一直担任摄影师,也拍摄过不少广告片,这部导演处女作颇具话题性,将猎杀海洋生物与难民两种抢夺眼球的话题融合的电影还是第一次看到。全程一言不发的难民令人联想到罗兴亚人在东南亚地区的悲惨现状,而后半段关于身份转换与取代的情节更是引人深思,给这个难民角色染上多重复杂的象征意义。然而,这个具有悬疑色彩的犯罪惊悚故事讲得语焉不详,极简主义的叙事方式令人疑窦丛生。类型情节突兀地闪现,难以将前后两段里渔夫杀人动机和莫名失踪合理地衔接上,令叙事陷入晦涩不明的境地,即便文本中再丰富的隐喻都难以展示用武之地。
4 ) SGIFF29映后与导演Q&A随记
Q: 为什么感兴趣拍雨林部分?
A: 因为那里是泰国的边境地区,涉及到一些难民的问题,难民们都是从那里来的。我也想探讨一些人们的身份(identity)问题。
Q: 怎么想到拍这部电影?
A: 我准备构思了八年之久,我想讲述一个关于身份的问题。
Q: 为什么影片是这样的格调?显得特别魔幻神秘。
A: 我以前是在博物馆工作,为他们拍一些东西,我想把那样的风格带过来。这个剧本只有30页(!!!),其他都是剧本之外扩充的。
Q: 为什么把被救的难民设置为不说话?有什么象征意义么?
A: 显示他的孤立(isolated)。不给他设计语言,这样观众就可以更多感受背景声和音乐。
Q: 为什么设计给宝石那些五彩的色彩?
A: 我没有想过要什么样的色彩,我只是想要闪光。这个想法是我去边境看的时候产生的,我在边境看到许多闪光,我想应该要有这些。我还听到一个故事,说二战的时候,那些海盗会过来挖宝石,所以我在电影里设置了宝石。
Q: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故事线么?
A: 我拒绝回答,上一次有人问, 我回答了,结果被认为非常荒诞,我现在回答的话,你也会那么认为的。
Q: 有多少剧本之外的扩展?
A: 很多了,很多剪辑,要知道剧本只有30页。
Q: 我看到youku是coproduction,怎么和youku合作的?
A: 2014年我递交了一个短片剧本去参加他们的比赛,最后我的剧本被选上了,于是我获得了一笔资金,我把它拿来扩展成了长片,就是现在这部蝠鲼
(欢迎同场的盆友们补充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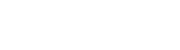




















主要是太出戏了,身上裹LED小彩灯的画面(号称全片最灵魂出窍的画面),完全是当年阿彼察邦的一个装置艺术呀。再,真的扯到罗兴亚难民的话,就让人更加觉得索然无味了…………emmmm,比《入黑之时》差多了
恭喜霓虹灯管派再添一员
#2nd PYIFF# 威尼斯地平线大奖。导演出身优酷釜山计划,片子虽说是邦哥一路两段式东南亚丛林神秘主义加霓虹灯美学,也有很强的政治文本(罗兴亚人-难民)。不过拍得确实棒,这个将钙未钙的微妙尺度拿捏得真是精到,况且视听上真是令人愉悦的沉浸感。
隐喻做的很好,被猎杀的海洋生物幻化成人类的样子,漂流到一片满地宝石的森林里,忘记了语言和呼吸的方式,加上主角社会底层的身份和适当的情节留白,导演将环保和屁民的主题做起很高明,视听风格是阿彼察邦式的,但是加入了迷幻装置艺术的东西,一度还有一股腐气,如果后半段的情节可以再连贯一点,可能会更好。
塞进了满满当当的隐喻和暗示。登堂入室取而代之影射难民问题;化身为人失语练习呼吸指向动物/环境保护的双重隐喻。结尾真好,收回了一部分的精气神,但是神经兮兮现在已经变成泰国文艺片的代名词了吧。果然每个地区艺术电影的窠臼各不相同,我真的,无论如何都没办法接受把霓虹灯泡缠在演员身上,然后在雨林里四处乱走,还美曰其名为“神秘主义”,真是自杀式的一招。氛围OK,声音OK,配乐OK。
满是彩色石头的滩涂树林,受了伤最终回归大海的蝠鲼。意境营造和光影效果都足够震撼,类海洋系阿彼察邦。
結果豆友大都不愛這部片,我倒覺得還滿好看的,這種似gay非gay的身份與身體遊戲,最終還是成為政治寓言,兩位演員到位,影像細節和剪接節奏都控制的不錯,只是最後進入超現實的段落有點不好進入。
近年的泰國獨立電影要面對的最大問題,在技巧和條件限制下無法走入題目深層的探索時,如何不讓自己變成別一部「當代藝術形式」,在燈光,聲音的運用上發現更新的可能性,電影中都是套路了。或正確來說,不要變成別一部「Apichatpong 電影」,確實有少數如Puangsoi 的《重返天堂之城》般,可貴在面對自身的情感歷史,嘗試在虛構影像與紀錄影像之間。電影原本應該要更冷眼去看,人物在空間的穿越與歷史性與難民的流動/流亡,動作演出去寫實化才可更有隱喻式,現在變成四不象了,什麼也做不到,對難民困境的保守想像,或者,根本沒有深入消化他們面對的問題,還幸多少有它的感性。但我寧願去看挑戰觀眾習慣而實則無聊的爆米花電影,至少獲得一點快感,也總好過以嚴肅話題為主,但表現出來非常保守,又沒有想像的電影,藝術化不代表對議題有任何關心的...
@PYIFF 2018 | 为罗兴亚人招魂。片头有行字“For Rohingyas”平遥字幕没翻译出来,所以不少人可能看完稀里糊涂搞不清这部到底在说什么隐喻在隐喻啥。建议看之前了解一下罗兴亚人的历史,然后联系本片:溺毙的难民,在各处受拒绝,无法融入;宗教矛盾,极端分子;历史遗留问题,悲惨的民族史……主题非常沉重。看时联想了《杀戮演绎》和《沉默之像》。另外,本片的影像之美也很值得留意。
既有人类捕杀鱼的隐喻,又有城市人看待外来移民的隐喻,同时对外来者接管本地予以控诉,包括失语和用腮呼吸都很贴切主题。
渔夫无名戴红色头套招魂,通猜无言染黄色头发重生。密林的亡魂会在月圆之夜破土,深海的蝠鲼会在口哨声中归来。浑身彩灯的战士在宝石之中迷路,满身腥土的亡尸在尘世之中还魂。前妻连宝石项链都带走,却愿把你当做我。苟延过活的房间,还有彩灯与镭射相伴。是你取代了我的身份,还是我吞噬了你的灵魂。
倒不是说没有情绪吧,而是没有为情绪找到合适的落点,所以感觉做的都还是精致的表面功夫。作为处女作而言也还行,这样的导演还是可以期待的。
现在的文艺片导演,有一半钻进丛林里装逼,另一半挤在霓虹灯下搅基。身缠霓虹小灯泡钻进丛林里搅基的还是头一回见,还在丛林里办起了霓虹灯展销会。南洋电影要进步,要在丛林前立一块碑,上面写四个大字——逢林莫入
“manta ray”应该译作“鳐鱼”、“蝠鲼”而非“射线”。鸣谢有王小帅诶?难民题材也能拍成泰式冥想片。恐怖片看多了的我总觉得森林里的死婴会睁眼,水底的光线会把人拖下水……
章宇出演阿彼察邦新片《森林、渔船、霓虹灯~还有被我捡回家の人鱼男子~》 / SIFF第30场
王家衛當年受訪金馬時曾說:《阿飛正傳》的張國榮和梁朝偉出生相隔了二十年,因為只有時間和水,可以讓上一個阿飛活困死陷進去的歷史追憶,到了下一個阿飛繼承時卻變得無足輕重。那麼,沒有時間也沒有水去舒緩的追憶,會有多重多混濁?答案便是這部《邊境幻夢》。
如果多点背景了解的话,对电影也会多点熟悉。但前半段太闷了,毕竟本来台词就少,后半段有了冲突后好点,优点在于导演对氛围的营造,但篇幅稍长一点,如果可以删减浓缩的话也许会更好。主题上,应该还是关于身份的迷失与认同。整体来说,还是不喜欢。2.5
正是此类电影的存在,给人以“阿彼察邦其实挺好模仿”的错觉。
当文本与台词都乏善可陈时,信息就隐藏在镜头中。当这种呈现方式占据主导时,导演能够引导观众更纯粹地关注画面本身。大量的正反镜头对比,意象化,蝠鲼、霓虹灯、山林、海水。坚守者与外来者近似亲密的关系。看到最后,才发现坚守者与外来者其实是同一人,就是那个喜当爹的剧情太狗血了。大概文艺片就是这样,你总是需要“代入”的,不管是代入到自我的情感,还是他人的情感,只有融进去了,才会收获到最真切的体验。如果说,对于艺术品观赏仍处于初级阶段的人来说(比如我),其实抛开对于其的成见,以及抛弃掉以往习以为常的观看方式,很重要。就像是在电影最后才出现的蝠鲼一样,你得投身于大海深处去。
别扯环保,你那些荧光灯管灯串理不清,东南亚浮躁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