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骨灰盒推销员小康(李康生)结束心力交瘁的一日后,悄悄潜入一幢公寓里的一间房,没想这间房里,还会潜入一个会是其欲望(投射)对象的地摊小贩(陈昭荣)。房子的暂时主人是一个售楼小姐(杨贵媚),她和小康性向虽然有异,却同样是没有爱情(情感)温暖心灵的人。 小康和地摊小贩一开始时时提防(售楼小姐和彼此),待他们认识了解到各自的生活后,提防心理消除,却也没有自此成为朋友(懦弱的小康也鼓不起勇气示爱)。售楼小姐和地摊小贩发生过几次性关系,清楚地明白彼此都是为了满足身体的长久饥渴,爱情(感情)并没有什么万岁之处,身体上的快感可以暂时满足,精神上的安慰却无法获得(即使有,也是短暂如烟花)。陌陌影视陌陌影视天路难寻追捕刺客国家公诉糟糕历史大电影:臭屁的罗马人奇葩料理大作战 第二季阿尔法城1965艾德·希兰:成名之路闪光的夏天第二季人偶,流放的精神死神傻了(国语版)公寓2024:柬埔寨版致命追击狮子王国反恐特警组 第五季角头设得兰谜案第六季绝命救赎人人都爱雷蒙德第六季街区男孩单身家长第一季抗击2011激战交易所 第二季人间大炮3恶魔玩具:小丑盒袭击蝴蝶:成人世界塞上迷情人狼游戏:死亡游戏的运营人龙虎地头蛇
长篇影评
1 ) 爱情已死
电影叫《爱情万岁》,里面什么都有,唯独没有爱情。
作为蔡明亮“台北三部曲”的第二部,电影不仅呈现了他对底层人物在台北生存的细腻观察,更是实现了对他们身心状态的一种原创性描绘。镜头对准了演员吃饭、睡觉、洗澡、小便、自慰等独处时相当“野生”的生存状态,包括异装癖等病态的身体行为,这种不唯美只唯真的对日常琐碎生活细节不加节制的选择让其电影呈现出了非同传统的美学样貌。如果说处女作《青少年哪吒》还带有些许“常规电影”气息,那《爱情万岁》则真正开始让蔡明亮走上了一条路:摒弃一切戏剧性叙事,建构于自然主义的表演风格和极简主义的长镜头美学中的,人物在异化都市内的孤独写生。
以杨贵媚和李康生为代表的演员为例,他们在电影中近乎于一种无语声的身体表演(在后来的《洞》中更为突出),对白只剩下了工作对话和无意义的生活交谈,台词的功能性被降低到几近于无,反而大量单调、重复、生活化、甚至有时会有些异质化的身体行为充斥着镜头,人物在时而巨大时而逼仄的城市空间中漂流迷走。这显现出蔡明亮后来电影中常见的母题:在这个高度物化的现代都市,人与人之间是失语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
从处女作《青少年哪吒》开始,蔡明亮的电影就开始呈现了与其深藏血缘关系的台湾新电影导演不同的一个面向,也许与其马来西亚华侨的身份有关,他的电影扎根于台北的地理空间,却从未关注台湾的历史记忆与个体成长的联系,他们的生活永远是现在时的,抽离于政治背景和历史背景,只存在于虚化过去与未来的象征性的“当下”,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劳动阶级每天在无意义的单调工作中摸爬滚打,加上人与人之间情感上的疏离让他们无异于某种都市幽魂。于是,蔡明亮的电影角色就渐渐地成为了一个个被社会和历史双重遗弃的孤独的封闭系统。
回到开头,电影中的“爱情”是缺席的。李康生饰演骨灰盒销售员的小康、陈昭荣饰演的地摊小贩阿荣、杨贵媚饰演的售楼林小姐,他们就像我们身边所有不起眼的普通人,做着没有创造性的工作,封闭而疏离。在林小姐的待售之屋里,小康与阿荣成为了擅闯空门的入侵者,三人在这个孤寂的空间中却又互相躲避,于是看似相连,却又继续孤寂。小康是同性恋者,被压抑的情欲在遇见阿荣后不断滋生,却只能偷偷穿着女装幻想被爱抚、躲在床底听阿荣与林小姐做爱的声音自慰。阿荣与林小姐之间的情欲发于肉体,却也止于肉体,没有灵魂交流,没有情感铺垫,没有甜言蜜语,爱情已简化为性欲,变成一种快餐。电影在结尾用一场名留影史的哭戏宣告了现代社会的悲剧——爱情已死。
这是场笔者认为最美的哭戏,美在真实,痛彻心扉。林小姐与阿荣做爱完的第二天早晨,她一个人走进施工中的大安森林公园,坐在长椅上哭了足足六分钟。镜头凝滞不动,她哭到泣不成声,仿佛这是一场给她自己举行的葬礼。当然,也是场现代人走向死亡的葬礼,在这个高度异化的现代社会,爱情被简化物化为身体的交欢,肉体和精神的分离让林小姐发现了自己正走向死亡的现实。
2 ) 爱是寻找灵魂的缺失

看毕,我想起三毛在《亲爱的三毛》中写下的一段话:“在这个日渐快速的时代,我张望街头,每每看到一张张冷漠麻木没有表情的面容匆匆行过,我总提醒自己,不要因为长时间生活在这般大环镜中,不知不觉也变成了其中的一个,他们使我黯然到不大敢照镜子……”。而电影中的每个镜头画面何又不是三毛所述文字的真实写照和射影——同样是台北街头、一张张冷漠麻木的面容、一座悲伤的城市……孤独的表象是一方面,但蔡老师还看到了表象之下的人与生俱来的欲望——爱欲,敏感地捕捉到最平凡而动人的细节,试图重新唤醒每个孤独灵魂对爱的认识和欲望。

#声
电影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少到基本可以忽视的语言,包括对话和旁白,从头至尾只有寥寥可数的对白,如果忽略背景音的话,它与一部默片可能并无二致。但这也正好成就了它的独特之处。不多的语言,使得电影可以留有更多的空间给电影最本质的镜头画面,达到了少即是多的效果。比如其中我最喜欢的一段镜头之一,蔡明亮凭借短短几组镜头,没有一句台词,全凭演员的表演和优秀的电影语言就极具张力地将男女之间情愫相生、暧昧不明的氛围表现出。而充斥全片的环境音——城市的产物,一种充满工业和金属感的嘈杂,城市生活一点点消耗人灵魂的证据,被刻意放大,在展现爱欲和孤独的镜头中,形成了一种微妙而极富表现力的视听体验,仿佛包裹住人的外壳被一点点剥离,使得人可以看到在里面的孤独和爱欲。而“无声”的城市生活,不也正是我们生活的现状?即使是在电话里,我们有几时能真正意义上和他人交流。

# 爱情
影片所试图探究的主题,人类文明永恒的命题。在蔡明亮的电影中,三个孤独的城市灵魂,在同一空间中渴望得到爱,很大程度上他们所渴望的爱也正好代表了城市中的大部分人对爱的理解。性,作为爱的一部分,但单纯的性终究不能带给人以爱的真正体验,它就如同一支支烟,给人以短暂的麻痹和安慰,随之而来的更猛烈的空虚感。而什么是爱,怎么去爱这一系列的问题蔡明亮并未给出答案,但这并非表示他是对爱情绝望的悲观主义者,正如影片名称《爱情万岁》所想表达的那样,哪怕承受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人永远都还是会渴望爱情,唯有爱,才能解救孤独的灵魂。生活的基础除了柴米油盐、衣食住行,还有爱。 (很主观的,希望小康、江姐和阿荣能在轻吻、流泪和熟睡醒来后能得到爱的解脱...)
初次看蔡明亮老师的作品,看完很是惊喜,又是一部引起我内心深处某个角落共振的佳片。

3 ) 生活。
——蔡明亮《爱情万岁》影评
巾城/文
剔除所有的抒情(甚至影片完全没有配乐),蔡明亮在这部都市电影中只留下残酷的叙事。三个迷失在空虚里的人企图用幻想建起欲望的纽带。他们性格不同,行事有异,但在一种行尸走肉的大环境下,却彼此找到了某个层面的共鸣。这种共鸣并不是灵魂或思想的共鸣——这样的共鸣太“虚假”,而这些无处可逃的主人公们要寻找一种更直接的共鸣。这种共鸣甚至击碎了性格的缺陷、世俗的羁绊,在彼此间变成一种温存。
在这里,导演要展示的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一种对理想的彻底嘲笑。艺术总是带有理想化成分的,那些被理想化的名词:爱情、生活、性、绝望,等等一切,被一次次以不同的方式搬上艺术的平台。而在这部电影里,没有理想,所有的一切都是现实的。我因此觉得它带给艺术家们的震撼甚至可能比普通观众更大,它告诉这些人,你们满腔的激情不过是一个无望的梦。你们在象牙塔尖搭造所谓的高层建筑,但生活在这下面的人却有他们自己的哲学。而上下两者间,根本就没有联系。你可以绝望,但你甚至连绝望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你看,他们过得顺理成章,发泄得顺理成章,表演得顺理成章。当然,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绝望,而这种绝望被融进他们生活的进程中,也变得顺理成章——他们根本就不会想到要为之去改变什么,或决定什么。
“爱情万岁”——爱情作为一种燃烧的火苗已被压抑在一种无声的龃龉中,只剩下一个干枯的词语(爱情!)依然万岁。也许阿荣在勾引售楼小姐时得到的满足感、后者与前者做爱时得到的快感,及小康的懦弱和那个几乎行为艺术式的吻都带有某种感情色彩,但这种感情是被剖去内核的,是冰冷的。影片最后一个10分钟长的固定机位的长镜头里,女主角凌乱着头发在台北市灰蒙蒙的清晨哭泣。她的哭泣是不能被艺术家所理解的,是不能被艺术,被理想,被任何一种精神所拯救的——现实已经丢弃了(艺术家们认为)她本该接受的这些东西,而她接受了现实。因此,她纵使在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下会觉得疲惫和悲哀,这种疲惫和悲哀也只能被她自己、被时间慢慢埋葬,却没有出路。
从1994年到今天,物质生活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猜想这样的一个镜头今天可能也见不到了,因为你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喘息,停下来悲伤。我猜想这位女主角若活在当下,一定至少在表面上比1994年的她更快乐。有功于物质文明的泛滥,世界变得更紧凑、更小,她甚至还能找到更多的朋友。
艺术家很多时候像是走在迷雾里的人,为了找寻某种自以为崇高的真相呼吁和呐喊,他们中的很多人最终陷入绝望,甚至带着绝望死去。但这是因为他们的内心深处充斥着一种对与他们看到的世界相反的光明的渴望。换句话说,他们致死都是相信这种光明是存在的,因为自己得不到,才会死去。可如果这种光明不存在呢?如果天堂不存在呢?如果你的理想根本就只是一个笑话呢?如果那些为数不多的人对你的尊敬、欣赏、附庸、迁就和鼓励都只是一种同情和怜悯呢?谁又会告诉你,在这个大大的“艺术”后面,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甚至,如果你连自杀都是没有意义的呢?
也许,只有无知的人才是快乐的,因为他们不需要思考明天。也只有无知的人才懂得无知的人的痛苦,而在他们互相安慰的间隙,艺术家所有的大作都像是一场手淫。
4 ) 爱情一瞬,爱情万岁
在《爱情万岁》中,爱情不作为一段完整关系,或是任何刻度丈量的存在;更像是一个影子,投射在不受时间限制的空间中,爱情虽不明确存在于主角三人的关系中,但有三人在场时,我们又不能说爱情不曾破壳而出,尽管只是无声的一瞬。
空间是一座桥
「爱情万岁」的片名打出后,第一幕是小康在便利店买食物,镜头对着店内的广角镜拍下反射画面,就像售货员需要通过看广角镜判断顾客是否偷窃一样,为影片定下了以广角镜头凝视空间与人物的视觉母题。而后,反复使用的平行剪辑联结着空间与人物,奏成一段精巧的台北流浪者复调。
空间也成为指涉三人共性的符号,最明显的当然是待售的空屋,同为社会底层的李康生和陈昭荣从一开始的互相隐瞒到阿荣发现小康后对他的威胁,再到为避开杨贵媚两人放下防备,了解彼此在寄居外壳背后的真实生活背景——贫穷是相似的。没有家的康荣二人穿行在纳骨塔的陈列室中,同样是一处空间指涉:既是小康唯一能带阿荣进入的与他生活相关的外部环境,与他后来主动去阿荣的地摊出于同样的动机;又如行过死荫之地,同自己爱慕的人。
此外还有单独空间中对人物的长久凝视,杨贵媚在待售的豪宅中抽烟,以及拍蚊子又一直拍不到,于是关上门窗和灯,将困顿锁在这里;亦或重复空间的喻示:永远立着「禁止跨越」的马路,三人在不同时间点横穿过;贯穿时空的浴缸——同样的姿势,他和她躺在不同阶层的浴缸;亦或不同的时刻,他和他寄居不属于他们的浴缸,相同的是,三条孤独而绝望的灵魂,在此间赤裸时才能获得完全放松的身体感受,正如海报展示的那幅画。

静默是一种语言
另一边厢,作为售楼小姐的杨贵媚,她是唯一要每天说大量言语的角色,却是出于生计而说的,大部分时候徒劳无用的,这些言语就像被后期音效调至失真的高跟鞋敲击水泥地时的声音一样,与台北车水马龙的嘈杂声一样,形成内外交迫、困压着这个人物的巨大能量场。因此在她静默处,才是语言开始的地方。即便片中的台词几乎都出自她之口,然而是她塑造了静默,让它成为三人与外部世界对抗的一种方式。无可否认的是,这对片中人物来说是带有自我消化/消解意味的反叛,可对这呈现绝望的影像而言,它当然是不可或缺的张力的一端。
当最后一组镜头,杨贵媚行走在建设中的城市公园,背景音却依然是高跟鞋敲击商场地面发出的声响,那不是她对荒地的美好想象,因为镜头不似《放大》结尾般随人物视角运动,而是以保持距离的姿态,并通过360°的运镜,凝视人物与这座城市,那声响是商品社会对她生活无时无刻的压迫的蔓延。或许相比康荣二人更糟糕的是,女性在性与爱上常常的被动与被剥削位置——阿荣可以在春宵一夜后安然睡在她人的席梦思上,而她要穿上半永久的高跟鞋,哭声延伸至黑幕后,无望的往复生活还将继续。
「爱情万岁」是一则宣言
镜头并不低级地展现片面不平等,而通过伪装成无偏向性的凝视,呈现不同性别的处境。反观小康与阿荣的关系发展,同时也是小康寻获性向的过程——伊始小康寻死的动作便是被阿荣的性爱行为打断,在这之后他的性幻想桥段是亲吻西瓜,并把它当作保龄球般撞毁,可以说他此时只得到了不面向任何性别的宣泄快感;而在他与阿荣互相了解后,他的性幻想变成穿上阿荣没有卖出的女装,用俯卧撑耗尽力量/冲动后睡去,此时他的欲望投射对象是阿荣,但当我们看到一个男性穿着连衣裙做俯卧撑时,也许他对什么是属于自己的性别依然是模糊的;直到最后,他感受着爱人与别人的性爱,藏在床底下自渎,于是他寻获了什么,在清晨的昕蓝中,安然而怯懦地轻吻了爱人,然后离开梦乡。
它悄无声息地宣告了一则进步宣言:人在商品社会处在弱势,女性与LGBT群体只有更加弱势,而后者可以在前者的引导下(不一定是主动的引导),寻找到自己的性向,这也预示着弱势群体的联合将带来「人」的希望——爱情万岁。

爱情只存在一瞬,
不在乎明天和过去,
或妳是男是女,
于是,爱情万岁。
5 ) 《爱情万岁》:独自一人更温暖
有的电影,就像这部,看完了你就一定得为它做点什么,因为你压抑的不得了。你不把心里的感受吐出来,你就难过得要死。 就是这部根本没有爱情的《爱情万岁》。 这里的那些人,一个卖房子的售楼小姐,一个摆地摊的,一个卖骨灰盒的,就是他们三个,在一所空屋里,轮番上阵,有时是他们两个,有时是他和她。他们总是互相躲避,怕被发现。他们可以做肉体的游戏,却几乎没有交谈过一句。 有的是喘息,是沉默,是静的杀死人的寂寞。 他们是些最普通不过的人,他们每天要去兜售商品,做的生意有:卖贵物,如房子;卖贱物,如地摊货;卖给死人(当然是活人出钱),如骨灰盒。有四处陪着看房的,有吆喝招揽生意的,有发夹名片的资料的,都过得挺忙碌挺充实。 他们都不是唧唧歪歪的小资,没时间吟风弄月,忙完生计后觉得寂寞,也全然不是为了寂寞的寂寞,绝没有陶醉其中、自我欣赏的意味,所以,你不可鄙夷他们。相反,你发现的是,你们之间有些共通的地方。 所以,有些细节你看到出神。小康亲吻他的西瓜,如痴如醉;和帅哥阿荣两度一夜情后茫然走在路上的阿美,坐在天色初亮的公园长椅上,哭个没完;小康和阿荣分别穿上女人的衣服和鞋子,扭来摆去;阿美在空屋床上沉沉睡去。 那时候竟是那么自由自在。全都是一个人的时候。 那么爱情呢。人们不是说它是摆脱寂寞最好的良药。为什么有一天你觉得你必须和另一个人分享,才不会寂寞。是他们的喘息声吗?一如小康在床下听到的那样。其实哪里有爱情呢。只是当早上小康从床底下爬出来,情不自禁吻了沉睡中的阿荣,爱情才悄然登场,在不被对象察觉的时候。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了隐藏内心。可以赤裸相见,却没有做好打开心扉的准备。惧怕。又不知怕的是什么。 据说女人长寿是因为她们比较懂得哭。所以阿美那样的对着你哭过了之后,你就只好把她放进你的心里了。她对你哭。尽管也对别人哭。她软弱的样子你全看到了。她跟你有了秘密。因为这个你压抑吧,是你跟她一样感受到了寂寞一样无助。原来,这样的人很多。这一刻你决定爱上阿美,爱上她的哭泣。 在独自一人时快乐,无力承担两个人在一起。 所以,这里没有爱情。 在凡世里决定热闹相见热闹往来,那种热闹格外有种虚浮的调子。至于死后——卖骨灰盒的老板在给大家介绍自己的新产品,这个是夫妻型的,是两个骨灰盒打通,有的人会买两层,另外的是给朋友,免得打麻将三缺一。还有家族型的,打开是更大的空间,似乎可以预见到很闹猛的样子。小康和阿荣在一边静静看着。 他们那时候会不会做邻居,比较有机会说说心里的话?
6 ) 我眼里的蔡明亮---<爱情万岁>观感
第一次知道蔡明亮是一个朋友的推荐,他让我关注《天边一朵云》,而我只找到《爱情万岁》,看过之后感到被触动,于是开始收集他的影片,履历及与他相关的一切。不知道这行为是否算做追星?而他虽然也是一颗闪亮的星,却并不被多数人接受,他的晦涩而沉闷的影片注定是小众的,不会象张艺谋冯小刚那么容易引起共鸣,自然也就不会那么容易在市场中找到了。
蔡明亮1957年10月27日生于马来西亚砂拉越古晋,广东揭阳人。幼年由外祖父母抚养,并轮流带他观赏电影,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1977年赴台湾,考入后来改名为中国文化大学的台北阳明山中国文化学院戏剧系影剧组。期间热忠舞台剧,并于1982年和几位同学组建小坞剧场,出品有舞台剧《快餐炸酱面》等。后来在为电视拍摄剧情片《小孩》时,于电动游乐场所中结识没有任何表演基础的李康生,从此成为他影片的御用男主角。1991年徐立功找他拍片,他以李康生为蓝本编导了第一部电影《青少年哪咤》1994年以《爱情万岁》获威尼斯影展金狮奖而从此被更多人了解。
处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我们的生存状态是那么的焦虑而无奈,在他的影片中充满了对这种焦虑和无奈的观察及深层挖掘。而他本人漂泊的成长经历,无根的生存状态决定了他观察社会生活的独特视角。
《爱情万岁》中的三个人物小康(李康生饰)是卖墓穴的,阿容靠摆地摊生存,林小姐售楼。虽然故事在台北,可这样的人就生活在你我身边,随处可见。小康卖的是死人的“家”,林小姐卖活人的,而他们自己都居无定所。小康和同事格格不入,并为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感到自卑由此想到自杀,但又没有勇气...林小姐和阿容在街边搭讪而发生一夜情。
片中有一个场景是当同事们在一起做游戏时,小康在一旁尴尬的观看,游戏是以家庭的角色转换为基础的,在爸爸妈妈和孩子之间做不停的变动。同事玩儿得很投入,对于小康来说,那意味着传统价值观下的家庭模式,他是同性恋,他将来可能拥有的家庭会是什么模式呢?他会拥有当下社会能认可的家吗?他的存在难道不是对传统价值观下的家庭的解构?当他观看这个游戏时,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并真切的感受到传统婚姻模式正在瓦解。可什么在取代传统呢?同性恋还不是主流,尽管有些国家已经为他们颁发合法的证书,但那就象是男性世界里也有女性的杰出代表一样,是社会显示宽容和理解所给予同性恋的妥协。片中的林小姐不是同性恋,但她一样没有找到传统意义上的爱情。
一夜情,这个不为传统所认可的形式,是林小姐找到的填补肉体欲望的方式,我认同王朔的说法,没有人能控制自己的血压、心跳、分泌多少酶...等等这些由生理功能完成的工作。这个世界没有圣人,谁能抗拒生理的需求?困了要睡,渴了喝水,我们难道有能力反抗?但林小姐的精神并不是龌龊的,片中最后的镜头是长达10分钟左右的哭泣,林小姐在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和阿容做爱后的哭泣,她一个人在公园的长椅上,抽噎到放声。她对爱情的渴望是发自内心的,同时也对因为不能得到真爱,并放纵自己的欲望而感到失望、伤心和无奈。
影片从来没有交代小康为什么是同性恋?林小姐的工作性质接触那么多的人,并且应该在经济上还算不错的人,为什么就不能找到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男友呢?她自己也该算是白领啊。还有阿容,他那么年轻,就靠每天摆地摊生存,有警察来检查还要随时逃跑,就象北京街头的小商贩一样,没有社会认可的生存方式,没有安全感。难道这是他想要的生活?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生存的困境,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社会的进步和竞争带给我们的负面效应以及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到底是什么在取代传统?是什么令传统丧失了原有的凝聚力?这样的迷茫正是蔡明亮让我们正视的。电影到底是什么?难道它真的只是让更多人在影院中和创作者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我想除此之外它还应该是作者表述他价值观的手段,观察社会、拷问人和人性的窗口。市场需要大片,应有之;但市场同时需要沉甸甸的思考,亦应有之。有记者采访蔡时说,你的电影是票房的毒药,这对台湾电影的整体恢复没有帮助。他回答,电影的现状和制度有关,你不能因为台湾没出现冯小刚就质问我为什么不是冯小刚啊。
我想蔡明亮电影的沉闷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没有太多人物,简单的关系,几乎没有对白,没有花哨的镜头技巧,蒙太奇...等等等等。这在当今讲究大制作,演员阵容,画面视觉冲击力及吸引观众的剧情等等话题的对比下,他的电影在市场中的苍白无力是注定的。但是我能感受到他对人的真诚,他的电影触摸到了我心灵最深的部分,令我感动和回味。
蔡明亮作品年表
电影部分:
编剧
1982 《风车与火车》〈张佩成导演〉
1982 《小逃犯》〈张佩成导演〉
1983 《策马入林》〈王童导演〉
1984 《阳春老爸》〈王童导演〉
1985 《好小子Ⅲ》〈王童导演〉
1987 《黄色故事》第一段〈王小棣导演〉
编剧/导演
1992 《青少年哪吒》
1994 《爱情万岁》
1996 《河流》
1998 《洞》
2001 《你那边几点》
2002 《天桥不见了》
2003 《不见不散》
2003 《天边一朵云》
电视部分:
编剧
1989 《不了情》
导演
1989 《快乐车行》剧集
编剧/导演
1989 《海角天涯》单元剧
1990 《我的英文名字叫玛丽》单元剧
1990 《丽香的感情线》单元剧
1990 《阿雄的初恋情人》单元剧
1991 《给我一个家》单元剧
1991 《秀月的嫁妆》单元剧
1991 《小孩》单元剧
1995 《我新认识的朋友》纪录片
2001 《月亮不见了》儿童歌舞剧
舞台剧部分:
1981 《速食醡酱面》
1982 《黑暗里一扇打不开的门》
1983 《房间里的衣柜》
1994 《公寓春光外泄》
1998 《小康跟桌子》
1998 《四川的好女人》
短片部分:
2002 《天桥不见了》
2001 《与神对话》(DV短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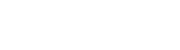




















片子里哪有爱情,却偏叫爱情万岁。都是拍都市寂寞人,王家卫是痒,蔡明亮是湿... 吃进去的西瓜,喝下去的水,都变成杨贵媚的眼泪流出来,她结尾这一哭,谁还受得了...
喝再多水,也解不了心里的渴。有那么多待售的空房,又有那么多无家可回的游魂。你卖阳宅,我卖阴宅,你在床上呻吟,我在床下自慰,人与人啊,多么近,又多么远,永隔一江水。那一场哭,为爱情,为人生,为你,也为我。
看这部电影是因为它是94的金马奖的最佳影片,看完的最大感觉就是完成了一个任务般如释重负,因为特别不喜欢这部装逼电影更不喜欢蔡明亮这个导演,整部电影充斥着神经病人的生活气息,最后的哭戏假的让人无比厌恶此电影,李安导演的饮食男女比它高不知哪里去了,看来金马奖也不过如此,有眼无珠。
蔡明亮确实将寂寞挖掘地很深,他把那些人寂寞时上不了台面的、猥琐的、自闭的、甚至丑陋的行为认真地展现出来,他精准地刻画这些行为并让其有根源可寻,那些觉得蔡明亮沉闷的人他们不相信世界上还有人会为欲望干出这么多无聊的事情,他们没有对白了便无法了解人物内心与沉闷中隐藏着的饱满的情绪。
就算做愛,自慰也不能解決寂寞。因為寂寞,所以人死後也要安放在一起打麻將。現代愛情是變形,高速,還有空虛,他們沒有得到愛情,因為愛情從來沒有發生過,愛情在電影中只是一個可待不可來的情感,將感情投放在別人身上是如此無力,終究人還是需要面對自我,就算多傷心人也會回復起來面對那不可知的未來。
其实还蛮好看的。十几岁的时候凤凰卫视电影台放过,觉得每一个镜头都漫长的像等待泡面泡发。现在看其实很有细节且富有律动,眉眼官司到身体语言,衣服在床垫上摩擦的声音。九十年代台湾真时髦,陈昭荣的黑皮衣,杨贵媚的套装,李康生的夹克和风衣,时装包裹着流动的的情欲。陈昭荣下颌线条硬朗,眼角温软,有淡淡的危险感。李康生是独处大师,西瓜当保龄球穿女装秀美腿自得其乐,他既不宣扬给别人看也不过分压抑自己。二人逆权侵占得如此和谐。杨贵媚打扮得漂漂亮亮,软语温存地带着男客户到空荡荡地大房子,是危险又孤独的工作,是真要好好哭一哭。这都市奇缘要是放在现在可能大家只是瘫在床垫上刷短视频了。
我们都是杨贵媚、李康生、陈昭荣,我们的生活有着卫生纸、脏衣服、中西药、快餐盒、房贷...琐碎事物,唯独没有爱情。因其没有,所以不朽。生活啊,就是面目可憎、但又不得不活。
“《爱情万岁》台湾中影修复蓝光版,导演亲自去调光。蔡明亮说有老电影叫《太太万岁》,张爱玲编剧,片名用万岁是向它致敬,但本片中没有爱情。片尾的哭戏,坐在杨贵媚前面的是李康生父亲,他在《洞》开拍两周前去世。杨贵媚因为和陈昭荣有床戏,想和他事先沟通下,蔡明亮说:没有必要,因为你们在电影里没有那么熟…
8/10。平行蒙太奇结构消解了潜在戏剧性,呈现私密的生活状态,如阿荣和小康一块从林小姐熟睡的床底落荒而逃,她始终察觉不到两人的存在。情节线的交叉产生了性别的内部替换:小康自觉扮演了女性角色,林小姐洗浴、起床喝水、办公室找钥匙和打车,分别对照小康洗衣、玩水、办公室独处和陪阿荣摆地摊,性别的模仿游戏在小康穿高跟鞋、吊带裙对镜摆手弄姿达到高潮,共吃火锅表现与阿荣建立同盟关系,最终如愿以偿地在隔着交合声的床底自慰,完事给阿荣送上亲吻完成性别的合一,阿荣不自觉地翻身把手搭在小康身体,回应小康深情的凝视。冷酷的长镜头将林小姐售楼打蚊子、穿梭马路将广告牌绑树上或置于车顶,以及小康无法融入同事们的幼稚游戏的工作环境对照,意在强调性欲被社会工具化淹没。小康给西瓜(私密欲望)截洞、摔碎吃了抹脸,寂寞到可笑的绝望感。
语言留给琐事,面对爱情才可尽情沉默。出售的空房子里床上两人床下一人,谁拥抱身体谁获得灵魂。性的暗示,性别的隐喻,爱与死的对照,极度颓靡,爱比死更冷。主色调灰蓝,清晨的空镜头渗出孤独者的抑郁,结尾长镜头中天气与情绪变化的表现方式极具魅力。当蔡明亮不再明亮,他才成为真正的蔡明亮。
最精彩的其实是小康把西瓜当保龄球扔那段
我们总是希望借助一件事情,去解决庸常人生的全部问题。于是我们把这些事情神圣化,比如婚姻,比如爱情。理所当然,最终的结局是幻灭的。(杨贵媚演得真棒)【7↑】
蔡明亮鏡頭里的光影聲音,是粘著情緒一點一點揮發掉的,那個城市的朝夕,在咖啡店、夜市、街道、空房子裡生動又沉默。當她踏著高跟鞋清脆的響在清晨穿過公園坐在長椅上開始哭,哭聲從無助到激烈再到平息。你就看明白這電影里什麽都有,就是沒有愛情。
迟一点看蔡明亮真是太明智了。他总能找到一个特别准确的喻体,空间喻体。比如这栋待售的空房间,三个流浪者的蟹居之地。这一部又想起贾樟柯。边缘的三角关系,发动不了的交通工具。最后杨贵媚的那场哭戏,又突兀又合理,无可名状的苦闷,导演常用的手段了。片名也妙,像是电影最后一句台词。
要是金基德来处理,估计就会让三人睡在同一张床上,抑或在二人构图里由三人来回变幻切换完成。与之比较,蔡明亮的形式感,差不多居于将成未成的临界点。
杨贵媚舔乳的那一幕那么大胆,又那么意味深长:她吮吸、盘弄男人的乳头,像一个饿坏了的婴儿在吃奶——对爱与性的需求与生俱来;然而乐园已经颓圮,正如康生和贵媚在贩卖“寓所”,却始终没有一笔成交,自己更是居无定所。三个人都寂寞极了。蔡用窥淫似的镜头语言带领观众窥视寂寞的痛苦而可耻的形状。
城市化,城市生活,本片可以说是城市化之后的一种缩影。台湾电影人已经很能够成熟的思考城市状态和人的生存,强列的孤独和寂寞,男男女女的暧昧和含混,两个无家可归的男人和一个精神空虚的女人在人生的长河中偶然邂逅,过后仍是寂寞。缺少言语乍看令人沉闷,其实镜头语言非常扎实。8.5
人到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
快进下去都看不下去,还是删除吧
小康有一块手帕 四方的 叠整齐放在口袋里 有时擦嘴 有时擦鸡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