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本剧改编自Jon Krakauer同名书籍,将讲述一系列事件,最后导致了居住在犹他州盐湖谷郊区的Brenda Wright Lafferty(黛西·埃德加-琼斯 饰)和其宝贝女儿于1984年被谋杀。 在Jeb Pyre警探(安德鲁·加菲尔德 饰)调查Lafferty家庭内部事务时,他揭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又称摩门教)起源,和坚定信仰带来的暴力后果。作为一名虔诚的摩门教徒,Pyre发现的东西让他开始质疑自己的信仰。陌陌影视陌陌影视玩的就是艳遇黑疯婆子闹监狱财叔之横扫千军国语共犯2014光芒照耀着爱反社会分子蓝桥月冷一个不落杂种狗湖中女神:朗科科马湖传说水浒客栈索勒斯角暗金丑岛君:完结篇不善之举夜深沉,爱难吟我的母亲萨梅迪黑人商业教父凤舞天下冲天小子粤语版再见了,爷爷小小飞虎队金发姑娘和两只熊死亡游戏(国语版)天赐的声音第六季追查到底东北狠人沙猩猩
长篇影评
1 ) 关于摩门、神、信仰和自己
(本人对摩门教并没有深刻的了解、不是信徒、对于基督宗教的了解也只限于大学的圣经课和西方文化知识相关课程。文章如有偏颇谅解。)
之前读到了一本比较有争议性的书,《二分心智的崩塌——人类意识的起源》。我们暂且不去探讨这本书理论的正确与否,但是可以把里面的理论作为一种参考。里面提到,人类开始是没有所谓“意识”的存在的。当人们的智力水平逐渐提升,人们开始有这种所谓“脑海中的声音”,即自己的两个半脑之间相互对话,而当时的人们却把它当作一个更高力量的存在与他们的对话——宗教由此而来。如果说千百年来,人类不断进化,终于通过各种的自我反省和深刻思考,意识到了那个声音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力量,意识到人类自己就有能力做出无数正确的决定,去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么我可否认为,类似当代许多宗教中将许多自己脑海中的声音无偏差的理解为The Holy对他们的启示其实是一种返祖行为?在世界上的各个地方,古代君王希望巩固他们的统治,将自己定义为“天选之子”,利用这种信仰的力量,让人们臣服于他们。而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逐渐意识到自己,每个人都不过是平等的,人们通过这种努力认识到自己脑海中的声音不是别人的启示,而是自己的力量,人们突破了这种“奴性”。而这时,如果人们还依旧相信“那个声音”来源于某一个更权威的力量,那难道不是另一种“现代奴性”的体现?
当然,世界上大多宗教并不是这样的,也不会像文章中的原教旨主义者那么极端。据我作为一名无神论者对于《圣经》粗浅的认知来讲,宗教和神的本意是希望传递一种普世的思想,希望人们能够通过聆听那个声音完成对自我的反思。《圣经》本身不过是像《道德经》一样希望通过那些或真或假的故事来告诉人们要像撒马利亚人一样爱人、要遵循戒律远离罪恶、要按祂所讲追寻快乐。但是,如果加以个性化解读,甚至是将这种偏颇的解读理解为新的“神的圣旨”,那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我们看到剧中Ron和Dan将启示作为借口,假以神之名而泄私欲;我们看到他们摒弃了几乎所有摩门教本身的优点而仅留下其劣根性而加以传承。我们不能确定曾经的斯密斯约瑟夫、杨百翰是否因为其他历史原因而反对政府,做出种种过激行为,但是我们知道的事Dan和Ron利用自己祖先曾经的行为当作借口,去将自己的欲望合理化——这里说到的当然不只是反对政府、反对税收,还有一夫多妻。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英雄的女性,在一个“girls help girls”的时代一个个的站出来。讽刺的是,在摩门教不知道可不可以说是极端男权主义的教义中,男人才是那个司铎,“Him”才是那个救世主,而在这场血腥的杀戮内部,女性才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同样是接受自己是救世主的的命运,Ron和Dan为证明自己的唯一大开杀戒,不惜牺牲自己的家人和兄弟。而Branda为了自己的孩子,为了家族中更多女性的命运,不惜牺牲了自己。女性是伟大的,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她们拥有共同的信仰,那种深植于基因中的母性光辉可以让她们放弃一切其他的桎梏而冲向火焰;而一些极端的男性是可悲的,他们可悲的在于只能够利用自己身体基因的优势去在物理上强调自己的伟大,他们不过是利用强壮的身体来掩盖自己弱小的内心罢了。
最后说回我自己。我不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是那种不止一次别人发出“你和她一样但是为什么你就没xxx”的感叹的那种人。在同等条件下,失败的总是我。我曾经也相信,一个叫做命运的更至高无上、更权威的东西总是不眷顾我,我也发出过为什么总是我的感叹,但是我更相信的是人定胜天。我很害怕失败,但是我不害怕挑战。我总是认为只要是我能够通过努力或者所谓智慧化解的挑战都不算事,而现在我也相信可能正是因为我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而使得所有神明和神秘力量都放弃了我,但我并不后悔,我就是自己的神。我非常理解信教的人的心理,甚至非常羡慕他们总是能够在不愉快、不得意的时候找到心灵上的慰藉,而通过这种依赖重新开始。这种精神支柱求之不得。神明会引导人们进行反思,会指引人们和自己独处、对话,而在当今这个已经拥有一定普世道德标准的时代下,我就觉得以上便是神明存在的所有意义。只要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内心,人类不需要神明的存在。我们只要能够按照普世的道德标准正确的引导自己,与自己对话和独处,自己即是自己的神,这便是我的信仰。
最最最后,不得不说一下这部剧实在是拍的太好了!无论是Jab这个摩门教警察的引入,还是那个印第安警察的存在都让这个剧的矛盾和深刻意义更上了一个台阶。还有就是加菲的演技真的太棒了!最后一集里面各种哭哭,面对自己从小到大建立起来的信仰体系的崩溃,加菲真的演的太有层次了。能不能有个艾美奖,能不能有个艾美奖啊!
2 ) 完结剧透预警 | “没有指南针的你怎么生活下去呢?”
最后pyre和家人团聚。镜头给到pyre独自在教堂和brenda泪眼相视,在心中了结了这个案子。
案情推进到找到两个瘾君子,审讯得到brenda被光天化日下谋杀的种种细节,在其中一个人说:“fu**,god” 时,pyre的神情像发泄了愤怒一样,完全不同于第一集说:“Hey,Language!”,由于十分担心Diana母女一行的安危,Dan和Ron又迟迟没有确凿的据点实施抓捕,pyre几乎快要崩溃了,于是在去犹他的路上,pyre曾泪眼汪汪向taba警探问:“How do you do this? How do you do it? Just walking through life with no compass?" Taba没有直接回答,甚至嘲讽了他一顿。
这是一点剧情摘录。其实,pyre这时候很脆弱的,他已经开始逃避这个案件,开始思索更抽象的更关乎自我内心的问题,pyre处于一个高压、缺乏休息、信仰被挑战、做了被Dan歌喉的噩梦的状态,就像一个兜了30kg重物的黑色塑料袋,表面都已经被扯白了。这时候,taba没有让他睡一觉,没有肤浅地鼓励他,只是残酷地将案子的目标扔到pyre眼前,让他思考,让他的搭档回来和他一起并肩作战。
在我看到e6,我就知道pyre会有一个撑过去的解法,所以这部片子没有想象地那么沉重,pyre最终仍是brother pyre,不过他的教堂里永远有brenda,家人,生活中的奇迹,而不是仅有永恒的上帝。但如果只将目光局限于主角,也好像就没那么有意思了。所以,期待他人的剧评。
最后一集将近90min,直到最后20min才开始将所有线聚集到一起,真的太吊胃口了。当然结束的也有些突兀。
*加菲钛色了,谢谢加菲,pyre明明在崩溃边缘、不知道该走向哪里,还凭着正义感带来的愤怒、人道主义带来的爱与善良、作为detective的责任感不停向前冲,这种复合型的柔软狗狗硬汉狠狠戳在我xp上了。
*taba和pyre有同人了踢踢我,我一定甘之如饴。
3 ) Dear Heavenly Father
When you were cuffed and you were facing charges back at the station, you called it murder. Now you are here, and it’s all just God’s command. No, you’re just using scripture,whatever scripture you wanna use, moment to moment to save your own skin.
And that’s what’s funny about so-called fundamentalists. If they wanna be so literal, wouldn’t they follow the doctrine that the church must evolve?
It’s what happens when you are taught your whole life that you need God to guide you. It’s frightening being alone with your own mind. I tried to defeat the church in my own mind, see what kind of person was left behind. I read our history, all of it, all of that personal revelation, it seems to me it’s just men listening to their own selfish desires and calling it God, so they can justify anything.
And I could look her right in the eye and truly see her, not for anything eternal, but for what we had right here.
一帮满嘴喷粪却又佯装逻辑自洽的人。
4 ) 《天堂旗帜下》原著作者访谈与写作幕后
美国顶尖非虚构作家 Jon Krakauer访谈
哪种想法会吸引你?
Jon Krakauer:我被冠以这样的作家之名,极端的观点、极端的场景描述、以极端的逻辑方式行事的人是我的写作专利。这样说也不无道理。我对狂热分子-被绝对者的诺言或者错觉引诱的人-很好奇,包括相信达到某个绝对目标,比如说知道某个绝对真相,就拥有了幸福、和平、秩序或最想要的任何东西的人。狂热分子容易对道德模糊感和复杂性视而不见,我一直对通常在面临风险以及社会面临危险时否认存在的固有偶然性的人很着迷。
你是怎样提出想法的?
Jon Krakauer:我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所写的大多数杂志文章都是由编辑提出来的。作为一名每年必须炮制出大量文章,以交付房租的自由作家(我每年必须写六十来篇文章),我发现写编辑让我写的东西比试图向编辑推销我个人渴望去做的项目更轻松,更有效率。刚开始做自由作家的那几年,我几乎什么任务都接。这些任务中更多的是不怎么生动有趣的,但我接受被扔给我的任何东西,并有一定的收获。我是个自学成才的作家。我从没上过写作课或新闻课程。我通过努力和大量的错误,在工作过程中学习写作的手法。
尽管我最棒的杂志作品探讨了我很熟悉的主题,但这些作品的很多想法都是由编辑提出来的。我的两部书——《荒野生存》和《走进空气稀薄地带》——起初都是编辑建议的杂志文章。
你怎样产生自己的想法?
Jon Krakauer:我一直保持警觉。当我看了一份当地报纸,或在与一个小城镇咖啡店里卖油炸圈饼给我的家伙交谈的时候,我都条件反射似的留心寻找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我认为住在西部是一种优势,因为就算把范围画在据此一百条经纬之外,西部的作家也是更少的,但能写的东西却很多。西部是个大地方,是许多有故事憋在心里的人的家。我好像时常会发现那些可能成为有趣的文章或书籍的萌芽的东西。
例如,《天堂旗帜下》原本是我对信仰和怀疑的本质性沉思,变成对原教旨主义的审查几乎是偶然的。某年七月的一天,我驱车前往科罗拉多,在一个偏僻之地的迷你超市停下来加油。一个指示牌指示出高速公路外有个相当规模的城镇,叫作科罗拉多城。我进去付钱的时候,收钱的女孩穿着一件19世纪的服装,就像是从约翰·福特1的西部电影中被拎出来的。尽管那天荫凉处的气温都达到了华氏104度,但她却穿着高领、长袖的长裙。迷你超市里还有其他几名妇女和女孩,我注意到她们的着装都是这样的风格。
我决定驱车进入科罗拉多城,适当地瞧一瞧。随后,我立即被大多数家园的巨大触动了:其中许多看起来就像公寓大楼。我进入住宅区大约30秒后,一辆警车就跟在我后面,一直尾随着我,直到我离开市区范围。我看到路边不远处有国家公园管理局的车辆,于是把车停在路边,询问公园管理员我后面的科罗拉多城究竟在搞什么。他说:“你不知道吗?科罗拉多城是全国最大的摩门教基本教义派群落。他们认为,如果你想上天堂,就要实行一夫多妻制。”我在西部生活了很长时间,然而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科罗拉多城,才知道生活在一位娶了75个老婆(其中好些都是在十几岁时嫁给他的),名叫鲁伦大叔的一位高龄税务会计出身的先知绝对掌控之下的数千名多配偶者。
好,所以你有普遍兴趣(信仰、宗教),并偶然发现了特定的环境(科罗拉多城)。然后呢,你是怎样把它发展成一个“故事”的?
Jon Krakauer:我是在小城俄勒冈州的摩门教徒中间长大的,他们的信仰之力让我着迷。儿时,我周围的孩子完全相信他们来世会去天国,会在那儿成为众神,掌管自己的星球。来自不可知论者家庭的我受到他们激烈信仰的冲击。此后,我一直想了解这种信仰的根基。无意中发现科罗拉多城,这让我第一次隐约感觉到或许能在摩门教基本教义派的神秘文化中找到故事。
我是个讲故事的人。我需要一个能够组织想法的架构。如果我确定一个潜在的故事足够丰富,并且决定努力争取的话,我就会疯狂地开始寻找能够使故事进展下去并能阐明我想要表达的观点的材料。
你寻找的是哪一种人物角色?
Jon Krakauer:我寻找的采访对象不仅要在我想讲的故事中扮演核心角色,还要恰好能说会道、复杂、坦率。他们是不是生气了,或者出人意料的聪明,或者有种古怪的幽默感一呃,那很重要。单单迷人的个性就能写成一本书,这是不可否认的。对非虚构作家来说,这是宝贵的一课,是我通过阅读特雷西·基德尔、珍妮特·马尔科姆和约翰·麦克菲的作品学到的功课。
你是怎样找到《天堂旗帜下》的人物角色的?
Jon Krakauer:在进行较早期的调研时,我写信给马克·霍夫曼(Mark Hofmann)。他从前是摩门教传教士,后来丧失了信仰。霍夫曼因伪造了一些损害摩门教会的历史文献,以大价钱卖给(不想让这些文献落在爱管闲事的学者和新闻记者手中的)教会领袖,之后又用炸弹杀死了两个人,徒劳地掩盖他所出售的文献虚假的事实而声名狼藉。霍夫曼被抓住,被定罪,并被送进监狱。他自1985年起就被关押起来,从未接受过新闻记者的采访。总之,我写信给他,委婉地请求采访他一次。两三周后,我收到了一封回信,不是霍夫曼写的,而是他的狱友,一个名叫丹·拉弗蒂(Dan Lafferty)的家伙写的。他因杀死自己的侄女和嫂子进行祭祀而被判无期徒刑。拉弗蒂在给我的信中说:“马克不会接受采访的。但我却很乐意跟你谈谈。并且我会是你所见过的最狂热的信徒。”
不管你信不信,我差点儿谢绝了拉弗蒂的邀请。我想跟霍夫曼谈谈,他的拒绝带给我的失望使我对摆在眼前的机会视而不见。但我决定走个过场,采访一下拉弗蒂,跟他在高度设防的监狱谈一个下午。走出监狱的门,走进犹他州灿烂的阳光里,我感到天旋地转。我因拉弗蒂向我讲述的事而惊骇不已。但就在那时那地,我知道我在书的核心故事和最重要的人物角色的抉择上碰到了困难。
其他人赞成这是个好故事吗?
Jon Krakauer:一开始不赞成。我知道这很难让人接受,因为宗教是个让许多人感到极端无聊,主题,也因为作者放弃自己家乡的地盘去写某些新鲜事物的时候,出版商就会紧张。我根本不觉得新书的主题有多偏,因为这些是我的作品中一直在探讨的主题,即使是在表象之下探讨。兰登书屋的反应特别冷淡,这伤了我的自尊。他们说:“怎么没有山呢?”所幸双日(Doubleday)的一位敏锐的编辑立刻就明白了本书的要义。所以,我最后跟他们签订了合同。
在决定是否要写一个故事时,你会有什么样的思维过程?
Jon Krakauer:写一部书是这么难,这么痛苦-需要投入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以至于除非这个主题抓住了我的要害,不肯善罢甘休,我是不会去做长得可以写成书的项目的。
例如,在1992年为《户外》杂志写了有关克里斯·麦坎德利斯的故事之后,我发现这孩子在我心里挥之不去了。我沉迷于他的故事,想了解更多他在最后的日子里的事。大家都跟我说,一个误入歧途的孩子死在阿拉斯加荒野的冒险故事写不成一本书,说我是在浪费时间。我没有获得大额的预付金,只拿到几万美金。然后,在我递交了一份六万五千字的原稿之后一年,我的编辑被解雇了。兰登书屋另一个版权标记的一位有名的编辑-被人们像神仙般敬仰、我也极其钦佩的一位编辑-寄了一封信给我的代理人,解释说原稿错误百出,甚至不宜出版。那对我是个巨大的打击。所幸维拉德的另一位编辑说服她的老板赌一把。这是一个残酷的、变幻无常的工作。要以长篇新闻为生,你必须至少有点天分。或许更重要的是要顽强,要坚决。最重要的是,要有运气。
你一直都是这样坚决顽强的吗?
Jon Krakauer:不是的。我放弃过一个故事,都做了大量的报道和研究了,是几年前,四州交界处地区三名反政府叛变者光天化日之下在科罗拉多科尔特斯的闹市用自动武器射杀了一名警察的故事。警察把这几个歹徒追进了荒原,其中两人被发现已经死在那里了。第三名逃犯始终没有抓到,或许还在那儿。我喜欢在荒原里消磨时间,为这个故事进行调研的那段时间是很快乐的。我开始探索科罗拉多高原偏远地区一些美丽的槽峡谷,但对于这个故事的主角,那名可能还活着的逃犯,我发现他不是合我心意的选择了。他是个讨厌的家伙。这个家伙还没可爱到让我投入几年的人生去写的地步。
可爱程度是你决定是否写一个人的准则吗?
Jon Krakauer:不完全是由可爱程度决定的。丹·拉弗蒂肯定不是很可爱,但他却是《天堂旗帜下》的中心人物。我发现他是个复杂有趣的人。我放弃的逃犯故事中的主要角色缺乏道德的复杂性和让我保持兴趣的深度。他只是个悲哀的、充满仇恨的年轻人。尽管拉弗蒂怎么说都很可恶,但我发现他有吸引人甚至令我同情的一面。他为我们讲述了有关我们自己的一些烦心事。
你做的是什么样的调研?
Jon Krakauer:本来,我干劲儿十足。在写《天堂旗帜下》这本书的时候,开始写之前我做了三年多的调研。曾经有那么两三次,我雇佣私家侦探帮我寻找躲避的逃犯(每次都是无果而终),但我从未雇佣过研究员来帮我调研一部书或杂志文章的背景。我喜欢做调研,远远超过对写作的喜欢。我总是先从整理图书卡目录、书店、优秀的书商、互联网和报纸档案开始。方位感-对所述风景的熟悉程度-对我来说始终很重要,所以我买了许多地图。
《天堂旗帜下》调研期间,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杨百翰大学、盐湖城公共图书馆和犹他州历史协会梳理卡片目录。摩门教徒是如此热衷于记录自己的过去,以致任何与摩门教的历史有关的的案都塞满了庞杂的资料。
我特别留意那些能帮助我把不相干的故事串联起来的名字或事件。例如,在(天堂旗帜下》的早期调研中,我了解到丹·拉弗蒂和他的兄弟罗恩加入了一个叫先知派的图体,在那里学习如何接受神启,包括神命令他们割开嫂子和女婴的喉咙的启示。所以,我研读了该教派的圣书,找出所有成员的名字,然后寻找它与书中其他一些故事的联系。因着对先知派的研究,我能够在拉弗蒂兄弟、科罗拉多城、伊丽莎白·斯马特(Elizabeth Smart)、杨百翰以及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一夫多妻社区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
有没有任何让你回头去找的特定资源?
Jon Krakauer:审判笔录是一座信息的金矿。通常,你必须直接向法院书记官购买这种笔录,那是出奇的贵(为了写《天堂旗帜下》,我花了几千美金买了审判笔录),但却物有所值。你会了解到你在任何别的地方都了解不到的事。你本来没指望能找到的人被传唤作证。而且,笔录中通常有这些人的住址以及其他生活细节。笔录也是故事的巨大源泉。这种故事与我所构建的不怎么相似,但律师们都试图讲述一个连贯的故事来推进他们的目标,这些相互矛盾的故事常常具有启发性。
你在哪儿或者跟谁学的做报道?
Jon Krakauer:20世纪80年代初,当发现自己破产并失业了的时候,我就成了一名新闻记者。我那时是个木匠,但建筑行业特别不景气。我刚刚结婚,妻子也没有可以领薪水的工作。我非常绝望,以至于反复考虑申请进入法学院,我甚至为了参加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而学习。我的朋友和攀岩同伴大卫·罗伯茨(David Roberts)把我从那样的命运中拯救了出来。他刚刚离开学术界,首先成为《地平线》(Horizon)杂志的一名编辑,再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他说新闻报道“比敲钉子要有意思得多”。他跟我说:“杂志会给钱让你去有趣的地方旅行,和有趣的人交谈。开始做就是了。慢慢就会了。”
我买了一本书,学习怎样用所有的手指打字。然后,我又买了一本书,学习怎样成为一名杂志作家。这本书基本上都是胡扯,但的确教了我怎样有效地写单页的自荐信,这可是一门非常宝贵的学问。你得有时髦的文笔,用新潮的语言,把你的想法的有趣之处通过最精悍的篇幅传达出来。这本入门书建议规定一个数量,每周大约投递十封自荐信,我就照着做了。我在杂志圈一个人也不认识,但我想地位、级别较低的编辑更有可能查阅自己的邮件,而不是居于高位的大人物,所以我把自荐信寄给了他们。我投给《户外》杂志的第一封自荐信给我带来了一项碰运气的任务,投给《滚石》的第一封自荐信也是。为打入《史密森尼》(Smithsonian),我试了好几次,最终也开始在那里接到任务了。
你是怎样从关于登山的写作转到别的主题的?
Jon Krakauer:我意识到,我不能专门写探险类作品,因为能给我足以谋生的工作量的户外杂志太少了。在我短暂的生命里,我干过很多不同的工作,所以我试着把我在其他领域学到的东西充分地利用到写作任务中去。我向《史密森尼》投了一篇关于阿拉斯加锡特卡商业鲱鱼捕捞业的新闻稿,那里整季的捕捞可持续六个小时,能使船长及其船员暴富。我之所以了解,是因为我在一艘58英尺长的阿拉斯加拉网渔船上工作过。我用我所学的建房知识为《建筑文摘》(Architectural Digest)写有关建筑学的文章,为《花花公子》(Playboy)的每月专栏写了两三年有关健康和健身的文章。
你的记者立场是怎样的?
Jon Krakauer:我力图做到公平、客观,但如果我足够关注一个要写的主题,那很可能是有目的的。我几乎一直试图提出论据,尽管我通常喜欢间接地提出来,而不是拼命向读者灌输。我想要触动读者,将他们置于紧张不安的事实之中。但我从不抨击谁,不论主题是什么,我都尽可能带着同情与共鸣去写。
例如,写《天堂旗帜下》的时候,我纠结于如何在提出“毫不动摇的信仰面临危险”这个看法的同时,表达我对有着根深蒂固宗教信仰的人的敬意。尽管我是个不可知论者,但我被宗教情怀的表现深深打动了。当我听到人们热心地讲解祷告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或者,比如说听着爱美萝·哈里斯(Emmylou Harris)用天使般的嗓音颂赞耶稣,我有时会感动得热泪盈眶。我理解人们渴望认识神。我自己也有相同的渴望,我感觉它深入骨髓。但那不会阻止我报道人们常常在虔诚的外衣下所做的恶行。我很赞赏摩门教徒的很多东西,在《天堂旗帜下》这部书中,我试图表达这种赞赏,同时尖锐地质疑管理摩门教会之人的某些行为。
你怎样设定自己报道的进度?
Jon Krakauer:我常常工作到濒临崩溃。我所写的人常常会邀请我待在他们家里,这从报道的角度来讲是难能可贵的,但也会很危险。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可以逃避的处所,我可能会过早地崩溃。我一般更愿意一天与他们一起待上六至八小时,然后撤退到我的住处或旅馆房间。
作家小传 | Jon Krakauer
乔恩·克拉考尔的自尊心被他的编辑对他最新的书《天堂旗帜下》的一份初期草稿的冷淡反应伤害了。克拉考尔最畅销的两部探险故事作品《荒野生存》和《走进空气稀薄地带》相继出版之后,这位编辑对接下来的这部作品-有关摩门教和1984年的一场活人祭,长篇大论地描述该宗教历史的粗鄙故事-感到很困惑。“新故事里怎么没写山呢?”他问道。
但那位编辑没有体会到,在《天堂旗帜下》这本书里,克拉考尔没有背离,而是延续了他的一贯的主题:那种看破红尘的极端信教者与信仰、理性间的微妙关系,无论他们是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登山运动员还是宗教狂热分子。克拉考尔没有重写这部书,而是换了出版社,然后《天堂旗帜下》成了他的第三部畅销书。
克拉考尔扭转了美国探险故事的传统。他对采访对象的认同、大量的个人投入都使他的自然/探险类著作与众不同。
乔恩·克拉考尔1954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市(Brookline)。在他两岁时,全家搬迁到俄勒冈州科瓦利斯市(Corvallis)。八岁时,父亲带他攀登俄勒冈州一万英尺高的三姐妹山南峰(未能成功),这激发了克拉考尔一生对登山运动的痴迷。
克拉考尔的志向与他父亲对他的心愿不同。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希望儿子也拿到他的文凭(威廉姆斯学院和哈佛医学院)。克拉考尔上初中时,父亲送他去波士顿参加一个为期两周的新英格兰学院的精英面试。克拉考尔在等待他的阿默斯特学院面试时,听取了另一位应试者的一些建议:“老兄,你应当考虑一下路边那所嬉皮士学校。”
罕布什尔学院是一所实验学校,办学才两年。克拉考尔在那儿看到的第一名学员是一个穿着透明衬衣的女孩。这所学校不分年级,有尸外活动和裸泳池。他没有征求父亲的意见,申请了提早决定,并被录取了。“当时,罕布什尔比哈佛还难进,我以为父亲会很自豪的。”他说。这件事后,父子俩两年都没有讲过话。
克拉考尔学的是环境科学,为了完成毕业论文,获得学位,他致力于在一座号称“鼠牙”的阿拉斯加山脉上开辟一条险峻的新路。大学毕业后,克拉考尔断断续续地做过木匠和商业渔民,以支持自己爬山的爱好。1974年,有人邀他在美国高山俱乐部的杂志上写自己攀登阿拉斯加三座未曾探索过的山峰的经历,这是他的第一个写作任务。这篇文章最终招来了更多任务,特别是《户外》(Outside)杂志给的任务。1983年,克拉考尔辞去了建筑队工头的工作,开始专心写作。
1992年,一群驼鹿猎人在阿拉斯加的荒野地带发现了一个年轻人腐烂的尸体。《户外》让克拉考尔写一个关于这个年轻人克里斯·麦坎德利斯——来自华盛顿特区的一位活泼的理想主义者-的故事。结果,这篇文章引来的邮件是该杂志前所未有的。许多读者认为麦坎德利斯是个鲁莽的傻瓜,也有人对他的精神追求表示同情。
克拉考尔觉得麦坎德利斯很像自己。“这孩子的饿死,还有他和我的生活事件之间那种模糊的、使人担忧的相似之处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他说。克拉考尔年轻的时候,有过一次特别危险的单独攀登“魔鬼的拇指”--座偏僻的阿拉斯加山峰-的经历,以及被许多评论家认为是自取灭亡的壮举。而这些,或许正是被把麦坎德利斯推向危险边缘的那股莫名其妙的力量驱使着。克拉考尔写道:“来到阿拉斯加,麦坎德利斯渴望踏入一个未知的国家,找到地图上的漏耕地。然而,1992年,地图上已经没有漏耕地了-不是阿拉斯加没有,哪儿都没有。但克里斯的逻辑很特殊,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他想出了一个优雅的解决方案:他干脆不要地图了。按他自己的想法,如果别无他处,这片未知领域仍会保持神秘。”
《户外》的文章发表一年以来,克拉考尔仍对麦坎德利斯无法忘怀。他得到一部书的少量预付金,用两年的时间追溯麦坎德利斯当年的路线。《荒野生存》是克拉考尔的第一部畅销书。托马斯·麦克纳米(Thomas McNamee)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写道:“通过麦坎德利斯的童年、他逐渐成年过程中频繁的社交和冷漠的退学,通过对那把他带到阿拉斯加的两年心神不宁的徘徊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克拉考尔先生精心构建的故事把我们从猎人发现的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刻带了回来。我们对他了解得越多,就越觉得麦坎德利斯神秘,越觉得故事新奇。”
1996年5月10日,克拉考尔随着一支23人组成的探险队登上了高达29028英尺的珠穆朗玛峰顶。一天下午,峰顶下起了暴风雪,使几支探险队的向导所犯的错误进一步加剧。最终8人丧生,其中包括喜马拉雅山脉最著名的两位向导斯科特·费舍尔(Scott Fischer)和罗布·霍尔(Rob Hall)。
从这次登山事件逃生后,克拉考尔起初并不想写一部关于此次经历的。杂志文章发表之后(该文章获得了1996年度美国国家杂志报道奖),他发现自己了几个想要更正的重大错误。“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经历使我的生命彻底被震想了。全面详细地记录事件,不受有限的栏寸约束,对我来说变得至关重要。”他在引言中写道。悲剧发生之后,他进行了无数次采访,对有关这次登山的许多矛盾的叙述进行权衡,并梳理大本营无线电记录簿,以寻求真相。《走进空气稀薄地带》高居畅销书排行榜长达两年之久,同时入围普利策奖和全美书评人协会奖。
少数几个那天攀登了珠穆朗玛峰的人-包括克拉考尔自己-都没有受到批评。“不争的事实是,我心里有数,但最终还是去了珠峰。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我期待着死亡的发生。这种想法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感到良心不安。”他写道。“围绕珠峰的争议改变了他。”《国家地理探险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Adventure Magazine)的编辑约翰·拉斯马斯(Jhon Rasmus)说,“乔恩觉得关于珠峰的这部书某种程度上是在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时间出现的结果,而他从最终成为悲剧的故事中获益了。”这是他对引起最大争议的向导的批评。克拉考尔指责阿纳托利·布克瑞夫(Anatoli Boukreev)在他的所有客户下山之前就离开了峰顶,并指责他没有补充氧气。在这部书较晚版本的附言中,克拉考尔称,但愿自己在珠峰事件后与布克瑞夫的争论中能“不那么尖锐”。在布克瑞夫自己写的关于珠峰灾难的书问世之后不久,他就去世了。1998年,克拉考尔创立了珠峰96年纪念基金,资金来自他自己的版税。
《荒野生存》和《走进空气稀薄地带》的成功给克拉考尔带来了财富,让他能够自由地停止为杂志写作,仔细地选择下一部书。第三部书,他想进一步探索贯穿于他作品中的主题。克拉考尔很多儿时的朋友都是摩门教徒,他一直惊叹于其信仰之激烈:“我的摩门教朋友的信仰是如此笃定、彻底。我却来自一个不可知论者的家庭。”
当他无意间发现了科罗拉多城-横跨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边界的一个大型摩门教基本教义派群落时,他隐约感觉到,这或许给他的冥思提供了一个环境。当克拉考尔获准采访丹·拉弗蒂(Dan Lafferty),一个在活人祭祀上杀死了自己的嫂子和侄女的摩门教基本教义教徒时,他知道自己找到了讲故事的话题。
《天堂旗帜下》完全脱离了克拉考尔先前作品的文风。尽管这部作品是由深刻的问题激发的,但直等到自注他才现身,并且表述了自己的神学信条:“我甚至不知道是否有神,尽管我承认在非常恐惧或绝望或因看到出乎意料的美景而感到惊讶时,会不知不觉地祈祷。”
人们对这部书毁誉参半。许多评论家指责他忽略了摩门教的正面特征。“有些事一定能说明主流摩门教盛行的原因,我怀疑这只是残留的独裁主义的黑暗能量。”罗伯特·赖特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写道。《当今时代》的马克·恩格勒推测克拉考尔不懂神学:“他将宗教和科学的复兴作为相互排斥的选项,重新引发了一场冗长的陈腐争论,几乎没有对深刻理解道德标准及其意义的问题产生多少作用。假如克拉考尔没有忽略现代神学的浩瀚,因其在理性和信仰之间提供了更微妙的和解,那么克拉考尔自身对宗教的寻求会更令人信服。”在《华盛顿邮报》上,安·鲁尔则称之为“必须细细品读的一部杰作”。
摩门教会更是恼火,在该书出版前两周发布了一篇五页纸的、单倍行距的辩驳文章,称这部书是“对现代教会真实性的全面进攻”。该教会谴责克拉考尔利用一个原教旨主义教派的暴力行为来诽谤整个宗教:“他的基本理论好像是说有宗教信仰的人没理性,因为没理性的人才会做奇怪的事。”
克拉考尔为他的报道争辩,并谴责摩门教会粉饰历史。“他们迫切需要攻击像我这样,呈现了对摩门教历史所做的公正的、经过用心研究的,却正巧与官方以及大力修正过的教会版本相违背的描述的作家。我感到特别失望。”他坚称自己写这部书的目的是高尚的。“我想写写他们怎样处理自己的历史,我没想到他们会那样恼怒。”
本文节选自《新新闻主义》
罗伯特·博因顿 著
刘蒙之 译
5 ) 正义旗帜下的残忍恶行 | 《天堂旗帜下》口语笔记
所谓悲剧,就是将一切美好撕碎给人看。在宏大的信仰与具体的人之间,我们究竟应该爱谁?我们是否真的有权力高举正义的旗帜去做邪恶残忍之事?
我一边跟着泪眼朦胧的加菲抽丝剥茧,一边整理了些实用口语表达分享给你——
1 Mormons 摩门教
摩门教在本剧中贯穿始终,这里简单汇总了一下相关的词汇:

摩门教Mormon Church一词,源于Mormonlism摩门主义,是美国的第五大宗教,犹他州首府盐湖城被信徒们尊为圣地。教会的信仰对女性、黑人以及同性恋者并不友好。
由于信奉的教义与一般教会相去甚远,普遍被基督教会视为异端。
最广为人知的是“一夫多妻”制度。据悉,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至少有34个妻子。在他死后,他的部分妻子被继任者杨百翰继承,杨百翰一生至少有55个妻子和57个子女。虽然一夫多妻制在1890年正式终止,现在仍有几个少数分支实行一夫多妻制,比如FLDS摩门教基要派。
BTW,剧名以及同名小说书名 Under the Banner of Heaven 就源自LDS 教会的第三任会长为“一夫多妻”制的辩护:God is great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en the Government conflicts with heaven, we will be ranged under the banner of heaven against the Government.
1.1 LDS 后期圣徒

LDS = Latter Day Saints = the Mormons. LDS全称为: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信徒”是摩门教的最主要分支。总部就位于本剧的犹他州盐湖城。
1.2 Joseph Smith Jr. 约瑟夫·史密斯

摩门教和耶稣基督后期圣徒运动的创始人,有着非常传奇的经历——
15岁时,在纽约州的曼彻斯特的家附近的树林里祷告,见到了异象(神的显现),得到了神的指引。
17岁时,再次见到异象,被一位神的天使摩罗乃交付4年后将“翻译”《摩尔门经》的工作。
21岁时,得到了“摩门经金属页片”。
23岁时开始翻译《摩尔门经》。
24岁时,出版了《摩尔门经》,创建了摩门教。直到14年后他去世时,已经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信徒。
1.3 Pioneer Day 先锋日

1847年7月24日,为了逃离迫害,摩门教先知Brigham Young杨百翰带着一批教徒穿越大半个美国,来到犹他州盐湖城,并称之为“建造圣殿的的地方”。为了纪念这一天,犹他州每年7月24日会以烟花、歌舞、牛仔表演等活动来庆祝。
1.4 BYU 杨百翰大学

全称为: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成立于1875年,隶属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全美最大的教会大学。
1.5 Zion 天国

一般指耶路撒冷,有时泛指以色列地,这里指基督教的天堂、天国。
2 have sb's back 保护某人

have (got) sb's back 意思是保护、支持某人,Don't worry. I've got your back. 别担心有我在
3 throw up dust 混淆视听

字面意思是扬起尘土,有点像放烟雾弹掩盖事情真相,混淆视听。口语中常用的表达是 throw dust in sb's eyes 给某人眼里扬沙让他无法看清真相,也就是误导某人、欺骗某人。Give my whole money back; you cannot throw dust in my eyes. 把所有的钱都还给我,你骗了不了我。

4 I've walked this road before 我是过来人

这句很好理解,字面意思是我之前走过这条路,也就是我有经验、我是过来人,中文里也有相似的俗语“要知山下路,须问过来人”还可以说成:been/gone down this/that road before
5 go-ahead 许可

go ahead 既可以作动词也作名词,去做吧、许可的意思,We'rereadytostartbut we're stillwaitingtogetthego-ahead fromourheadoffice. 我们一切准备就绪,但仍在等着得到总部的许可。
6 under wraps 秘密的

wrap作动词意思是把东西包裹住,常见短语 keep it under wraps 把某物包裹起来、藏起来不被发现,也就是保密的意思,其中 under wraps= secret,"保密"的短语最早源于19世纪的赛马比赛中,练习的时候让马放慢速度,以此来隐藏真正的实力。They tried to keep the report under wraps. 他们试图对该报告保密。
7 get wind of sth 听到风声

这句表达和中文非常相似,听到了某事的风声,或得知了某个秘密消息,I don't want my colleagues to get wind of the fact that I'm leaving. 我不想让我的同事们知道我要离开的消息。

8 rip through sth 席卷

rip 撕裂,rip through sth 快速猛烈地穿透、毁坏某物,A hurricane ripped through the Caribbean. 一股飓风席卷了加勒比海。
如果你也喜欢本剧,不妨帮我点个赞吧,赞多的话我来继续更新~
|本文作者:枫叶依蓝
|审校编辑:Juliet
|总 编:大风哥Wind

6 ) 比邪教还吓人,无数女性成为它的祭品
一位年轻母亲和她15个月大的孩子被人残忍杀害,负责调查凶案的警官Pyre发现背后大有隐情。
一切要从他的宗教信仰开始聊起。
Pyre是一位虔诚的摩门教教徒,他和妻子恩爱多年,育有两个女儿。作为该教的主要分支,LDS(即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简称,中译名习惯翻译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在Pyre生活的社区享有极高威望,社区主要成员大多也为该教信徒。
别看LDS名称中带有耶稣基督字样,它的创建历史并不久远。
相传,生于1806年的约瑟夫·史密斯,在15岁时声称自己频繁看到异象(信众更愿意称其为“圣迹”),作为对异象的回应,约瑟夫创建了摩门教,并于1830年发表该教创教经文《摩门教》。

与严苛教规形成鲜明反差的部分则是约瑟夫的婚姻,在其短暂的一生中(1844年被暴徒冲进监狱打死),他一共拥有34位妻子,他的宗教继承人更是夸张的拥有过55位妻子。直到受制于主流舆论压力,让LDS自发宣布废除一夫多妻制以前,这样的配偶关系差不多是每位男性摩门教徒的常态。
今天,分裂出来的原教旨主义分子依旧保留了这一传统,他们集中生活在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的接壤地段。多年来,该团体一直游走于法律边缘,并尝试将一夫多妻制无罪化(美国50个州宣布此类婚姻违法)。
针对外界批评,LDS团体大致分为两大阵营,一部分人如前文介绍选择故步自封,至今仍生活在一个极度封闭的圈子内,因此极易滋生类似剧中的恶性犯罪事件。
另一部分人则相对开明,他们接受主流社会同化,选择普遍的一夫一妻制。Pyre作为后者,在见证了原教旨主义分子犯下的罪行后,不禁开始对自己的信仰产生动摇,这也为他的婚姻带来麻烦(女方为坚定的摩门教信徒)。

Pyre调查的案子带有明显的宗教仇杀色彩。受害人Brenda原本来自外地,因和摩门教背景的丈夫自由恋爱,遂决定加入这一拥有众多家庭成员的大家族。
这家名为lafferty的家族在当地势力庞大,大到经营企业,小到可以帮社区教众排忧解难,处理和政府之间的矛盾。
如果仅仅只是以路人身份对其了解一个皮毛,lafferty一家或许和普通的美国白领阶层并无太多差异,但过门以后,Brenda发现情况远比她想象的复杂。
这是一个男性主导绝对话语权的家族,女人在家中的地位只不过是一层附庸,男人几乎决定着家里一切重大事务的走向,女人则在该类事务中处于架空位置。
作为这场不幸婚姻的受害者,Brenda拥有和皈依摩门教女性截然不同的性格特质,她勇敢、独立、自主,并敢于对男性的骚扰予以聪明而决绝的反击。遗憾的是,这一特质并未帮助她在lafferty家族内赢得尊重。相反,随着和家族内部成员的朝夕相处,迎接她的只有来自男性家庭成员的白眼。

不光女性在家族内部存在明显的话语权不足,lafferty家族男性成员的内部关系也非常紧张。虽然只有7集,但故事前两集就将lafferty家的权力生态环境勾勒得一目了然。
家里的长辈——同时也是家族的绝对权威老Lafferty,他有着说一不二的行事作风,即便只是和Brenda的首次会面,对方的“不安分”就给他留下极坏印象。
老头行事武断专横的作风被耳濡目染的几个儿子如数继承,唯独老大除外。
在外界从政的老大拥有和Brenda一样的开明思想,这样的立场自然和专制的父权背道而驰,被家族视为异端,长期游离于家族核心权力阶层之外。


继承家业的老二和其余lafferty家族的男性成员被视为是整起凶杀案的重大嫌疑人,这和他们对原教旨主义的极度狂热有密切联系。
剧中不止一次向观众展露了被极端宗教思想洗脑的信徒对生命的蔑视。在他们的信条中,挑战男性权威不单单是对男性家庭地位的质疑,更是对“天赋神权”的严重践踏。
而这些秉持所谓“天选之子”或“上帝旨意”对别人施加暴行的家伙,我们当然明白那不过是人为自己罪行开脱的借口。本质上,他们不过是替人性的幽暗面寻找一个合法化载体,一夫多妻和针对女性的制度化奴役即是载体的具象表征。
就像Brenda在案发后反思和妻子生前的关系时所忏悔的那样,LSD的教义要求摩门教女性信徒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家庭的做法,无异于剥夺了女性的个体尊严和价值,让其彻底沦为男性的附庸。

在拥有绝对话语权的摩门教家庭中,当繁衍事务优先于女人事业,并被视为理所当然,类似Brenda一样的独立女性便只能被迫禁锢于家庭的日常琐碎中。
这样的婚姻和其带来的后果,《革命之路》有过生动表现,但对Brenda而言,要在她的社区堕胎简直是奢谈——社区文化不允许,家庭环境也不支持(Brenda本人是纯正的基督徒,该教不允许女人私自堕胎)。
经过一番权衡,Brenda最终在事业和爱情中选择了后者,她的丈夫也为这个小家庭做出“牺牲”,选择和家族里的狂热分子分道扬镳。
二人的理想并未给他们换来善果,反而为其招来杀身之祸。《天堂旗帜下》为我们还原了任何信仰偏向极端后所具备的邪教特质,并让非信教受众难得目睹宗教世界里长期存在的性别权力失衡。

和《圣母》里表达的女性性取向自由截然不同,《天堂旗帜下》更侧重于信仰危机引发的家族悲剧。在这场悲剧中,女人成为了男性权力的献祭品,他们口口声声的“替天行道”,无非是权力的滥用和再巩固。
而这恰恰是宗教最吊诡的部分,它一方面强调世俗欲望的多余,另一方面却又不计代价地维护其自身的世俗利益(比如LSD的多妻和某宗教团体进军房地产),与其说宗教是神的诏谕,倒不如说它是一种统治工具的变种。
通过该作,我们看到了自由意志和专制思维之间的显著区分,毫无疑问,其在海外的播出势必会引发一场围绕存在合理性的口水战。LSD的原教旨主义支持者和他们那不受法律控制的婚姻模式,将再一次被舆论推上风口浪尖。
撰文 / Zed
策划 / 轻年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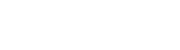




















美国人民也是水深火热…
提前刷完Jon Krakauer的原著就是为了不被剧情牵着可以好好欣赏加菲,如果想进一步读读有关摩门教(尤其是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的起源和发展的话可以去读读同名书,如果只是来看加菲的话,Pyre警探的角色并未出现在书里,是根据当年调查该案的警探角色改编加入剧中的。摩门教所谓每位虔诚的信徒都可以直接获得上帝启示的教义不仅弱化了该教领袖的统治地位,更是为极端主义教徒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和道德支撑。摩门教创始人约瑟·斯密的初衷并不是要挖什么预言,就是因为太穷了要挖宝藏换钱糊口。加菲在采访里说"I'm a sl*t for true crime"哈哈哈,除了再次花痴加菲外,在提前知道案件来龙去脉的情况下,我只想说全体卡司的演技都很在线~
摩门那种压抑畸形的氛围拍的太好了 好需要第三集受不了一个礼拜了求求
有潜质成为2022的《真探》。全员演技不想说炸裂,就想说舒服,太舒服了。
缓慢,沉重,像一首厄运金属。信仰的泥泞,现实的悲戚,从命案开始回溯,可能一切都是注定的。
原书是本纪实文学,在女主被杀后探究极端宗教FLDS的起源和谋杀动机的关联,不要以上帝的旨意和信仰这些来粉饰你暴力犯罪的动机,杀人就是真真实实地杀人。摩门教教导女性要顺从,要侍奉自己的丈夫,看看里面那群儿子的太太们,好好的女孩子,都是极端宗教害的。加菲演得是不错,作为一个教徒,在破案过程中开始质疑自己的信仰。很多对白教义相关,无法共情,也理解无能,阐述教旨的过程中还穿插了摩门教起源,拍得非常神神叨叨,节奏又巨慢,看一集我可以翻无数个白眼。我对摩门教的全部认识都来自The Book of Mormon,原来我觉得摩门只是一种宗教而已,看完这个剧,我真觉得摩门是一种邪教。
加菲眼含泪光的时候,不管几岁都是我的宝!
我确信这是一群宗教狂徒的极端主义和破坏性行为所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说实话,对我这种不信教的人来说,看别人信仰崩塌的过程其实有点恶趣味。(第六集,我承认我开始有点不忍心了)但是,对于一切教派的狂热信徒(利用教义旨更多为了满足自我),我的反应都是,去你妈的!第四集,单拎出来这一集我会给5分,剧情设计的很巧妙,也讲清楚了很多东西,不过看这一集的剧情,我一半在愤怒,一半在感慨女主的“天真”和善良,会有点难过。以及男女主选角真好,我不知道还有谁能替代他们的气质和氛围。
以前看过一个纪录片感觉摩门的人都长得奇奇怪怪的,女主太好看了或者因为normal people印象太深了不像这个宗教的人。
借宗教之名 行一己私欲 根本就没有什么天国 有的只是自己就是the one 一群不想交税还推崇一夫多妻制的邪教渣男 有什么样变态的父母就会教出什么样变态的后代 还全是men 可想而知嫁入这样家庭女性的命运 除了自己被主动洗脑 就是觉醒后在逃亡中担心受怕 珍爱生命 远离邪教
刚啃完前两集的生肉,比较肃杀沉重的宗教主题,父权和夫权对女性的压迫。叙事和剪辑都很有意思,有一些关于摩门教起源的闪回和宗教本质的思考。演Allen的小演员挺亮眼的。加菲在里面有种禁欲的美,可远观不可亵玩的圣父一样的角色,但是他越一丝不苟穿着西装越让人想……更新一下,第六集看完了,观后感之一:Religions are full of shit.观后感之二:天父对我说了,让我立刻马上和安德鲁加菲尔德睡觉。加菲你看着办吧~
两集下来悬疑感没看出来反倒像看了两小时摩门教传教宣讲还是极端的那种,宗教部分能不能拍通俗点...节奏和故事实在提不起精神。And behold, these Lafferty mormons are bunch of伐木累侠,让他们去演速激吧。btw黛西是真的美出境界
4/5 | 宗教最吊诡的部分在于,它一方面强调世俗欲望的多余,另一方面却又不计代价地维护其自身的世俗利益(比如LSD的多妻和某宗教团体进军房地产),与其说宗教是神的诏谕,倒不如说它是一种统治工具的变种。
ep6结尾加菲哭得特别好,如何表现一个男人在和父权制下的女人共情,不是让他咒骂世道、开挂颠覆或是英雄救美,而是让他坐在车里像个孩子一样无助地哭。/一开始觉得Daisy演太美艳了,后来一想确实要给她光环让她圣化,临死那场戏她满面带血大声赌咒,用生命在说:十字架上被钉的其实是一个女人。
好多英国演员 大家都演技炸裂 Allen让我想起权游里的Theon
这个阵容真的太强大了…吸血鬼头头+狼人爹+阿凡达+新美队+蜘蛛侠…还有棋后妈+威尔士王子…当然了加菲在里面还是闪亮亮
加菲走出犯罪现场,双眼泛泪光说“过分”的时候,心也要碎了
没有人性 信仰只是犯罪的借口
极端宗教生殖癌男性,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谎称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样他们才能自圆其说。简直就是恐怖片。加菲把信仰逐渐崩塌的警探演活了。
加菲只需要慢慢说话 他的演技就进入了另一高度 和以往太不一样了 魅力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