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爱丽丝,是一个单身母亲,也是一家新品种植物开发公司的高级植物培育员,工作非常勤奋。她设计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暗红色花朵,不仅外观让人注目,其健康价值更是出众:如果气温合适,营养足够,人们能时常跟它说话,这棵植物就可以让它的所有者开心起来。爱丽丝违反了公司规定,带了一株回家送给自己的青少年儿子,乔。他们给这朵花起名“小小乔”。但随着花朵生长,爱丽丝越来越怀疑“小小乔”也许并不像它的名字那么无邪。陌陌影视陌陌影视爆裂魔神少女行规2000德云社烧饼曹鹤阳相声专场成都站侠盗联盟粤语摩斯探长前传第一季下女1960吸血刑警罗道烈芭比之圣诞颂歌请回答1994GADDAR-血腥之水当幸福来敲门2006鱼味男孩俗·再见,绝望先生外洋尘埃去联谊却发现没有女生玫瑰的故事亲友皆死威震八方斯文加利东京卍复仇者通天拍档1988明日传奇 第二季恐惧中的恐惧歪星撞地球第三季
长篇影评
1 ) 专访艾米丽·比查姆:艺术的作用,就是让你质疑
(原载于《电影》杂志与“电影杂志 MOVIE”公众号,图片版权归《电影》杂志社。导演采访→《专访杰茜卡·豪丝娜:人不一定生来就是为了追寻快乐的》)
艾米丽·比查姆很瘦,略大的连衣裙并不贴身,紧勒的腰带摘下了,布料就有了种要飘起来的假象。
不在乎。衣服的缺陷,正好拿来大咧咧地自嘲。
照片没拍多久,似乎被镜头追到了穷途末路。她定住,笑了笑,有些不好意思地表示,哎呀,不知道该摆什么姿势了。
似乎只习惯在镜头前诠释角色,而不是摆弄自己。
于是当摄影师让她想象要抓住点什么,或是心情突然放晴时,她一下子俏皮、生动起来。
剧本是一桶燃料,没有注解也不打紧,她可以用演员的格调来完成明星的使命。而那种谦逊与诚恳,又赋予她高于本职的魅力。
有一瞬间她玩得特别开怀,特别忘情。不过等到结束后问她,晚上是不是要去吃烤鸭呢,她笑得更加灿烂。
(注:以下涉及剧透。)

1 我不介意角色是什么,只要剧本好,而且导演有意思
5月17日,《小小乔》在戛纳放映。活动结束后,艾米丽·比查姆就回了英国。
一天早上,她醒来后接到一个电话,被告知要火速赶去机场,搭乘最早最快的班机折返戛纳。她的确是去了,只不过,从英国尼斯启程的漫漫长路,她乘坐的是摩托车。
风尘仆仆,却也酷劲十足。
紧接着,她成为了最佳女主角。聚光灯打下,才满35岁的她被定格在影史的光辉一页。
只是向来低调的她,就连社交媒体也几乎不发工作以外的内容。很多人还不熟悉这位新晋影后,更不知道她的大半人生经历,都与表演息息相关。
其实就跟许多演员一样,艾米丽自小就对表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在那会儿,她还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成为演员,于是18岁时,她去伦敦音乐戏剧艺术学院参加了面试。
可即便幸运入围,她依然不知道演员能否成为自己的职业,毕竟“这个行业太难进去了”,因此她还准备了应聘简历,预备去酒吧工作。
总是欠缺一点信心的艾米丽,其实彼时非常享受跟学院的老师合作。“他们总能让我受到鼓舞,而我也能学到很多,他们的恩情,我欠了不少。”在学校里,她还遇到了一个不错的经纪人,使得她在竞争激烈的演员行当里,慢慢地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来”。
“过了好一阵子,我才能跟合适的人在一起工作。我觉得每个演员都会有适合自己的不同项目。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想参与独立电影制作,而且这种表演是我所喜爱的,让我很有感觉。”
艾米丽深感幸运,因为无论是影视表演还是剧院表演,“都能跟很好的导演合作,饰演一些有深度与风格的角色”。
2006年,拿到学士毕业证书的艾米丽正式踏入影视圈,接拍了《牵引亡魂》(2006)、《一路顺风》(2006)等剧集。
这些年大大小小的角色试下来,还是要等到电影《凯撒万岁》(2016)和剧集《百年乡情》(2013-2014)、《荒原》(2016-2018),才能给予她更高的知名度。
在吴彦祖主演的《荒原》里,她演活了一位非同凡响的寡妇,被人们用“能将剧集据为己有”来夸赞表演的出彩。
等到独立电影《达芙妮》(2017)找上门来,她更要大呼这是“意外得到的天赐之礼”。评论界不吝笔墨地盛赞大放异彩的艾米丽,最终她也收获了伦敦独立电影最佳女主角、托里诺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等表演类奖项。
当然,她仍旧没有当红的境遇,也没有翻红的功利。
不断感激一路尽遇贵人之余,身为演员并以演员自视的艾米丽只是一再强调,“这就是我的口味,能去做一些真心实意喜欢做的事情真是太赞了。”
她说,“我不介意角色是什么,只要剧本好,而且导演有意思,我就会非常渴望去合作。”她又说,“我的确很享受看到一份好剧本的喜悦。而且,当作品能有好质量的时候,那种感觉简直美妙无比。所以,我真的是非常走运。”

2 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而这就是我想要去做的
《达芙妮》之后,就是杰茜卡·豪丝娜的《小小乔》(2019)。这种偏向独立的作者电影青睐艾米丽,艾米丽也对自身的又一种可能性跃跃欲试。
在这部电影里,她饰演爱丽丝,一位新品种植物开发公司的高级植物培育员。
她领队研发一种特别“有爱”的植物。除了定期浇水、保持恒温这些基本操作,这种暗红色的美丽植株还“希望”人们来抚摸它,并且跟它倾谈。作为回报,它会释放一种气味,激发人们的快乐。
像是养一个小孩或是宠物,辛劳付出后,可以期盼一些难以用物质标准来衡量的愉悦。于是她以儿子的名字给它命名,称之为“小小乔”。
但在爱与温暖的表象之下,人们似乎开始被小小乔改变本性。
饶有兴致地看了剧本后,艾米丽去跟杰茜卡见面,表达了自己的喜爱之情。杰茜卡则向她展示了小小乔的设计理念,给予她一个近距离观照导演思想的机缘。
“我非常喜欢杰茜卡之前的作品,跟寻常电影相比,它们相当有趣,而且很有深度。她每部电影都挺不一样的,我尤其喜欢《卢尔德》(2009),那种黑色幽默和出色的视觉效果,真的很厉害。”
加盟《小小乔》是必然的,特别是本·卫肖和凯瑞·福克斯已经答应参演,“我一直都想跟他们两位一起演戏,而且之前也跟制作公司合作过,所有一切都很棒。”
拍杰茜卡的电影是去开展一场未知的冒险,“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电影会是什么样子的,但不管怎样,它一定会很有意思。一切都在杰茜卡脑子里布置好了,她有自己的想象,而我们都很想知道,她会希望电影以什么形式呈现出来。”
在一切尚未揭晓时,杰茜卡先给他们设计造型。
“她问我愿不愿意剪短头发,然后给我发了些照片,又问我愿不愿意把头发染得更红一些。我说可以啊。”于是,那个有些保守、呆板却又颇为耀眼的发型,开始把爱丽丝的内在性情给外化出来。
艾米丽笑说自己的发型、实验服都很搞怪,而本那个有点“舔狗”特质的角色克里斯也是,总穿着衬衫,搭配米黄色休闲裤子和休闲夹克,还挎了个小包。
“很好笑哎。”艾米丽这样形容。
就像“跟他一起拍戏,总是很好玩”,尤其是当“如此绅士的人,要去表现暴力的时候”,所以打斗场景也是她极为钟爱的。
玩笑话说得轻松,事实上,准备工作还是很严肃、很繁杂的。他们要提前做好很多调研功课,还要一起长时间地探讨,从而保证所有与科学相关的术语、操作,都经过精心打磨。
艾米丽觉得基因工程的内容和美学很有革命性,很吸引人。她特别喜欢培植房和实验室,那里摆满各种科学仪器,还会有科学家解释自己手头的工作。
“他们要从一片叶子里提取DNA,实验非常复杂,但非常酷。我们不太能理解实验结果,但兴趣就是会被吊起来。”
可无论表面有多少好奇、兴奋,艾米丽表演起来,还是要以收敛为主。
“这个角色需要把全景给拼出来。她总想读懂别人的想法,总是疑神疑鬼,怀疑别人是否在戏弄她,欺骗她,嘲笑她。他们都是她的敌人,已经被小小乔感染,这让她觉得自己要负责任。”
因此,面对周围环境的悄然变化,她总是显得比其他人淡漠。在草木皆兵的当下,连喜怒哀乐的表露都是一种危险。艾米丽在很多时候,就是要在尽量小幅度的动静里传递细微的情绪波动。
回想当时,她说,“当你在做一些基础表演的时候,要学着去集中注意力。你要想,这一幕能传递什么?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而这就是我想要去做的。至于每个角色要做点什么,我们相互之间都会谈论很多。”
她又补充,“这还是很需要勇气的,因为这跟你之前的表演和其他人对你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会不会演得很糟糕,于是特别紧张最后呈现的效果。不过,似乎大家觉得还不错。”
“这就是演员要去承担的风险。”但就跟参演一样,艾米丽对杰茜卡有着百分百的信任。“她不会让我做任何不好的事。但这个表演确实很不一样,这对我来说也是新的体验。”

3 电影就像是一件艺术品,不是为了娱乐大家,而是逼着你去思考
小小乔是那么精致,那么美丽,通体包裹着呵护、亲昵与爱,释放着开心的迷人信号,但它却是一切未知的缘起,如同看不见的根部,岔开了众多叫人不寒而栗的事实。
因为要生存,被绝育的小小乔通过花粉来改变人的习性,让他们千方百计地维护它。
艾米丽看得透彻,“这绝对是植物想要生存下去的本性与办法,是它们的一种竞争方式。让苍蝇帮它们繁殖,就像人类操纵别人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一样,不管这目的是好还是坏。”
由此衍生的强烈对照在电影里比比皆是。可爱与可怖,人类的善意与植物的恶意,人为的操纵以及被动的报复,全都在相绊相生。
到头来,小小乔让观念不同的人们之间出现裂隙,产生矛盾,甚至引发争执与冲撞。
在艾米丽看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去爱。对某些人来说,爱是很好的,但对另一些人而言就不是。此外,每个人应该怎么去定义快乐呢?当你开始质疑快乐,那它就成了你无法控制、抓住的东西。这是很实在,很主观,很哲学的。”
关于爱与快乐,《小小乔》谈了很多,并以此作为探讨其他问题的基底。“我觉得之前的情节就是为了营造出这个电影高潮,这个完美的一刻。”
艾米丽称善杰茜卡的聪明,“她之前也没有尝试过这种做法,但这一切就像是生活本身,像是真实生活的一个版本。什么才是完美结局?什么才叫终极快乐?你试过人为制作吗?你能够找到并且到达那个目的地吗?《小小乔》是能够激发很多思考的。”
这些问题全都压到了爱丽丝身上,她成了探寻答案的主体。
艾米丽说,“当她发现自己可能创造了一些具有毁灭性的危险东西时,感到非常害怕,与此同时,她的爱好、生活、工作也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所有东西都在彻底改变她的观念。”
当她失去理智,感到尴尬、羞耻、受伤、失望后,“她就变成了孩子,而孩子变成了家长。杰茜卡也是在探讨家长与孩子的关系,探索关系的变化。”
但在千头万绪之下,还是杰茜卡所谈到的核心,“爱丽丝创造了一个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她不再有能力去控制,但她对此负有责任,必须去终结它。这是一种很不舒服的感受。”
弗兰肯斯坦可以泛指失控的创造物,通常会毁灭创造者,这可谓小小乔极佳的注解了。
在面对潮般涌来的众多问题时,导演处理得非常聪明。艾米丽解释,“观众跟演员一样,在经受角色的经历,一起去完成那个拼图。但在最后,什么都是非常模棱两可的。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但对她而言,这就是想要的结果。”
由无从怀疑到怀疑他人再到怀疑自身,由异化到同化,又在一个更大的层面,让大家自以为根深蒂固的情感,会被轻而易举地连根拔起,叫人反问假装与本真的距离,世情与人性的荒谬。
在这个思维背景下,干净、简洁的《小小乔》展现了一种深层恐怖片的自律。而东瀛风的诡异配乐跟独树一帜的用色、剪辑,更让效果翻了倍。
艾米丽笑谈“杰茜卡在玩她喜欢的把戏”,因为就连演员,“看着这样的场景、服装,怎么也没觉得是个恐怖片。”
但这是一次有趣的体验。艾米丽评价,“杰茜卡喜欢在紧张感上做文章,让观众觉得马上就会出现危险或恐怖的情节,感到不自在,突然间,却发现并不是这样的。门后没有怪物,只是一个小孩。就好像所有东西都坏掉了,然后又回到那个疑神疑鬼的状态去。”
对此,“有时会让人受挫,但有时又会让人非常喜欢。有时候观众特别想要看到一个怪物,想要一个结果,但她却有特别高明的想法。”看得透这一层,艾米丽非常理解《小小乔》口碑的两极分化。
对观众而言,可以为惊喜而兴奋,可以为落空而懊恼。这是一场由始至终就没打算讨好大众的游戏。
艺术世家对杰茜卡有着深刻的影响,“电影就像是一件艺术品,不是为了娱乐大家,而是逼着你去思考,让你感觉不舒服,让你质问自己。这就是艺术的作用。”
从很多层面来看,艾米丽身上也透露着这种良性的艺术气息。就像当年她曾说过的那样,“我进戏剧学院,不是为了在镜头前装可爱。”
如今她已贵为戛纳影后,也许意味着日后会有更多选择角色的机会。
但由始至终,艾米丽强调的都是“明智”,希望自己能够“选对了”。
相比起数量,她还是更倚重质量。“因为你想要做到完美,做到最好,那你就要竭尽全力。假如你没法跟角色产生共鸣,那就很成问题了。”
换句话说,“你可以拍很多很多烂片,但这会将你引向一条自己并不想走的道路”,而“当你选对了一个好项目之后,它能让你走得很远,给你带来很多收获”。
“所以,还是要在空闲的时候,学习,体验,读好书,旅行,跟好的人接触,这能够提高你的生活品质,更能让你成为一名更好的演员。”


2 ) 一朵花如何从“万恶之源”到“幸运之神”……
电影《小小乔》惨淡的评分,有些令人惊讶。也许大家已经厌倦了人被“人造物”操纵的戏码,异种通过“寄生”满足生物的繁殖本能,这种设定已经被《黑镜》《爱,死亡和机器人》等暗黑影视剧玩得过滥,也不新鲜。但本片的奇特性,在于这种“阴谋论”只是电影的一种解读,它还另含着一种治愈论,即所谓的花,借着散播花粉,杀死真我,让人变样,甚至像是附体在了人身上,不过是女主植物培育师爱丽丝在巨大心理冲突下的臆想和投射,最后她冲破了心理障碍,对于爱花“小小乔”的恐惧也就烟消云散了。导演在访谈中,强调了本片侧重对亲密关系的探讨,但也没否定其他方向的解读,至少结尾到底迎来的是一个僵尸的世界,还是一个每个人都更快乐的世界,没有定论。
从个人观感来看,一开始觉得女主的心理冲突不足以让她混淆现实和幻想到如此地步。但还是顺着治愈的思路盘一下,她到底遇到了哪些冲突,令她时常恍惚甚至错乱?按照片中的精神分析师的理解,她认为爱丽丝相比儿子更爱工作,但作为母亲,不爱孩子这件事,让她无比内疚。整个社会要求父母必须把孩子放在第一位,尤其是女性,更是应该把孩子当作是自己的头等大事,在这种社会规训下,她自然会陷入“天人交战”中,一个母亲怎么可以更爱工作呢?那么“小小乔”,她培育的新品种,就会成为她工作的象征,担心它有害,就是觉得她对工作的过分投入,会伤害她与儿子的关系,甚至会因为疏于照顾,而让孩子遭遇不测。哪怕连孩子有时妨碍到了自己,成为了自己的负担,有时自己想要摆脱孩子,这样的想法都是危险的,需要竭力克制和压抑。想要灭掉“小小乔”就好比是顺从了社会对她乃至所有母亲的苛求——女性尤其是母亲不可以以工作为重!然而单是这一重内疚,不应该会突然让她觉得周围的人都变了,至多就刻意地多关心、多陪伴一下孩子,比如片中送一株“小小乔”给孩子,代她陪伴孩子,减少自己的内疚感;至多就不乐意接受同事克里斯的示好,毕竟自己一旦有了新伴侣,能分给孩子的时间,就更少了。
第二个冲突就是同事贝拉给她敲的“警钟”,指责她不该剥夺花朵的生育能力,这会逼它以诡异的方式繁殖。她还把她狗狗的“突变”,怪罪到女主爱丽丝的花上。按照基因编辑的设定,花粉应当可以促进人体合成催产素,使人变得更温柔、有爱、包容,与他人的关系更亲密。但贝拉的狗狗吸入花粉后,反咬了她一口,甚至与她形同陌路。这点触发了爱丽丝的两重冲突。
一个是对自己“杰作”的怀疑,它也许带不来幸福,甚至会发生不可预知的变异。照她后来的袒露,她确实使用了违规的病毒,让花香味更浓,最开始她是撒了谎的,她一直都掩藏着一份被揭穿的恐惧。而当时研究所的BOSS似乎还耿耿于怀于自己培育的品种意外死亡,迁怒于她品种的存活,各种挑刺,不知会不会引发过敏啊,是不是有违规操作之类,对她的品种还未全力支持。这令她陷入了惶恐,毕竟这一得意之作的失败,可能会导致她整个职业生涯的崩盘,对于一个工作狂而言,这是无法承受之痛。
另一个是曾经贝拉与狗狗亲密无间,而今关系破裂,这也触发了爱丽丝心中的隐忧,那就是自己的儿子乔,是不是也会有一天跟自己决裂?如同她当初对“小小乔”的设计,大多数新品种的花,都是减少照料,让主人可以更自由,但相对应的,花香也更淡,但“小小乔”却要悉心呵护,以换来更浓烈的香味。这其中隐约透露出她对自己在孩子身上投入过少的遗憾,也因此母子之间的爱意是寡淡的,若有似无。而在与孩子的“happy hour”中有多少全神贯注,多少心甘情愿,还仅是因为母职所迫,也未为可知。如果当初她倾注更多心血,是否可以让他们之间的爱更香味四溢呢?不能说她对她的选择完全的无怨无悔。
贝拉这个人物在很多人的解读中,被当作了先知,她最先察觉到了“小小乔”是最大的BOSS,意欲通过花粉给全世界人洗脑,而“小小乔”的创造者,爱丽丝应当背负所有的罪恶。在“阴谋论”中这是成立的。然而,在治愈论中,她可能就成了造谣者,毕竟是爱丽丝抢了她的位子,而她被降级了,无法再重现自己曾经的辉煌,难以释怀,就开始觊觎后辈、同僚,尤其是当后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站边“小小乔”,看好它,守护它时,她就更加控制不住自己的心魔。而给爱丽丝灌输“小小乔”威胁论,就可以促使她辣手摧花。
第三个冲突,是她的儿子真的变了。贝拉给她看的其他试用者的访谈又佐证了这一点。但她的儿子更快乐了吗?并没有,反而是变陌生了。他跟爱丽丝更少交流,很多事不再跟她商量,父亲、朋友成为他更重要的依靠,而不再是母亲。他变叛逆了,会偷拿她的门卡,去偷花。两人还暴发了口角,甚至肢体冲突。就好像是贝拉和她的狗狗一般。她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她没有想到这是儿子进入青春期,追求独立、挣脱束缚的必经过程,她想到的是,自己太爱工作,对儿子关爱不够,酿成了恶果,两人的关系一去不复返了,这令她深陷内疚的泥沼。而作为超有掌控欲的女强人,她感觉儿子不受控了,唱起了反调,而自己居然在“夺子大战”中输给了与儿子相处时间更少、自己还看不上的前夫,自尊心也受到了重创。
在种种冲突交杂之下,她变得敏感多疑。她虽然擅长种植植物,但不善于与人沟通,她对儿子,更多的是干涉、管教,很难自然地与人交流情感。当大家都把“小小乔”捧上了天,对它百般照顾之际,她前所未有地觉得落寞,那种其他人对“小小乔”的体贴多于自己的感觉,何尝不是她的儿子乔曾经饱尝的——比起我,妈妈更爱工作。她若有此念,内疚感自是无以复加。这时“小小乔”就会成为她归咎的对象,似乎除掉它,自己的痛苦就会荡然无存,一切又会重回正轨。
贝拉的自杀,大概是把她推向灭掉“小小乔”的最后一根稻草。此时她眼中的“小小乔”已经是“万恶之源”,所有人都为了它而结成了“同盟”,自己被排除在外,它让儿子变了个人,让“执着于真相”的同事丧了命。剧尾的转折过于仓促,仿佛是弹指一挥间,似乎仅是她吸入了花粉而看淡了一切,让她再度成为“小小乔”的守护神。也可能是因为克里斯愿意与她共同担责,让她有了儿子之外的情感寄托,让她可以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经营新的关系,像是养育“小小乔”那样;她接受了过去的无法挽回,自己在做母亲这件事上并不成功,而工作就是她的最爱;儿子与她的关系虽没那么亲,也没那么糟,青春期学会放手,过后又会重归旧好;而根据检测结果,无事实依据证明“小小乔”有害,新产品推出后大受欢迎,事业蒸蒸日上;在事态转好、心理疏通之后,“小小乔”摇身一变,成了她的“幸运之神”。
这么梳理一下,治愈论也完全说得通。那么比较古怪的就是“小小乔”到底是怎么让人更快乐的?当然我们可以大而化之地说,当人人都坦然面对了真实的自我,放弃了假我,哪怕这种真实不那么美好,有时需要经历更难熬的阵痛,那么人人都可以更加快乐。所谓的“小小乔”帮助我们灭掉过去的自己,也可能就是剥去假我的伪装。
然而我们也要说说,“小小乔”的另一面,它虽然可能是女主爱丽丝的“幸运之神”,但未必是全世界、全人类的;虽然它未必有“思想”、有“意志”,整天处心积虑地借人撒种,但不要忘了它主要的运作机理,是靠激素让人更快乐。催产素的获取有其他途径,即靠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接触,对视、对话,所有饱含爱意的行为,都可以让人产生催产素,无需依赖外物。花粉的效力也不可能是持续的、终生的,对于渴求快乐感觉的人而言,这可能成了新型“毒品”,把本该靠人与人之间亲昵行为产生的,转求于人与花,这虽然可以应急,可以替代,但不该成为全部的来源。
再来,如果爱丽丝或是贝拉觉察到的,周围人的快乐有异样是真实的话,那么也许“小小乔”还有其他的副作用。由它人造的这种快乐是否是以掩盖其他所有情绪为代价?又或者让他们变得只顾自己快乐而不顾其他?是否会让人不自察地做出更恐怖的事情?片中从爱丽丝的视角看去,是颇惊悚的,比如她受伤后,儿子和他女友非但没有显露出担心、难过,脸上挂着的竟然还是笑意。也许儿子的离开,只是为了不被母亲管束,可以更wild。而一看到爱犬玩具就失声痛哭的贝拉,被大家旁观着自杀(也可能是被推下去,她也是反对“小小乔”量产的),可能快乐大家庭里是容不下一个会伤心的“异类”的,这会让大家不舒服。如果为了让自己快乐,灭掉别人也可以,那会有怎样的残忍?如果大家只是为了“小小乔”上市大卖,为了获取更极致的快乐,而伪造了所有的检测结果,包括克里斯看似由衷的安抚和支持,也不是因为真心爱女主,而是为了事业成功的终极快乐,那可不就是一个更可怕的世界了吗?也许就像片中的BOSS所言,感情的真假谁能分辨,谁又在乎?看似皆大欢喜的结局,也许已为未来埋下了更大吨数的炸弹,只是用一种更精妙的伪装,替代了一种更易被拆穿的伪装。
以上可能是该片最有趣的地方,那就是为什么同样一朵花,不同人、不同心境下看去,不同角度、不同时间点看去,会有着天差地别?一朵花到底是什么样,不开启上帝视角,没有人能看得清、看得全。作为人,我们只能说,看不懂一朵花,看错了一朵花,那很正常。只愿每个人都能保有对全局的敬畏,清醒地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局部,我们以为的事实,只是偏见。
3 ) 视角的侵入与抽离
本文含有大量剧透,建议观看正片后阅读。

上图来自电影《横道世之介》,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景深镜头,前景是分别位于画面左右两点的世之介与祥子,而后景第三点(即画面中心点)的主被摄物体(为两人爱情动容的保姆)实际上就是一个与观众位置对立但视角类似的第三方旁观者,随着镜头慢慢推向第三点,旁观视角完全占据画面的主导地位,观众就被带入了这个视角。

同理,本片中的这个镜头是完全一样的处理手法(如上图)前景是爱丽丝与贝拉位于画面左右两点,而镜头缓慢地推向位于后景的中心点,但诡异的是,后景中空无一物,随着镜头的推进变焦,爱丽丝与贝拉出画,画面变成了空镜头,本该出现的第三方旁观视角消失了,而这样的镜头处理在片中多次出现,这就让人不得不怀疑其中有特殊的含义,于是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大胆的推测,本应该出现于后景画面中心点的第三方视角其实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被导演豪斯娜隐藏了起来,换句话讲,影片中一直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在监视着主人公,同时也在与观众对视,而这个被隐藏的第三方视角,就是小小乔。
让我们先梳理一下设定:小小乔是一种被人工培育的花,吸入它的花粉会让人快乐,而它在进化的过程中渐渐有了自我意识,吸入花粉的人则被异化思维;是不是听起来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也很难设身处地地体验到被这种花粉感染是种什么样的感受?那么豪斯娜是如何让观众浸入到影片中呢?
开场6分钟,“画面左右两点人物交谈,镜头推向中心点”的处理手法第一次出现,被拍摄的两位主人公正是影片最核心围绕的女主角爱丽丝与她的儿子,小小乔的命名来源:乔,而当镜头已经完全聚焦于装食物的袋子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剪辑点,视角变成了从外往里看,这一次突然的侵入与抽离向观众明确了第三方视角的存在。

这个被隐藏的视角载体究竟有何用意;在影片内部的系统中,小小乔作为一种花只能生活在实验室或花盆里,而它的花粉却可以无处不在,没有了一个具象化的载体,即使是作为了一个旁观视角也无法成为具体的被摄物体,这就是它被隐藏的最主要原因;而在影片的外部,豪斯娜利用了这个与观众站在对立面的视角,通过将镜头推向后景第三点的方式让观众与影片合二为一。
影片第20分钟,本喵成为了第一个被小小乔花粉感染的人

从这个节点开始,被隐藏的视角渐渐有了具象化的载体;比如下图这个镜头,此时的乔与他的女朋友塞尔马已经被小小乔的花粉感染,镜头的拍法依旧选用的是定机位然后推镜,镜头最开始左右对称,未被感染的爱丽丝与已被感染的乔和塞尔玛占据画面左、中、右三点,完全平衡,但随着镜头向左缓慢推移,爱丽丝渐渐出画,乔和塞尔玛占据了画面的主支配地位,构图打破平衡,彻底明确了被感染者与未被感染者的不同,而观众也被慢慢侵入其中。

被小小乔附身(感染)的人最终与它一样成为了“第三方视角”,审视着未被感染的人,而观众被拽进了影片中,代入了那个站在对立面的隐藏视角,从一个彻底的旁观者变成了小小乔花粉的载体本身。
全片最后一次出现“画面左右人物交谈而镜头推向后景第三点”的处理手法出现在1小时20分钟,之后,全片最核心的三场高潮戏出现

第一场是贝拉的死亡,豪斯娜使用信息量缺失的处理手法来保持悬念感,比如上图中这个镜头,她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仰视视角,极有可能是杀人凶手的本喵看向下方,却并没有给出任何的反打也没有让镜头反向绕旋,贝拉死亡的声音元素得到了保留,但视觉层面上的信息量是缺失的,是被隐藏起来的,因为彼时的本喵已经被小小乔附身,成为了那个一直被隐藏的第三方视角的实体化载体,于是被隐藏者就变成了站在对立面的正常人;视角渐渐发生转变。

贝拉死亡之后的下一场戏极为关键,第1小时27分钟,豪斯娜使用了一个与前推完全相反的镜头,以主被摄物体的特写开始,镜头渐渐拉远展现全景,因为剧情发展到这里,几乎所有人都已经被小小乔的魔力所控制,已经不需要任何侵入,视点被完全抽离,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紧接着接的是一组感染者与未被感染者的正反打进行最后的审视;再然后,爱丽丝终于也在上帝视角的注视下被小小乔的花粉感染,1小时33分结束高潮;这三场戏的连接完成度极高。
除了小小乔与被感染的人,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更高维度的视角:旋转监控摄像头

开篇第一个镜头就是以这样一个上帝视角俯瞰人类与小小乔,而全片最令人胆战心惊的镜头也都出自这个旋转摄像头,这是全片最大的抽离视角,也是内核高潮“爱丽丝被感染”的落脚点视角,以此为影片的信息结点,把浸入影片的观众重新抽离出来,明确宣告:整个世界被完全感染只是时间问题
抽离视角起,视角侵入中,视角的二次抽离结

写这篇的主要目的是其实想说一说豪斯娜的技法运用与镜头语言的出色,片子带来的所有悬念感与恐惧感绝不仅仅是来自于吊诡的配乐,更是她作者属性与才华。至于影片的最终的剧情走向究竟是HE(导演本人的解读是HE哟)还是BE,自然就见仁见智了

4 ) 专访导演豪丝娜:人不一定生来就为了追寻快乐
(豆瓣首发:Mr. Infamous ;原载:《电影》杂志)
杰茜卡·豪丝娜第一次到中国,去了澳门,第二次则来到上海。到了酒店还没歇够,她就带着同样清瘦的儿子前来接受采访。
初来乍到,她总是有点不太好意思似的说自己知之甚少,关于上影节的模式,关于中国电影的制作,关于中国观众对《小小乔》(2018)的反应,以及,关于儿子玩的那个无法在奥地利外登陆的足球游戏。
谦逊得有些害羞,连笑意都会朦胧起来。
从电影到见闻,聊到自己独特的想法,也总是略有腼腆地笑笑。
可她的电影,是如此先锋、大胆。 表现手法,呈现结果都是如此之外,还有对评价两极分化的坦然甚至期许。
她质疑希望、信仰与爱,更质疑真相。这样的电影人,不知不觉就把自己泡出了哲学家的深度。听她侃侃而谈,真知灼见俯拾皆是,原来竟有那么多事情,我们从未想过另外一面。
她把电影奉在圣殿中,却点燃了圣殿不容置疑的存在。而她,杰茜卡·豪丝娜,成了影坛上又一位可敬的战神。
每个人都成了问号
本·卫肖之所以欣然接下《小小乔》中的角色,就是因为“对杰茜卡之前所有的电影极感兴趣”。
从维也纳电影学院毕业后,杰茜卡以处女作《任性天使》(2001)登上影坛。等到《卢尔德》(2009)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拿到竞赛单元费比西奖,她实现了职业生涯的突破。以德国文豪克莱斯特入题的《疯狂的爱》(2014),成为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开幕片。而首部英语作品《小小乔》首次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就为艾米丽·比查姆赢得了影后称誉。
作品不多,但总能让人看到跟其他电影不一样的内容以及精神内核。走到这一步,跟她所处的环境不无关系。
杰茜卡生在奥地利的一个艺术世家,父母和大姐都在绘画界闯出了名堂,尤其是父亲鲁道夫,可谓维也纳幻想现实主义画派的大将,二姐谭雅在服装设计领域颇有建树,而她本人则在电影领域崭露头角。
这次《小小乔》能够吸引好演员,还能够打动戛纳评委,正因它不只在讲述一个科技与人心的故事,而它搅动的,更不只是这一片小小的精神天地。
女主角爱丽丝(艾米丽·比查姆饰)是个科学家,在新品种植物开发公司里带队培育了新植株“小小乔”。它非但不是速成的,还要人们怀着爱意去抚摸、倾谈,才能成长。相应地,它会释放气味,激发人们心底的快乐。
但是,小小乔渐渐有了控制人们情感与思想的能力,甚至“意愿”。
有人说这像《黑镜》,用冷冰冰的科技来推演一个潜在的未来。杰茜卡表示,“我喜欢《黑镜》,但我觉得《小小乔》是不一样的,我不是在想象一个未来。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这不是对未来作一个明确的预判。”
事实上,创作《小小乔》的基本思路,就是“设定一个女性版本的弗兰肯斯坦”。科学家爱丽丝培育出小小乔,从某个角度看,确实是把生命赋予了一个未知的怪物。
有了这样一个故事前提,才能进一步探讨电影的核心,即爱丽丝如何在对儿子的爱和对工作的爱之间左右为难。
而在这个斟酌的过程当中,爱丽丝惊骇地察觉周遭的人在一步步变质、异化,自己再也无法确定应当如何去看待他们。“他们变成了一个个问号。”
这种疑虑状态的投射,来自于杰茜卡在现实生活里或触动或困扰的经历。她接连举例说,有些人变了,你会想,“哦,那可不是我十年前认识的人”。又或者,你的孩子变了,因为他们长大了。当你发现自己所爱的某人,其实并不完全就如想象那般,你会觉得惊讶不已。两个人去结婚,两年后,他们就变得相互厌憎,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以为很亲密的人,有朝一日,大家的距离会变得非常遥远,这又是为什么呢?
爱丽丝的同事贝拉(凯瑞·福克斯饰)到后来,越来越“不在状态”、“不是自己”了,但这时候,“是自己”还有什么意义呢?当你疯了的时候,你还是不是你自己,或者说,当你吃药了,你会不会没那么“是你自己”?
这恐怕就要跳到另外一个话题“疯狂”,而这也是很让杰茜卡感兴趣的。
《小小乔》令人惊恐而又兴奋的一个地方,是始终想要牢牢控制一切的爱丽丝,发现自己渐渐深陷于内心的流沙,曾经以为稳固的关系、观念甚至自我,都在随之下沉,但与此同时,她又像是一个接连押错筹码的赌徒,再憧憬鸿运都好,也会有一瞬间动念——不如,就让一切尽毁吧,落得个人神共灭,也好过这灰头土脸。
有人觉得,到头来什么都变了,爱丽丝妥协,放任,看来什么都不会好了。杰茜卡谈结局这种放松的状态,“也许她是迷失了,也许她是高兴的”。这就看你要把寻常逻辑,摆在精神状态的什么位置。
在挑选演员来诠释这种不一般的状态时,杰茜卡相中了艾米丽。
不久前,艾米丽在《达芙妮》(2017)里演了一个顽固、好斗的疯女人。“这是一个非常摩登的疯女人版本,因为这些古怪的地方,都挺让人喜欢的,而且是很正常的。艾米丽有不可思议的天赋,而我的电影正好需要一个看重工作多于儿子的女人,我不希望观众去指责她,说她是个不好的妈妈。”
正式拍摄时,杰茜卡就会经常跟艾米丽探讨,什么时候爱丽丝会发现别人变了,而通过什么方式,她会觉得自己是在胡思乱想。
杰茜卡盛赞艾米丽的表现,“她是在一个很不稳定的基础上表演,因为这不是一部心理学的电影,不会有大场面来展现她的感受,她在电影里只能跟那种不安感合作,而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这是角色所承受的压力,我觉得她完成得很好。每一场戏,你仿佛都能听到一些内心独白。‘他现在是在撒谎吗?还是说,他正在说出真相?谁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而这种情状下,观众不知不觉地就会以一种特殊方式潜入角色身上,甚至是代入到看似遥远的电影世界里。
单一性的真相并不存在
能潜入《小小乔》世界的人会更明白,对于心理状态的质疑不过是一角冰山,对真相的质疑才是海面之下叫人惊诧的二级内涵。
爱丽丝、克里斯(本·卫肖饰)和贝拉,全部都是科学家。可即便是科学家,也无法厘清当下发生的事态。杰茜卡分析,“他们发明东西,发现事情,能够拯救人类,却也有可能毁掉人类。”而仔细一想,能让科学家也失去自我意识,其实是一件更有讽刺意味的事情。
在创作剧本的阶段,杰茜卡跟曾经合作过《卢尔德》《疯狂的爱》的编剧拍档贾拉尔丁·巴哈德有过许多考量。二人最终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剧本,力图保证每场戏都有一些模糊的特征。
比如,贝拉最后倒下了,那么,是克里斯他们把她推下去的,还是她自己跳下去自杀的?究竟是小小乔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和脾性,还是说这一切,不过是爱丽丝自己的臆想,只为了能让自己顺利工作,不用带小孩?
这些不确定的场景,就是杰茜卡觉得有意思的所在。
“当你在质疑别人的时候,你也在质疑自己。”对这种视角问题,杰茜卡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就像我们这会儿坐在同一个房间里,我看着这个方向,而你看着那个方向。这就很像电影的摄影。”
她很喜欢摆弄摄影机,譬如让镜头凑近某人,然后又把镜头移开。“镜头的位置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想要做的是,让观众感受到不安。”
也就是说,她想让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脑子里不断出现各种泡泡,“我这样判断,是对的吗?”或者说,当有事情发生,角色离开了电影画面,然后又回来,那作为观众,就会有一种感受,“嗯,怎么回事?有什么东西是我漏看的吗?”
杰茜卡笑说,“我不会把整幅拼图都摊给你看,总有几块是找不到的,而我手上并没有拿着。”
这就是为什么说,她的电影两极分化,很挑观众。
其实她也明白,绝大多数观众都希望能在电影里找到线索,并得到明确的答案。但她觉得,既然自己都还处在寻找答案的阶段,又如何能给观众提供呢?“作为一个电影人,很难在拍电影时稍微留出一个缺口,让那种怀疑精神保持活力。”
这种曲折隐晦的做法,当年杰茜卡在《鬼饭店》(2004)里就已经做过尝试。到了《小小乔》,她用了一个新的手段,那就是提供至少2个答案。真相不再具有单一性,并开始背离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
在《小小乔》的试映环节,特定的一批观众会做好“被质问”的准备,所以能够欣然接受电影的特色。但是到了戛纳首映,面对大批不同背景的观众,情状就不同了。
杰茜卡说,“当我看到观众在我觉得该发笑的地方笑起来,我会很开心。但我也会跟评委会成员说,《小小乔》是多面性的,会有很多不同的主题,你得让观众选择是关于这个,还是关于那个的。”
电影的主线是爱丽丝在儿子与工作之间的权衡,但很显然,许多不管是意料之中还是意料之外的观点、指涉、意蕴,都随着故事发展渐次出现,并被真相与假象之争给联系到一起。
“要是真的存在真相,那会是什么?一切事情是否会有一个绝对的答案?我在提供答案这方面,确实是很犹豫不决的。”
人类就是一些观念的集合体
杰茜卡在自己的电影世界里探究真相,这真相连皮带肉的,什么粉饰都不加。越敢直面,越显勇气。
她深入许多常见的议题,在别人的陈腔滥调里,别有一种赤诚。
“我有时候会觉得压力很大,当我在广播里听到一些所谓‘会让你感觉很好’的音乐时,我会想尖叫,我没法听。包括一些‘很浪漫的、美妙的’电影,我没法看。因为这是不真实的,它们遮盖了事情的本来面貌。”
而爱丽丝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取舍,其实多少投射了一点杰茜卡目前的状况。她谈到当爸爸和当妈妈之间存在的不公平,“我必须得说,很多母亲就是很难放手。而且我经常想,为什么她们不能说,‘请照顾我的孩子,我要去工作了。’那种愧疚的不好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
她笑着看了看跟来采访现场的儿子,小孩正在打游戏,还处在习惯跟着妈妈的阶段。“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但没那么多。我试图保持平衡,也希望能给孩子找到一个好的保姆,所以这并不难过,哈哈。”
所以在她看来,电影结局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绝望。
杰茜卡自己就挺喜欢爱丽丝和心理医生(琳赛·邓肯饰)谈话的那个场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解脱。电影里很模棱两可——她现在是变了还是怎样?但这也是个真相。那为什么不放手,把孩子给爸爸?反正爸爸正好想要孩子,而她至少能专心工作……这应该是个开心的结局。她为什么不能过这样的生活呢?”
正是让爱丽丝有了一段纠结、骇然的复杂经历,她才会有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而观众同样如此。很多困扰我们的事情,其实正因为有一层困扰我们的所谓道德在,只是,道德由谁定义?道德为什么没有随社会变化而变化?而我们是否太习惯于被不完美的道德所束缚甚至折磨?
在最初打算拍摄一部关于人们改变的电影时,杰茜卡总是想,“结尾就是要拥抱人的天性。”《小小乔》的结局是坏的,因为所有人都改变了?还是说结局是好的,因为所有人都被治愈了?又或者,哪怕在结尾出现一个充满丧尸的世界,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这其实正是我想要的感觉。所有东西都会改变,但是,没关系的,生活并不会介意如此。”仔细一想,杰茜卡近乎荒谬的“残忍”,其实已经上升到了某种哲学高度。
“人类说白了,就是一些观念的集合体。其中,最强烈的观念就是爱。每个人都渴望爱,但爱并不存在,它只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观念,而它使得我们能够沟通、生存,尽管我们当中有些人知道,它并不存在。这就跟我们其他观念是一样的,比如信仰、希望、科学。在当下,我们并没有那么相信上帝,而我们很多人都会离婚,所以信仰和爱也没有那么强大了,但是每个人都爱科学,我们总希望科学家会给我们终极答案。《小小乔》则说,科学家也并不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就像是牧师,他们假装给我们最后的答案,但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任性天使》里的女主角丽塔(芭芭拉·欧斯卡饰)就是个始终得不到爱的中学生,哪怕“爱”被有形无形地强调多次,而最终,对于爱的索求,让她走向了某种无爱的毁灭。《卢尔德》在一群病患信徒的朝圣之旅中展开神迹是否存在的谈论,到头来,似是而非的一个“神迹”让众人在信与妒之间摇摆,也不知道这宣示了上帝的慈爱抑或是残忍。《疯狂的爱》在爱与死的关系上大做文章,在平静的语调里,透过起起落落的戏剧冲突,掠过一丝丝嘲讽。
而在《小小乔》里,还有个看起来有趣,但却有很深意味的设定,那就是培育小小乔的时候,需要付出时间,更需要付出爱,甚至要跟它说话,而它会让人感受到快乐。可以说,快乐也是一种可以等价交换的东西。
杰茜卡补充说,愉快也是一个强烈的观念。她在报纸上读到一篇关于奥地利学校体系的文章,说的是学校正在摧毁学生的快乐。“我就会想,这是指哪种类型的快乐呢?我觉得这很值得质疑。一个人做他或她想做的,就会开心是吗?我觉得,在所生存的社会体系里,能够担当一个受尊重的角色,这才是快乐的本源。”
她笑着加了一句,“人不一定生来就是为了追寻快乐的。”
5 ) 《海底速報:小魔花》
小魔花既是商品,也是小小喬(little joe),即一種家庭成員的投影,這使得本片的雙重性從電影一開始就確定了,從類型來說,做為科幻電影之科,裡頭的科可以說是不盡令人滿意的,尤其在劇情細節上有許多邏輯硬傷,而幻的部分更是更是過於單薄,這是其失職的部份,然而當我們轉一面來看,作為對天外魔花的一次改寫其也有其可觀之處。
一開始看到小魔花這個翻譯,當然首先會想到科幻電影史上著名的天外魔花(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這部電影有很多版本,但大致是在講外星植物來地球透過各種滲透手法來施行其擴張。所以一比對《小魔花》當然就很像天外魔花的某種當代改版,只是其走了「未來即現在」的風格,將天外魔花改為當代人類基改的產品,誕生於類似孟山都的大企業實驗室,而女主則是小魔花的「母親」,但是對於這個她自豪的產品,她漸漸感到不安,因為她發現這個她自豪的商品/兒子似乎改變周遭的人,甚至改變自己血親上的兒子喬,讓她覺得他的寶貝兒子被變成不一樣的東西。
而所謂的「外星」不再是某種外部共產勢力入侵的象徵,而是資本主義內部生長出的異化的象徵,小魔花正是這樣與過去的天外魔花做出一種反向的對比,其揭示了資本主義何以如此牢固,因為其是合於人性的,而不人性的地方在稍一衡量之後也就成為了體制內的必要之惡,比如公司內部最先從自己身上的狗聯想到小魔花之毒的神經質老資歷同事,便以一種瘋癲先知的身分預告了一切,她宣告著對異化的奮鬥
「這不是我的狗!這不是我的狗!」
然後她便把自己的狗拿去安樂死了,做為對抗者,她也有自己的必要之惡。
換句話說,本片觸及了一般商業科幻電影較少觸碰的面相,那就是如果異化是真實存在,但卻是往對他人好但對我們不好的方向,我們要接受那個被異化的「他」並尊重「他」嗎?這個議題在之後女主發現自己兒子喬的漸變而逐漸發酵,她因此得站上那個神經質老資歷同事的位置,將這個問題嚴肅以待,包括去檢視愛慕自己的男同事的漸變。
開頭有提到本片的一些硬傷,比如作為一個高經濟價值的未發售原型,小魔花竟然這麼容易被盜走,而實驗室居然只需要一張id卡即可進入,且大樓一樓沒有警衛24小時輪班,使得這一切變得如此輕而易舉,這些東西是無法去深思或許也是電影導演沒有要我們深思的。
就氛圍塑造而言,本片做的不賴,尤其比起走有奇觀來嚇人的套路(當然本片還是有跳躍式驚嚇),本片則是因為低成本所以必須在背景音樂還有色彩與音效上讓觀眾給受到詭異的氛圍,一些東洋音樂的使用讓其在西方人耳裡聽來或許增添了些神祕氣息、高頻的音效則幾乎要引爆觀眾的耳膜,而小魔花綻放時的音效也讓人感到不安,即便它是如此被動而非主動進擊的「怪物」,但正因為本片缺乏高動能的情節,反而使得觀眾對這種細小的聲音更敏感,你可以拿其與稍早環球的《隱形人》比較,兩部同樣是小成本電影,故都不約而同採取了較低限的手法來拍攝,利用觀眾感官的相對性來節省資源,於是對於本片「故弄玄虛」便並非是種貶意,而是種讚揚。
你不知道什麼正在傳播,是小魔花的病毒正在感染眾人嗎?還是老員工的歇斯底里?又或者是女主自身的愧咎?電影刻意的不去說破反而使得一切更使人焦慮不安,因為它不再是個可以引出然後擊破的他者,比如作為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象徵一般,從資本主義的象徵來解讀小魔花也許只是我的一廂情願。
如同電影時常出現的向空無一物的背景而去的手法,全片擺盪在「想太多」跟「無可救藥」之間,小魔花改變了人,但這是壞事嗎?如同電腦、網路、手機……改變了現代生活,我們最終只能過問自己,而當我們不喜歡時,也只能接受自己已成少數,不再有任何既成解答,也不再有任何改變可能,如同女主從孤立無援到接受一切。
如果我們從「對抗外星勢力」那種科幻片來去給它評判好壞,那本片絕對是會被嘲諷缺乏智商的那種,然而另一方面其卻也說出了某種當代人心的真相,那就是資本主義改變了一切,而我們不應該去留念那些被改變的事物,包含我們的家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自己的選擇,你的往昔不變或許是他人的不堪地獄。
6 ) 一点零碎的观后感
1.魔花这个元素的加入和抽离,对人物的粗线条行为不构成影响。这个设计是高明的,置整部作品于一种真正的猜疑腔调之中,从而区别于常见的异类入侵题材。
2.某条短评中提到的的“信息缺失”的处理方式同样也是,如同片中小男孩养的蚂蚁之家,导演截取观察展现的人类生活可以等同于小男孩观察的蚂蚁之家的截面,都是静观之下的姿态,光滑、平整、表面化、渺小化、无机化。大多数电影作品在于对人物和情节的拆解、溶释、分析,通过增加信息量和情感浓度来提高观众的共情和自省力,在某种意义上是为对现实的“过分”解读。此片不然,导演颇有机心的祛除信息,个体固守自我思想,与外界交往中呈现出最简化的行为,与他人之间亦不存在真正的情感沟通。
3.人工感与人工感。在Hausner之前的两部作品中,无论是《卢尔德》还是《疯狂的爱》,题材都并非具有人工感的题材,而这是它们与《小小乔》差异最大的地方。在其他方面,此三部均是影像上祛除情绪的人工感无机感较重的运镜风格(除了此片镜头更运动),作者态度均是疏离的审视角度,其主题均是“人”这一柔软主体的柔软情感的无力、冷淡与荒诞。前两部在人文类题材上佐以人工感极强的画面镜头及电影节奏,得以幻化出某种冷淡但凌然凡品之上的灵气。《小小乔》的内核仍可谓是人文主旨,但形式上是人工感极强的实验室、魔花组合,于本片则是人工感(题材)再加人工感(影片制作风格)的叠加,而双重的人工感对于不同的观众也是观感完全不同的。
4.是过程的、空间的作品而非单向线性运动的作品。装置。镜头、画面及奇特配乐,共同组构成一个完满空间。导演在镜头运用上也通过在一组人物对话中镜头推进到虚空第三点的方式来强调空间的存在。有结局的电影,但并非完全单向线性运动的作品,企图在有进度条的媒介中塑造空间,任意拉动时间线,空间均是完整的可独立的疑惧空间,是为装置影像作品。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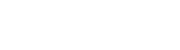




















黑镜什么时候能回归这个水平
#72nd Cannes# 影后。7分。影片观感就像兰斯莫斯拍了一集《黑镜》的剧场版。豪斯娜的研究工作做得还是相当细致的,片中各种生物学技术细节都很说的过去,对科学原理和话语都保持了很好的尊重,影片的美术和服装设计得相当出色,惊悚感主要是来自希腊诡异浪潮式的无表情表演(营造某种“uncanny”的感觉),但更多的还是靠日本风的音乐来营造一惊一乍的气氛,写得虽好但是真得有点滥用了。影片对(技术带来的)“快乐”的伦理探讨十分有趣,也讨论到了“主体性”这种大问题。影片显然是有着颇为精心编排的的隐喻和丰富的哲学探讨面向。最可惜的一点就是花粉控制人这件事,其实由爱丽丝的心理咨询师给出了另一个解释:作为工作狂的爱丽丝对自己疏于照顾儿子这件事心怀歉疚。如果能保持住这种暧昧性就更好了……
【今年的SIFF惊喜】就是非常特别。声音设计做得真好,soundscape as a (vital) role,伦敦公寓门外的摇曳树影搭配古筝过耳难忘;每一个角色都是既模糊又坚定冷静,女主也是,在这种超现实设定里还能演出(让我)可以identify的效果(我与世界:我?世界?爱咋咋滴吧),我觉得影后是实至名归;难以定义的小尺度叙事创造巨大文本空间(存在主义?探讨幸福?自我意识?心理分析?随便怎么解释吧,但这可解读性没有消弱我看故事的乐趣);影像语言既有诡异独特风格(比如每一场对话的zoom in镜头都是对准一个虚的点)而且成体系,形式主义强迫症也没啥可抱怨的。
风格接近“圣鹿之死”,剧情却是“天外魔花”。声大于形,伊藤贞司的诡异配乐比鲜红欲滴的画风还惊悚。女主全程表情呆滞,竟然KO“燃烧女子”拿下戛纳影后,除了分猪肉我找不到别的解释了...
赤色恐惧
花吃了那男孩,原来我非不快乐。
前半程特别讨厌,觉得又一惊一乍又故弄玄虚。然而渐入佳境,惊悚悬疑逐渐引入心理学和形而上的悖论,真假虚实、假快乐与真现实的界限逐渐模糊,以至于结局一黑到底,假快乐最终也变得胜似真快乐,everyone is happier,导演的聪明劲儿真是用对了地方。电影完成度很高,配乐也可能是年度最诡异最wtf,吓得几次差点从座椅上跳起来。
7.5/10。我观影的两个角度:中产阶级矫饰的完美和对母性角色的质疑。被花粉侵染的人们以维持表面一切完好的假象来保护魔花,最终女主也被侵染,却俨然一副中产或上流虚假平和之“圆满”结局。女主从不以为意到渐渐焦虑,心理医生提示她也许魔花的恶果恰恰是她自己潜意识的浮现:儿子对自己的依赖感消失也许正是她所希望的,她并不想履行母亲的指责,而是投入满足自我的工作中。科幻和心理戏平行双线齐下。女主对男主示好的不投入、对儿子无暇关心的歉意……被花粉感染……一切都美好得可怕(联想到《Pity》中男主只能在悲伤中感到愉悦):似乎产生了爱意和理解,但都是为了魔花而形成的同盟cult。终于她自由了,她也不再自由。影片同预想的(概念书)几乎一样,完成度不错。错过了开头。观影于戛纳电影节。05/14/2019
韦斯·安德森凭借本片中男扮女装的精湛演技,成功获得戛纳最佳女演员奖。
全场都被这鬼畜惊乍的日系配乐吓得啼笑皆非,诡谲的音效、横向移动的字幕、向着对话人物间空档缓慢推进的摄影,视听手法新颖的后现代科幻惊悚片。看到最后,人类被自己所培育的魔花控制情绪、放下包袱、欣喜地接受当下,表面上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结局,实际上则是对人类一个个变成行尸走肉般“快乐僵尸”的隐喻。
惊呆!学生作业一样的质感居然进了戛纳竞赛单元!这配乐真的是审美扭曲的典范了。
#22thsiff#《小小乔》绝对是我上影最大的惊喜。它是一部存在主义的恐怖电影,讲述了我们无法理解自己复杂的情感,以及对一种无思想、无负担的幸福的诱惑。特别要说导演豪丝娜为电影做了一些令人不安和特殊的事情,除了在原声带上偶尔的无调性尖叫,她提供了一种更克制的不安,电影中的女主角无法理性地接受可能发生或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她采取了一段微弱的恐惧和不确定性的时期,这段时期通常会引发这个经常被讲述的故事。从隐喻的角度来说,这不是一部容易归类的电影。从视觉上看,这是一场盛宴,将装饰艺术的粉红色和薄荷绿与对称的白框形成对比,隐约地唤起了70年代一些失传的科幻电影的美学。
7分,仍然保持了之前作品闷蛋风格。不过,这次选择了一个相当现代的题材(其实是科幻)。美术还是各种大块的黄绿红这种,摄影倒是运动起来了。主题其实在之前很多科幻恐怖片都有涉及,好似《天外魔花》之类,好在风格明显。以及,配乐非常诡异。
B / 开头干瘪,但之后随着配乐表演多个层次的旁逸斜出调性逐渐丰富,甚至在这个一眼能望到头的单薄科幻设定之下发掘到了极其细微的当代症候。它并不同于《圣鹿》一般直接的病态具象,而是着力于捕捉对“常态”与“非常态”进行“分辨”这一行为本身的焦虑,这恰似一种“塑料”包被的困顿状态:批判与批判的无力之间的无休止缠斗。为了呈现这种状态导演所采取的手法可以说是无比谨小慎微了,她让几乎每一个部分都出现偏离与失常,又让它们相互团结成一副欣欣然的科幻类型模样。
怪异而有趣。从开头第一个画面起就陷入一种催眠又一惊一乍的情绪,弹幕般飘过的字幕,旋转着的培育室监控画面,一朵朵红艳诡谲的花。见过太多人工智能颠覆人类世界的故事,但你听说过植物智能的危害么?它甚至很难被判定为有害,因为每个人都因为它变得更快乐,相敬相爱,不再纠结,保护着小小乔花。结尾那声“晚安,妈妈”过后,旁边老外抽了口气说,scary!各种东瀛风竹笛、击鼓、犬吠等奇怪大音量音效突然冒出,真真科幻惊悚片。PS,半英国片,有句台词是我们将把这种快乐花推向全世界,甚至欧盟XD
饲养蚂蚁观察如何筑巢,饲养爱犬相信足够忠诚,饲养孩子需要陪伴孤独。温室里的花朵,它不用说话就能带来快乐,于是人类终于集体放弃了悲伤与痛苦的情感。某天小小乔终于上市推广开来,每个人都培育小小乔并吸食了它的花粉而变得快乐,作为地球上唯一一个知道真相且清醒的人,你,会选择吸食小小乔吗?
在软科幻的外衣下,讲述的其实还是当代人内心深处隐秘的不安全感。尽管满屏的红色花朵显得如此触目惊心,它们弥散出的花粉亦可能只是人们潜意识中的幻觉。这也是豪斯娜在《小小乔》中做得出色的一点,正如影片中不停复现的挠人音乐,也许只是某种焦虑情绪再明显不过的外化。故事本身并不完美,甚至某些部分带有后现代式的空洞(特别是影片前半部分),但随着叙事的深入,究竟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臆想,逐渐混做一团,解读的空间也随之被打开。
被配乐吓死…如果把小小乔的病毒看成另一层面的“母性”,是否可以理解女性变成母亲后的一切以孩子为中心的失去自我行为?
概念先行的电影,但文本其实十分贫瘠,意象搭建完全失败,颠来倒去还是浮在这个概念框架上,经不起推敲。冷感梳理的镜头和怪异的配乐十分刻意,导演一头钻进形式的囚牢。
政治意味很强啊。片中很多极具装置艺术气息的场面辅助电影叙事,比如老研究员爬窗户回头看到一动不动却似饿虎扑食的花丛、心理医生墙上的画医患相拥,现实中却冷漠地例行查问的对照...当然,这部电影最后也像一个装置艺术,很好地抛出了议题,却欠缺电影真正应有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