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不幸的童年经历让盲女阿玲(岩下志麻 饰)早早就失去了父亲,六岁那年,迫于生活的贫困,母亲抛弃了阿玲另寻出路,留下孤苦伶仃的阿玲一人,在黑暗里看不到任何的光明与希望。 幸运的是,阿玲遇见了善良的齐藤先生,后者帮助阿玲进入了盲女学校学习唱歌。专心刻苦的阿玲进步很快,终于,她 如愿以偿的成为了一名歌女,得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这个冰冷的世界上存活下来。尽管辗转在各种各样的男人之间,但阿玲的内心里充满了寂寞,她希望能够拥有一个专属于她的温暖怀抱,带着这样的渴望,阿玲和鹤川相遇了。让阿玲没有想到的是,本以为今后可以同鹤川一起开始安定的生活她,却还要面对更多的悲伤与挫折。陌陌影视陌陌影视黎明时分飞驰人生非常旅途特工神童3天狗夺命手术消失的她宠物坟场仲夏之夜来去匆匆风云再起我本坚强第四季燕子符心跳回忆ONLYLOVE神勇双响炮粤语版怪物山杀死那只野兽唐朝诡事录飞虎狂龙车保罗有话说好男好女海市蜃楼(原声版)皇后镇球王ST红与白的搜查档案电影版建群囧事余生,请多指教印度母亲史前星球
长篇影评
1 ) 冷暖时代路——《盲女阿玲》三味
现在掉过头去看,倒是可以做一个荒唐的猜想,《枭之城》不好看,大概是因为主角最后没有挂掉,有违我迄今为止总结的“必拍到死”的“筱田法则”吧?玩笑。
最近看到的三部作品:《暗杀》、《在盛开的樱树林下》、《盲女阿玲》彻底更新了我对筱田的认识,对弱小的同情,娓娓道来的复杂叙事,还有彻底的虚无主义,都是很对我脾胃的元素,加上以前积累的好感,我好像找不出理由不欣赏他了。而三部中间,最能打动我的,正是《盲女阿玲》。
故事改编自水上勉的小说,发生在大正(1912-1926)年间。自幼盲目的贫女阿玲生长在若狭的小滨,电影从阿玲的母亲与情人私奔,溺死海中开场,一个好心的卖药老人将阿玲送到里见盲女歌团去学艺,从此阿玲跟着团长和姐妹们在村庄之间旅行,以卖艺为生。盲女团体的行规森严,绝不允许失身,然而日渐成熟的阿玲没能坚定自己的意志,与男人发生了关系,从此被逐出了社团,从此一个人过活。
一天,阿玲遇到了自称伐木人的鹤川,同为天涯沦落人,鹤川主动为她引路,从此二人结为旅伴,以兄妹相称。和那些一心想占阿玲便宜的人不同,鹤川始终不愿与阿玲发生关系,甚至在她主动要求下也不肯答应。为了让两人的生活更好,鹤川拾起了家传的木屐手艺,渐渐地,两人有了积蓄,阿玲可以不用卖艺了。
然而好景不长,在一次与地痞的冲突中,鹤川被带到了警察局。同住一家客栈的的卖药人别所趁机奸污了阿玲,出狱的鹤川一气之下扎死了别所。为了不连累阿玲,他们二人各奔东西,相约来日再见。
阿玲重操旧业,与另一位盲女结伴流浪。直到一日在善光寺与鹤川重逢,二人抱头喜极而泣,混不知一张大网已经撒向他们。原来鹤川的真实身份是逃亡的士兵,本名平八郎。因为家贫卖身顶替富家子弟从军,中途出逃。军部根据种种线索,在阿玲的故乡抓住了正准备回乡定居的二人。在严刑拷打下,鹤川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与阿玲话别后走向刑场。
失去了心上人的阿玲继续一个人上路了。若干年后,一群铁路工人遥望山顶,绿树上挂着阿玲的红衣,树下的阿玲已是一堆白骨,旁边遗落着陪伴她一生的三味线。
寒冷
观看这部电影,感觉到的第一个意象便是寒冷。阿玲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失去母亲,宫川一夫(黑泽明的老搭档)的摄影机镜头在铺陈拜师之路时,不断通过雪花与裸露的手、脚之间的切换强调幼女的孤苦无依。卖艺路上,团长心疼小阿玲,给她穿上了一双袜子,想不到反而冻坏了她。“赤脚走吧,只要一直在动,哪怕雪地里也是暖和的”,这是盲女歌伎们的经验,从此,阿玲打了一生的赤脚。
旅途中,初潮的经血在冰冷的雪地上绽放,超现实成了一朵红花。
盲女的世界是黑暗的,然而却充满了相濡以沫的温暖。在一场大雨中,怀孕的师姐恶心作呕。团长的教诲告诉了她盲女人生的真谛:“佛祖慈悲,赐我等天生不能视物,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看见这世上的苦难。阿玲,你要记住,别和男人鬼混,否则,我只好将你逐出师门。”据说,盲女是嫁给了佛祖的人,所以不能再贪图人间的情欲。
习惯了寒冷的阿玲或许是太需要哪怕一点点的温暖,即使是被逐出了门户,她依然不断与男人发生关系,有些是自愿,有些则是被迫。有些寒冷的夜晚,她甚至生怕自己被冻死。事实上她的唯一一个孩子,就是在出生的当夜冻僵的,那个所谓的父亲,早已不知跑到了什么地方。无论是男人的好心还是歹意,身为盲女的她都无从拒绝,唯一的希望只是最后他能良心发现,留下一点钱。冷,是盲女世界的基调,也是理解阿玲的根本。
影片最让我的动容的场景之一,在后半部分。一个老妇把失去了父母的盲眼孙女送来学艺,而阿玲能做的只是写封信给当年的团长,求她收留。结果祖孙二人当夜跳海自尽,阿玲和同伴听得消息,在雪地中一边行进,一边为无力保护比自己更弱小的人而放声大哭。在狂乱的雪花纷飞中,武满彻的音乐巧妙地与背景的海鸥悲鸣交织成一片,这个世界的寒冷真到了极致。
也正因为冷,她才分外需要鹤川的热。
火热
如果说,冷是理解阿玲的豁达和随遇而安的根本,热就是理解鹤川的根本。这个身高六尺的大汉面冷心热,顽强地伸出拳头,对抗一切遭遇的不公。因为家贫,他卖身参军,旋即逃跑。摆摊被勒索,他的第一反应是用拳头讲理。心爱的阿玲遭到侮辱,他想都不想,掏出锥子就扎死了别所。他的愤怒针对的不只是一个个的坏人,更是这不公的世道,在军部监狱,他咆哮出了他对“圣战”的蔑视:“打仗牺牲的尽是穷人!”
在鹤川的心上,阿玲是一尊菩萨。贫困的童年,伤痛的经历,只有在与阿玲的相依相伴中才能得到抚慰。所以他坚持拒绝阿玲的示爱,生怕自己一碰她,就会和那些其他的男人一样,从此缘分如露珠般消散,各奔东西。
阿玲在他的庇护下,真正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岩下志麻(我现在叫她芝麻小姐)即使闭着眼睛,仍然把阿玲的心理变化演得入木三分。从饱经风霜,脸上挂着机械的媚态的歌伎,到一个柔媚天真,惹人疼爱的女人,仅仅两年的时间,这哪里还是《在盛开的樱树林下》中那个神秘而骄横的“花妖”呢?好演员,当如是!芝麻小姐凭此片夺得第一届蓝丝带影后,果然绝非幸致。面对这个有着猫一般的鼻尖,以及比猫更精致的表情的“摆摊人的妹妹”,原田芳雄吼出了我的心声:“声音不要这么娇,表情不要那么嗲,你就不能像个正常女人一样吗?”
咳咳,扯远了,继续阿玲的悲惨人生。
时代
与中国电影不同,中国电影谈到这一时期必然牵扯到新文化运动或者复辟-宪政之争(没办法,这是基本的大叙事,吴天明的《变脸》大概可以算一个例外),日本在反映这一时期的电影作品中或多或少总会牵涉到时代与社会的变迁。彼时的日本,正处在国力和野心不断膨胀的时期。要说大事,触目皆是。然而原著和电影捕捉到的,都是一些很小很细微的变化。万才师的段子里开始赞美“电气化的新生活”,盲女的歌词里加入了“乘飞机旅行结婚”,让人想起《鬼子来了》和《戏梦人生》里面日军来了赞日军,国军来了赞国军的民间艺人。然而与中国电影专注政治风云不同,这些看似细微的生活上的变化,反而更持久,更坚决,正是它们一点一点,无可逆转地把整个社会拖向了现代。
盲女阿玲身处的,就是这么一个民众咸与维新,传统艺能与生活方式日渐消亡的时代。在影片的前半段,筱田正浩通过阿玲与鹤川在营火边的叙述,错落有致地交待了阿玲的生平。这几乎是一段标准的民俗展示,极其细致地展现了盲歌女的生活,从这些残疾人如何收拾房间,如何穿针引线,到她们的行规和组织,巨细靡遗地详述了一类特殊的生活方式。搁在中国第五代的手里,这些材料大概已经够撑起一整部影片了,然而在筱田这里,只是故事展开的一个引子而已。
影片结尾,孤苦的阿玲失去了鹤川,穿着渐成褴褛的衣服穿行在日新月异的乡村,盲歌女千百年来栖息的领地正在迎接现代化的洗礼。最后一场戏以隧道口的一架机器开始,象征着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镜头拉远,穿着制服的工人涌出,铁路已经修到了崇山峻岭。而阿玲的遗骨,就散落在对面的高山上。生于旅途,死于旅途,本来就是盲歌者的宿命,别所并没有虚言恐吓阿玲。作为观众,我也清醒地意识到虽然同属盲人,阿玲并不是座头市,不可能长生不死地流浪下去。然而筱田的这个直白的结尾,多少还是让习惯了“奇迹”的观众有点吃不消。人生终究尘归尘土归土,一切归于虚无,莫非是筱田幼年出家,师傅成天跟他叮嘱的就是这个?
从这个意义上说,阿玲的悲剧是双重的,她既背负着身为盲女的不幸,又背负着传统艺人身处大变革时代的不幸。即使她回到师傅的门前,师傅也已经不可能出来向她微笑了。剧团的破败已经分明喻示了盲歌者的没落,在过去,“盲女可以做按摩师,也可以做妓女,当然,还是做歌伎体面一些。”人们认为,成群结队的盲歌者是永远在路上的修行者。而在一个新时代,残障已经失去了神性的光辉,变成了彻底的医学意义上的缺陷。
如果这么看,盲女阿玲悲惨的一生或许也不失为一种圆满。
PS.感谢止痛片兄的推荐,电驴拖了半年,终于把这部杰作下到,幸甚。可惜无缘欣赏片兄翻译的中文字幕。
感谢侠兽兄关于筱田的文章,获益良多。
2 ) 岩下发志麻
轻狂少女那段,怎么说,也是败笔。筱田的电影一贯有逼人的美,却原来,会输给感情
3 ) 聖馬丁鳥的宿命
大正以前的日本盲女歌手,介乎于艺人、行乞者和妓女之间,传说中她们是嫁给佛祖的人,所以不能再与男人同寝。
记得张国荣在《阿飞正传》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世界上有一种没有脚的鸟,它的一生只能够一直飞翔,飞累了就睡在风中,这种鸟一辈子才会落地一次,那就是死亡来临的时刻。”我查了资料,这种鸟叫做无足鸟,又叫圣马丁鸟,学名岩燕。盲女阿玲,以及她的那个群体,就像圣马丁鸟一样,一直在路上,不知道终点在何处。当她失身于男人,与其说是为了生存,与其说是为了男人的体温,不如说是在寻找一种方式休息,以圣马丁鸟在天空中睡觉的方式休息,因为看不见世界的人生太冷、太累了。
用这种方式,阿玲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尽管在她身上的男人只不过图一时之欢娱,不过这也足够了。直到她遇见鹤川,一个对她的身体敬而远之的男人。如果说男人有“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般的思想,女人大体上也会有“被拒之于千里之外”的落寞感。所以,当药店老板想诱奸阿玲时,她半推半就的表现直到最后鹤川的杀人,都是对这个男人的试探:一个会为我杀人的男人还会拒绝我吗?
阿玲终于在鹤川身上找到归宿,可惜杀人犯和逃兵的双重身份又让这种归宿感像窗户纸般一捅就破。这就是命,盲女歌手的命,注定像圣马丁鸟那样不能落地。电影结尾处那一堆白骨和一把三味线,以及树顶上一大群缭绕的乌鸦,是暗喻一个悲剧的结局吗?我以为阿玲终于找到可以休息的地方了,圣马丁鸟终于落地,死亡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开始。
这是我第一次看全英文字幕的电影,可能有些词理解得有偏差,但对于美女天生敏感的我来说不得不错过岩下志麻的美丽,这种美太精致,尤其是侧脸和鼻尖。出演过《雪国》和《秋刀鱼之味》的岩下志麻配得上“昭和十大最美女优”的称号。
以下是我借用的一段话,权作本文结束语:我生为盲女,本就不应存世,我们扶着背一路吟唱乞食,初潮入雪成花,直到碰到了你,坐在你车后是这一生最快乐时光,我喊你"哥哥“,你却当我菩萨,乱石滚过,你却紧紧拥住我,你为我杀人,陪我归乡,却永隔两世,从此我成孤魂,终化为海边一堆白骨。
4 ) 阿玲的歌
阿玲的歌 鹤川: 冬天嘴唇会干裂吗? 雪上行走脚会痛吗? 早晨醒来仍然冷吗? 还在乞求男人的温暖? 你更容易感到孤独吧——一直在黑暗中徘徊。 很想背你走过漫漫长夜, 很想听你唱歌, 用木车拉你到海边, 回到你的故乡。 很想抱着你, 给你一个男人仅有的温存。 很想给你一个家, 不再流浪。 阿玲: 天气凉了, 我的眼睛感到下午阳光的温暖。 听说故乡很美, 我看不见 但我听见海的声音。 融雪后你回来, 我们一起回家。 你在吗? 时间会抹掉一切? 包括爱情。
5 ) 一个盲女的一生
听到过一种说法,对贫苦人士的最大伤害并不是贫困本身,而是来自生活富裕的人们的怜悯,认为他们一定很苦的意识。
赤脚在雪地里走,只要一直在动,也不觉得雪地很冷。反而为了御寒,用布套上步,却把脚冻坏了。这是电影里的一幕。却很好地象征这样一个事实。伤害人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别人强加在你身上的现状。
盲女的一生,献给了佛祖,看起来好像很软弱,很可怜,但确是对现实最好的臣服。阿玲的一生,在外人的眼里看来,凄惨无比。自小失明,成年失身被逐出师门。四处流浪,寄宿寺庙。靠卖唱谋生,但却因无力自保,而经常自愿或不自愿地被男人强暴。如果一个人自怜地活在这种现状中,只怕除了自杀,别无他法。所以阿玲麻木地臣服着,她只想活下去。她能靠嗅觉分辨道路,分辨时辰;她满足地吃下一块馒头,满足地喝水。当鹤川告诉她无需再卖艺,只要摆摊就能满足生活所需时,她更是高兴地不能自己。
阿玲是个可怜人,这个社会万恶,可能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之一。但导演另一方面,又很矛盾地表现着生存的本质,臣服的力量。我看着阿玲,总想到余华的《活着》,老百姓在痛苦现世的生存故事。都不是反抗,都是麻木地生存着。而这些人的最大特点是,他们都是弱者,他们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
大自然是一个体制,一个宇宙或神制定得宏大的生存法则。而人类社会,则是人类模仿自然生存法则,所制定的又一套生存法则。这套生存法则依附于自然法则,而小于自然法则。阿玲在社会法则中看来,无疑是生活在最底层,但从自然法则看来,她顺应天意,克服自身的残障,自给自足,其实过得也不差。如果那些男人不强奸她的话。其实她有时甚至是愿意和男人睡觉的,因为温暖。可是那些男人却认为睡过即得到。男人对阿玲所为,是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双重作用下的结果。
另一方面,鹤川的参军,又是另一场悲剧。穷人无钱,卖身替富人参军。但又不愿意打仗,于是当逃兵被杀。这是军国主义造成的悲剧。
所以阿玲和鹤川的悲剧的最后根源,是大男子主义下所铸造出来的各种畸形怪状的产物。但我觉得,这大概并不是筱田正浩想要表达的,而是我过度思索的结果。
有一部美国片,对男人和男性社会做过很好地解剖,叫《搏击俱乐部》,这片名很雄壮,却是以双重人格和悬疑片出名,真叫杯具。
6 ) 日本电影往事:筱田正浩的夜光水母
“只描写别人留给自己的伤痕,不描写自己留给别人的伤痕,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揭示别人心中的恶,不袒露自己心中的恶,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最大的悲悯。”
筱田正浩的电影《孤苦盲女阿玲》便是讲述了一个关于悲悯的故事。
自幼双目失明,探寻这个世界的方式便是自己的身体,阿玲倔强的成长,正如她赤脚走过的那些山坡上的野草。这样的女性角色,多多少少都是值得人们同情的。而筱田正浩却用自己的方式,将阿玲放置于一个残酷的世界之中。
中学时代的筱田正浩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军国主义少年,现在看筱田正浩的这些影片,很难想象那时候的他经历着怎样的人生。尽管他对天皇有着与生俱来的崇拜,不过,战争的失败,依然给筱田正浩带来了一种幻灭感。而这种幻灭感和阿玲的幻灭感有着如出一辙的相似,阿玲对逃兵的依赖和期待并没有让她真正摆脱悲悯,而是从一个黑暗的山谷进入另一个黑暗的山谷。
从美学的角度来看,筱田正浩继承了日本电影的感伤传统,并将此升级为一种唯美的悲剧,使其具有了筱田正浩的个人风格。在《孤苦盲女阿玲》这部电影中,阿玲并没有对人生充满绝望,而是在这样的境遇之下,一直燃烧着生命的喜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筱田正浩电影中角色的悲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悲苦,而是非常体面,非常有风度的悲苦,在《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也可以看见这种桥段。
上个世纪的日本电影大多都很厚重,或许是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已经深深地根植于导演的灵魂之中,所以,他们的电影总能看见一些对战争的控诉,这部《孤苦盲女阿玲》也是如此。尤其是鹤川的逃兵身份,更是告诉了观众,阿玲的悲剧是这段历史造成的,是战争造成的,是那个时代不得不承认的宿命。双目失明的阿玲总是可以让人感动,虽然她眼睛看不见,可她的心中总是充满了对相濡以沫的期待。她渴望的不是鱼水之欢,而是那种可以一直依靠的温暖胸膛。
影片的结尾非常直白,是一种可以遇见的结果。不过,这恰好符合幻灭的情感基调,尘归尘土归土。阿玲所代表的除了有女性本身的悲剧身份之外,还有传统艺人在战败之后的尴尬地位。不同于其他的日本导演,筱田正浩是一位注重技巧的导演,在这一点上他和黑泽明有些相似,不过,他比黑泽明更浪漫一些。筱田正浩从不可以卖弄技巧,而是通过流畅的叙事来展示自己纯熟的拍摄技巧。
筱田正浩其实是同情阿玲的,因为阿玲就是另一个筱田正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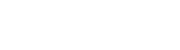




















24th SSIF No.08@黄浦剧场。“世间如地狱,我不能和你睡觉,只是想与你,再走一段路。”盲歌女们的每一首歌,都是水深火热的苦,如何听来取乐呢?阿玲特别动人的是声音,明明活得如此艰难,讲话的声音却始终清脆明亮,浑若无事。电影里的树木希林、小林薰都还年轻。只是西田敏行叔,跟现在看不出多大差别。读佐藤忠男日影史,得知这部电影是70年代津轻三味线和盲女歌得到再评价后拍摄的。p.s.黄埔剧场这反人类座间距伸不开我这大长腿…
雪地、温泉、海边、山林,在自然的霜风雨雪中颠沛流离.相聚、别离、战争、厄运,在世事的变迁动荡中求得一席.这是一个人的编年史,说什么世人洗罪的尊佛,只要一个温暖的归宿却求不得.命运注定在先,有时候有缺陷的人不得不用一生来寻求对生命的弥补.岩下志麻不事雕琢,原田芳雄真乃好汉也.
岩下志麻太美了……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阿玲在开头面对一众男人唱戏时,她的语调及笑容很是俏皮,这是一个闯荡江湖多时的形象。而当她渴求着男人拥抱占有她的时候,是那样让人心疼。她是艺妓,不是妓女,但看不见世界的人往往缺乏安全感与温度,与男人躯体纠缠能够暂时填补她缺失的温度与想象力,想象力可以通过触觉在脑海中建构一个男人的形象,对盲人来说,身体接触是最可靠的认知方式。阿玲被强奸的段落里她最后主动屈服,她在等待与鹤川重逢,这是不得不做的退让。阿玲与鹤川在一起的日子是唯一幸福的时光,他们摆摊做木屐让阿玲不用再四处流浪卖唱。而鹤川杀掉强奸者后逃走,又因底层出身被迫顶替富人参军,参军后又逃走的元素有着极强的社会批判性。最后鹤川被处刑,只剩阿玲一人重新流浪,多年后被人看见了她挂在树上的红衣以及树下的白骨,她是怎么死的没有交代,这样的留白让人寒心。
为了暖和随便和那么多男人睡,不怕怀孕搞坏身体吗。一被男人吻或碰下就自动脱衣和男人做,太敏感了。鹤川原来是不去中国东北的逃兵、被通缉的杀人犯,被抓后阿玲去找盲女屋收留自己的盲女但屋中空无一人,去找生母也没找到于是跳崖自杀了。真是悲剧
那個陌生的男人猴急地進入她的身體的時候,她感受到疼痛的時候更多的卻是一種溫暖,對於性的渴求,除了生理上的,也許更多的是對於孤獨和冷漠的畏懼,但是,那些男人只貪求一時的魚水,天沒亮,他們就漠然離開,把寒冷留給女人。她被趕出那安身之所,遇到那真正關愛她的男人,但,他們一起遭遇了死亡。
在这部片里突然体会到了岩下志麻的美,柔美的面庞带着清雅的欲望,那是男人迫不及待的占有欲念,也是阿玲在这孤单世上能抓住的少有温暖。如果能一直和“哥哥”相伴卖草鞋下去该有多好,最终还是从孤苦中来,从孤苦中去。打酱油的西田敏行和树木希林可爱。
@2021SIFF.因为寒冷从光脚下开出红花开始寻找温暖,盲女用嘴唇穿针,投海自杀的老妇和孙女,穷人是战争的牺牲品...重复出现的海浪是阿玲记忆中家乡的声音,被铁路和电话削弱,新的时代容不下盲女了...时代一去不复返的悲怆一如莱昂内的往事系列;当外部战事受挫,疯狂指向内部和弱者,一如夏布洛尔的女人韵事;招供时权威的视而不见与逃避一如大岛渚的圣诞快乐;笑意盈盈地流浪和相依为命,一如费里尼的大路,私心觉得筱田正浩一定看过大路,也许非常非常非常喜欢... 筱田是本届siff大师单元唯一在世的大师了好年轻的树木希林和小林薰
岩下志麻演得真好,日本导演真的是非常善于刻画此类女性形象,和西方爱情、婚姻悲剧不同,这种完完全全是女性个体命运的悲剧,而男性的存在只会加剧女性的痛苦,包括曾给予她虚妄的希望最后幻灭成泡影的鹤川。结尾镜头扫过树叶上的红衣和草地里的头骨,一声唏嘘。《西鹤一代女》是如此,本片亦是如此。
①如此冰冷而凄苦的电影,沉静地勾画出盲女阿玲的一生,颠沛流离的孤寂命途与昙花一现的温暖拥抱,历遍风霜血雨,迎来短暂幸福与刹那芳华,转身依旧空无,终如霜花零落。②影片亦浸染着物哀与幽玄之美,一如时而插入的空镜(大多为两两一组):雪野,苍松,夜月,密林,海岸,远山,夕阳,配上武满彻的怆然音乐,洞穿心底。③岩下志麻的表演无可挑剔,全程闭眼仍然美到发光。④反战主题隐现,还有不少对20世纪初日本的时代侧写:对外征伐,买穷人代替服役,传统曲艺卖唱的没落,街头摊贩与节庆仪式,铁路繁盛。⑤盲女大家庭里的光与暗:穿针引线,驱逐严规,互绊设陷。⑥雪地上的点点经血,初潮开出的红花。⑦两人在雾气弥漫的山溪中沐浴,鹤川说:阿玲,你在夕阳下活像个慈佛。⑧吃馒头与喝水时的笑靥。⑨一群乌鸦,一袭红衣,一地白骨。(9.0/10)
生活本已不易,盲女更为艰辛,抚琴编鞋,都是为了能够在这凄冷的世间生存下去;黑暗中,既经历了深沉的痛苦,幸而也得到了短暂的幸福;但纵使再坚强,也没能抵住这举世的冰冷与凄凉!除了散乱的衣帽,破损的古琴,还有谁记得你曾在这世上来过?
如果说心中天网岛美术和音乐风格是我们熟悉的典型栗津洁和武满彻,那这一部里他俩或许还有点一反常态,大地色系内景,有点芥川附身的哀伤交响乐,你别说后半开始破案命运捉弄人伦惨剧了特么是有点在看野村芳太郎的错觉..不过他还是比野村好看一些,就冲那结尾的狠劲!前半七八分钟一首歌特别喜欢,只有一把琴伴奏的近乎清唱的民谣赶脚各国有共通之处不过以前卖唱助兴的歌咋非黄即惨而且惨得居多orz 70年代彩色胶片四比三画幅这种浅景深多中景如画一样平面的构图,难以复制的美。ps原田芳雄演时代剧好像从来就是直接顶着自己当时的长卷发上阵的从来不剃头么...@新天地
生存本就艰难,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心灵的慰藉,经历了无可倾诉的痛苦,也经历了短暂深刻的幸福。昙花一现的幸福过后,眼前却仍是幽深的黑。
7.5/8 孤独的灵魂 悲凉的命运 大正时代日本民间残像;战后日本电影好看 不仅演员演技无可挑剔 更在于剥离历史时代背后那光怪陆离的人性与人心的故事
旧时对女性欲望的压抑,苦命的阿玲尽管目盲可她拥有善良的心灵和正常的生理欲望。她在鹤川眼里是个圣女,不容被任何男人沾染包括鹤川自己,我猜大概因为自己是逃兵怕连累阿玲吧。通过鹤川的供述,表现出导演反战和招兵腐败(有钱人可以花钱不用去当兵,当兵的都是穷人家娃)的事实。
阿玲与鹤川的第一次拥抱真是感动。孤独无助且隐忍,这成为活下去的方法,影片的情绪也很好,没有太过激的情绪释放,很冷静的观望,却带来隐痛。岩下志麻演的真好,脚下开出的花。
太有魅力的一部电影,同时也是一部无法展现视线的电影(拍盲的电影让人看,实在是件美而残酷的事情),气候和景观成为主角。初潮之花和结尾的红摄人心魄,筱田正浩故意在全片压制红色,为的也就是这两个瞬间。背景并没有设置在二战期间,而是在之前,似有点《白丝带》的意思,不过反战只是一个方面,阶层也是重要部分(莫名想起印度三傻)。冒昧说一句,树木希林演盲女真的太合适了。
结局太悲了。最后一组空镜头导演显然也不忍正面表现阿玲死亡过程,但飘荡在树间的红色和服,盘桓在枝头的乌鸦,以及地上的头骨说明了一切,阿玲最终凄凉而去,告别了这个没有一丝温暖的世界。
东方佳人,不过岩下志麻尔。
人间料得极难看,且喜生来已丧目,人生难有一知己,原来只有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