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长篇影评
1 ) 《咏鹅》:跨文化下的多声部情愫
在东亚,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导演时常关注于盘踞在中日韩历史和当今的社会流动的身份认同问题。他就是延边大学的教授张律。从张律的拍摄履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在东亚跨国界的游走。在其早期的电影中,其强调的是生存在中国的韩国人和朝鲜族人:《重庆》的中韩跨国情感下的社会现实记录和《芒种》中对于少数民族边缘化的批判。之后张律前往了韩国,开始拍摄了一系列具有独特韵味的情感,其中包括《春梦》的虚实结合的“三人行。”黑白的色调以及散漫的叙事让人回忆起些许戈达尔《法外之徒》的趣味,但同时也夹杂着对于对边缘群体,包括“脱北者”等身份的关注。随着其电影在韩国的声名鹊起,其多部电影都成为了韩国釜山电影节的重点制作。《春梦》是他的电影第一次成为釜山的开幕片,这部电影在选角上更像是对韩国独立电影的一次巡礼。三位韩国当代重要的独立电影人成为了《春梦》中的三位男性角色:拍摄过《绿头苍蝇》的夺得鹿特丹金虎的导演梁益俊,戛纳参赛电影《特工》的导演尹钟彬,以及拍摄《茂山日记》而获得釜山“新浪潮”奖的朴庭凡。由三位导演作为主角撑起来了一部电影,也增添了其电影的观影趣味。
自从2018年的《咏鹅》,我感受到张律的电影变成了一种更加“多声部”的场域。这种“多声部”不仅呈现了一种角色身份政治上的多声部,也同时还有语言的多声部。在《咏鹅》中,角色的出身和讲话方式都让角色本身的身份谜样或复杂。电影的开始,我们看见朴海日演的允英和文素丽饰演的颂贤来到海滨旅游城市群山,然而在这座城市见到的人都有着截然不同或者难以捉摸的身份。开餐厅的老板娘在被问及其故乡时没有答案,但却在之后讲起了连贯的日语;在群山的日本殖民时期的房屋开办民宿的老板,与日本旅客交流用韩文,最后却声称自己是来自福冈的在日朝鲜人;而允英和颂贤的身份也是谜一样。被错认为中国朝鲜族的颂贤是不是朝鲜族?会说中文的允英是否是韩国人?其实这部电影在角色上,总会引起观众不断得询问“他们究竟来自于哪里?”这样的问题。而在群山,朴素丹饰演的少女却仿佛是犹如鬼魂版,在群山这些扑朔迷离的角色之间飘来飘去。她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允英对颂贤表达欲望,在他一次对颂贤的亲密碰触和颂贤的故意离去之后,电影突然出现一个不知名的岛屿,而这个少女拿着日本的布偶,走向丛林之中。她的身份是什么?虽说她是民宿老板的女儿,她却仿佛一句朝鲜话都不会说,而她的日本语却表达流畅。她也逐渐接近着允英。
文化和身份是存在叠加的。语言,宗教,符号,信物等属性能指涉文化和身份。但当这些属性存在交叉,文化和身份也不再变成一种本质主义的范畴。这一点当然在张律这部电影中也出现。当我们观众或许还保持一种本质主义的视角去观察每个角色的身份,我们却发现根本无法解读。它的无法解读甚至就像男女之间暧昧时传递的信息,是一种蛊惑人心却莫名其妙的距离和趣味。或许这就是张律用一种情感的时而疏离时而靠近去阐述历史和当下碰撞出的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之间的状态。
在《咏鹅》中,角色和角色之间都是暧昧的。但是当影片到达中间的时候,对于允英而言,这些暧昧都最终失效,留下来的只是他一个人的怅惘:颂贤越来越亲近民宿老板,允英因为少女未成年而被疑为流氓,而之前见过的任何人,就连他的父亲成了老年痴呆,都不再认为与他存在任何关系。在这个群山故事的末尾,被骂被嘲讽的允英落寞得躺在公园椅子上,当他看见一个公园里健身的女人时,他却靠近紧紧地盯着她,当然结果是,她很不舒服,就逃走了。而允英一个人孤独和哀愁得沉思着些什么。
之后,电影出现了公园的夜景,片名才出现,用中文书写的《咏鹅》,以及朝鲜语书写的:《群山:咏鹅》。电影为什么叫《咏鹅》,这一点在前半段允英回家的时候给出了一个答案。我们看见了他痴呆的父亲,对着一直鹅,呼唤着允英儿时的小名“允儿”,但是这个윤아,却听起来很像中文的咏鹅。在我理解,这个电影其实最终讲述的,就是男主人公允英的故事。在这时电影由回到了时间顺序上的某个起点,我们看见允英参与到了在韩朝鲜族的抗议,我们由此看到为什么允英为什么见到颂贤,以及这次群山之旅的起因。当然这种时间顺序的倒叙在叙事结构上都在揭开电影前半段种种事件的成因,但在感情上,或许这段是允英和颂贤感情最浓的状态,是一段珍藏的情感,以及一种永恒的心灵。张律热衷于未果的爱情,这一点在他电影中通常的主题。然而在我感觉,张律和洪尚秀还是不一样的。洪尚秀中的男性是游手好闲之徒,有时过于主动,有时摇尾乞怜,当然这种状态换来的结果是一种尴尬的邂逅,洪尚秀爱用变焦来模拟窥视的视角,放大这种初遇的尴尬。而张律中的感情,女性往往是主导的,女性在靠近男主人公,但是最终先离开的也是女性本人,或许张律影像下的情感,更强调的是安东奥尼奥式的疏离感,而并没有洪尚秀那种偷窥狂式的诙谐。
当然到了《福冈》,这种忧伤给了两个岁数更大的痴情老男人。。。。。悲伤到极致的喜剧。不过,在本文的最后,我不由得想为即将在北京尤伦斯举办的张律影展做个人肉广告。《咏鹅》也即将在那里放映,张律和男主角朴海日都会到场,希望各位北京的朋友能过几个多种语言交相辉映的“春梦”。
2 ) 隽妙!这是今年最性感的文艺大闷片
看死君:年关将至,你的年度十佳选了么?每年12月,都是影迷们疯狂补片的时候,仿佛生怕错过哪部好片,毕竟选年度十佳需要一点仪式感。纵观今年压轴出炉的几部热门电影,想必都会成为很多影迷的年度榜单上的常客,比如《罗马》,比如《摄影机不要停》。

而我们今天要推荐的这部,同为不少影迷的心水之作,来自于张律导演的《咏鹅》;本片也入选了Cine21选定的2018韩国电影十佳,排名第九。在导演拍于韩国的几部作品中,无论《庆州》还是《春梦》,同样都备受赞誉。有人说他是“第二个洪常秀”,但真正看懂他电影的人,显然会发现另一种独特的味道。

作者| 县豪
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到第77分30秒,这部电影才露出片名,清晰的城市夜色中,片名在熄灭的台灯上浮现——《咏鹅》。

这么骚的操作,平生第一次见,而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张律导演的片子。看完电影后,对张律导演非常感兴趣,我就去了解了一下。原来他是中国朝鲜族导演,出生在中国吉林,他甚至拍过以《重庆》为名的电影。

但他现在主要在韩国拍片,虽然他曾在采访中透露,想回中国拍华语片。张律这个名字本身就挺暧昧的,有点中国味儿,也带些韩国味儿;而“暧昧”,也是《咏鹅》这部电影的关键词之一。

似乎一直以来,张律导演都是在拍摄同一类型电影,而这部《咏鹅》所代表的,其实是一种危险的电影类型——它文艺,闷,甚至虚无,对情绪的拿捏要求很高;在它述及男欢女爱或家国情仇时,会采取相当清淡的表达方式;而这种清淡,能否勾起观众的审美情趣,还真说不准,因为它要求观众极度敏感。

所幸《咏鹅》很妙。妙就妙在几个关键词。
暧昧
影片《咏鹅》极度暧昧。这里的暧昧,不仅指片中角色之间的情感关系暧昧,更指片中的一切。
有哪些暧昧?人物的情感暧昧是显而易见的。男主角张允永与他的嫂子也就是女主角松贤,两人之间的关系简直暧昧出了极其丰富的层次——

两人到民宿,起初只开了一间房,他想摸她,就是单纯的摸,刚开了头,她就阻止了;她于是主动向民宿老板提出加开一间房,并和老板越走越近,他不开心了;老板患有自闭症的女儿对允永颇有青睐,松贤看见同样不开心;他陪她去前夫的咖啡馆,她又在他面前和前夫再续前缘……

两人就这样一直蜻蜓点水,将暧昧推向下一次暧昧。
当然不只这一组人物,电影中凡彼此有关联的人物,之间或多或少都有暧昧。药店女员工送允永止疼药,这本可终止于一种干净的善意,但允永偏要问一句:「我值得信赖吗?」,由此勾起一丝隐约情愫。

松贤在海滩请民宿老板为她拍照,老板将镜头对准她,却缓缓将之移动,最终令松贤出画,拍下了三个在海边劳作的渔妇。镜头答应了一次摆拍,却被更具生命力的情景吸引,这点艺术性的无情,又何尝不是一种暧昧?

除了人物情感,片中的文化与历史也很暧昧。
影片《咏鹅》一共三种语言,韩语、日语、中文,韩语又分散为正宗韩语与带朝鲜味被视为某种方言的韩语。而片中也出现韩国人、日本游客、中国游客三种角色身份。

电影故事发生地群山,当年则是日军殖民地之一,留有不少日式家屋,日本文化的影响至今未消。男主角走在街上,甚至能看见当年屠杀的摄影展,片中也时而传出隐喻战机轰鸣的飞机声,伪装的朝鲜族则在街道拐角进行非常小众的示威宣传……

这所有一切,都在主角「片叶不沾身」式的游荡中,成为影片一种疏离而又深入的时代背景。
这种背景是很迷人的,它似乎不只是历史,也不只是现在,而处于历史与现在的交融与缝隙中,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时间文化。《咏鹅》中群山的这种文化特征,中国台湾同样也有,并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赛德克·巴莱》等经典台影里有更深的体现。

这里多说一点。我们看到不少香港电影比如像《香港制造》《树大招风》等,都在以一种悸动感非常明显的叙事,强调香港回归前后港人那极为强烈的精神躁动。而台湾电影或《咏鹅》一类的韩国电影,则完全是在呈现文化的融合或者说「继发感染」,完全没有香港电影热衷的那种「时代断裂性」,这还挺值得玩味。

而《咏鹅》的人物形象本身,甚至都是暧昧的。
松贤在酒意中这样评价允永:「你的说话暧昧,行动暧昧,就连名字也是暧昧的。」

的确,说话暧昧从他对药店女员工的反问已可看出;名字,允永,既不是完全的男名,也非彻底的女名,介于男女之间;小名永儿,在韩语中和「咏鹅」发音极似。而永儿这一小名,又是他已离世的母亲常唤的,如是种种,已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又极迷人的味道了。

而允永平日的行走坐卧也是暧昧的。他躺在民宿房间,是侧身,静谧轻盈小幅度蜷缩在日式和屋的阴翳中,盆骨与腰身之间形成高耸的曲线,一种孤独,又孤独得不需要任何人;他行走在街上,蓝衬衣、白T恤、灰长裤,以及黑肩包,像一个孩子,又似乎很苍老;他坐在屋檐下……

总之,他仿佛随时随地处于一种状态,但又好像完全在这种状态之外。
而所谓暧昧,不就等于是,又不是吗?

一半
影片《咏鹅》拍的是一位诗人,但奇特的是,这位诗人从始至终未曾写诗。
李沧东《诗》也拍一个想写诗的人,至少,她最后在鲜花的覆盖下,交出了一首完整的诗,而且这首诗,成为整部电影最迷人的悬念。

而《咏鹅》中的张允永,渴望成为一名诗人,但他在十几岁写过诗后,就再没写诗了。用松贤的话说,「写到一半就不写了,你做什么都是做一半,所以我才不敢和你发生关系」,是调侃语气,揭示了允永的暧昧从何而来。
正是来自这种「一半」。

同时,张律导演同样通过「一半」,使影片拥有了令人惊讶的结构。电影前半部,允永与松贤在群山游荡,电影后半部,以一系列情感纠葛交代他们为何去群山,奇就奇在中间,允永跨进家门的一瞬间。

这一瞬间将电影分为两半,但或许有点难以厘清哪一半在前,哪一半在后。允永告诉阿姨,自己刚去了一趟母亲的老家。看来是先去了母亲老家,再去了群山?但种种线索表明,母亲的老家就在群山。所以他回来的一瞬,究竟是刚从松贤的群山回来,还是从母亲的群山?

而电影以允永看向某件事物结束,这一事物,必然就是电影开场车站标示的群山地图。
真是无尽的暧昧如衔尾蛇。
按导演自己的话说,这部电影从中间开始,在中间结束。

而中间,在《咏鹅》中是一个如此神秘的时刻。允永站在这中间,正如群山酒馆老板娘对他的奇妙评价:你年纪轻轻,却有旧时代的感性。
这是一句何其性感的对白。

张律与洪常秀
有人将张律的《咏鹅》和洪常秀的电影做对比,认为相比之下,《咏鹅》显得尴尬。

对比是难免的。尽管张律更多一些历史痕迹,洪尚秀电影则更深入艺术家的情感世界,但两类电影中那些悠悠晃荡的男女、无处安放的寂寞、朝圣般的叩拜,是如此相似。

甚至可以说,他们独自开辟了韩国电影的新类型,一种暧昧、神经、虚无,却又执着的闲晃式电影,以区别韩国那些著名的社会、犯罪、纯爱题材,甚至区别于金基德、李沧东等人的深刻度文艺片。

我曾在某段时间集中看过大量的洪尚秀电影,《咏鹅》与其早期《猪堕井的那天》、《剧场前》等作品在叙事体量上是类似的,并同样具有巧妙的结构。

但洪常秀后期《独自在夜晚的海边》、《之后》等片,就实在不如《咏鹅》这般具有灵气与创作性了,甚至可以说,洪常秀后期电影几乎都是“草稿电影”,据说他现在拍片也确实不太怎么写剧本了。

骆宾王与尹东柱
鹅,鹅,鹅,
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清波。
——这是唐代诗人骆宾王七岁时的《咏鹅》。
我只是为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抬头仰望悠远苍穹时敢言我生命中没有一丝悔恨。
我要以爱恋星儿的心
讴歌一切的生与灵。
要走完给我注定的路。
今夜又见高远繁星,在阵阵狂风里隐闪。
——这是朝鲜爱国诗人尹东柱的名作《序诗》。
这两首诗,都在《咏鹅》这部电影中出现。

对于骆宾王,据说张律导演是汉语言文学出身,对中国古诗词有特殊情感。2003年,他就拍过一部名为《唐诗》的剧情片,主角是一个偶尔会在电视上看「唐诗讲座」的中年小偷。这首《咏鹅》,语义相当通俗,甚至很简单,但在《咏鹅》这部电影中,却具有难以言明的精神意义。

男主角的小名是「咏鹅」的第一个层次,「咏鹅」的第二个层次,是男主角父亲养了只大白鹅。他会对着鹅「永儿、永儿」地呼唤,也会抱着鹅暗自哭泣。「咏鹅」的第三个层次,是允永在酒醉中吟出的诗。

他用中文在酒馆咏诵《咏鹅》。四肢做出鹅引颈之状,近似于一支舞,但又决不是一支舞。允永的动作有自己独特的疏离间落,不像金惠子在奉俊昊的《母亲》中,也不像廖凡在刁亦男的《白日焰火》中。这种动作是对嫂子松贤充满佛性的108拜的回应,是姿势和含义的双重暧昧。


而「咏鹅」的这三个层次,到底在影片中抵达了怎样的意义,似乎不能言明,或许它们只是层次本身,使诗人骆宾王的《咏鹅》这首无比简单却又相当有才的诗,在朝韩现代化语境中成为一种朦胧、斑驳而又神秘的意识流美学。

而尹东柱的意义就清晰多了。他是允永的偶像和精神支柱,也是电影文化伤痕的一个人物标签。尹东柱这种具有民族气节并充满抒情才华的诗人,自然对允永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而尹东柱作为无可争议的朝鲜族诗人代表,对于观众而言,也更容易理解允永对他的痴迷。

尹东柱的诗歌主题之一,便是移民者的身份认同问题,而在《咏鹅》中,每个人的身份都具有移民者的暧昧性。比如民宿老板对松贤讲述妻子离世经过时,有意使用松贤听不懂的日语,这与他将镜头对准松贤却最终移开一样,是种介于说与不说、靠近与离开之间的永恒试探。

片中也多次提到尹东柱死于日本福冈的监狱,而民宿老板也正是来自福冈。2016年,《素媛》导演李濬益拍过一部黑白传记电影《东柱》,90后小生姜河那在其中饰演尹东柱。片中交代了日军对尹东柱实施的死亡酷刑——用针管将盐度很浓的海水不断注入诗人体内,导致诗人皮肤皲裂,在体内的灼烧中痛苦离世。

这种死亡方式,在黑白影像的表现下,本身便具有极为残酷的诗意,对应到《咏鹅》中允永对尹东柱孩子们般天真的敬意,我们似乎就可以理解张律导演对诗人的真正的定义了——诗人并不完全是写诗的人,还有那些不写诗却怀有诗性情怀的人。
而《咏鹅》本身的运镜和空间便具有这样的诗性。

比如我们看见男主角转入一间废弃的屋子,在窗外绿意与屋内阴影的映衬下走向我们,然后他消失在画面中。
镜头开始推过阴影,推向那扇蓝色木框的窗。树叶在外面拂摆,我们听到生动的风声。窗越来越近,我们以为电影将就此转场。
但突然又仿佛必然——
诗人允永出现在了窗外的诗中。

作者| 县豪;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3 ) 没让你睡我,是因为还不够爱
虽然我从小就会背鹅鹅鹅曲项向天歌,虽然我平时也无病呻吟地写两首小诗,虽然我也经常吹嘘我对某件事情看得很透,但是这次我真得坦白,这电影要表达什么深层次的东西,我真是没搞懂。
浅薄的我谈不了韩国与朝鲜族的问题(片中多次涉及),也不了解韩国的大诗人。我只想谈下女主为何自始至终没让男主睡。
我也是看到结尾,才发现这电影的剪辑不是按照正常的故事发展顺序。以一小时十七分夜景《咏鹅》这首诗的出现为分界点,本片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分界点以后的情节是先发生的,影片结尾两小时左右男女主才到群山,正好接上整个影片的开头。这样看影片一小时十七分之前才是故事真正的结尾。发生了什么?
男主要去女主开牙科医院的表姐那里看夜景,表姐和女主通了电话后让男主滚蛋。
男主去公园板凳睡觉,彻底凉了。

女主是男主的嫂嫂,和老公不和,男主作为爱慕者一直默默地在等机会。后面机会真的来了,女主离婚了,男主看到了希望,可是即使女主和老公离婚了,两个人之间的近密仍然远非男主所能企及。那天在酒馆两夫妻喝个烂醉还是搂搂抱抱卿卿我我,男主带着女主离开,女主直接告之甭想睡我,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不过故事似乎出现了转机,女主同意和男主去群山,而且还要在外过夜。男主暗爽太早,发现自己真是土羊土心魄,还是不给睡啊。于是男主就每天郁郁寡欢地房前屋后转悠,直到察觉并目击女主和爱玩摄影的民宿老板亲密勾肩,然后他也放纵了自己,把手指放在了老板女儿的胸前。

至于男主离开后,老板的女儿尾随着他,有没有被伤害,她自己作证说没有,反而救了她。从男主整体表现来看,他应该不是一个坏人。
他唯一的痛处,就是苦苦追了很久等了很久的女主,为何不给自己睡?甚至刚刚有些肌肤之亲就喊停说不合适,却和才认识的老板各种主动接触。
正好这几天逛论坛看到类似的帖子,什么男孩子说和女友相处三年,女友守身如玉,结果对方分手后没多久就有了新欢而且很快滚了床单,男孩子苦思不得其解,悲痛欲绝。
其实和本片的女主一样,一些女孩子确实是有关于何时上床的原则,但是具体是放在毕业后还是婚后还是哪个时间点,不必太过深究。女人二十三四以后,和男人相处很久了还说什么没准备好、时机不够成熟、对男人的考验等等应该都是托词,实际上就是还不够爱,因为情到深处,自然会奋不顾身。
本片中不能说女主对男主没有感觉,不然天天在一起还总买单是嫌钱多?男主独自离开群山后,她自知破镜难圆,还去一个人喝闷酒。酒馆老婆婆上来就问,“做了么?”女主哭而不答。

没那么爱,可心中还是有一点留恋和遗憾吧。
男主的名字听起来像“咏鹅”,他没有工作,喜欢写诗,“曲颈向天歌”地骄傲地自在地活着。
应该是不会回来了吧。
4 ) 我好像做了一个梦,太狗血了。
张律导演镜头里的那种迷人大概是因为身份特征吧,和密不可分的中日韩之间的羁绊与纠葛的历史。 已经习惯他的标志性影像:黄绿色滤镜,模仿动物姿态的行为/舞蹈,男人和女人之间由“也许我们在哪儿见过”或者“你还记得我吗”开始发展的关系,墙上的画,相框里的构图,通过镜子反射,穿插的间歇性黑白色画面,晾晒在庭院里的植物或食物总会遇上下雨的天气,街道旁不起眼的算命店。 女人表面上看起来更主动、追求刺激,在很“容易”的男人身上找到自信,并给他们贴上“魅力、特别”的标签来引起另一个男人的注意和妒忌,受伤之后却只能从同性那里得到安慰,然后深呼吸,重新挺起背,其实表面反复无常的情绪化爆发,都是敏感又清醒的内心,脆弱,需要爱,但也想保留自尊。 男人其实更懂男人,永允一看到民宿老板就觉得这个老板很奇怪,而松贤对老板说的是“你对我不好奇嘛”这种意味深长的暧昧,又不同于永允——名字、说话、行为的暧昧,他在隧道里问松贤:你喜欢白天做还是夜晚做。 松贤主动提出分别住两个房间,迅速了解了老板的妻子女儿的信息,和老板一起在厨房里吃拉面,早上一起在楼顶上做一百零八拜,去海滩上散步。 老板有个自闭症女儿,整天躲在房间里看民宿的监控录像,陪伴她的只有那只日本式娃娃,或许饭店里的女老板是她母亲也说不定,有一天下雨,她打了一把伞坐在楼顶上,隔天永允也坐在那里,像个思想家的雕塑,那天晚上,她给他送去一碗拉面,坐在门口听他吃面的声音。 松贤看到永允和老板女儿坐在门口,问他,“你在干什么?”,永允回答:“你行,我就不行吗?”,后来换成松贤坐在门口抽烟,警察问那个头上贴着创可贴的女儿是不是受害者,女人淡淡地说:“我已经23了,他没有对我做任何事情”。 那些出现片刻的人像更像是浮世绘的旋转,和鹅说话的父亲,半夜推开女佣的门,在路上遇见儿子又假装不认识他,是因为儿子对别人说父亲已经去世了,演讲募捐煽动情绪的男人,健身器械上的女人,信任永允的药店老板,松贤的情敌(恩彩真是好美啊,超级适合穿衬衫,清冷气质型无敌了),神秘的饭店女主人,她一眼就看破永允和松贤的关系,夜晚打拳的男人,将松贤错认成顺尹的女人。 不铭记历史的民族就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你留在哪儿,哪儿就是你的故乡。 注:UNICEF;尹东柱;群山(地名)。 :)文素丽真的保养得很好啊,自律又优雅的美。韩艺璃身上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太适合这种电影风格了。
5 ) 一只鹅的姿态
我们小时候学的第一首诗是什么来着?是《锄禾》还是《咏鹅》? 如果说电影的前半部分在进行社会批评的话,后半部分就是在自我解嘲。韩日关系里面掺杂着近代历史、现实政治和文化联结,抛开哪一个去作判断都不准确,在一国国内还要再加上各方的立场,就更复杂了。同样的胶片,对着不同的东西拍,就会有不同的事实被记录下来,随之吸引不同的观看者,进而唤起不同的回音,最后导致不同的结果。就像连演歌的起源各方都说法不一那样,历史总是任人装饰的,本来应是幸事一桩的同出一源,被人各取所需后只能天各一方,虽然都不乏举旗拥护者,却苦了只想好好谈恋爱的普通人。 为了在参与公共话题的时候不被当作外人,叙述者的身份(朝鲜族)在前半段被抛弃了,电影甚至专门为此安排了一场戏。但“以什么身份去批评”、“有什么资格去批评”这样的问题不可能被一直回避掉,所以后半段,身份又被捡了回来。作为副作用之一,“外人”这个标签也如期而至,结果就像在咖啡馆和小饭店里那样,尴尬成了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面对尴尬,大义凛然是会被消解掉的,所以就算电影打算回应关于身份的质疑,最后也只能始于被迫而终于自嘲。至于《咏鹅》,因为关乎于记忆,换句话说也就是关乎于自我认同,大概是这自嘲之中最严肃的部分了。 前后两段分别构建了两种人物关系,前一个是追求与被追求的三角循环,后一个则是“外来者”与“自己人”的二元对立。无论是哪一种,无论这些修辞的背后是社会实际还是个体处境,它们都指向现实。就像《咏鹅》一样,精心雕琢的语言之下,其实就是一副客观的景象:一只鹅的姿态。
6 ) 骆宾王遇见尹东柱
既然都是诗人,那就有某种相似之处。中韩文化原本并不隔山越水,张允永的诗人身份,让他身上油然而生某种暧昧的情调,在“姐姐”的调教下逐渐适应了成年。开篇站在路边地图前,两人相互的距离已经给出明确的关系,在接下来的隧道中,让人们领略了《咏鹅》不一样的理解。骆宾王写的是一种静态描写的诗歌,而张律拍出来了电影的感觉。
首先,倒叙的结构给人的印象是,这对男女由密而疏,再从疏到迷的关系变化。从嫂子到姐姐,再到疏远的变化,是一个诗人从理想走到现实的精神蜕变,如果按照时间逻辑,不是流水账就是方言剧,所以,整体结构上的蒙太奇效果,给人一种曲项向天歌的宛然。
其次,巧妙的场面调度。每一次人物出场方式都匠心独运。张父看鹅,保姆从摄影机这边入画,两句台词后张父退场,然后晚上去敲保姆的门,你在外面拽,我在里面拽,儿子忽然发声:要不要帮忙。三个空间连在一起,真妙。房主女儿坐到允永身边的台阶上,然后转到他对面拉起他的手放在自己胸前,被松贤撞破之际,三人的尴尬被日本房主打断,女儿逃去屋内,一个环境中,四个人物不同心境昭然若揭。监视器的设置更是精彩,一个外边冷漠的父亲,望着监视器中门口的来客,伸手想去触摸女人,而当女人依在身边的时候,却说自己很久没有,已经不习惯了。女儿一如乃父,也在监控中偷窥心仪的帅哥,被发现后先躲在屋角,她的视点和观众重合,允永看着监视器,我们和女儿一起看帅哥。帅哥听见响动出门,女儿钻洞子逃回自己房间,帅哥进来发现洞子,探身出去给观众新的环境,这些技巧不是一镜到底这么机械,而是每次都有新设计,每回都能吸引人。而从屋内定镜摄影拍摄张允永在民俗之家四处探寻,形成内视角之余,把23岁少女的怀春之情不动声色地展露无遗。
喝完酒踉跄回去路边,看见学猴戏的表演,互相简单问询,你继续表演,他去远处撒尿,依旧是长镜头,在画内形成蒙太奇效果,这种技法在费里尼《八部半》中多次出现,没想到本片中也能驾轻就熟。
整合松贤聊到要不要见父亲,父亲恰好从右侧入画,俩人的尴尬被父亲的任性发作冲的一干二净,毕竟没几个人会直接对别人说自己父亲死了。也许大家都是对越熟悉的人越陌生,对不相识的人反而更客气。日本房主讲给松贤自己的婚变,女人演出自己的出轨男人,这些锁闭起来的情节,让本来看似平淡的剧情平添几分波澜。女儿的自闭,松贤调教咖啡店漂亮女招待,接着踢摩托也就合乎情理了。
再者,骆宾王的《咏鹅》,题目变成了主角名字的谐音,而诗句中的色彩,分明就是松贤的打扮。白外套,红鞋子,周围环境郁郁葱葱。女人在片中是舒展的,自在闲适的,不过一个人喝酒并不轻松,所以酒馆儿老美人一眼就看穿男女情事,而中年少女这种人设,恐怕国际范围都是海量存在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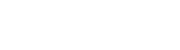




















这幽默感可以的!时间的倒置、身份的错乱和人物情感的错综暧昧。以前执着固定长镜头的张律,这次还贡献出一个超漂亮的幽灵视角调度。
这是真正的野心之作,想把整个东亚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纠葛尽收眼底,然而切入点又是那么小,每个人物的背景并没有很好地融入到角色的性格、生存状态或他们之间的关系中,造成了一定的表达断裂。相比起来还是觉得春梦更佳。尽管如此,张律可能还是这个地区唯一有如此宽阔视野的导演,如果仅从题材上比,洪尚秀实在有些小家子气。
作为一对老爱被人放一块儿比较的导演,张律和洪尚秀的电影都喜欢从人物的“出游”讲起,《咏鹅》在气质上就与洪早期的《江原道之力》非常相像,而类似的出游当然也早在同样是朴海日主演的张律此前的《庆州》里预演,除此之外,容易给人造成联想的还有本片令人熟悉的结构上的小把戏,当然,把上述一系列电影放一起还会发现不少奇妙的共同点,但有一点,和张律此前所有影片一样,除了琐碎稀松的日常,《咏鹅》还出现了大量自觉或不自觉的人与人、人与历史以及民族身份议题,张律的特殊身份让这一系列议题变得有趣但深刻,甚至是独此一家的,如果能够将台词情节一一吃透,你会发现如果一定要做比较的话,张律的作品更具厚重感和焦虑感,也更具解读空间(但往往又难以一言以蔽之),说得更吊诡一些的话,某种程度上张律可能会让不少导演生出一种无言的嫉妒。
1.首尾相衔的两段式(时间上)/三段式(空间上)环形叙事,恰似男主于屋内屋外(画外空间)来回逡巡的运动长镜头般轮回往复。2.故事由中间开始,由中间结束,与片中的男女关系及父子关系一道着力突出了一种悬空的暧昧感。3.以中日朝韩四国的纠葛历史来映衬孤独边缘的个体(以及中日游客),兴许,朝鲜族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与分歧隔阂,终究如时而发作的牙痛般萦回不去。4.张律继续着迷于梦境与镜像,黑白照片中的海中孤岛(亦真亦幻)与其后的梦境及现实诡秘地缀连,一如在牙医诊室旁看窗外夜景的疯狂要求(之后该场景的空镜头与片名同时出现,是为两段分野)。5.以监视器屏幕作为镜子,反照出女性对陌生男性客体的凝视。6.私以为,前半段2男2女的错位角力与暧昧关系比后半段的尴尬日常更为有趣,而男主那段酒后[咏鹅]吟舞则尬出新境界。(8.5/10)
“让我摸一下”,进入民宿房间,短暂沉默后,男人说出了第一句话。几分钟前在饭馆,当她提议要不要找个民宿休息一下,男人还故意提高音量叫她“姐姐”,跟饭馆阿姨解释,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在情欲面前,男人总是这样的,短暂的道德挣扎,便迅速攻势猛烈。前面的犹豫为后面的行为做道德安慰,房间内外,两种气概。
張律式外部者視角的“觀光”電影(第一部分),劇本設定很大程度依據空間。第一個鏡頭裡的遊客朴海日仿佛是剛剛離開“慶州”造訪群山。全片過半才出標題,打破時間順序分為群山和首爾延禧洞兩個時空段落,群山的日本歷史與延禧洞的華僑痕跡,前半如《慶州》般的巡遊,後半則如《春夢》的探訪。唐詩、命理、夢境與寫真,再到更頻繁地被提出的朝鮮族和社會公平問題,張律用“日常”二字對記者們的提問一帶而過言指無意傳達社會訊息。韓藝璃白賢鎮李俊東鄭恩彩的客串好驚喜。‘영아’一語雙關既是小名又是詠鵝。這部看完後,突然似乎想明白了為什麼張老師會離開韓國,好像隱隱感覺到了某種界限。2018BIFF1005C1.
基本上同样是在陌生异域的游走,多半是男男女女的羁绊,大致上都是缓慢的调性,张律偏倾韩国文化圈后,电影中对国家,文化乃至族群杂糅形成的复调相比于洪尚秀始终如一的浪漫旋律平添了更多回味与悠长。本片语焉不详的因果链,打乱的非线性叙事,有意但无意的镜头和历史底蕴更蒸腾出遐想与况味。不敢说张律可与洪尚秀比肩,但绝对被低估和值得称赞。
群山中后部分真的有点拖沓,首尔部分又很絮叨。如果在剪辑上能有更多取舍,可能会是一部杰作。
D+ / 某种程度上和《此房》一样存在着自我折叠的倾向。区别在于这一过程中自我消解的危险可能没有被创作者重视。假如前半段是以影像的空间将文本压抑为暗流,后半段便是溢出的文本让空间支离破碎。观众如朝菌不知晦朔,游历此番盈亏轮回。但回到原点却发觉作者在时间返程中试图叠化的阐释是褶皱甚至断裂的,因而不得不怀疑前往时间“中点”的旅程是否也只是真实的假像。
给章明拍就好了。
4.5 张律也终于迎来了自己随便拣点食材就开始做家常炒饭的阶段…小的巧思需要更有故事性的内在驱动
时间是个伪命题,在同一空间中发生的“过去”和“现在”便摆脱了线性的束缚,张律对空间有着极致的影像体觉,他一直在最简单的表层之上做着最明显的时间把玩儿,然而在这之下,实质是对空间记忆和人物关系的反复拆解重建,在不同的缝隙里将弥漫于其中的丰富人文情感“驱散”出来,溢满整个银幕。乡愁,旧爱,思念,历史,其实都是发生在包绕角色的环境之中,不要试图用时间的流逝来假装和欺骗,曾经的空间化作幽魂,注视着现在正在此地发生的故事,我们对身旁一切的理解都近乎无知和幼稚,唯有被动的遭遇,周而复始。
关于文化的往事和关于政治的现实凝结成同一块琥珀,困住了人物。东亚的性情和历史交织成一层层迷惘,深处的深令我们恐惧,于是处处未知的前半段几乎是恐怖片的拍法。咏鹅是人们试图与阴影对话的声音,因此关于咏鹅的表演是一种从日常情感贯彻到身份思辨的宗教仪式。
【HKAFF】如预期那般,东亚民族关系圈的太极高手张律,绝不会满足于简单的爱情小品。怅然的男女情感,仅仅是厚实文本最上面那一层。群山篇冲洗日韩历史(殖民建筑)记忆胶片,咏鹅篇素描旅韩朝族(示威平权)生存状态,可细嚼的,实在不少。(ps:油麻地奇妙夜小记,加到了张导的微信……)
如何拍历史?历史是凝聚于人体,空间之中?散落在街头演讲,酒后醉言和诗歌当中?还是见于错置的结构?张律的策略有些摇摆。《咏鹅》这首近乎俳句的诗歌,只有能指,没有所指。在这种“空”里面似乎能找到东亚民族共栖的空间。朴海日贡献出了惊人的表演强度。不过他在剧中先天的“沉思者”身份显然是割断了他和他人的联系。
把一个发生在首尔,而后群山,最后首尔的故事,用先群山,再首尔,又群山的顺序来讲述。故事从中间开始,向一头一尾延伸,结构之妙,令人一赞三叹。内容以男女关系为切入,引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父为实,母为虚),历史与当下的关系,乃至在韩朝鲜族人的身份焦虑等多重问题。观影如梦游,若虚若实,恍兮惚兮。
尽管如我这样的华语片忠实簇拥者也不得不承认,电影之中出现的汉语段落影像质感一下子落到网大级别,真得是很一言难尽。其余部分都是极好的。
剧作拉扯得观赏性还算好看,但看的过程里没啥感觉。拿回溯的时间做人物的复杂性,不过由于人物过分庞杂的历史符号特征而没奏效,无法代入、共情。历史凝聚在人身上?当代人最大特征,往往是去历史化的。
6/10。摄影机的圆周运动、禁锢感的房屋构图和声画分离实验,意味着一种时空相遇上的重复(街头民权集会和反赤色份子的父亲,历史问题上的相遇),前半段中允英走入废弃空房的长镜头,镜头没有继续跟进允英而环摇整个房间向前推到窗前,允英才从窗户经过,而后允英站在庭院里往长廊凝视镜头的远景固定机位,这种诡异的视点象征日据时代的幽禁(日式旅馆的监控、老板怀旧地使用胶卷拍照,分别象征韩日身份间的警惕和留韩日本人的怀乡情),阳台上沉默不语的日本女孩象征无法言说的流亡身份,当允英和女孩从岛上返回后,女孩开口是否证明这是一场寻根之旅?允英嘴边常挂流亡日本的诗人尹东柱,醉酒后吟诵咏鹅的杂耍表演指涉他中韩民族身份的错位,群山是亡母故乡,善意款待的饭馆老板娘填补了母亲的位置,告诉允英“心在故乡就在“,化解了身在异乡的困惑。
【釜山电影节展映】此前因为懒并且不太看盗版,一直到现在才看张律作品。身世、家乡、父子、日本、咏鹅诗、朝鲜族、尹东柱等元素,在首尾呼应的倒叙剪辑下,构造出喜感、温暖又有内涵的表达。全场观众笑了很多次。看完方才恍然大悟,回味无穷,不禁莞尔。男女情感部分处理得有种洪尚秀的浓浓喜剧风。醉舞《咏鹅》,是否就是Young-Ah的所指呢?比较遗憾的是,朴海日的那句中文说得再标准一点就好了。(后来吃饭巧遇张律导演,咏鹅和Yong-Ah发音有意为之,解释朴海日是帅哥所以会被女孩奉承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