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珍妮(Anne Teyssèdre 饰)是一名哲学老师,一日在宴会上,她与娜塔莎(Florence Dare 饰)相识,也许是因为寂寞,两个本无交集的人成为了朋友。娜塔莎邀请珍妮到自己家里做客,后者欣然前往。娜塔莎有一个奇怪的家庭,父亲离婚,交往了一个年龄和自己相差无几的漂亮女朋友伊芙(Eloïse Bennett 饰),这一点令娜塔莎无法接受,同时,一条项链的失踪也加深了她与“后妈”的隔阂。珍妮的介入让这个家庭里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娜塔莎的父亲显然对知性的珍妮抱有好感,而娜塔莎也渴望能和喜欢的珍妮组成新的家庭。 对于娜塔莎的热情撮合,珍妮显得有些被动,她坚持听从自己内心的感情,不愿掺和到这个复杂的家庭中去。一次四人的乡村度假中,酝酿已久的矛盾终于激发了,娜塔莎同伊芙发生了争吵,而她吃惊的发现自己一直信任的珍妮居然站在敌人的那一边。她该怎么办?在这个春天里,友谊和爱情能否同时播下可以成长的种子呢?陌陌影视陌陌影视仅此而已2019国家葬礼可接受风险第一季“中国梦·祖国颂”——2020国庆特别节目甜蜜杀机佐藤健的无计划之旅美国人在平壤炮弹飞车2风再起时老男孩2018醉城佳酿年少轻狂顽主1988爱情的剪刀石头布恶途若要君不知百年物语雷霆追击新闻播音员第一季搏击少年盖尔王有点心机又如何塔古特 Thaghut老男孩[电视剧版]堀与宫村真人剧版达格利什海街日记
长篇影评
1 ) 如歌的行板
我不爱看电影,尽管有的电影感染我至深,但总体来说不大喜欢。自己也不懂这是为什么,这几天看侯麦,突然明白了。
大多数电影,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讲尽可能完整、尽可能多的故事,所以它就会很赶,节奏很快。一开篇就忙着介绍人物,埋线,推进情节,据说连几秒钟出一个小高潮都有专门研究。看电影成了一种竞赛,一场考试,要留意的东西太多,看不懂就白看了,看懂了还要分好多层次,有时候看完要特意去看分析文章,才能理清脉络,搞懂情节——我不是说电影拍的不好,而是这种状态让人着急,不能好整以暇,觉得自己被放到一个很低的位置上,不知道,不理解。或者被视为弱智,揉开了掰细了讲,或者被视为天才,一眨眼,轻舟已过万重山——考试总是让人紧张。
侯麦的电影,一个人他走,走,走,走上半天,啥也没遇上。一个人他进了一个房间,拿拿书,翻翻外套,洗个澡。两个人出门溜达,一路上尽讲尽讲,路边野花开着,河水流着。两个人争执,一直把话说得透透的,不去留什么伏笔。镜头给的很足,不慌不忙,不赶时间。我常常想,电影里的镜头很珍贵吧,要留给疯狂、流泪、崩溃、甜蜜,它不给流过泪以后,累的睡着了的人的镜头,也不给崩溃过后,一个人变得空洞的镜头——不疯魔不成戏?但是通过镜头,一个人走过海边和山脊,风景是他眼中的风景,他也是风景里的人,这种相互融合,有一种洒脱的味道在里面。我自己是一个喜欢四处游走的人,看到这些简直跟自己走过一样,心旷神怡。
侯麦他从容,演员也用的从容,歇斯底里的情形非常少,你会觉得演员他可能平常就是这个样子待人,这个样子恋爱,这个样子思考的吧。这几部电影看过来,觉得侯麦他戏剧性一点儿也不少,转折一样让人惊奇,可全没有为戏剧而戏剧、为惊人而做惊人之举的行为,这种节奏真的是太棒了,你看不到把控的痕迹,微风过水,自然成纹。
喜欢他电影里的中年人胜过年轻人。年轻人烦恼很多,而中年人,尽管烦恼更多,可是多少已经跟生活对抗过,顺应也顺应的很好,自我也保有的更完整,就是更笃定的样子。所以活得更直接,也更纯粹些。中年人的对话,非常舒服,跟缎子一样。中年人的相处,更加不互相迁就,反而能真正地有朋友。中年人的皱纹,也无忧无虑自然舒心的样子。一生总得有一个阶段拥有从容吧,像河流从山地流到平原,开阔舒展,两岸风景画轴一样缓缓展开。
他的电影,适合人到中年,忙碌,负重,在难得的闲暇里,拾掇一下自己内心,过一个真正午后的时候,看。
2 ) 【侯麦·四季故事】《春天的故事》:先验与内省
为什么选择首先观看侯麦的作品,其实很简单。相比「新浪潮运动」另几位干将如特吕弗、戈达尔,包括「左岸派」的雷乃等人更加肆意表现反常规的个人风格,侯麦的电影显得相对保守一些,不至于让人看得云里雾里。其次,侯麦有三大成系列的作品(「六个道德故事」系列、「喜剧与箴言」系列以及「四季故事」系列),通过这些影片可以更加系统地认识其风格和理念。
《春天的故事》是「四季故事」系列中的第一部,这一系列成片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时的侯麦已年逾七旬,可以看作是他个人思想与导演造诣臻于顶峰的作品。对于看惯了好莱坞视觉大片的观众来说,《春天的故事》或许会使人觉得缺乏乐趣,但依本人的观影感受,如果当我们舍弃浮躁,真正安下心来细细品味,便会发现侯麦的电影相当醇厚绵长,具有能被反复咀嚼的迷人魅力。
与「新浪潮运动」其他导演一样,侯麦的作品也是典型的作者电影,有着鲜明的个人烙印。侯麦出道于文学教师,也做过《电影手册》的主编,因此从他的电影中可以嗅到浓郁的文学和哲学气息,比如对人物心理和细节的描摹,又如对白的生动睿智,看他的电影便如在阅读一本小说。另一方面,侯麦本人恪守古代隐士般的极简主义生活,追求朴素无为,甚至到了晚年仍然每天坐公交上下班。因而,他的电影亦很好地体现了化繁为简、返璞归真的特征,侯麦对自然和真实的热衷近乎痴迷,低成本+实景+自然光+同期录音便是其电影的全部。于是,在平淡、随性与真实中,我们才能在过滤了所有技术赋予的花哨虚像后,看到侯麦真正想要告诉人们的东西。
《春天的故事》人物关系十分简单,主要角色只有四个。情节线索也一目了然,哲学老师让娜在朋友的聚会上邂逅了年轻的姑娘娜塔莎,并被卷入了对方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庭关系之中。这里面没有完整的人生脉络,也没有高潮迭起的戏剧冲突,取而代之的则是随意撷取的一段生活片段,以及剧中人物微妙的内心想法与情感。
这部电影看似散碎,但侯麦巧妙地运用了人物行为的动机和一些小事件将这段平凡无奇的日常生活串联起来,并指向一个关于「先验」与「内省」的主旨。影片中的让娜和娜塔莎是侯麦为此设立的两个标本:让娜崇尚井井有条的生活,对杂乱无序充满了排斥,并由此形成了理性多于感性的爱情观;而娜塔莎对父亲的女友伊芙有着极深的成见,潜意识中希望用让娜来作为对抗伊芙的工具。在本片的中间部分,让娜和伊芙有一段涉及「先验」的哲学讨论,这段貌似无关宏旨、絮叨琐碎的对话除了蕴藏着思辨和智慧以外,还是侯麦有意设置的点题之笔,悄悄地在观众心里预伏下线索。
到了影片的后半段,那场别墅夜谈以及项链事件的水落石出终于使让娜和娜塔莎得到了「内省」,两个朋友冰释前嫌。尤其是前者,表面上的「内省」是错怪了娜塔莎有意制造机会把她父亲伊戈和自己撮合在一起,而更深层次的「内省」或许连让娜自己也难以意识到,她对爱情也有暂时失去理性的一刻,哪怕只是暂时的。
对于现实中的人或事、甚或自身,无论是用眼睛(以娜塔莎为例)看,还是遵从先验(以让娜为例),我们观察到的可能只是片面的一部分,但本能驱使我们宁愿相信自己的主观判断,于是导致了误会乃至敌视的产生,或者走入迷局,这也便是影片中那么多猜忌误解的缘由(娜塔莎与伊芙、娜塔莎与让娜、让娜与伊戈)。有时候,我们能发现真相及时醒悟,可更多的时候真相会被长久地掩藏,这时就需要人们去反省,去相互理解、相互体谅。
不过,侯麦对此保持着冷静。到了结尾,让娜仍然回到了她并不喜欢的住处(男友脏乱的屋子),只是用一束新鲜的花朵换掉了桌上业已枯萎的花朵。或许这才是侯麦的真正本意,「先验」是必然的,「内省」却是偶然的,就像春天般美好而短暂。四季轮回、循环往复,人们的本性和生活的常态始终难以改变。
3 ) 三个愿望
人生因为一个拙劣的玩笑持续糟糕透顶得不到任何改变,而真的人生里,这种玩笑又何止千万个。
很感意外的是,让娜的丰厚知识似乎起到了作用,不过最终,是让娜的淡定内敛使得她魅力倍增,超过了年轻娇艳的伊芙。
让娜的聪明使得她放弃了一段她不敢确定和许诺的爱情,她捕捉到并且拒绝了于她不能接受的安排和谎言。不能说这样她就失去了什么,她只是没有得到什么而已。她又回到了属于她的单身公寓里,继续她的哲学教师生涯。
我甚至不怀好意地觉得娜塔莎是恋父情结起的作用,从她找的男朋友的年龄看来,从她对年纪相仿的伊芙的敌意看来。她很像是跟别人抢夺父亲给予的爱感。可能是母亲对她的影响,可能是让娜的个人性格,使得她过分重视让娜,并且希望她和父亲走在一起,这样至少让她比较舒服。
在末段听到了娜塔莎的申诉之后,只能把她的真实意图悬置,表面现象不允许观者探测她的欲求,她本来就是一个易变的女孩子。
整个下来,也就是末段让娜和娜塔莎的较量最为精彩,前面的对话,我老觉得散射到了生活的外面,不是很好。
法国的人文教育真是不一般,可见是有深厚传统的,这也就是影片里人物知识来源和沟通方法的基础。我看到了侯麦的影子。
4 ) 春天的苹果花开了
2017.11.26 画面很美,春天的花园和房间都很美。开头女主角去男朋友家,没说一句话,长镜头却把情况都交代了,凌乱的床,扔着没洗的衣服,还有食物残渣的餐桌,书籍乱扔的办公书桌,一切凌乱都是那个男人的秩序,没有人在的公寓她不想停留,甚至会以为她是从分手的男友那里拿走自己的东西。
偶然遇到娜塔沙,然后和娜塔沙的父亲,父亲的女友产生交集。四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会提到哲学,台词量非常密集,偏偏还很难听懂。三个成年人,哲学教师让娜,想做文艺评论家的行政父亲,哲学硕士伊芙,你来我往,说的话都是让人去理解台词会耽误看画面的。
让娜第一次遇到娜塔沙就说,不想破坏别人的秩序,后面他她又提到,她讨厌男友的混乱拥挤,但是她对人的自由秩序空间有着暴虐的克制。对男友甚至没那么爱他,但是她计划着两个人以后要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会结婚。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当娜塔沙的父亲出现,她觉得唐突,她破坏了别人的秩序。
表妹住在自己家也一样,保持着礼貌,心底里又克制,自己不破坏别人的秩序,是不是同样不要别人破坏自己的秩序呢?
电影里出现过5处寓所,每处都有很大的书架,这个真叫人羡慕。
2017.11.27 娜塔沙带让娜去度假小屋的楼上,先给了一个空镜头,在房间里面对准上楼楼梯,这个紫藤花的壁纸就这样让人不能忽视,我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国外的碎花壁纸非常常见,为什么我就注意到了这个壁纸的不同。然后娜塔沙和让娜上楼,说这个壁纸是她妈妈弄的,自己不太满意,想要重新弄,让娜表示其实还挺好看,我也觉得挺好看,但是让娜我不知道是出于礼貌或者说是不破坏他人秩序而回应这样中立。
5 ) 春天的气息催生着暧昧迷离的情感波动
故事很简单,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有的只是丰富的对话和角色细致的心理活动。风格平淡自然,像一部精致的文艺小品。项链作为整个事件的“真相之钥”,很长时间隐藏在幕后,见证着角色之间彼此的猜疑,就连观众也开始怀疑这些角色是否有着什么不单纯的动机。虽然最后项链被找到了,但真相依然像朦胧的春天一样暧昧不清,只是角色之前的所作所为,都难以就此抹去了。 春季篇的项链揭露人间真相,尽管结尾用巧合化解了“阴谋论”一般的剧情,可真相仍十分暧昧;侯麦通过这个故事很细腻的描绘出人们潜意识里的动机和“隐晦的欲望”,却未给出明确的判断和评判。侯麦选择了相对暧昧的方式来演绎这个故事,演员表演也因此扣得很细,真相也藏匿于他们看似自然却又似是而非的表情和行为之中……
6 )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Jeanne一直在跟自己对抗。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闯入者,局外人。她拥有两所公寓的钥匙,可是她却无家可归。她与男友的房子一片狼藉,她自己的房间被表妹与男友所占。她只能接受“纯礼貌性的邀请”去一个陌生的派对,一个人无所事事心不在焉得坐着。她甚至希望拥有“吉斯之戒”,变成隐形人。可是,她遇上这个Natacha把她带回家,而她也差点卷入了他们家的风波中。正如舒曼的“黎明之歌”,Jeanne说,这是写给黑夜的歌,而她自己的内心也正在面临着漫漫的黑夜。
Jeanne是这样一个女人,“我对别人的秩序很敏感,我在这方面很讲究”“我很怕碍着别人的事”“我顾及别人的自由,几乎到偏激,甚至是暴虐”,“对于自己的事反而镇定”……
她对自由、对空间到了Natacha家住了她爸爸的房间/沐浴时碰见Natacha的爸爸/回家却不敢用钥匙开门怕打扰表妹/去Natacha的别墅闯进其爸爸与情人的世界……她跟Natacha说:“我是一个闯入者。”她总是有一个局外人的感觉。对于这个世界。她说:“‘三’封密的空间。”她介入了恋父的NatachaNatacha之父的三角关系,聪明如她,怎么可能将自己卷入其中,于是她及时醒来,她说我不做那个外力因素,我不受外力牵引,是自由意志。
当她解开困扰Natacha家的“项链之谜”时,她掉眼泪了。她说:“我总算有点价值了,我不仅是闯入者,不仅是客人。”因为她也解开了自己的心结。她太在乎自由最后失去了自由。可是此刻她也找到了自由。她愿意学着去爱人,去容忍人。其实,我们自己为自己构建起来的秩序有时候就是一道围栏,别人进不来,我们也不愿出去。最后只能内耗致死。
导演给了马蒂斯那张画三段镜头,加起来将近90秒,纯属偶然。有心人不难发现,这部片里包括女主角貌似漫不经心的拿起的书(康德的理性主义)、所听的音乐(舒曼的“黎明之歌”和“交响练习曲”)、鲜花美景都是别出心裁的。最后打出这幅五彩斑斓的画,有水下的珊瑚、海草、小鱼,还有那各在一方的两个造型优美的主角都向我们诉说着女主角所经历的黑夜休止,黎明到来,终于找到了自己,自己与别人合适的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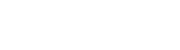




















娜塔莎是水,任性无常柔软,一根失而复得的项链就能使其破涕为笑;让娜是土,理智成熟知性,哲学老师的洞察力和绝不妥协的原则;娜塔莎父亲是风,儒雅睿智风度翩翩,在不同年龄的女人面前都能魅力满满;父亲情人是火,热情冲动火爆,有一种随时剑拔弩张的攻击性。春天在哪里?春天在侯麦的人间喜剧中。
候麦的镜头所对准的永远都是那一群法国知识分子,常看到两三个人就像为了填补配乐的缺失不停说话,却很少有“交流”,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展示。在他们看似闲散惬意的生活,反而上演着难以平息的冲突和波澜,于是,在这些如诗画般美丽的景致中所展开的话题沉重且悲观,揭示着生活的终极无奈。
首尾呼应的鲜花,却是怒放到凋零再到更换而来,恰比项链的失而复得,绕了一圈回归原点,可这弯弯绕绕里,尽是侯麦的心机和转折,于是,原点业已不只是原点。
法国郊外的春天花园,真是美得让人流连沉醉。这是四季中最云淡风轻的一部,一切充满了不确定性,也充满了可塑性,让人回味无穷。在春天乍暖还寒的天气里,感情的触碰、试探、亲近、疏远,就像园子里开花的苹果树,枝头吹过的微风,那样自然而细微,春去了无痕。
春天,春天应该有人告白,有沙发上偶来的倦意,有一次郊游,有友人的离别,有无用的思考。可惜呀,少年只记愁滋味,往时不知春天好。回想已觉浪费了太多,这时就好希望有人开口和我说一句:“其实呀,浪费也是好事一桩。”然后我就能心安理得继续愉快地浪费下去,一直这样惬意下去。
非常厉害的场面调度,大大超越对侯麦的想象:虽然每个人都很话痨,但却并不让人厌烦,其中充满了令人惊奇的视觉引导。男主角的视线始终在犹疑/游移,几乎从来不去直视,这从根本上揭示了他的内心,而三个女性显然都比他直率太多,也可爱太多。四季故事的一大主题是偶然和宿命,但却比伍迪·艾伦和科恩兄弟有趣得多也乐观得多,以至于让人无法停止傻笑。没错,让人想要继续生活下去的傻笑…
两个女孩在party上偶遇,这份偶遇是带点奇迹的,再到邀请去家里住,深夜弹钢琴,对谈如流,这样的开篇是流动的诗,是梦一样的。
春暖花开之时,最适合看侯麦。影片围绕着一场反常而并不复杂的四角关系展开,由谈天闲聊推动情节,以“项链”式的巧合澄清误解,对话中漫溢着微妙暗示与暧昧情感。内敛克制的哲学老师与浪漫狂想的少女,平素感性的人,其实潜藏着理智的一面,看似理性的人,终归亦有受制于情欲之时。侯麦作品中的色彩调配、室内设计与服饰穿搭美得令人叹服。影片里法式中产知识分子的生活世界太使人艳羡了:随处可见书的影子,伴着舒曼的音乐,看看马蒂斯与霍克尼的画作,读读康德、柏拉图和胡塞尔,细细品尝新鲜的番茄,在花草芳菲的庭院中漫步,吮吸春天的味道。PS:对先验/超验/分析与综合判断的餐桌探讨与人物个性隐隐契合,还有对“凡事皆三”的感叹。(8.5/10)
谈话内容比剧情本身精彩,平淡但不让人觉得无聊,舒曼,柏拉图,康德,胡赛尔,现象学,先验论,属于法国的知识分子传统,这是我爱这个国家的原因。数学不好可以拿出来说,但哲学不可以,哲学不好让人觉得没有思考问题的能力。哲学不是改变你的想法,而是拓展它。尊重艺术与思想,让人羡慕极了。
花已开,料峭春寒,坐于室内火炉旁,他和她升腾起一种情感。尺寸很难把握,但侯麦不愧是大师,感觉电影比小说更具视觉美,更有质感。那个春天的花园真是美翻天。好想自己在那里待着,聊聊天,看看书,喝喝茶,晒太阳,闻花香。音乐里有暗潮涌动,虽然结尾那枯萎的花象征了隐秘的感情。短而美。四星半。
喜欢侯麦的电影,不如说是喜欢着一种生活方式。人是自由的,流动的,无序的,随意的。人具有基本的知识情操,可以自由而深入的思考、了解自己的内心、了解自己的由来,对所在的世界感到疑惑而进行寻找、发现、探寻。人是独立的,是自我的,是自我意识的客观存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在现实里找到这样一种生活很难了,生活过于秩序性,人不再关注问询自己,工作时工作,闲暇时也工作或者靠快捷娱乐来缓释工作的疲惫心情。不再关心自己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要去那里,为什么会爱上谁。秩序是如此的理性化,人成了秩序本身。
木心说,越是现象复杂的事物本质越简单。侯麦深以为然,所以他的电影永远是两性之间的组合、拆分和搭配。从康德主义者的眼界看来,人总是期待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事物。两个被这种先验判断所困扰的女孩在绿意盎然的《春季》相遇,一见倾心的二者既是同病相怜却也互为镜像和因果。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明显不能帮助从事哲学教育的女主角作出清醒而深刻的自我剖析与自我批判,因此影片需要不断的对话和思辨。当她与女性相处时,她是作为理性(父亲/男友/老师)存在;当她与男性相处时,她是作为感性(女儿/女友/学生)存在。影片在这种视角不断流转切换的驱动下走到两性辩论的高潮阶段,然而二者都想赢得对方的认同,即永远深陷先验主义的怪圈之中。可见西方哲学探讨的核心总是主客关系的对立统一,难怪木心要说中国文化精神的最高境界是欲辩已忘言。
本片讲述了人均两三套房的法国年轻人,房子轮着住,不痛不痒的小资生活。
侯麦总能给我情感和道德上舒服的中间值,逻辑自洽、故事简单却讲得异常丰富、完全不必害怕冗长,简短又清晰;巴黎公寓房子的挑高真的有电影里这么高吗?“自由总会退化为暴虐”;“我不会刻意给学生推荐作家,我追求先验性”;侯麦在电影中具像化了依赖直觉和信任先验性的女性的生活与交谈,他质疑信任直觉的人常因为先验性对天真和单纯的怀疑——让娜被娜塔莎丢在枫丹白露的小屋里,与她父亲独处,她在本该尴尬的氛围里因为“证实”了自己的直觉而十分自在,镜头对着娜塔莎的父亲,暗示那条丢失的项链就由这个男人戴着,他因为情况复杂而对情人撒谎,变相坐实了让娜的阴谋论。结尾鞋盒里的项链把娜塔莎从让娜的阴谋论中解救,侯麦借由娜塔莎之口说,你不能凭借想象生活、与人交谈,你要真正地信任他人。
侯麦的故事尺度之小,同比其他故事时会觉得几乎无情节,但用敏感的视角去看又觉得充满张力,戏剧性十足。主人公们保持观察自己对外部世界的真实反应,理解自我,行动并反省行动的意义,为之欢欣、低落 。这些过程散落在日常里,显得矫情又有趣。
这个粉白的小女孩,像一条透明线绳一样串起珍珠项链。不论是交谈、争吵还是沉默,我只喜欢有她参与的部分,不理性的,不思辨的,不成熟的,不复杂的,她就是春天本身。
正如片名一般,全片简单朴素却蕴藏各种各样的生机与未知,三个女孩都与片中的父亲有着或清晰明了或不可言说的联系,你来我往的对话之中几人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在被花草围绕着的乡间别墅中明晰起来,配乐和摄影等电影元素都无太多炫技之嫌却仍让人看后感慨于侯麦对简单纯真生活片段超凡的驾驭和解读能力。
特别有魅力的电影,滋味隽永、耐品味。美妙的音乐和配色好像是侯麦标配,不用说了。故事有春天咋临时的暧昧和混沌不明,比如主人公们在人际界限上的试探、探险和防卫。片尾重现的项链恰似迷失而复得的“自己”,但我已不是我,因为毕竟一个新的春天来了。
全片充斥着对白,像那个院子或是找不到的项链,侯麦似乎已经顾不上打理电影里的难以寻觅的视听语言了,仅仅专注于讲一个故事。因此我想借电影的话评价电影:“人们不想打破侯麦的秩序,太费神在其电影的思想上,试图引导自己思考思考本身。”电影井然有序,而我的注意力却混乱不堪;我不断的分神去识别房间里的画册,有戈雅、塞尚、毕加索……我甚至对那只小熊维尼的杯子、还有那扇巨大的拦在路中间的凯旋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电影到底是什么意义,于我已经不重要了、也没必要说了;我只不过是拿着票闯进了这场放映,电影结束我就离开,期待另一部独属于我的“春天的故事”发生。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有钱。一个教Philo的老师在巴黎有两套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