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巴黎热闹的街上,美丽的女子Garance(阿莱缇Arletty饰)先是认识了演员FrédérickLemaître(皮埃尔·布拉瑟PierreBrasseur饰),然后又认识了BaptisteDeburau(让-路易斯·巴劳特Jean-LouisBarrault饰),她还有一个追求者Pierre-FrançoisLacenaire,一个偷东西做些坏事的人。某个夜晚,Baptiste又在酒吧遇见了Garance,他向她表白爱意,Garance也喜欢Baptiste,两人来到Baptiste居住的旅馆。Baptiste希望Garance像他爱她一样爱他,于是离开了她的房间。恰巧Garance的隔壁住着的是Frédérick,两人遂一夜春宵,坠入爱河。Garance也加入了Baptiste和Frédérick的剧团。在一次演出上,一位花花公子,ComteÉdouarddeMontray被Garance的美丽深深吸引。他来到后台像Garance表达了他的爱,但被Garance拒绝。于是Édouard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希望Garance有难的时候可以找他。不久,Garance卷入一宗谋杀案,她只能寻求Édouard的帮助。多年过去了,随着Édouard走遍各地的Garance又回到了巴黎,又遇到了Baptiste、Pierre-François和Frédérick.....陌陌影视陌陌影视暗金丑岛君:完结篇需要浪漫2011暴风眼(1994)血乳交融大人物2011试婚99天扑克脸2022焦点新闻彩虹2015第14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千秋赋幻影追凶2011神偷谍影神奇的犬科家族第一季风骚俏佳人3非理性命运之夜 天之杯Ⅱ:迷失之蝶世上只有爸爸好综艺新时代沼泽王的女儿滴水之恩就算是爸爸,也想做你所不知道的水韵江苏
长篇影评
1 ) 狂欢节的孤独
每天都在舞台上扮演别人的演员,会不会有真正的爱恋?
我不知道,也许《天堂的孩子》知道。
一个是默剧演员,所有的情感都用肢体表达,一个是正剧演员,用长篇的独白来宣泄情感。
他们共同爱上一个女人,一个赢得了她的心灵,一个赢得了她的身体。后者用对前者的嫉妒,完美出演了《奥赛罗》,而前者却被淹没在狂欢节的人群中,再也找不到心爱女人的身影。
戏剧是人类生活在天堂的重现吗?也许吧
那么天堂的孩子还是一样的在爱情的重围中无路可逃。
试问:又有谁能?
2 ) 杂想
相比于看前三部,这一部至少专心看了。这几部电影都似乎有种相似的奇怪感,也许是法国优质电影的某些特征,但是也不知道优质电影究竟是什么。书上说奥尔菲斯的电影形式上精致但并非是优质电影,卡尔内的雾码头是战前的诗意现实主义,而天堂的孩子好像是战时的带有逃避性质的、为战后优质电影铺垫的那种。这些只是标签。再回想雷诺阿战前那两部作品,事实上他们似乎都有着各自独特的某种奇怪的趣味~总体上和好莱坞的古典电影很不一样。我太喜欢大幻影,也许和这题材的独特性相关;游戏规则,伯爵夫人的耳环,包括西尼玛斯科普宽银幕(真不知道中文译名是不是这么写的)的彩色的罗拉蒙特斯,都与上流社会的爱情纠缠相关,都有精致的镜头,各方面的,以及各种复杂的态度;看雾码头时纯粹不在状态,就不谈了;而这部天堂的孩子,它更加包容了,借那第三层看台“天堂”,仿佛将一切世间无论戏中戏外都囊括于眼下。这是一群有着超敏锐又纯粹的观众~是一个寓言。我没看过哑剧,第一段偷盗表演时立马就想到卓别林了,那些动作真像,上一部分他的那些追求和设想也有某种程度暗合。总之这些电影都有着一种共同的特征,即作者的态度很暧昧。但是这部的的确确是爱戏剧的,爱舞台的。(如果迷影可以解释为爱电影的,这就是相类似的。)它似乎并不想把戏与人生做一个像劳拉蒙特斯或者红菱艳那样的比较,或者是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式,这部有观众,有自觉的表演。而且这部电影的故事也如此复杂,真是法国式的爱情故事?并且,就像无数多这类电影共有的,它的结尾,恰到好处,甚至这里的迷思更多~想来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真实从这里学来了不少。最后,就是这位次女主角了,她是奥菲斯里的死神,我真是记得她了。
(补:按照书上所说,优质电影/优质传统在特吕弗的语境下,与上述关系不大。他用编剧以及“场面调度者”来指称这些优质电影,与之相对的则是“作者”,几乎完全的个人控制,不经剧本中介的,纯粹电影的,......个性。46年后的法国主流电影应当有一套成型的模式,特吕弗他们所抨击的大概是这套“稳定”的、趋同的、停滞不前的电影制作模式。问题的核心是“图解剧本”。)
3 ) 失去真的爱,就不会失去真的爱。
多年后,她和他回来,一个人悄悄每晚去看爱着的他演戏,曾经喜欢她的他发现后不忍,告诉他她回来了,在等和他见上一面。一向敬业的他正要登台,在舞台上却发现无心继续无以为继,就这么抛下观众和妻儿奔向她。
那夜,他说:是啊,就像你说的,love is simple。
早晨妻子找来,震惊饮泣哭诉,她对她说,你想走就走想回就回,你走了,有人思念着你,你回来,那份回忆仍然缠绕,这多容易。而我,我和他每日每夜在一起过——和一个人一起生活,是不一样的。
她低低地回答,我也一直都在和他一起生活啊。这些年里,每一个白天每一个夜晚,他一直都在,从未离开——尽管我睡在别人旁边。
说完,她推门离去。
她不死心,揪住他说,我不管你们到底如何,我只想知道,你有没有剩下一点爱给我?够我能继续活下去的那么一点爱?你告诉我,这些年里,你是不是还在一直想着她?甚至在那些夜晚里?
他挣脱开她,夺门而出,只想着要追回她。
此时巴黎的大街上正挤满狂欢节的人群,他举步维艰,眼看离她越来越远。
在无数张忘乎所以的笑脸中间,有两张绝望的面容:只能眼睁睁看着她离去的他,和沉默着离开他的她。
想起木玛一首歌所唱的:
失去真的爱,就不会失去真的爱。
在没有冷气的电影院里,黑白光影之下,我独自还是淌了一脸的泪。
4 ) 《天堂的孩子》片名还是没太懂
诗意现实主义代表 法式浪漫通俗剧/克制的镜头(如吻戏摄影机的横移 Lacenaire枪杀Édouard时给到助手的反应镜头以及掉落的烟斗)/套层结构 戏内戏外的表演和情感的边界也变得模糊 使得剧中人和影中人的角色互文 在奥赛罗那场戏达到顶峰 但在电影层面看 也导致演员的表演过于舞台化 有些僵硬和夸张/喜剧主要体现在Baptiste的哑剧 滑稽剧和Frédérick的表演 悲剧主要体现在难以逾越的阶级差距 无法成全的一对“眷侣”/Garance有四个追求者 她与Frédérick发生关系 与Édouard同床异梦 又曾在失业落魄时与Lacenaire偷盗 心中住着Baptiste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在一起 在道德伦理层面无疑是会被批判的“爱是如此简单”但她始终孑然独立 /属于Garance与Baptiste的夜晚拍得诗情画意(月、雨、烛光、衣袍、吻) 在巴黎狂欢节的街头 被人群湮没的Baptiste试图寻找Garance的身影 开放性结局 留下想象空间
5 ) 台上台下
戏剧舞台的大幕掀开,影片随即开始,这一出戏中戏的开篇方式与随后角色们的戏中戏演出达成了一致。哑剧,戏剧,无声,有声,baptiste(简称B)是优雅的默剧演员,frederick(简称F)是风流的戏剧演员,当他在与Baptiste合作演出哑剧后,他回到后台不断强调要给自己加几句台词,他不是表演哑剧的材料,但他是个伟大的戏剧演员。至此,哑剧与戏剧这两种艺术形式之间巨大的鸿沟被清晰的勾勒出来。无声和有声,不禁让人联想到了默片与有声电影,大量默片演员随着有声电影的出现和流行而失去了演员的工作,这在《日落大道》里已有悲情的展现。而让如今的演员再去出演默片,同样也难以达到当初的效果。影片中有大段大段的舞台表演,舞台之上与舞台之下的界限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感的变化渐渐变得模糊和暧昧,这样如梦的表现形式在当时毫无疑问是极其富有创造力的,同时也给往后的电影创作带去了灵感,比如约翰.卡索维茨的《首演之夜》。
这是一部复古味十足的极具腔调的电影。无论是影片故事所处的19世纪,还是角色们舞台感十足的表演方式,以及经典的爱情通俗剧结构模式,所有元素的组合诞生了这部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电影的集大成者。女主garance(简称G)充满神秘感又时常展露风骚的女人,她与B的相遇方式也很有意思。B在街头舞台上扮演一个一动不动的“怪人”,但他游动的眼神看见了围观群众里发生的一起盗窃案,小偷是追求G的P,但受害者误将G当成了小偷,在众人面前指责她的偷窃行为。而B则在舞台上以哑剧的表演方式还原了事情经过,证明了G的清白。这样浪漫又颇具现实主义的相遇方式奠定了影片的基调。B、P、F、以及后来在戏院里观看表演时爱上了舞台上饰演女神的G而前去化妆间表白的富家花花公子E。四个男人同时追求一个女人,而女人则在四个男人身上获取着不同的生活资源。她爱着B,但她不排斥和F上床,她也能在陷入了P制造的谋杀案泥潭时求助于E,并跟随着M前往印度。影片的上半部分着重刻画了人物的性格和展现了人物的关系。其中最有趣的地方是B在路边与一个乞讨的盲人交谈,随后两人来到酒馆消遣,结果另一个男人拿着手里的金子找到盲人鉴别真假,而盲人此刻瞬间变成了视力一流的鉴定师,论演技,高手在民间........随后G和P来到了酒馆,B立刻上前搭讪朝思暮想的G,并邀请她一起跳舞。而P的同伴则将沉溺于爱情中的B一把推出了酒馆,随后B以表演哑剧的姿态优雅的重新回到酒馆,并一脚将推自己的人踢翻在地,然后和G一起离开了酒馆。
影片下半部分将时间跨越到了多年之后。B以结婚生子,而G从印度回到了巴黎,她无法忘记B,所以前来戏院观看B的表演。得知G回到了巴黎并观看了自己的演出,生活稳定下来的B重新唤起了对爱的痴狂。这看起来是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但对于B妻子和孩子来说,这是生活中最沉重的打击。妻子在家中撞见B和G在一起后,妻子绝望的质问让人动容,可B最后还是丢下妻子跑到拥挤的街道上寻找离开的G。戏剧舞台的大幕落下,人群中无所适从的B是影片最后的画面,这是一个没有传统意义上结局的结局,却也正因此制造出了诗意的效果。有情人不见得能相守,相守的人却往往被有情人伤害。
6 ) 《天堂的孩子》浪漫史
摘要: 《天堂的孩子》是一部经典名片。作为法国人当时所拍过的最昂贵、最群星荟萃的电影,它成为导演马塞尔·卡尔内(Marcel Carné)事业巅峰的标志,为他的战前诗意现实主义宿命论增添了荣耀,并在壮丽的自我展现中印证了想象战胜失落、艺术战胜政治。 作者:达德里·安德鲁(Dudley Andrew) 《天堂的孩子》(Les Enfants du Paradis/Children ofParadise)是一部经典名片。作为法国人当时所拍过的最昂贵、最群星荟萃的电影,它成为导演马塞尔·卡尔内(MarcelCarné)事业巅峰的标志,为他的战前诗意现实主义宿命论增添了荣耀,并在壮丽的自我展现中印证了想象战胜失落、艺术战胜政治。在被希特勒的战火之狱禁锢了四年之后,法国电影又能在国际舞台上接受检阅了,以一部被认为是其“黄金时代”绝响的作品。民族自豪感激荡在该片1945年3月的首映礼上,那是纳粹刚刚被从法国赶走两个月之后。这部电影曾短暂地被分为两集放映,随后被整合成单集的190分钟银幕体验。它在巴黎连续上映了几十年,这座城市正是片中所有悱恻私情的产生之地。它既是一部商业成功之作,又是一部世界艺术电影珍品,多年来在法国最优秀影片的投票中,始终居于接近榜首的位置。甚至几乎历来都不是卡尔内支持者的《电影手册》,也曾将此片列为“有史以来最伟大影片”的第八位(仅位于两部其它法国影片之后:《游戏规则》(TheRules of the Game)和《亚特兰大号》(L’Atalante)。 影片摄制花了两年时间,这一曲对戏剧和激情的史诗般的颂歌,从一开始就旨在成为艺术史意义上的经典。它跟随无忧无虑而又神秘莫测的名妓嘉让丝(阿莱缇主演)穿越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巴黎的街道与阶层,招徕妒火中烧的情人们。影片促使人们去欣赏:对立力量间错综微妙的平衡(女人们、追求者们、社会各阶层、剧院楼上楼下)、场景设置的曼妙比例(从影片壮观的开场横移镜头,到隐匿私密的情爱镜头)、强大演员阵容的难忘语音交响、精妙优美情节的自如展开。第一部分中出现的各个主题无不得到呼应,而且往往在第二部分中发生逆转,例如,悲剧演员弗雷德里克·勒梅特(皮埃尔·布拉瑟扮演)变得嬉皮戏谑,而滑稽默剧演员巴普提斯特(让-路易斯·巴劳特扮演)却变得悲剧化了。剧院的建构令这一切成为可能,一道帷幕将发生在公众场合和台前台后的故事分隔开。从帷幕的一侧走到另一侧,卸下妆或穿上戏服,片中的各个人物便在众目之下转换了他们的角色、或发现自己被暴露——就像嘉让丝和巴普提斯特在演出完《奥赛罗》后在阳台幽会,却被罪恶累累的诗人皮埃尔-弗朗索瓦·拉瑟奈尔(马塞尔·艾让扮演)宿命般的当众“揭”穿两人的私情。而在这样一场我们受邀进入却被帷幕隔开的视觉盛筵当中,我们也始终不会忘记自己的角色。 这样的技法,是对马塞尔·卡尔内固有风格的手法化夸张,这种风格在卡尔内和诗人兼剧作家雅克·普莱维尔(JacquesPrévert)较为含蓄的早期作品中,已被打造得趋于完美,如《雾码头》(1938)和《天色破晓》(1939)。影评家安德烈·巴赞将卡尔内和普莱维尔在1930年代的诗意现实主义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经典”,各种元素间有一种自然的平衡,直接反映出战前社会的种种焦虑。《天堂的孩子》虽然拍摄于被占领下的动荡时期,却有意让时光倒流回十九世纪,通过舍弃即时性,换取了震撼人心的效果。比如马幽(Mayo)所设计的服装完美衬托出“人生如戏”的主题,那巧针灵剪中的自我表现,令每个人物的特点展现无疑。又如亚历山大·特劳纳(AlexandreTrauner)制作的布景,直接来自于卡尔内在巴黎卡纳瓦莱博物馆找到的蚀刻画。至于对白,普莱维尔字字珠玑的措辞用句明显很有份量,被巴劳特、艾让、路易斯·萨鲁、皮埃尔·雷诺阿和玛利亚·卡萨雷等舞台剧大腕朗朗诵出时,常常更像诗歌而不是现实主义的白话(而无与伦比的电影演员让·迦本,则已在《雾码头》中,以含混的嗓音完成了他的大部分独白)。 形形色色的小角色,如那位捡破烂的人和福南布勒剧场的滑稽业主,俨然像杜米埃(Daumier)讽刺画中的形象。这又未尝不可呢?杜米埃正是在1834年观看了真正的弗雷德里克·勒梅特表演马凯尔(Macaire)之后,受启发而创作出著名的若贝尔·马凯尔(RobertMacaire)漫画系列。至于主要角色的造型,卡尔内明确提到:当美到难以言喻的嘉让丝告诉警察,自己在为安格尔先生当裸体模特时,这一场景的构思是以晚期手法主义绘画中的大师作品《大宫女》为原型的。其他人物则像从维克多·雨果(《一个死囚的末日》)、司汤达(《红与黑》)甚至巴尔扎克(《高老头》)时期的浪漫小说的插图中走出来的。总而言之,《天堂的孩子》令我们深深着迷,不仅在于其情节和主题,更在于表现这一切的精妙方式。如同一部宏大的歌剧,影片的悲欢离合由优美抒情的嗓音交织而成,通过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以及由特写镜头推出的咏叹调华丽呈现;而咏叹调的效果之所以得以扩增,是因为它们与摄人心魄的合唱构成了反差。 如此一部豪华巨制,属于当时即将销声匿迹的黄金时代,影评家塞尔吉·达内(SergeDaney)在把《天堂的孩子》与布列松的《布劳涅森林的女人们》(Les dames du Bois deBoulogne)做比较时,就暗示了这一点。几个月后问世的《布劳涅森林的女人们》以其安静的语气宣告,一种现代的电影审美来临了。达内呼应了巴赞的观点,后者是最早指出经典与现代之间的这种对立的。在巴赞看来,卡尔内在三十年代时与法国社会是同步的,但《天堂的孩子》虽令人印象深刻,却显得自我满足,脱离了当时的人们为电影和文化的新生所做的求索。1945年3月,广受欢迎的《巴黎人报》刊登了是年26岁的巴赞为《天堂的孩子们》撰写的影评,这可能是最早一篇关于此片的评论。巴赞不无嫉意地承认:这部看似不需要他的影片,对他有着不可否认的吸引力。“它的轮廓是精到的,那是肯定的,有着罕有的智慧……但影片始终带着冷淡,似乎非常藐视我们已准备好臣服于它。它的主要失误[在于]……只不过是令人钦佩而已。”《天堂的孩子》可能是一个激昂酣畅的奇观,却充分地留了一手,正如那位谜一般的美人嘉让丝,在结尾时离开了她的每一位追求者,特别是巴普提斯特。巴赞想抓住一些终究不存在的东西。他写道:“自相矛盾的是,这幅巨大的壁画,有四、五个命运交织其上,看上去却并不完整。”卡尔内和普莱维尔在三十年代摄制的经典电影(尤其是《天色破晓》)有着紧凑缜密的剧本,通过简洁明了的戏剧化手法取得成功;而《天堂的孩子》则充分利用超乎寻常的长度,在情节叙事的错综复杂之上又叠加了心理深度,刺激着我们对于续集的胃口。“他们是胶片不够了,还是时间不够了?”巴赞问道——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我们很想追随其中几位人物,进入他们之后的历险,了解他们应有的背景故事(有几位肯定不缺背景故事,因为历史上确有其人)。 十三岁的弗朗索瓦·特吕弗肯定读了巴赞的这篇影评,他第一时间就跑去看这部影片。毫无疑问,当他从影院走出来的时候,一定也是意犹未尽、满心渴望更多,因为他在之后两三年中,又跑回去看了八遍。有些人可能认为,他会诋毁这部影片,因为他之后正是以大刀阔斧地讨伐二战期间和其后几年中发展起来的自我骄纵的优质电影而著称的。但是,《天堂的孩子》并未摆弄他所痛恨的玩世不恭和新潮自由价值观,反而大胆地站在雨果、德拉克罗瓦和泰奥菲尔·戈蒂耶时期的浪漫主义人生观一边,也就是波德莱尔在其著名的艺术评论《一八四六年的沙龙》中为之欢呼的时期。作为一个疯狂热爱那个时期的小说的人,特吕弗只会对卡尔内如此不加掩饰地追求浪漫主义的勇气深感钦佩。因此,尽管特吕弗在后来的岁月中无情地刺痛了卡尔内,但他最终向卡尔内承认:他愿倾献自己所有的作品,去换取一次拍出《天堂的孩子》的机会。 没有电影比《天堂的孩子》更直接地重现浪漫通俗剧(romantic melodrama)的手法和氛围了,而浪漫通俗剧正是这部电影的首要参照对象。影片在鼎鼎大名的“罪恶大道”上拉开序幕,在这条大道上,处于鼎盛期的浪漫戏剧如日中天,而我们则跟随嘉让丝,一个接一个地邂逅三名非同寻常的男子,他们令这部影片根植于戏剧和历史之中:名演员弗雷德里克·勒梅特和让·嘉斯帕·杜布拉(艺名:巴普提斯特),以及浸淫黑道的皮埃尔-弗朗索瓦·拉瑟奈尔。历史上的勒梅特,的确是在福南布勒剧场以表演一头狮子开启了演艺事业, 他在巴黎的戏剧舞台上享有盛名,以至于剧作纷纷被改写,以便能用上他的声音。和普莱维尔一样,狂放不羁的勒梅特完全不在乎在演出莎士比亚作品的同时,将取悦大众的通俗情节剧纳入自己的表演剧目。 与勒梅特的外向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无声的默剧演员的内向——而杜布拉则被公认为所有默剧演员中最伟大的一位。这一对元素,正是彼得·布鲁克斯在其影响深远的1976年论著《通俗剧的想象力》(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中所认定的通俗剧的主要对立元素之一。1836年,一场真实生活中的戏剧笼罩了杜布拉的私人生活,他因那个时代最为轰动的一起谋杀案而遭到指控。法庭变成了一个挤得满满当当的剧场,在那里,企盼若渴的公众终于听到了他们所钟爱的默剧演员讲话的声音。波德莱尔曾经以此为题材进行过创作。不过他对片中出现的另一人物——拉瑟奈尔的描写更加有声有色。那位风流成性的花花公子,将勒梅特在舞台上塑造的浮夸而自大的人物奉为榜样,在自己因谋杀案而受审时(与杜布拉的审讯几乎同时进行),妖言惑众地滔滔陈词,宣告自己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他还在狱中写就的浪漫主义诗歌中,津津有味地吹嘘其犯罪行为的无法无天。最终他走上断头台时,也没让蜂拥而来的看客们失望。 《天堂的孩子》毫不屈尊地再现了这样一个浪漫主义的社会环境。法国影史学家马塞尔·奥姆斯(Marcel Oms)写道:“电影艺术最伟大的创造者们——卡尔内理所当然地位于其中——从不对拍摄通俗剧有所犹豫,因为那正是令大众喜爱其艺术的真正精髓所在”。所有表现手法都被调动起来,以增强角色的情感;不同人的生命由一根主线编织到一起,以一种宿命的图案纵横交贯。每个角色、每种道具、每句道白似乎都是种预兆。例如那个捡破烂的杰里科徘徊街头,哭诉着厄运,念经般地诵读他的台词。原始对象通过不断再现和如此富有韵味的名称(月、镜、花),变得纯洁而神圣化。用布鲁克斯的措辞来说,这些对象和词句的“简约与夸张”,体现了一个道德和美学至上的世界,在那里,所有事物都取决于一句话、一件衣袍的色彩、月的阴晴圆缺。 通过多元化故事情节、命中注定的相遇、社会阶层间的冲突、决斗和绝对选择,《天堂的孩子》所力求达到的,正是布鲁克斯说的“[通俗]剧在宏大道德层面的完全表达”,日常生活通过帷幕的分类和一幕幕的拆分,嬗变成为戏剧舞台上的必然世界。奥姆斯写道,正如巴普提斯特在福南布勒剧场中面对观众、面对影院中的我们、面对代表最高艺术欲求的嘉让丝,无声施展着他的魔法,同样的,卡尔内力图“向观众证明,另一个世界就在他们自己的内心,并通过让他们体验来证明”。嘉让丝的第一次出现,是在狂欢节的表演中作为“真理本身”惊艳登场;她一直望着手中的镜子,这让她在目光淫荡的男人们向她狂抛媚眼时依然泰然自若;她的一切全都暴露无遗,除了她的美丽。与其说每个人都梦想占有她的美丽,不如说是都想拥有她那含羞似怯的自制力。但是她只把这个献给巴普提斯特,他和她那样,是众人之中一个毫不造作的静默之声。然而,正是他魅力中的纯真,阻止了两人间鱼水交融的真正实现。巴普提斯特在其生命中所有人物悉数登场的一出滑稽短剧中,演绎了一个爱情落空的寓言。舞台上,他在朝思暮想的月亮女神雕像(嘉让丝扮演)边做着美梦,却没有留意丑角(弗雷德里克扮演)盗走了她。而当洗衣妇(娜塔莉扮演,巴普提斯特未来的妻子)进入时,我们通过镜头特写,和她一同隐约捕捉到了巴普提斯特那真实、而非表演出来的绝望。此时,巴普提斯特并未望着舞台上的娜塔莉,而是看向后台,在后台侧翼,弗雷德里克正与开心的嘉让丝调情,在她耳边亲密私语。 这部滑稽短剧不仅道出了嫉妒的寓意,更呈现出这位默剧演员的失败,因为他唯一在意的观众,已被那个口若悬河的演员所拐走。接下去当弗雷德里克再出现在镜头中时,他的堂皇演技、老于世故以及洪亮的声音,不仅博得了嘉让丝的芳心,而且征服了整个巴黎。他以压倒性的气势,在一部新剧中异想天开地把玩他既定的角色,肆意戏弄剧作家们,迫使他们在观众的掌声之下,不得不接受他对其剧作的公然征服。用影片所描写的时代还没有过时的的弗利德里希·席勒的话来讲:巴普提斯特代表着法国大革命后,情节剧所具有的“天真”而近乎宗教的功能;而与此相对,弗雷德里克则代表戏剧舞台上“多愁善感”的老道;在一个世纪后更新一下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把巴普提斯特看作是无声电影的纯真精神,而风度翩翩、恣意滥情的有声电影,则从它们那里抢走了观众。(据卡尔内的传记作者Edward Baron Turk记载,这部电影的最初灵感,是扮演巴普提斯特的巴劳特看了默剧电影大师卓别林在1940年的《大独裁者》中扮演的、他此生第一个开口说话的角色后萌生的。) 《天堂的孩子》激发着人们去探求其所蕴含的寓意。例如,嘉让丝被解读成象征德占时期纯洁无暇的法兰西之魂。不过撇开所有其他象征意义不谈,嘉让丝首先是“完美观众”的化身:她对默剧演员那催眠术般表演的凝神注视,换得他报以忘情的回望,直到两人一起望月,在那块纯洁而遥远的天屏上投映他们的梦想……而我们则投映自己的梦想。如此这般的痴迷,若没有主演们摄人心魄的演技,就只能停留在空想的层面。若是表演得差劲或仅仅过得去的话,《天堂的孩子》就显得呆板而老派,仅仅是一则有关痴迷的寓言而已。但奇迹般的,它将所要象征的东西表达的淋漓尽致,尤其是让我们体验到默剧演员的登峰造极的才华。James Agee认为,在让-路易斯·巴劳特之前不曾有过一位电影演员,能够真实地去刻画艺术天才。《青楼情孽》(Moulin Rouge,休斯顿导演,1952)中的何塞·费勒(José Ferrer),仿佛只是其所扮演的图卢兹·劳特莱克(Toulouse-Lautrec)的听差;哈里·鲍尔(Harry Baur)在1936年阿贝尔·冈斯执导的贝多芬传记片中,也只是贝多芬的一个荒唐可笑的影子;但是,巴劳特却原汁原味地采用杜布拉在福南布勒剧场震惊观众的同样方式,震惊了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以至于我们不禁在想:当年的观众,会不会更喜欢看巴劳特的表演。 单单巴劳特的表演,就将《天堂的孩子》提升到不朽于所诞生年代的旷世杰作的高度,让影片具有超脱尘世的气息,始终令我们高山仰止。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巴赞觉得它“只不过是令人钦佩而已”。他一定是希望出现这样一部重磅大作的,它虚无缥缈地谈论月亮,却反而和我们地球人更贴近。然而,难道他不早该在第一次看完本片离开影院的那个夜晚,就感受到它的历史关联性吗?毕竟,他步出影院后,进入的正是电影中展现的城市,那里依旧有卖国贼、黑市商贩和抵抗运动游击队员在蹒跚而行。但是他却认为,这部电影承载的诗意现实主义传统——尽管高超——一旦被带入到战后的文化运动中,其风格就不再自然。事实上,卡尔内的战前作品可谓是举起镜子去照当时的年代,而《天堂的孩子》则如同那位迷人的女主人公,举起镜子对着自己,一览无遗地欣赏着自身风格的真相。 《天堂的孩子》是一部“优质”电影,它的伟大从未被质疑过,即使在“法国电影新浪潮”巅峰时期也没有过,而那场青年运动正是要涤荡掉卡尔内之类的挑剔大师的。而后,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法国电影的剧本创作和制作设计出现了回归专业主义的潮流。“视觉系电影”(cinéma du look)标志着新一轮手法主义的兴起,由此诞生的一批电影,与卡尔内和普莱维尔的感性遥相呼应,其中包括让-雅克·贝奈克斯(Jean-Jacques Beineix)的《明月照沟渠》(The Moon in the Gutter)、吕克·贝松(Luc Besson)的《地铁》(Subway, 由特劳纳担任美术设计)、让-皮埃尔·热内(Jean-Pierre Jeunet)《黑店狂想曲》(Delicatessen)和《天使爱美丽》(Amélie)。 令《天堂的孩子》在二十一世纪重获瞩目的,不仅仅是它的华丽风格。这部影片的长度曾经令人望而生畏,如今却与变化中的标准两相谐调。早在“法国电影新浪潮”时期,《宾虚》和《日瓦戈医生》这样的好莱坞史诗片,就彰显了电影在长度和视觉比例上,有着电视无法企及的优势。而《教父》的问世,标志着一部宏大的小说可以分成两部甚至三部电影,每一部的时长在三小时左右。从《根》开始,电视凭借一大批剧本一流的迷你剧集发起了反击。如今,不少观众会选择在一个周末之内,一口气看完一部剧集的一整季,的确,影迷们也定会以同样方式,在大银幕上连续观看任何一次路易·费雅德(Louis Feuillade)系列默片的重映,例如《吸血鬼》(Les vampires)的连放要超过九小时。《天堂的孩子》激起了我们对内容恢弘到难以轻易消化的电影的强烈兴趣。要知道,卡尔内和普莱维尔都曾经崇拜费雅德,巴赞也一样,他相信电影的叙事能力能让中世纪的古老故事或浪漫传奇重新焕发活力。因此,当巴赞渴望通过续集来追随《天堂的孩子》中那些精彩人物的前世今生的话,他所渴望的首先是小说。《天堂的孩子》可能并非派生自任何一部可经辨析的文学原著,但观看这部影片的感觉,就像忘情于一部鸿篇巨著之中,其人物居住在一个超自然的绝对道德世界,相比之下,日常生活显得苍白无趣。难怪特吕弗要一次又一次地去观看这部电影。也难怪无论在哪种意义上,它始终是一部超越时代的永恒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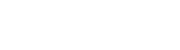




















我算是明白为什么会有新浪潮了,因为有人在古典的方向上已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原来是关于男欢女爱的鸿篇巨制,穿插了杂耍、哑剧(Baptiste第一次亮相)和戏剧(电影第二幕)的舞台春秋,台前幕后的设定,打破了距离,也增强了观看者的妙趣。对暴力凶杀犯罪之类的表现,大多使用屏障手法,制造心理反差。结尾陷入拥挤的狂欢人群更像一个开放结局,他们都变成了输家。
不要回想往事,它们会像疯狗一样,冲向你的喉咙。 你爱我吗?不,不要回答。我不会索求任何东西,你在这里,这就是所有的一切。 不,我不索求什么。只要可以感觉到你身体的温暖,你的嘴唇,你的眼睛。
#SIFF2014#重看加分;世间众生相,人间悲喜剧,巴黎清明上河图,三六九等浮世绘;爱情有甜蜜伟大,也有嫉妒卑贱;人性有丑陋黑暗,也有高贵善良;感谢卡尔内为古典与诗意写上圆满注脚,完美融合戏剧、哑剧,雅而不俗,笑中含泪;运动长镜美妙,群戏调度精彩;献给猫一样的小丑。
的确是明白了为什么会有新浪潮,因为优质电影中的价值观爱情观真的不能再代表新一代的年轻人。台词很美,摄影佳,间接表现各种血腥场面的处理挺有意思。但真的并不为其中的爱情感动,最后的别离并未让我唏嘘,反倒是觉得巴蒂斯特缺乏责任感得很。相比之下还是更喜欢前半部的古典味道,后半部有些闹剧了
巴黎爱情故事,四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男人与女人的对话:“一直至今,我受不了蠢货的骚扰,我孑然一身,但是这样的命运又有什么不好呢?既不爱人,也不为人所爱,连你也不爱。我只要自由。”“我也不爱你。”“那再好不过了。”男人与女人的对话:“我因快乐而颤抖,因为你在我身边,我爱你。你爱我吗?”“你说起话来像个小孩。这只适合出现在书中或者梦里。”“梦...梦就和现实一样!”男人与女人的对话:“你不害怕孤枕独眠吗?”“今天日出很早。”“如果它起得比我们早,我们就关上窗户,而你,你现在的门还锁着吗?”男人与女人的对话:“男人通常不会对美人交付真心。他们只是想占有。而我不同。”“是吗?” 女人爱上了其中一个男人,可是直到最后,我觉得在她脑海里,偶尔还是会浮现出某句她说过的话:要是世上存在无需开口的爱情该有多好。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戳到了本专业G点的片子同看的人又是师姐很容易想象看完后在那里叽里呱啦一堆卢梭到狄德罗到布莱希特。但是最好的地方还是在于,如此如此多面的法国,既浮夸又优雅,既造作又真挚,套用管风琴的话,人能这么锲而不舍地轻佻,骨子里一定有哀世伤生的肃穆在支撑。和大江说漫才一样,滑稽与心酸一线之隔。
3个多小时,一部同样和乱世佳人分为上下部,有着复杂人物关系及剧情的黑白巨作。虽然厅不大,但是百分百上座率,排队场面好比看Skyfall,还有一家4口大人小孩的一起来看一部40年代的黑白片,这种状况不知是不是法国才有。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3NDc3NzEy.html
剧本为主。各式男人,一个小丑。各式女人,一个绝代。人生如戏,戏不如人生。戏与现实,梦与惊醒,真实与虚假,电影与戏剧。结尾这样安排是因为导演没法下个决心么?
美不美我不好评价,但是这部片子的伦理内容太多,戏剧化内容太多,属于电影的部分太少。四个男人为了各自的理由而爱着同一个女人,于是这个女人被物质利益和虚荣所满足,然后回头寻找所谓丢失了的爱情,随便应付他们而逢场作戏,她的嘴角时刻挂有轻佻的笑。能让人动容的只有这些人物在多年后的重逢,可惜他们还是一样,并没有放下对于彼此的执念,一个男人抛妻弃子,一个男人因之而死,只剩下最后所有人都被淹没在狂欢的游行中。
戏子有情,婊子有义。有种精巧的平衡感。前半段充满灵气,后半段沉重下来以后我就有点儿走神儿了,一种可能是我没到理解这种感情的年纪,另一种可能就是这不是我的感情。戏剧和电影如果不离婚,做情人也挺好的嘛。古典电影是“表面的艺术”,大概类似于文学里的巴尔扎克,作为经历过现代主义洗礼的现代人,得重新看待这里发生的一切。
一个女人和四个男人浮夸的多角恋爱故事。作为法国史上最伟大的影片之一多少感觉有些过誉了。上集4星半,下集3星。
唯有法国文学和戏剧底蕴才能催生出这样的电影。这样的手笔,这样的故事,写成书就是名著,拍成电影就是巨作,如同古希腊雕塑般的不会退色的完美。Jacques Prévert的台词诠释浪漫多情,Garance的气质和人设描绘高冷聪慧与独立,Baptiste负责表现这民族骨子里的决绝和疯狂。真的太法国了。
马塞尔·卡内代表作,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经典。影片时长3小时多,摄制于纳粹占领时期,讲述了1830年代巴黎剧院的一段多角恋爱故事。片中华丽生动的林荫大道是法国影史最宏大布景。滑稽剧、哑剧与戏剧穿插其间,戏中戏、打破第四堵墙的互动、演员和角色的对位都令人难忘。狂欢节开放式结尾。(9.0/10)
prevert的台词过于戏剧化,尤其是男女互相勾引的那些所谓的诗语言,月亮是我家巴黎太小之类的,舞台人生人生舞台的混淆 两女四男的纠结 哑剧 自杀绳子用来跳绳晾衣服。。剧情可谓十足的无聊以爱的名义无视道德践踏人性,和维果雷诺阿的片子比比吧,没看出半点诗意现实主义来充斥着戏剧化的虚情做作
从第一分钟巴黎闹市街景的横移镜头开始,就彰显着超越时代的历史画卷感。黄金时代末期的伟大通俗剧,聚焦在1830年代的剧院,戏中戏的模式产生多艺的互文性,而每一次戏中演出又都起到推进剧情的作用,无一闲笔。非凡的演技,华丽的舞美,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足可以成为巴黎城市的名片。
奇艺网你是不是病了啊?你买上集不买下集,你还要不要人活啊?继“偷自行车的人”我的另一个超级最爱电影,我完蛋了。。。。我他妈的怎么对古典的东西这么有激情?
精彩!每位主要演员都有戏!特别是Barrault的默剧!最喜欢的台词:You saved me from growing old, dull and used-up. 正中红心。1945年的片子竟然拍出了浸入式戏剧的感觉,特别过瘾,连看上下两部。可能随后还会再看几遍细细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