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A seemingly happy Swedish housewife and mother begins an adulterous affair with a foreign archaeologist who is working near her home. But he is an emotionally scarred man, a Jewish survivor from a concentration camp who found refuge in the U.S.,and, consequently, their relationship will be painfully difficult.陌陌影视陌陌影视变种动物园电影配乐传奇红心的杰克秘密的校园一个美国女孩的故事-玛莉琳1955:非凡的圣诞节乡间趣事家和万事兴之双喜临门超级富豪异乡人小公主胡桃夹子和四个王国纹身2013夺宝幸运星第一季小马王蛇犬大英雄谜证2007机械手臂热血高速鬼作秀 第四季特别突击队(国语版)日瓦戈医生生死96小时第二次二十岁2015怨灵人偶聚客镇黑天鹅湖第85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洁西卡 柯森 有事找我
长篇影评
1 ) 笔记(2023.4.5)
随手写。看上去是洪常秀拍了一部村上春树写剧本的《回转企鹅罐》,同时加入了大量先锋即兴戏剧(🤯😍)和林奇元素……特别喜欢这个梦幻组合。从第五集开始——就像《罐》中从第十二集开始世界(男权)秩序的逻辑和连续性逐步崩塌瓦解,这种二部结构、以及结尾部分与前文在质地上被强调的差异,都是很有番剧性的特征——声音首先开始从秩序中抽离(排练时的海浪声,后来某些场景中环境音效频繁的消失),接着是人物(Quentin意义不明的出走行为),最后是图像本身:到最后一集,整个影像都几乎成为了某种降神会的器具。一个小例子:对着镜子的那段镜头多么像是直接来自于在镜中直视我们的Sarah自己的视角,这个怪异的摄影把戏因为间或插入的短暂黑屏——仿佛Sarah在眨眼,因为画面中的她从来不闭上眼睛——而更加逼真;然而接着几分钟后摄像机缓缓离开镜子,转向床上的Émilie,于是我们有了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仿佛在我们和电影*之间*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出现了某种投影的差错,在原来坚固的事物周围产生了幽灵。也许可以说,里维特所痴迷并在作品中不断追求的就是这样的幽灵,事物在意义的边界和转角处投下的阴影,图像侧面的隐蔽空间中闪光留下的残像。当然,里维特作品的问题也通常出在这里;那些像凝结核般悄悄聚集着所有晶体的非理性点——我想到了Frédérique拿着枪喊的最后一声“转过来!”,还有Colin的口琴——很容易变得虚弱,就像几年后的《决斗》中那样;事实上,人们很容易会得出结论,认为里维特是影视界的故弄玄虚之王。大概这也是对的。但是除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注意到——套用日本传统能剧理论中的术语——还有“花”(hana)存在于此,它是这样的一种美好,在穷尽了一切技巧和可能性之后仍然长存,就像花朵的样子总是永恒不变,但无论来自哪里的人们也都会一再停下欣赏,直到永远。它存在于所有漫长镜头的角落,所有细节微小的游戏性和物质性中。里维特给予了这些人物细节一种舒展的地位,几乎可以称为民主:属于一切物的民主;尽管,这种民主在最后并不能取得胜利,而是被忧郁——时代的忧郁,时间精灵(《赛琳与朱莉出航记》?)的忧郁——所击碎,余下只是自由的幻影。 A-(纯属个人偏好)
2 ) 关于《出局》的随堂笔记和碎念
E1
大段落歇斯底里的临场编排;即兴演绎与进入捕捉;参与释放与调和控制;侵入性的排演intro(二元),偏执、游离和独处。
E2
文本围读;关于“十三”的谜面初现;排练剪接和“跳出肉体的灵魂视点”;令人几近昏睡的车厢对白(想起I’m Thinking of Ending Things的冰冷触感)。
E3
体验渐入佳境;The Deaf & Dumb开口说话;更丰富而明媚的外景,喜剧和暴力的刺激元素。
E4
角色关系和时空开始产生联结;“十三人组织”浮出水面;新成员的注入却为为剧团带来疏离感;弗雷德里克的狩猎触及到地下组织的丝网。
E5
两则别致的屋顶对谈,女人识破女人的伎俩; 柯林对宝琳的欲动,宝琳却因伊戈尔的旧信勾走心思;大起却又随即大落的七将剧团,突破瓶颈的普罗米修斯(或应以体悟舞台剧的方式去理解肢体与嘶吼);自然的触发明显优先于逻辑的框定。
E6
巴黎切割,城景游戏,被察觉的记录者角色;分裂的七将剧团,莉莉向海湾逃离,昆廷开始无主无尽的徘徊;街角咖啡店里随心所欲的哲学探讨,收纳消逝时光的酒杯和烟灰缸;托马斯的浓情流露和亲密相拥;关于皮埃尔的传奇,普罗米修斯被点燃,柯林以“神秘暗喻带”闯入地下纽带,又带着被回绝的无尽思念重新上路,一个人成为一支队伍。(个人最爱之章节)
E7
教科书式、实验性的即兴表演迎来爆发,所剥离出的“局外人”视点在被强调;鲜血与尖刃,爱情与谎言,“红皇后”的“高塔”与“白国王”的“宝藏”;普罗米修斯被肢解,“十三人”组织同样历经着分裂重组;柯林会前往终点拯救“公主”吗?(为什么他们说着加密语言?)谁又将在终章迎来“出局”?
E8
旅途的终点,情绪的高点;艾米丽于房间中超现实化镜式自省的处理堪称全片表现力的峰值;托马斯以普罗米修斯的姿态独自倒在沙滩上在夕阳下迎接落幕,昆廷和玛丽沦落成大都市的拼图;露茜同沃克探讨理想化神秘组织的幽灵,留下精英式的企盼和旁观;柯林在不得“入局”后重归“聋哑”的虚无,弗雷德里克则“情不自禁”地探向命运深渊;导者(作者)兴许为掌控着一切的皮埃尔,那么缺位的观者或即从未露面的伊戈尔?

3 ) 写不下的短评:关于《出局》的真实与虚假
没想写什么长篇分析,只是实在写不下了放这里,就当看短评。
电影是四条故事线,两条戏剧团线(其中一个剧团和一个叫13的神秘组织有关)和两条追查神秘组织的单人“侦探”线。最后四条线交织在一起全部走向理想的破灭与虚无。
电影视听最大的亮点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人感到「真实」(当然也不一定,我后面会细说,先说完这个思路)。具体技法包括:①粗糙影像。这个没什么好说的;②极其缓慢的电影节奏与独立发展、缓慢汇合的subplot。四条线一开始各自独立发展而且每条线发展到一半就切来切去,而且一条线切走后往往这条线后面的发展不会过多交代。这使得观众一开始无法搞清楚到底在发生什么。电影两小时后故事线才开始交汇,四五个小时后观众才逐渐感受到故事主线。电影之所以搞这么散这么去戏剧化/冗长,是为了既能制造真实感(通过冗长/去戏剧化的节奏)又能制造悬疑/神秘感(通过很散的subplot和subplot之间关联性的缓慢升高);③两个戏剧团编排戏剧时里维特大量使用推拉等长镜头。长镜头与「真实感」的关系,无需多言;④大量即兴表演以及捕捉街头群众反应,比如那段很有名的Colin在街上不断大喊、两个小孩跟着他,就是完全的即兴表演+捕捉街头群众反应。这类做法当然也是为了增加真实感,毕竟这些演员“自己演自己所想”会比别人人工给他们设计怎么表演来的更自然,而且直接捕捉街头群众反应比群众演员来的更真实更少人工设计感;⑤画面内看到摄影机和录音师、镜头出现裂纹、倒放声音、死时的假血等“穿帮”也是为了让电影显得更真实。
个人认为的问题:
1、要么节奏全程冗长式,要么全程紧凑式,电影却是前面冗长后面相对紧凑,甚至越来越紧凑,节奏有断层;
2、电影故事是假的,所以里维特的那些“穿帮”设计更像是揭示了故事本身的虚假与人为设计,而不是通过揭示真相反映了真实感,而这种「虚假与人为设计」的揭示与电影其他视听技法试图营造的「真实感」多少有些违和。
当然,也许还有另一种思路,那就是整部电影并不是为了渲染「真实」,而是为了渲染某种「虚实相交的奇幻魔力」,或者说是「神秘感」(「虚实相交的奇幻魔力」只是这种神秘感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上面很多视听因素的目的都可以重新解释:缓慢汇合的subplot是《朱莉与塞琳出航记》那种去目标化叙事的变体,但目的殊途同归皆指向的是「神秘感」,即兴表演也是指向的这种神秘感;那些戏剧团编排戏剧的片段也是营造了这种虚(戏剧)实(电影故事)相交的魔幻气氛;粗糙影像则也类似在《朱莉与塞琳出航记》中那样通过与“虚假”片段(戏剧编排片段、“穿帮”片段)的并置营造介于真与假之间的神秘魔力。
然而问题是,这些“穿帮”片段的出现实际上直接宣布了所有电影故事都是假的,甚至直接否定了粗糙影像的纪实质感(因为粗糙影像也因为“穿帮”而被揭露了是假的、具有人工性的)。因此,一旦任何一个“穿帮”片段出现,观众就会意识到接下来的电影故事(以及在重刷时全篇的电影故事)的虚假性,这就导致之后所有的非“穿帮”片段(包括戏中戏片段——这在观感上直接变成了假与假相交,而非真与假)都丧失了虚实相交的魔力,变成了观感上从头假到尾的一个个段落。
4 ) 评论翻译 | 《出局》及其替身

作者:Jonathan Rosenbaum 翻译:Annihilator 原文地址://jonathanrosenbaum.net/2021/08/out-1-and-its-double/
本文是为Carlotta发行的《出局》蓝光碟套装而写,并在他们的允许下在网站上转载。—— J.R.
全文约11000字 阅读需要28分钟
[奥尼特·科尔曼(Ornette Coleman)的自由爵士乐]在听第一遍时会引起耳朵疼痛,特别是对那些刚接触科尔曼音乐的人来说。第二遍时,它的刺耳减少了,其复杂的平衡和制衡开始发挥作用。第三遍时,一层又一层令人愉悦的配置——节奏、旋律、对位、调性——变得可见。第四遍或第五遍听时,人们轻松地徜徉其中,深入十英尺,像呼吸空气一样呼吸音乐。
—— 惠特尼·巴利特,摘自《早晨的恐龙》中的《抽象》一文
如果说得了多疑症还有什么安慰的话(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是宗教上的安慰),那就是反多疑症的存在:一切事物间都没有联系。这种病症恐怕也没多少人能够忍耐很久。
—— 托马斯·品钦,摘自《万有引力之虹》
1970年春天,雅克·里维特(Jacques Rivette)和超过三十名演员用16毫米胶片拍摄了约30个小时的即兴表演。从这些大量的、极其开放的材料中诞生了两部电影,二者都试图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的观影体验。《出局》(Out 1),长达12小时40分钟,为八集连续剧结构,最初的副标题是“禁止接触(Noli me tangere)”,它为法国电视台设计但被其拒绝播放,只以工作样片的形式公开放映过一次(1971年9月9日至10日在勒阿弗尔)。17年半后,在1989年2月的鹿特丹电影节上,一个经过某种重新剪辑但接近完成的拷贝为包括我在内的少量观众放映了数天,然后在90年代初,一个显然经过里维特进一步重新剪辑(包括删除最后一集中让-皮埃尔·利奥德(Jean-Pierre Léaud)的长镜头)的版本在一些电影节以及法国和德国电视台上放映,而这个版本,据我所知,就是此处呈现的版本。

我记得,1989年在鹿特丹,愿意完整看完这部剧集的观众不超过五个,甚至连试看的观众都很少。但潮流变化的迷惑之处就在于,当纽约皇后区的移动影像博物馆在2006年底的一个周末放映这部剧集时,门票早早就被抢购一空,整个活动被重新安排在次年3月,以满足其他想看的人。(在本例中,丹尼斯·林(Dennis Lim)在《纽约时报》周日版上发表的一篇赞赏文章显然起到了作用。)
《出局:幽灵》(Out 1:Spectre)是里维特用了大半年时间从第一部电影中剪辑而成的——时长为255分钟,大约是前者的三分之一,并设置了中场休息(正如里维特的前作,1968年252分钟的《疯狂的爱情》(L’amour fou))。这部电影于1974年初在巴黎上映,而据我所知,其版本与本次发行的版本相同。

Ⅰ
里维特在拍摄这两部电影的素材时所依据的组织原则是来源于巴尔扎克《十三人的故事》(Histoire des treize)中的关于一次阴谋的奇想。在小说中,十三个位居法国不同社会领域的个体组建了一个秘密联盟以巩固他们的权力。在有意着手批判自己的第一部长片《巴黎属于我们》(Paris Nous Appartient)中的阴谋主义时代精神的同时,里维特也用这个原则来安排他的演员之间的会面和对抗,每个演员都被邀请来根据整个阴谋创造和即兴表演自己的角色。作为准备而进行的唯一编剧工作来自里维特的联合导演苏珊·席夫曼(Suzanne Schiffman),她帮助准备和编写了不同人物的相遇,而里维特自己写了三条不同的加密信息,这些信息被其中一个人物截获,暗示着阴谋和“十三人”的存在。

矛盾的是,如果观众可以经受得住戏剧排练部分的相对乏味,那么《出局》可能是里维特所有作品中最易于接近、最娱乐性的,也许除了《赛琳朱莉出航记》(Céline at Julie vont en bateau)之外。它与《幽灵》截然不同,后者可能是里维特最艰深的电影。(可以说,这三部电影展示了里维特最有创意和趣味性的色彩运用)。但是,由于它最初被法国国家电视台拒绝播出并且后来一直没有观看途径,它的名声具有很强的传奇色彩,人们对其所谓的艰深程度的看法由于剧集的总体长度(很少有观众会考虑将这个标准应用于其他电视剧和迷你剧,尤其是那些英语剧集)而被夸大了。在意大利电视台的盗录版本出现在互联网上、并由业余爱好者提供了英文字幕后,英国评论家布拉德·史蒂文斯(Brad Stevens)在《录像猎犬》(Video Watchdog)杂志上写道:“电影的至高杰作之一无法为英美观众所欣赏无疑证明了其仍被广泛认为是二流艺术;如果在文学方面设想一个类似的情况,那就是我们只能通过偷偷传阅的影印本来阅读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英译本。然而,当我们发现《出局》这部聚焦于阴谋的作品最终却因为一次互联网‘阴谋’方才得以广泛流传时,我们很难不露出一丝讽刺的微笑。”

值得注意的是,多次观看《出局》和《幽灵》有助于弄清楚的不是它们的“情节”,而是它们形式层面的不同构造。然而,前文提到的里维特和科尔曼之间的类比更关于表演层面的概念。就像科尔曼和其他七名音乐家大胆尝试的38分钟集体即兴表演一样,《出局》的表面是由风格迥异的“演奏”之间的调和、组合和冲突所决定的。这些韵律涵盖了全部音域:从让-皮埃尔·利奥德[科林Colin]和朱丽叶·贝尔托(Juliet Berto)[弗蕾德丽克Frédérique]的纯电影化技艺到弗兰西丝·法比安(Françoise Fabian)[露西Lucie]的舞台式方法;从迈克尔·朗斯代尔(Michel Lonsdale)[托马斯Thomas]和米歇尔·莫雷蒂(Michele Moretti)[莉莉Lili]的相对紧张到雅克·多尼奥-瓦克罗兹(Jacques Doniol-Valcroze)[艾蒂安Etienne]和让·布伊兹(Jean Boise)[瓦罗克Warok]的相对平静;从布鲁·欧吉尔(Bulle Ogier)[宝琳Pauline/艾米丽Emilie]的缄默到贝纳德特·拉封(Bernadette Lafont)[莎拉Sarah]的健谈。最激进的当属这一假设:演员所做的“一切”都是有趣的——它有效地从前提上废除了对表演的是“好”是“坏”的传统区分,后者总是基于某种关于现实的固定概念。

对于科尔曼和里维特来说,主题材料(thematic material)被降低至最小限度,并主要用作一种权宜之计——一个推动每个独奏者进入自己的“陈述”、并引起其他人的回应的发射台。除了科尔曼编写的简短合奏段落外,自由爵士的背后没有作曲家,因此也没有作曲;科尔曼作为领导者的主要作用是集合乐手,并为他们的即兴演奏建立一个出发点。
里维特在两个版本的《出局》中发挥的作用与前者相似,但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即他事后剪辑和重新安排了素材,组装了镜头以及演员。而这种组装是一种反对情节连贯性(continuity)概念的组装:持续的意义,这一电影作者的领域,被故意地隐瞒——对观众如此,对演员也是如此。因此,在两个版本的《出局》中,“十三人”始终是一个虚构的妄想,其实质从未被揭露。最终,很明显,这个阴谋只是一个从未实现的白日梦,是十三个人讨论过的、但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想法。某些角色(主要是托马斯和露西)努力隐藏其真实的或假设的存在,其他人(科林,弗蕾德丽克,宝琳/艾米丽)则试图或威胁要“揭发”它,除此之外,“十三人”从未呈现为一个可辨的形体——无论是在对白上还是在影像上。

这两部电影的开场都假装同时向我们讲述四个不同故事,尽管第一版也即长版本的开场也许可以被更准确地描述为:四块不同的纪录片素材交替出现,彼此之间没有叙事上的联系。我们看到两个剧团在排练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戏剧作品——《七将攻忒拜》(Seven Against Thebes)(由莉莉执导)和《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由托马斯执导),同时还注意到了科林和弗蕾德丽克——两个相当疯狂而充满好奇的孤独者,他们都设法从咖啡馆的陌生人身上索取钱款(科林发放卡片宣称自己是个聋哑人,在某人犹豫是否给他钱时激烈而不着调地吹奏口琴;而弗蕾德丽克,除了与其同性恋朋友米歇尔 [由她当时的同性恋丈夫米歇尔·贝尔托(Michel Berto)扮演] 一起玩之外,她通常会开始和别人调情并/或编造有关她的身份和背景的故事)。

在《幽灵》的前三十几个镜头中——其中十个是带有电子嗡嗡声的黑白照片——里维特在这四个自主的部分之间剪辑,没有建立任何情节联系。唯一建立的联系是偶现的形式上的重复:一个场景被后续的一个静止画面所再现,科林和弗蕾德丽克房间内不同镜头中的两次摇镜。即使在每个部分之内,许多镜头也都“过长”或“过短”以至于无法被传统地视为具有叙事性。里维特经常在一句对白或一个动作的中途进行剪辑,而且缺少的部分并不总是被补全。相反地,科林的门房提醒他留下钥匙的一个镜头毫无关联地结束于她从镜头前走开并坐在桌前写字。正如分割了电影之后部分的那些神秘静态画面一样,此类突然的转向提出了——但从未实质上证明——另一个与之互补的虚构叙事的存在。


接着几乎是奇迹般地,《幽灵》进行到13分钟35秒——剧集的第二集进行到35分钟28秒(或整部剧集进行到超过两个小时)——四段“情节”中的两个被联系在了一起:莉莉的剧团的成员玛丽(埃尔米娜·卡拉戈厄(Hermine Karagheuz)饰)突然递给科林一张纸条。纸条上面写着一个似乎被加密的信息,科林开始着手解密这一信息、连同接下来收到的另两个信息,而线索则是其中所引用的路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猎鲨记》(The Hunting of the Snark)和巴尔扎克(由埃里克·侯麦(Eric Rohmer)出演的客串角色优雅地解释)。当科林的推断最终把他带到了一个嬉皮士服装店“偶然角度(l’Angle du hasard)”时,“情节”明显变得复杂起来:这家精品店由宝琳经营,后来我们发现,她是托马斯和莉莉的朋友,是集体中的另一个成员;三人都是所谓的“十三人”的成员。

与此同时,弗蕾德丽克,即第四条叙事线,不知不觉间也建立了一些自己的联系。在她以敲诈为目的从艾蒂安(他与其妻子露西同样是“十三人”的成员)的公寓中盗走了信件之后,她戴上假发并安排了一次与露西的会面:二人的配对十分不协调,让人联想到米基·鲁尼(Mickey Rooney)遇上了侯麦笔下的慕德。接下来,在未能收到钱后,她去了那家服装店,试图用同样的手法来勒索宝琳。

这第二次相遇标志着所有四个“情节”的融合,它出现在《幽灵》的中场休息之前,但在剧集中出现更晚,直到第五集才出现。这是弗蕾德丽克和科林唯一产生交集的时刻(他们是重要角色中唯一没有见面的),观众此时可能会感到他们终于被引导着走出了混沌。但在四条线索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后,两个版本的故事的剩余部分又开始将它们解开。《幽灵》的最后一个小时和剧集的剩余集数让我们和最开始一样一无所知。
此时,许多角色已向我们抖露了他们的秘密。例如,科林中段的一集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话,有好几个小时不再装聋作哑——但矛盾的是,阴谋似乎在加深,两个剧组开始分崩离析。尽管结尾的某几个场景无法被解释或解码——第七集科林和莎拉的对白中她的一些台词和他的一句台词的音轨是倒放的,而第八集中,弗蕾德丽克与她新近找到的情人在屋顶上一桩模糊的阴谋中被杀死,涉及到决斗手枪和一个黑色面具(实际上,这又是一个浪漫的19世纪幻想,似乎与科林对巴尔扎克的迷恋相呼应)——但随着剧集的展开,《出局》的整体设计和含义变得越来越清晰。到最后,演员们所创造的妄想症式的虚构几乎完全吞没了纪录片式的部分,尽管电影所暗示的阴谋仍然超出了他们的理解,也超出了我们的理解。乌托邦梦想——1968年五月风暴的理想主义遗产——的接连建立和破灭因此在所有角色的命运的起起伏伏中得到了再现,勾勒出了整部作品的重心和轮廓。

正如《疯狂的爱情》和《赛琳朱莉出航记》以二联性精神病(folie à deux)为重点,失败的二联性精神病渐渐成为《出局》和《幽灵》的核心要素。无法“连接”被揭示为无力维持虚构的重要原因,而这一失败最为痛切的体现是欧吉尔和利奥德之间的关系,他们一开始相互吸引,最后疏远。在所有“二部创意曲(two-part inventions)”中,他们的关系是最为处于不断变化的张力之中的一对,而他们之间不断增长的分歧在两人的服装店场景中得到了绝妙的强调——尤其是当他们分别被安排在银幕两侧的相邻房间里、并以不同的方式争取我们的注意力时。这种空间上的张力在他们最后一个共同的场景中达到了顶峰,在街上,欧吉尔逃离了,而利奥德则以哑剧的方式表演着阻隔着他们的无形屏障,他痛苦地推着它,最终沿着对角线的轨迹走出画面,用口琴吹出一声刺耳的哀号。



Ⅱ
观看这部电影的理想形式是像阅读一本书,比如一本厚厚的几千页的小说。即使是读书速度非常快的人——碰巧我并不是——也不会一口气读完整本书,而是会放下它,停下来吃午餐等等。最理想的方式是分两天左右观看,这样可以让人足够地投入其中以跟随情节,同时也有可能停下来四五次。
—— 雅克·里维特向吉尔伯特·阿代尔描述该剧集,摘自《虚幻的采访者对谈里维特》,《电影评论》,1974年9月-10月刊
杜拉斯和斯特劳布(顺带一提,他曾经完全沉迷于一次13小时的《出局》放映)的印象主义风格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于他们的低预算方法。而我在我的近作中追求的目标有点不一样;你甚至可以说,我试图恢复老式的米高梅特艺七彩(Technicolor)!我甚至觉得《出局》中的色彩也会让纳塔莉·卡尔穆斯(Natalie Kalmus)(1934-49年间的好莱坞色彩顾问)感到满意。
—— 雅克·里维特对约翰·休斯说,摘自《作为精神分析学家的导演》(1975年春)
阴谋作为动力驱动着一系列清晰了然的姿态:行动之幽灵在虚无中玩耍。我们看着演员们如孩童般玩耍着身份和意义,而这些游戏中有许多陷入了死胡同或僵局,有一些在到达任何地方之前就精疲力竭,还有一些创造了坚实的角色和行动,它们在思维剧场中短暂起舞,然后溶解成别的东西。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一切都显现出不祥之兆。经由科林坚持不懈地调查,并被弗蕾德丽克盲目地用以谋取私利之后,“十三人”的幽灵重新激起了想要成为其成员的人们的妄想症,大体上扩大了他们之间的隔阂。期间发生了其他危机(一个陌生人卷走了莉莉的剧团的一个演员的钱;宝琳威胁要发表被截获的信件);恐惧引发了恐惧;两个剧团都分崩离析;艾米丽和莉莉最后一次出现是开车去见常年失踪了的伊戈尔;而弗蕾德丽克和科林各自回到了孤立状态之中。《幽灵》最后一卷胶片中重复的意大利门(Porte d'Italie)“空”镜头——小津式(Ozu-like)空无和弗里茨·朗式(Langian)恐怖的令人悚然的混合体——体现了这种不断增长的虚无感,它最终扩大到吞噬了电影中的其他一切。

将第一条信息传递给科林的行为完全是无端的,这个行为从未被解释、甚至从未被暗示,其它大部分“联系”都是由同样方便的手段引发的。在莎拉、托马斯、艾米丽(又名宝琳)和莉莉在不同时间居住的一座乡间别墅里,里维特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戏仿了“隐藏含义”这一概念,确保每个房间都能看到一个平平无奇的、与剧情没有公认关联的半身像。它甚至出现在那个可能住着艾米丽失踪的丈夫伊戈尔的上锁的房间里,而艾米丽直到电影快结束才进入这个房间。显然,这个半身像是一个玩笑,但它为什么在那里?是为了暗示一个阴谋。根据《出局》的策略,暗示一个阴谋既是荒谬的,又是必要的:它无法引领我们到达任何地方,只会引领我们继续前进——这种强迫性的行动在剧集中常常导向喜剧,但在《幽灵》中主要产生一种苦闷之感。

在文章的先前部分,我一直把《出局》和其缩短且碎片化的“替身”的情节看作是相同的,但实际上,剧集和《幽灵》的体验和意义在很多方面都是根本不同的,它们也本应如此。例如,《幽灵》的开场镜头在具集中出现在几乎第三个小时,而剧集最后一集的素材很大程度上在《幽灵》中是缺失的。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差别是,托马斯(朗斯代尔)在长版本中几乎成为中心人物(在《幽灵》中他显然不是)——不仅因为他是一个引导他的剧团进行即兴表演和心灵探索的角色,还因为他模糊地担任了一个相当孩子气的大家长(patriarch)角色,后者的高潮发生在海滩上最后一组较长镜头中他崩溃之时,这成为了情节总体发展的关键。

在逐渐被虚构取代之前,这部剧集是作为一部纪录片开始的,它没有序幕,只有一个简省的开场,依次播放五张字幕卡——“斯特凡·查尔加吉耶夫(Stéphane Tchalgadjieff)出品/ 《出局》/ 第一集 / 从莉莉到托马斯/ 1970年4月13日”——接下来的开场镜头是五位演员在一个空荡荡的排练场地中表演精心编排的体操,伴随着打击乐声。后续的每一集都以相同模式——除去日期——的字幕卡开始,每一个标题都标志着两个角色之间的进一步接力,以前一集中的第二个角色作为本集中的第一个角色。(在第六集中,接力的是同一角色的两个不同身份,即宝琳/艾米丽。)








剩下的七集都有序幕,它们结构类似:由皮埃尔·祖卡(Pierre Zucca)拍摄的15至28张黑白剧照,伴随着第一集开场镜头中的打击乐声,它们回顾了前一集的部分情节,然后是前一集的一两个结尾镜头,以黑白呈现,带有其原始的直接声音。因此,链条上的精确连接——从一集到下一集,从一个角色到下一个角色——作为形式原则,也作为严格的实践原则,被贯穿始终。每个黑白序幕既提供了前一集的幽灵般的抽象,作为记忆辅助物(aide de mémoire),也提供了“十三人”(大约2 x 13 = 26张照片)的一个版本,作为对现有信息的强制重新排列,这也许会为即将发生的事提供某些线索。

类似地,每个接力式标题都规定了每集中角色轨迹的起点和终点,同时确立了一个机制:每个新的开端都曾经是一个终局,每个新的终局都将形成一个新的开端——概要式抽象(abstraction-as-synopsis)的另一种形式,回溯情节,好像它是某种可能会产生隐藏含义的谜题。(在《幽灵》中,这些标题消失了,但在各个接合点处重新置入了黑白剧照,以提供情节的神秘延伸和回忆总结,伴随的是嗡嗡声而非打击乐声。正如里维特在1974年的一次采访中对此种声音和功能的描述,“我们只有一个仿佛由机器产生的毫无意义的频率,它打断了虚构——有时向它传递信息,有时与我们已经看到或将要看到的东西有关,有时则毫无关系。因为有一些剧照中的场景,尤其是在[《幽灵》的]尾声部分,并没有出现在电影的主体中,实际上是相当难以理解的。”)

与剧集相比,《幽灵》也许可以说是开始于一个虚构叙事、但逐渐被纪录片所取代——这与它的前身完全相反。尽管两个剧团都被设定在准备演出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但剧集中除了弗蕾德丽克外根本没有死亡,而在《幽灵》中显然也没有任何死亡。(虽然我们无法确定由电影制片人斯特凡·查尔加吉耶夫扮演的信使是否死亡——原因不明地,宝琳在她工作的嬉皮士服装店后面用瓶子猛击他的头部,此后他没有再次出现。)此外,许多单独的镜头和场景的含义和作用显著地产生了区别。科林试图让埃菲尔铁塔小饰品来回摆动13次——在剧集中只是一个小小的笑话,夸张地表现出他疯狂地试图在没有任何意义之处强加意义,将偶然转变成命运——成为了《幽灵》中最后的镜头。在那里,它讽刺性地隐喻了观众尝试弄明白后一部电影时的懊恼。重复尝试多次后,科林最终断定:“行不通。”现在这句话不仅代表里维特的观点,也代表了观众的观点:这一物理(physical)行为变得形而上学(metaphysical)。

Ⅲ
罗森鲍姆:你为什么选择了《出局》这个片名?
里维特:因为我们没能找到合适的片名。它没有意义。它只是一个标牌。
—— 《虚幻的采访者对谈里维特》,《电影评论》,1974年9月-10月刊
作为一部统一的作品,或者至少作为同一部作品的两个版本,《出局》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它是我们所拥有的最伟大的关于19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电影。我要赶紧补充一句:不同于人们可以援引的种种英美电影之例,《出局》中没有关于迷幻药的任何内容(尽管有一些五彩斑斓的、迷幻的颜色),而作为一份与五月风暴失败革命后的幻灭有直接关联的时代声明,它呈现出一种明确的法国时代精神。(或许可以推测,在北美使用迷幻药才能抵达的思维状态,在法国文化中却由法国思想的笛卡尔主义基础提供了某种进入其中的捷径,从而延迟并限制了它们的文化影响。)
然而,如果更宽泛地将其视为对反文化运动的乌托邦式梦想——正如它们在大西洋两岸已然自我证明的那样——的一次史诗般的反思,《出局》仍然是一块无可估量的试金石,特别是它对集体和孤立之间的选择的认识,这是里维特早期作品的主题。事实上,《出局》中的一切都可以被解读为对种种集体努力(戏剧排练、共谋、各式反文化活动、宣言)和从孤独和疏离中生发的活动和情境(解谜、耍心机、曲折的情节、最终的疯狂)之间的辩证关系的一次沉思——某种程度上,这正是法国左翼在1960年代所面临的选择。
从形式上看,这部剧集偏爱长镜头和深焦场面调度(mise en scène in deep focus),而不是以蒙太奇来传递意义,因此它可以称为巴赞式(Bazinian)的和雷诺阿式(Renoiresque)的,而在这一方面,被侵略性地剪辑、切碎的弗里茨·朗式的《幽灵》与之形成了一个惊人的辩证关系。在剧集中,这最终通向了对巴赞的现实主义观的讽刺性总结——一部鲁什式(Rouch-like)的、深陷于幻想之中的伪纪录片(pseudo-documentary)——可以说这不仅仅是阐述了巴赞主义理论,更是从根本上破坏了它。

里维特的剧集与菲拉德(Feuillade)的犯罪连续剧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这一区别解释了它们,至少对其各自年代的观众而言,在大众吸引力上的巨大差异——在于种种阴谋的表面之下或幕后是否存在一个稳固的基础。在《吸血鬼》(Les Vampires, 1915-1916)和《提明》(Tih-Minh, 1919)中,对于英雄和恶棍的固定的类型化身份、对于主人和仆人的固定的社会身份有一种至高的信心,这使得所有对这些角色的“修订(revisions)”和表演中的即兴精神都成为一种游戏,从未威胁到他们作为叙事人物的根本功能和身份。

在《出局》中,这种社会和艺术层面的信心的缺席——一种将社会与虚构相等同的真正的不可知论,它似乎既源自1960年代末期的怀疑主义,也源自施加在所有演员身上的即兴表演的责任——赋予了叙述一个非常不同的状态,使得从角色到演员、从虚构中到非虚构的频繁滑移变得必要。因为没有一张面具是完全安全的,所以虚构创作的过程本身——它的乐趣,它的危险,甚至是它的陷阱、死胡同和失误——成为整体主题和趣味的一部分。(利害攸关的问题并非里维特的演员的演技——他们的演技千差万别——而是他们创造的许多虚构部分的敷衍性质。)在这里,种种不断增殖的虚构之下,没有一个固定的文本可以保证它们的社会和类型层面的功能;相反,可以找到一系列的引用和影射——巴尔扎克和雷诺阿、埃斯库罗斯和朗、大仲马和鲁什、雨果和菲拉德——这些只能提供理论层面的托词(pretexts)或转瞬即逝的、不可持续的模型,以及一种漂流和玩乐的整体精神。
Ⅳ 三个事后的思考
“跳入虚空之人无需向旁观者解释。”
—— 让-吕克·戈达尔,评论电影《蒙巴尔纳斯19号》
1.
或许关于《出局》中的两个剧团之间最为详细的比较,是由克里斯蒂娜·阿尔瓦雷斯·洛佩兹(Cristina Álvarez López)和阿德里安·马丁(Adrian Martin)的两个视频和配套的文本中所提供的,它们是2014年底受墨尔本国际电影节委托制作的,作为正在进行的一系列《出局》的视听论文和书面文本的一部分。(我和凯文·B·李(Kevin B. Lee)制作了该系列的第二个视频,阿尔瓦雷斯·洛佩兹/ 阿德里安·马丁制作了第一部和第四部,大卫·赫斯林(David Heslin)和克里斯·卢斯克里(Chris Luscri)提供了第三部,而卢斯克里一个人使用查尔加吉耶夫的一段音频访谈制作了第四部。)以下两段摘自在2014年8月7日发表于mubi.com/notebook上的一篇文章,以配合第一个视频,《类剧场:无舞台的戏剧(从第一集到第五集)》(Paratheatre: Plays Without Stages (from Ito IV)):
“事实上,《出局》是一份非凡的整合文献,涵盖了戏剧领域的许多实验运动,可以追溯至战后初期,并一直持续到我们的时代,出现在全球范围内大大小小的表演工作坊中。尽管一些评论指出,里维特(通过他的演员)综合了包括波兰戏剧大师耶日·格洛托夫斯基(Jerzy Grotowski)和美国的生活剧团(The Living Theatre)的多种影响,但一旦意识到里维特如此精心地、如此长篇幅地记录下来的这些表演者的肢体表演中,到底引用了多少传统和流派,依旧会感到目不暇接。这部电影就像一个巨大走廊,贯穿了当代实验戏剧的历史。”

“一个剧团使用手势和声音的表演来高度风格化地探索和表达埃斯库罗斯的《七将攻忒拜》;另一个剧团使用一种即兴表演的激进形式,名义上以改编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为托词,它不完全是心理剧(psychodrama)(其目的根本不是治疗),但肯定深入了阿尔托的残酷戏剧(Theatre of Cruelty)的根源——在后者中,书面文本消失得越来越远。两个剧团都将他们的表演建立在种种缜密的排练之上(格罗托夫斯基的排练,心理物理学(psychophysical)排练,以及镜像模仿这类古老的游戏),这些排练,举个例子,对于理查德·谢赫纳的表演剧团(The Performance Group)(后来成为伍斯特剧团(The Wooster Group))至关重要,其戏剧作品《狄俄尼索斯在69年》(Dionysus in ’69)由布莱恩·德·帕尔马(Brian De Palma)于1970年(以分屏形式)纪录下来。”


“两个剧团都会讨论、分析和评论他们的表演,但是《七将攻忒拜》剧团倾向于从实践层面重新排练(根据语音和动作的不同“得分”),而《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剧团更注重在每次从“出神(trance)”中清醒过来后进行研究和自我批评。同时还要注意到两个剧团的双重面向:它们无论如何都完全是前卫的,然而它们也试图重回神话性、宗教性的起源——去复兴作为仪式的戏剧场面,这在1960年代末既吸引、也困扰了帕索里尼(Pasolini)。”

根据我个人在这一时期观看戏剧表演的有限经验,我想对这段描述做一点补充:即《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剧团的一些“出神”状态与生活剧团演出的《天堂此刻》(Paradise Now)(1968年秋季,在整个剧团和演出在欧洲巡回结束之后,我在布鲁克林音乐学院观看了它)中的某些幕间表演非常相似。
2.
四个看似自主且无关的叙事线索最终被编织在一起的结构——在《幽灵》中更加仓促,但在剧集中却极为重要——可以被视为埃里希·冯·斯特罗海姆(Erich von Stroheim)原版《贪婪》(Greed)的创新一面的一次迟来的实现,后者长达40卷胶片左右,但在发行版本中完全缺失。正如我在关于《贪婪》的专著(BFI Classics, 1993)中所指出的,斯特罗海姆向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的小说《麦克提格》(McTeague)的情节中添加了大量的叙事素材:“将近五分之一的情节([我们拥有的最新版本的]剧本的四分之一——277页手稿中的69页)发生在麦克提格周日在售票员咖啡馆吃晚餐的场景之前,后者是小说开篇第一句话的主语。麦克来到旧金山之前的生活占据了这段序幕的四分之一篇幅——在已发布的剧本中超过24页——构成了对小说中短短两段内容的详尽阐述。”

“在已发布的剧本中的4页之后,有一个设计精巧、长约为30页的长段落,在发生在小说开篇之前的一个‘平常的’星期六中介绍了电影中的所有主要角色[包括在发行版本中完全删去的三个角色] ,但没有在他们之间建立任何联系,除了告诉我们他们住在同一栋楼里。完全合乎情理的是,哈里·卡尔(Harry Carr)——他描述自己看了《贪婪》的45卷胶片版,从早上十点半看到晚上八点半——至少部分地想到了这一段落,当他在1924年4月的《活动影像杂志》(Motion Picture Magazine)上写道,‘有些片段你觉得与故事无关,但在十二或十四卷之后,突然间狠狠击中了你。’”
3.
在里维特在1989年至90年代初重新剪辑这部剧集时,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无疑是他删除了利奥德的极具感染力的高潮场景,这一场景目前已不再是电影的一部分。(我知道的唯一其他变化涉及某些场景的顺序。)这个长时间的段落镜头原本出现在布鲁·欧吉尔和贝纳德特·拉封之间的一场同样长时间的场景之后。(实际上,最后一集的原版,即90分钟的版本,展示了全部四个主要角色——欧吉尔、利奥德、贝尔托和朗斯代尔——在独立的长段落中崩溃;《幽灵》中没有这四个段落的任何痕迹。朗斯代尔的场景被放在最后,他从导演-大家长到在海滩上嚎啕大哭的人的退化,似乎将剧集带回了起点,带回了他的剧团的第一次排练时的无言的歇斯底里。)

我猜测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它展示了科林独自一人在房间里,处于一种在绝望和(更短暂的)欣喜之间反复摇摆的歇斯底里状态——太容易让人联想到利奥德随后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困难,以至于里维特觉得不舒服,不愿意保留它。2013年的维也纳音乐节上,当利奥德与这部电影的英雄般的制片人斯特凡·查尔加吉夫(他冒险制片的其它影片包括《印度之歌》(India Song,1975)、里维特的《决斗》(Duelle,1976)《诺娃》(Noroît,1976)和《旋转木马》(Merry-Go-Round,1981),斯特劳布-于伊耶的《福尔蒂尼/卡尼》(Fortini/Cani,1976),布雷松的《很可能是魔鬼》(The Devil, Probably,1977);此外,《出局》是他制片的第一部电影)以及我本人谈起这部电影时,他没有提到这一删除。但很明显,他从未完整地看过这部剧集;他谈到的主要是他与里维特的早期友谊以及北非音乐对他口琴声的影响。
根据我在1989年鹿特丹放映会上记录的笔记,这个缺失的段落——穿插了几次黑屏——展示了科林哭喊,尖叫,像动物一样咆哮,在墙上猛撞头,打烂衣柜门,在地上扭动,然后冷静下来,拿起口琴。在将他一直试图破译的三条秘密信息全部扔掉之后,他开始狂热地演奏口琴,把他的衣服和其他东西扔到走廊上,疯狂地跳舞,然后再演奏口琴。从戏剧和结构上看,这段生猛的心理剧不可避免地使人想到里维特《疯狂的爱情》中无情地记录让-皮埃尔·卡尔丰(Jean-Pierre Kalfon)用刀片划伤自己的段落——一个令人不安的自我暴露的片段,在其中角色的虚构设定似乎瓦解为了真正的痛苦和悲伤,在两部电影中,这都代表着对某些边界的一次危险的跨越,进入某种只能被视为疯狂的领域。

注:本文吸收了之前的两篇文章(《在虚构之屋中工作和玩耍》(Work and Play in the House of Fiction),《视与听》,1974年秋,《〈提明〉与〈出局〉:关于两部法国剧集的未被接受》(Tih-Minh, Out 1: On the Nonreception of Two French Serials),《天鹅绒灯光陷阱》,1996年春)和其他一些先前的文本,其中大部分可在jonathanrosenbaum.net上找到。
往期推荐
访谈翻译 | “一切都已死去但引擎仍在运转”:阿尔伯特·塞拉访谈

5 ) 《Out 1》及其倒像
“假设——故事地点:巴黎及其复象;故事时间:1970年4月或5月”(《出局:幽灵》)
关于对“两年前”的五月风暴的指涉,在各种对话中我们得知从未出现的Pierre是建筑师、城市规划师,曾在两年前有城市改造的理想,而显然并未实现。同时,影片展现出对于城市空间的兴趣(使我们联想到10年之后的《北方的桥》,那里对“空间”的探讨到达顶峰),突然插入的拍摄街角广场的空镜头,Quentin(《七将攻忒拜》剧团成员)(Pierre Baillot)在路口无望的来回踱步,在城郊公交车站对巴黎地图近乎荒诞的测量与计算……人生存于一片并不属于自己的空间内,而对地图的精确测量既是任由偶然摆布的运气游戏(Quentin想再次利用让他彩票中奖的逻辑),又似对于“严密理性”的空间规划的戏仿。
上述这一视角和它之外的其余场景共同组成了五月之后的集体幻灭。但我们更多看到的不如说是对五月风暴的反思。里维特并不掩饰展现阶级性,无论是通过Frédérique(Juliet Berto)和Colin(Jean-Pierre Léaud)居住的“女仆间”,还是对les treize所出自的巴尔扎克《十三人故事》(Histoire des Treize)的引用:“仅在精英中招募成员”。在此之上所展现的则是各人物的相交与断层,是“入局”的不可能性之辩证:
如果说《Out 1》是一个声效的奇迹或许不会有人相信,毕竟全片的音轨上几乎只有环境音和几处鼓点。但声效在《Out 1》里具有了叙事效果。Émilie(Bulle Ogier)的小店里的一处画面被分割成两半的同时,一边是Émilie和Sarah(Bernadette Lafont)几乎不可听见的交谈,另一边是发出“噪音”的Colin;《出局:禁止接触》第七集结尾Sarah和Colin谈话的音轨被倒放;第八集Émilie和Sarah交谈的信息时常被Colin的口琴声盖住,似乎他成为了一个飘荡于海滨别墅上方的幽灵。当然这种用杂音掩盖关键信息的手法并非《Out 1》所独有,类似的还有布努埃尔《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里的飞机声。但《Out 1》里的口琴融合得无疑更加高明。不仅Colin和les treize间的交流被失效化了,而且我们还看到失效的原因是一方的话被视为“噪音”,而他的坚持只意味着继续吹奏口琴并自我强化了交谈的不可能性。正如朗西埃所说的“治安秩序”里所涉及的感性分配,一部分人的话被视作有意义的信息,而其余人则被视作噪音。于是那些多少游离在外的人物即使都一个个都因les treize而被卷入局中,打破区层隔断的某种“接触”却是不可能的。
既然《Out 1》的制作动机之一,是在十年之后对于《巴黎属于我们》里流露出的对世界性阴谋和秘密组织的着迷的反思,那么对于这一反思的表达方式,如果说《出局:禁止接触》用明语说话,《出局:幽灵》则可以说是在用暗语说话,而这无论是在内容选择上还是剪辑逻辑上。《禁止接触》中Béatrice(《普罗米修斯》剧组成员)(Edwine Moatti)和研究马达加斯加的人种学家(Michel Delahaye)的对话里,已经讨论了马达加斯加和法国两个分别“封闭的世界”,无论是人种学研究意义上还是当地族群自己的话语声音意义上。另有在一系列“调查”之后Colin在Warok(Jean Bouise)那里直接讲出了“十三人”故事是“纯粹的幻觉”。
而在《幽灵》里,我们看到的只是Béatrice和人种学家对话之前的一次碰面(在其过程中他们约定了下次碰面的时间),他们的第二次出现仅是在近结尾处的一张黑白剧照里。且《幽灵》以Colin对les treize偏执狂的信念与幻想作结,坚信着铁塔吊坠会在摆动13次后停下,他试图计数其摆动的次数并在数到“13”后停止计数,纵然吊坠仍继续摆动下去。保留的则是Thomas(Michael Lonsdale)和Étienne(Jacques Doniol-Valcroze)的谈话,其中Thomas认为《普罗米修斯》和《十三人故事》之间的联系是,les treize在停滞、“被缚”的社会环境中“促使事情前进”。如果不进行任何延伸理解,《幽灵》呈现的首先是一种偏执狂式的幻想,而它无论来自“十三人”团体的内部还是外部。相比之下《禁止接触》里Thomas的结尾则呈现了《普罗米修斯》和《十三人故事》关系的另一面,仿佛回应了Thomas和Sarah此前一次非正式的谈话里不经意谈到的对普罗米修斯结局的构思,即淹死在海边,Thomas在《禁止接触》的结尾俨然成为了普罗米修斯,而不是所谓将其在束缚中解下的人。此外《禁止接触》还保留了一段普罗米修斯与朝圣者的表演练习,那里盗火者重新成为需要被服侍的神(Noli me tangere! 是他的叫喊),如同乌托邦理想幻灭而始终处在顶端的les treize。
不同于《禁止接触》的明晰,《幽灵》里的暗语需要另做理解,然后我们才能看到对于无处不在的阴谋的幻想是怎样被消解掉的。除了尝试通过计数验证关于数字“13”的假设失败后的一句“不灵”,近乎怀疑论的剪辑也在质疑关于les treize的各种意义上的信念。场景变得更加破碎,并且使人感到对话时常在关键信息出现前被剪断(相反,在《禁止接触》中只是对于少数的对话,其意义的接收受到阻碍,以放大阶层之隔和交流的失效),并穿插着配有单调的嗡嗡噪音的黑白剧照,而杂音“纯粹人造的”,仅仅是“无意义的频率,好像由一台机器产生”。这时我们意识到,《幽灵》不过是一台通过剪辑制作意义的机器,而神秘的“十三人”组织是这台人造机器的虚构。
从《Out 1》开始我们常能在里维特的电影里看到这样的过程,情节先通向一个谜题(往往涉及某种阴谋)和对其的寻找和调查,然后又有各种方式将我们所深陷其中的这个谜题消解掉,而对于此,在《Out 1》里尤其发挥作用的是影片构建自身的逻辑。如里维特对于《幽灵》的观影所说,观众“进入到虚构中”,之后又逐渐意识到“虚构实际上是一个陷阱,它充满裂缝,是彻底人造的”。如果说《幽灵》通过伴随着侵入的剧照和噪音的碎片剪辑,将电影关于阴谋和谜题的虚构揭示为虚构,那么《禁止接触》则是通过可以强烈感知到的即兴表演。Pauline/Émilie这个拥有两个名字的角色,也正处在对谜题的妄想与超越阴谋构想的即兴之间,前者事关Igor的失踪(而在幻想的顶点她看到的却只是自己在镜廊中无尽的镜像),而后者则发生于与Colin在L’angle du hasard的相遇。并不是说《幽灵》不含有这一即兴元素,毕竟两部影片来自相同的由即兴表演构建起来的素材;而是说《禁止接触》里每个场景由即兴表演积蓄起来的能量,由于更少被打断(尽管有时也有短暂地提醒我们另一条同时进行的情节线的平行剪辑),而集中爆发出来:尤其是当《禁止接触》进入到最后三集时,Colin反复背诵着Lewis Carroll的《猎捕蛇鲨》(The Hunting of the Snark)冲下巴黎的街道,Colin和Sarah那段我们无法理解的对话后呼喊着“Pauline”逐渐远去,或是幽灵般的Sarah在半弃置的海滨别墅角落里凝视Émilie,“你为什么这样盯着我看”“我正常地看着你啊”,我们不可能不感受到一种能量和张力。
具体地,这种能量来自何处?内容很少是预先已知的,演员需要根据现场环境接收到的,尤其是对方的反应,调整自身的反应,由此形成一种双向的反馈机制。因此对手戏里的张力是双重的,除了意义层面一方对另一方(Colin和Émilie之间、Émilie和Sarah之间、Frédérique和Lucie(Françoise Fabian)之间)的质问,还有表演层面双方互相的影响、依存和调整(Colin和Émilie伸出手对对方距离的试探)。《普罗米修斯》剧组的“镜子练习”走出(剧中的)剧场,便成为了《Out 1》里面的即兴表演,因为两者的互动过程遵循着同一个逻辑。在对手戏之外呢?当Colin大声吟诵《猎捕蛇鲨》冲下街道,偶然路过的孩子的兴趣被其吸引,并跟着他一同疾走。如果说《塞琳和朱莉去划船》里,塞琳和朱莉闯进鬼屋彻底打破了现实与幻想和虚构的边界,那么《Out 1》则在即兴表演所发生的街道上向我们呈现了现实与虚构和创造从未有边界的共存。现实和对虚构的创造同时发生,好奇地望向镜头的路人等待传统意义上的穿帮镜头,在我们这里同时产生了尴尬感和自由感,因为我们意识到这是一部未受条框限制、“正在发生”的电影。于是complot(阴谋)变成了com-plot(共同-情节),不是仍在影片内容中的les treize曾尝试过却因精英团体的封闭性而未能有实际成果的共同-情节,而是指向这一即兴电影自身逻辑的共同-情节。在一圈阐释之后,我们回归到里维特对于元电影、对于电影自身之“真理”的理解:“唯一的真理是关于电影胶片和演员的真理”。
而这其实在现实的中心打开了虚构与创造的空间,Colin和跟着他奔跑的孩子不过是这一逻辑的具象化表现。让我们再来对比《禁止接触》和《幽灵》四条主线结局的相似与差异,除了同样走向解体的剧团,《幽灵》里停止于偏执狂阶段的Colin,在《幽灵》里Frédérique通过信件和les treize发生短暂的联系后又回到了出发点,身旁放着一把枪躺在狭小的房间里(甚至还丢了骗到的钱),而在《禁止接触》的最后她则戴上一幅带有巴尔扎克时代指涉的面具,死于一场决斗。这就是为什么罗森鲍姆说《禁止接触》是里维特最易接近、最令人愉悦的电影,相反《幽灵》则是他最难的一部,除了前者的连贯和后者的破碎(我们几乎是在插入的剧照里猛地知道剧团的解散和Quentin等《七将攻忒拜》剧团成员测量地图、对Renaud(Alain Libolt)枉然甚至荒诞的找寻),除了前者用明语而后者用暗语说话,“与《禁止接触》相反,《幽灵》从虚构叙事开始而逐渐被纪录取代”。 两种剪辑版本的差异甚至可以说大于其共性,虽说四条主线先交汇缠绕在一起又迅速解开是两者共同的命运,但《幽灵》呈现出的是一个密不透风甚至令人窒息的世界,如其隐晦,如跌回原点的Frédérique,如其结尾的纪录性叙事,它结束于纹丝未变的阶层区隔和由其导致的偏执妄想。而《禁止接触》则向创造与解放开启,它甚至可以看作一篇关于感知和创造力解放的宣言,宣告了一种不需要外部的启蒙或灌输就一直在那里的创造潜能,影像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将它呈现出来:尽管交流的失效和被当作“噪音”的话,Colin最后仍在Warok面前发表了关于les treize的演讲;而Frédérique则踏上了游戏与创造:
决斗或对决斗的戏拟(Frédérique衬衫上的一滩假血提醒着我们),Frédérique在《出局:禁止接触》里的结局不如看作一个开始,当她跳转过身出现在Renaud面前时,未尝不能联想到Juliet Berto在《塞琳和朱莉去划船》里作为Céline出现在鬼屋和表演戏剧的幽灵前的场景,那是想象与虚构开始的时刻,也是里维特《Out 1》之后接下来的三部宣告l’imagination et la fiction au pouvoir的作品开始的时刻。
参考文献/ Jonathan Rosenbaum, Lauren Sedofsky, Gilbert Adair, Phantom Interviewers over Rivette Jonathan Rosenbaum, Out 1 and its Double
6 ) 我只是觉得大家都好厉害
我在电影院看它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是可以主动放弃一切思考的,自我意识就像暂停一样没有任何反馈和流动。意识从第一部分开始涣散直到消失不见,一切都是那么和平和美好,睁着眼睛但是好像又什么都没看,张着嘴也只能感受到呼吸,一切都在发生,影片在播放,但是我的意识好像和影院融为了一体,感受一切在周遭发生,但好像又没发生,像一束光透过介质没有痕迹。直到下午倒数第二幕我实在是撑不住打了退堂鼓。对不起,我只是个垃圾,我没文化我有罪。
最近失眠得厉害,在思考人类的意识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晚上会活跃和兴奋,又回想起这部电影,可惜它太难得了不怎么有机会看,不然可能会再去一次。
7 ) 出局
不太了解这片对于《纽约提喻法》这样的片子影响多少 但观看本身亦像是参与了一场13小时的行为艺术//整部电影13个小时 实际上在做一次五月风暴的运动排演,运动为什么发生 人们对于共产主义与毛主义有多狂迷 运动为何又分崩离析。两个剧团的嘶吼着排演,像动物期待雷鸣一样 期待共产主义的到来。从这一点看 不断打破壁垒的大段戏剧排演与13个小时的时长显得十分有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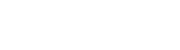




















第一集昏昏欲睡,之后渐入佳境,六七集陷入焦灼,第八集打散了此前积攒起来的所有期待,散发出浓郁的迷惘和哀愁。有人躲在排练厅里重温浪漫理想,有人培养下一代的努力无疾而终(出版物没下文,成员性别比糟糕/关店铺/皮埃尔找的口琴男孩最后重回装聋作哑),大部分人还是在做最符合阶级身份的事-当精英,这帮理想远大衣食无忧的中产知识分子,行动力远不如需要讨生活的帮派混混,后者不仅卷了一百万跑路,还一枪就把女朋友给崩了-现实如那滩假血讽刺/整个巴黎都是幽灵导演的剧场。一个感慨:上海的法租界就是按照巴黎的房子建起来的吧?今天在法租界住一个亭子间,四舍五入就是在巴黎讨生活,牛啊。以及感受到的三大culture shock:上床不脱鞋、抽烟不回避小孩、面包放包里掏出来直接吃 @和平影都 2021法国影展
用我给中文名称更正一下,不能直接叫出局我在B站花了3-4个月时间8个部分都已上传了,观众只需下载下来配SUB字幕即可,可方便理解剧情和内容
729分钟的迷醉光影之旅。我想,我已经爱上了里维特。1.与其归纳为电影,不如将《出局》视作一部剧集相待。巴尔扎克,“十三人”变奏麦格芬,古希腊戏剧于古典、现代的两面诠释,个人与组织(记者作为局外人始终无法嵌入局中/剧组内部关系的纷繁复杂)、演绎及人生的交汇碰撞。2.和里维特执导的其他作品一样,《出局》在看似零散的片段中逐渐聚焦主题,并借以“拖沓、沉闷”的叙事推进堆砌神秘与悬念感。场景布局及情节构思极具设计感,戏剧编排时的推拉长镜更是行云流水赏心悦目,演员的即兴表演在借助戏剧张力延伸表达空间的同时,亦起到拓展作品整体内涵的作用。3.解谜方和游戏方的重心接转;别墅镜子同质《决斗》。4.剧组成员(职责)/朋友恋人(情谊)的背离皆是出局。(9.3/10)
Improvisation, unscripted-performance,所有Interpretation都是过度,因为试图架构意义本身就是无意义的。最后反而给出了一个很漂亮的结局:入侵者杀死了守城者,普罗米修斯消逝在沙滩上,将两部古典悲剧原剧作彻底解构(诅咒与命运,革新后的报应)。这对应着五月风暴后的巴黎,演员还会潜意识喊出imperialism,街头列宁的海报,人们仍然相信Freemason和13人的存在。可李维特最让我感动的还是他积极打破第四面墙的努力,巴黎属于他们,每个巴黎人都是这场时代剧不可或缺的演员。 把电影还给生活,我们都要去追捕Snark.
戏剧和电影的无限可能,即兴表演和场景编排,视频剪接还是堆砌素材,谦逊理性还是自说自话洋洋得意。花了三天时间,有看到剧场排演的放松和快乐,但总体如坠云雾;也许若干年后突然发神经拿出来重温终于可以理解,也可能再也不想看到了。
整体散漫跳脱的氛围中却有着一种无形的驱动力量,推动着叙事的前进:13的被发觉,深究;剧团的离散与崩溃;伊戈尔的失踪与重新出现;柯林成为侦探却又回到起点。就仿佛在表层组织下隐藏着另一种无法被人发觉的图景,就好像秩序的巴黎真正地被隐藏在幕后的13所操控着:人物的所有行为全然出于这种无形的驱动力与当时情境的激发作用。创作的即兴与讥笑使得影像中充满了一种目的为虚构的虚构:一方面是剧作层面的虚假与随性,另一方面是叙事中对埃斯库罗斯的现代演绎。巴黎被演绎成为拥有七个大门的忒拜城,而普罗米修斯的悲剧则被转化为对现代的戏谑与团体的仪式姿态随后极速消散在阴影之中。
三点印象深刻:1. 细部无处不在的虚构性/防共情暗示(暴露的录音师;打断的画面;倒放的声音;费德莉克死时的假血;入画的群众…),让人始终对影像和人物保有意识,并刻意留住悬念(或不存在的真相);2. 大面上强调的对称性结构,四条线索交叉对称(两组多人戏剧 - 两组单人“侦探”;两组直觉型 - 两组逻辑型),直到后半部分相互融合不分你我携手走向虚无;3. 戏剧训练方法令人惊叹,一组强调直觉/即兴由内向外,一组强调造型/精确由外向内,二者各有所长但没成想最终全部归于失败。无他,戏剧终究不是解药,短暂麻痹后仍需面对无法控制的现实——古典式团体粘合力的彻底失效。13个小时看下来,原本对角色和情节的期待一一落空,也正是在此建立起巨大的关于时间和影像的惊喜。如果有机会,还可以再看很多遍。
如河流,身體讓它在身上任意流動,這是導演和時代玩的遊戲,但終結一刻,全身被擊倒(無論是精神還是身體),魔咒無法解脫,也無法逃離困局,這是《2666》,《傅科擺》,一群理想主義者的幻滅,虛構反咬真實,以表演對抗(和逃避),是我們無法達到真相和人際關係以至解決,noli me tangere ,偉大的電影。
主要还是看个情怀吧。论情怀其实四星没什么问题,甚至五星也可以。全程并没有昏昏欲睡的时刻,吸引人的点很多。可是、不能不疑惑,究竟为什么要这么长?其实,完全可以更长,或者索性很精简的。
68之后行动和组织都消散了,好日子也过上了。两年后,有人愤愤不平,其实所有人都不好过,但组织和行动也不会再有了。被期望的年轻一代,迷失在这些乱码和噱头里面,最终以回归日常(骗钱)和戏剧化的极致(死亡或者表演的血浆)out——还有那办不起来的进步杂志。最具行动力的组织,是最后一声枪响的小帮派。很是悲伤,但又终归是“巴黎社交圈”(人类学式自反敲门砖)里的第一世界的悲伤。可能有戏剧即兴的身体经验的人来看那些长段的伪纪录片部分会更有感触。
7。非常粗糙的看了一遍,到此1000部就全部看完了……即兴占的比重非常大,里维特挑女演员真有一手
待重看。暂时提出几点:最理想的观看模式或许不是一群惊恐倦怠的面孔在黑匣子陷进窄小的空座,束手束脚地窝上两天,而是应该像Youtube的《房间》直播现场那样,观众被允许和两组剧团一起手舞足蹈,满地飞奔打滚;在Colin于巴黎街头冲撞横行的时候跟他一起重复密码,冲着银幕大吼。这应该是一场激发身体的运动,而不是在行动面前主体被禁锢的休眠,里维特真正的魔力就在这里,他不制作一个形式完整的世界将你震慑于无言之地,而是打造一个半开放的空间和词语,邀请你的暴力侵入,甚至,有且只能由你的热情和信念来为他续写和补足,仿佛在说:成为一个作者吧,像我一样!
最想知道一点:在影片的台词剧本和整个拍摄过程中,即兴发挥的成分占了多少。里维特在访谈中谈到了这部影片立意构思上的几个(记得是三个)概念性来源,提供了一把理解影片的钥匙,使它变得不再那么神秘,那么不可索解了。这部夸张的实验叙述电影是世界电影史上曾拍出过的最美的电影之一!
辉煌而庞博的结构,观感犹如「追忆」——正如科林反复吟诵的“消逝的时光”,两个剧团分别自「这一边」和「那一边」靠拢,终局得以庄严合拢。“普罗米修斯”剧团从拜神的吞噬式狂喜(以身体/语言的共能寻求人和神的共情)过渡到原文本渐行消失,即兴生长的走向;“七将攻忒拜”剧团对应巴黎地图上的区域划分,风暴过后的城市景观。两出戏剧指涉“五月风暴”中这些人曾有的位置、境况和目标,两个始终在谜团外围打转的局外人破坏或重建“休眠”地下组织秩序,是历史/政局阴影下窥测的视角。新浪潮的核心是悬疑,里维特惯有的神秘与暧昧留白,人际网络的交叉和回环(核心/边缘人物各自的丰富前史太有趣),现场调度掌控的能力,皆令人着迷。一场盛大的观影体验,一次在文字/影像迷宫中的突围,浸淫的两天被抽干了时间的概念。
侯麦演的真可爱出场大家都笑了。13个小时分成了两天八场放映中间休息十分钟喝水嘘嘘。精疲力尽腰酸背痛。但确实是独一无二的观影体验。电影本是描述并抵抗时间。这部片子成为了时间本身。当作一场13小时的seminar来看也很好。black mountain college。戏与人生的倒错
无始无终。从形式的自由度到瘆人的神秘质感,几乎可以断定是电影史上独一无二之作,里维特创造了一个世界,一个在五月风暴运动后颓废、混乱、封闭的时空,然而他在这个天地里,便能用他最爱的演员、最奇异的巧合来拍摄出最具想象力的电影,它那中邪似的、催眠似的魔法,令观者的身体会不禁的发生物理上的扭曲,和影片一起运动,而它的摄影机又是灵魂式的,可以在一个时刻远远观看,也能突然成为角色之一一起跳舞,即像是大脑魂魄出窍,被影片断裂的剪辑点撕碎,飘荡在巴黎写实却悲凉的每个角落,13个小时过后,我们不禁问道:13究竟是什么?
群体的共同行动使得忠诚和承诺成为一种初始的狂热奉献,新人的加入离去又迅速瓦解和扭曲原本目的即不明的团体,虚构的迷恋和梦想被消灭,普罗米修斯在沙地上沦为只身一人。观众发现其难以从残骸中找出叙事的主线,十三个小时的电影在不断拼凑中又不断将自身宣泄扬弃,五月风暴的后遗症引出整个社会的追问,却只换来等待戈多的空缺和偏执的破坏性暴力,这场革命由外向内逐渐瓦解,在巨大的怪物面前倒下,而另一头的十三人又将重启这场猎鲨之旅——一种存在主义式的悲剧浪漫情怀,轮回延续。难以说这是杰作,却一定是壮举,几场伟大的实验性的剧团即兴和跟拍长镜头必载入史册,尽管时间流逝和沉浸是作品不可或缺的元素,但在多大程度上必要却是一个问号。
终于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断断续续看完了这部影史垂青的最长电影,比它还长的有一些,但大部分是实验电影。然而这部13个小时的电影的拍摄居然只花了6周!电影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但是人物较为繁多,甚至还有几个从未出场的重要人物。影片的展开极为缓慢,充斥大量猜谜一样的纪录片式的长镜头,到大概4、5个小时的时候才开始进入故事主线,里维特仿佛在用时间作为他的工具,来让观众相信他的故事。除了长度,影片并没有过多的炫技,更多时间是在追求一种客观的现实主义,甚至你会在一些场景里看到摄影机,还有镜头的裂纹等。总的来说是一次奇特的电影探索。
两天八场13小时。像是与剧中人亲密共处了两天 非常独特的观影体验。 “十三人组织”是笼罩着所有人的麦格芬 是中产阶级注定无法实现的终极理想 所以他们献祭了一个哑巴和一个小偷。事情慢慢变化 哑巴开口说话 小偷变成斗士 但幻想注定破灭。于是在这个周日夜晚 伴随着银幕上的海浪 所有旖旎的戏剧梦想 最终都走向消亡 曲终人散 梦醒时分。 神奇的摄影 晦涩的书籍 奇妙的演技 像是剧中人的不停的质问“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上海和平影都 法国大师展
我花了12个小时没有找到不给该片1星的理由,别新浪潮,别实验叙事了,就是一群沉迷于神秘主义,史诗中的空虚至极虚伪至极的资产阶级,别无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