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故事发生在二战后的意大利,战争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伤害无法估量,短时间内造成的痛苦和破坏,需要更漫长的时间才能痊愈。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中,穿梭着一群天真的孩子们的身影,他们是小小擦鞋童,帕斯克里特(弗朗科·英特朗吉FrancoInterlenghi饰)和居赛派(里纳尔多·斯默东尼RinaldoSmordoni饰)也是其中的成员。\r居赛派的哥哥是个坏胚子,在他的威逼利诱下,居赛派和帕斯克里特拿着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加入了诈骗团伙。警方逮捕了居赛派和帕斯克里特,在挑拨离间计谋的驱使下,帕斯特里克供出了主犯及其团伙,居赛派的哥哥随后落网。虽然罪恶得到了惩治,但两个孩子的童年也被永远的蒙上了阴影。陌陌影视陌陌影视狩猎2016他叫我马拉拉神探可伦坡第十一季困兽2001出柜第4格画壁托勒密·格雷最后的日子第一季欲念纽约圣诞节恶搞之家第十七季欢天喜地开心鬼一路向暖第二季神鞭1986生化战士:王者再临寅次郎的故事46:寅次郎的相亲雪人亲吻的人们高山下的花环1985迷案追踪英格兰奇葩联合谋杀事件爱上我父亲的情人朱莉娅的困扰
长篇影评
1 ) 宝琳·凯尔评《擦鞋童》:电影与世界【译】
作者:Pauline Kael
译者:csh
译文首发于《虹膜》
当《擦鞋童》在1947年上映的时候,我独自到影院去看了这部电影。在那之前,我刚刚与恋人进行了一场可怕的争吵,处于一种难以理解的、绝望的状态之中。我走出影院的时候,已经泪流满面。在无意之中,我听到一个大学女生对男友娇声抱怨道:「我不明白,这部电影究竟有什么特别的。」我走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哭泣着,我已经不知道自己的眼泪究竟是为什么而流的了:是为银幕上的悲剧,是为自己的无奈,抑或是为了方才的疏离感——为那些体认不到《擦鞋童》的光辉的人。如果他们感受不到《擦鞋童》的光辉的话,他们又能感受到什么呢?我如此强烈地认同着那两个失落的男孩,这也影响了我对这个不满意的顾客的态度。我不仅仅只是单纯地怜悯、厌恶她,我对所有的事情都充满了绝望……后来我才知道,和我吵架的那个男人也在同一天晚上离开了,他走出家门的时候同样流着眼泪。但是,我们为了彼此、为了《擦鞋童》所流的泪,也没有能够让我们走到一起。正像《擦鞋童》所展现的那样,生活太复杂了,我们无法得到一个简单的结局。
《擦鞋童》并不是以浪漫主义或情节剧的模式构思的,它属于那些最罕见的艺术作品,几乎完全从人类经验的洪流中涌现出来。与此同时,它并没有磨平原始的棱角,也没有失却大多数电影失却的东西——人类情境中的混乱与意外。詹姆斯·艾吉在观看这部电影时的直观反应是:「《擦鞋童》可能是你所看的最美丽、最动人、最触动内心的一部电影。」但在几个月以后,他收回了自己对它作为艺术作品的评价,他写道,它不是一件已经完成的艺术作品,而是「艺术的原始状态,至多是艺术粗糙的质料。」我想,他应该相信自己的最初的感觉:《擦鞋童》的伟大,恰恰在于它触及人类情感的力量,它未曾经过加工,未曾被框定成某种东西(一种所谓的模式?一种结构?),它也绝不可能由这种结构组成。我们所接收到的,是某种更为赤裸的东西,是某种从银幕上倾泻而出的东西。
1960年,奥逊·威尔斯对这部影片的这种品质表达了敬意。他说,「在处理摄影机这方面,我觉得自己没有同仁。但是,德西卡可以做到的事情,我缺无法做到。我最近又看了他的《擦鞋童》,我发现摄影机消失了,银幕消失了。那就是生活本身……」
当擦鞋童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生活》杂志写道:「这部意大利新作将会震惊世界……它将会成为一个拳头,打在美国观众的肚子上。」但是,很少有美国人感受到了自己肚子上的那一拳。或许他们就像那个大学女生一样,他们需要一个真正的拳头,才能获得某种切身的感受。又或许——从一个更为良善的角度来说——他们害怕电影中的痛苦。几乎每个人都听过《擦鞋童》——它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著名的电影之一,但有多少人真正看过它呢?甚至连许多意大利人也没有看过。正像德西卡所说的那样,「对于制片人来说,《擦鞋童》就像是一场灾难,它的成本不到一百万里拉,但在意大利的观众却很少。因为它的上映,撞上了一波新的美国电影浪潮……」或许在美国,人们之所以不看这部电影,是因为它被宣传成一部社会抗议电影——这就像是把《哈姆雷特》看作是处理权力斗争的政治研究之作。
《擦鞋童》拥有某种美感与朴素感,它们指涉着那种伟大的情感,这在电影作品中是非常罕见的。如果你想要举一反三,可能只能在电影媒介之外寻找——如果莫扎特撰写了一部以贫困为背景的歌剧,或许就能创造出这种痛苦的美。这部由切萨雷·扎瓦蒂尼的「社会抗议电影」,已经超越了它的目的。它以一种抒情的方式,探索了两个被社会背叛的男孩,背叛彼此与自我的过程。这两位年轻的擦鞋童,在战后罗马的冷漠中,维系着他们的友谊与梦想。但是,当他们因黑市交易被送进监狱的时候,却被自己的弱点和欲望摧毁了。这是一场悲剧性的探索,它聚焦于纯真之物的衰败。它是一部强烈的、富有同情心的电影,更重要的是,它是一部人道的作品。
2 ) 9月5日 于法国电影资料馆
放映厅很大,上座率百分之70,一半观众是老人。老人们见面时,几个老朋友隔着好远互相问候,影厅像是一个和谐的小村子,电影村。
我这么大的年轻人差不多占百分之三十,是电影村的新生代。和平年代的我们在影院看着影片中战后意大利的孩子,而他们在影片中看着经济萧条下美国的卓别林。他们为了自由爆发一阵骚乱,而我们噤声静坐。
故事的开头简单而轻松,当两个男孩骄傲地骑马走过银幕时,观众席中传出阵阵笑声。当小男孩振振有词的说,“我们是一伙的!”时,我们能感觉到他初入世故的自豪:我与人结盟,为人所信。
紧接着,剧情急转直下。不得不赞叹这两个小演员的演技,在被警察推着去警察局时,把孩子的无知与不加掩饰的恐怖诠释的特别到位。
其他的剧情简单明了,成人的世界有信任,也有阴谋与背叛。现如今的年轻人也已经将这些规则烂熟于心,所以淡然地看着孩子们之间信任与友情的崩塌——作为成长的必修课。其中最让人心疼的就是那个有病的小演员,他被大家所保护,也对世界充满善意。当他的妈妈没有来看他时,他委屈的哭了,也引得我眼眶一热。难道每个孩子的童年都有让人空等,不守信用的家长吗?
最后以死作为结局于我而言过于平淡,因为比起直面世间之恶,死简直是最简单的办法了。那匹白马在友谊消散之后寥然走远,放映厅的灯光亮起,bon ben... 欢迎回到成人世界。

3 ) 《擦鞋童》孩子知道!战争是什么
题记:
如果我们硬要说这些孩子有罪的话,那么,那么我们这些大人首先要受到惩罚
――――影片台词
[img]http://202.108.15.241/boardfile/movie/20061/20060105203001.jpg[/img]
在影像里孩子们的命运最容易打动观众的,影片开头擦鞋童们利用黑市交易换取了一匹马。当孩子策马驰骋导演赋予了自由和童真的意义,骑马的开心自由和后来因为参与诈骗的被教养管束的对比,那些在街头和人擦鞋顺带销赃的孩子是战争造就的必然,令人辛酸。他们根本看不清未来的走向,直至被人利用充当诱饵,无辜的孩子在战败国是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在囚车上孩子通过铁栅栏目光充满着诉求和爱怜,铁栅栏代表着他们失去自由的开始和骑马的快乐互为参照。音乐也恰如其分烘托了这样的情绪,逆光拍摄的他们进入牢房的镜头更让观众产生对于他们命运的联想。教养院院长查房时和幕僚的对话里导演刻意加入了对这些孩子命运忧患的话语,矛头直指社会不公平和现实的动荡。
孩子在监狱里饿着肚子而唆使他们犯罪的巴尔特一伙却悠闲地在外面吃着牛排,少年监狱里卫生的糟糕表明着成人社会对于少年命运的漠视,这样的设计无疑加强了影片现实批评性。而监狱中陷在耶稣神像在阴影里的存在有着导演对于宗教的怀疑,现实的严酷和上帝的缺席造成的疑问。
在教养院里有个细节十分有趣,看守扣押孩子的苹果,孩子用烟卷和看守换火柴,这些细节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意大利当时经济的窘迫和物质的匮乏,这也是孩子们充当黑市贩卖的重要原因。而狱方利用假装鞭挞从而产生恐惧让孩子招出幕后的做法却反证了欧洲司法制度的严谨。在监狱放电影的戏里银幕上出现的字幕是自由世界的新闻和这些成人社会造就的少年罪犯形成了极大的讽刺,法庭审判时擦鞋儿童穿过威严的法院院子的场景孩子们仿佛被高墙压迫着,这些带有导演主观判别的镜头我们看到导演了对于孩子的怜惜和同情,也描绘了监狱对孩子心灵的扭曲,为了各种目的他们打小报告,拳头说话,这些成人世界的龌龊在监狱里成为孩子的人生,导演通过孩子们的沉沦控诉悲惨的世界,他们是不公平社会的牺牲品,因为过早卷入社会,他们往往陷入了自相残杀的境地。
同其他新现实主义大师相比德·西卡更加注重对于儿童在战败后悲惨命运,讲述他们因为社会动荡造成不公而导致的不幸境遇,其后他的《偷自行车的人》1948成为了那个年代的代表作,而《擦鞋童》也因为它流畅的叙事和生活化的表演以及人性关怀因而获得第20届的奥斯卡“特别荣誉奖(也就是以后的最佳外语片奖)
片名:《擦鞋童Shoe-Shine》1946意大利
片长:90分钟
导演:维托里奥·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8.6/10
演员:Franco Interlenghi、Rinaldo Smordoni
个人评价:艺术性8 欣赏性7.5(导演最好的作品)
此文首发于《DVD银幕内外2005.12》
独立影评人:卡夫卡·陆KavkaLu
版权所有,请勿私自转载
联络方式:MSN:[email protected]
邮箱: [email protected]
4 ) 社会如此不公,给了孩子们不应承受的沉重。
《擦鞋童》是一部抗议社会的电影,更是一部不朽的现实主义杰作。它以诗意般的手法,诉说了在战后罗马经济凋敝,人心彷徨不安的时期里一些身处社会底层却天真烂漫、心怀梦想的孩童被社会所背弃,相互背弃并背弃自己的过程。将孩童置于社会的黑暗中自我沉沦,是导演对当时意大利社会黑暗现实的抨击和控诉,显露着人性的光辉。正如保利娜·凯尔所说“这是一种人道。”在电影中,导演没有玩弄过多的电影手法,但却将其裹上了一层特有的清冷和粗粝。使我全然忘记了摄影机的存在,并有种直抵心灵的深的感触,对片中主人宫朱塞佩和帕斯瓜尔的凄惨遭遇以不忍和同情。 可叹,世事无常造化弄人。就在两位男孩还沉浸于购得"狙击手"的喜悦之中,社会给了他们当头一棒——被算命师揭发而后锒铛入狱,是其二人被社会所背弃的一个体现。而朱和帕二人被分在不同的牢房中,是其被社会所背弃的又一体现。这些死守规矩之人是如此残忍而不近人情,将两位不分彼此的好友拆散开来。 可笑,经不起考验的人性。警员将皮带抽出佯装抽打朱塞佩,以怀柔之策让帕斯瓜尔说出实情。与其说他们利用了帕对朱的真心,不如说是导演对孩童之善的赞扬及对无辜孩童的不忍之心。而这一切,朱赛佩毫不知情——他只知道帕是他痛恨的“告密者”,是帕让哥哥受到牵连,使得朱最后走火入魔,受他人指使而陷害于帕。这强烈的反差,是如此的无情,它化作一条无所顾忌的鞭绳,抽打在每个观众的心上,疼痛难忍。 可悲,毁于软弱的友谊。影片将尽之时,帕终于得以让朱一尝他所受皮肉之苦,却让朱失足落于桥下而死。帕和瓜二人既背弃了自己,也背弃了对方,而这一切都属于社会之恶,是社会的冷漠人情让帕朱二人变得如此不幸。社会让朱收到背叛,让帕吞下千夫所指的恶果,他们在最后又以一种凄惨的结局结束,让整部影片染上了一层浓黑的悲凉。 狙击手眨了眨眼,随后头也不回地遁入了无形的黑暗中,似是看不过这人世悲欢,似是奈不住这人生凄凉。
5 ) 失去的童真 凡人的淚影
影片開頭擦鞋童們利用黑市交易換取了一匹馬。當孩子策馬馳騁導演賦予了自由和童真的意義,騎馬的開心自由和後來因為參與詐騙的被教養管束的對比,那些在街頭和人擦鞋順帶銷贓的孩子是戰爭造就的必然,令人辛酸。他們根本看不清未來的走向,直至被人利用充當誘餌,無辜的孩子在戰敗國是無法把握自己命運的。在囚車上孩子通過鐵柵欄目光充滿著訴求和愛憐,鐵柵欄代表著他們失去自由的開始和騎馬的快樂互為參照。音樂也恰如其分烘托了這樣的情緒,逆光拍攝的他們進入牢房的鏡頭更讓觀眾產生對於他們命運的聯想。教養院院長查房時和幕僚的對話裏導演刻意加入了對這些孩子命運憂患的話語,矛頭直指社會不公平和現實的動蕩。
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中幾乎每部都有孩子(尤其男孩)為主角或配角,通過孩童無辜之眼去看千瘡百孔世界,更為慘痛。通過孩子的眼睛所帶出來的震撼性可以說是最強烈的。前者有羅西裏尼的《德意誌零年》,德西卡的《擦鞋童》;後者有羅西裏尼《羅馬不設防的城市》,德西卡《偷自行車的人》和《孩子在看著我們》;安東尼奧尼《喊叫》中則是小女孩。
“我的用意,就像我曾經說過的那樣,是要尋找日常生活中的戲劇元素,從其他大部分人看來早已成為老生常談的材料中發掘出神奇的因素。”說這句話的人,是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的旗手維托裏奧·德·西卡。作為世界電影史上最重要的電影思潮之一———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運動的主要發起人和代表人物,德·西卡通過一幅幅深刻豐滿的寫實畫面揭露社會現實,對世界電影的發展和走向起了深遠的影響作用。
1946年,德西卡完成了他的重要影片《擦鞋童》,上映之時,這部才華橫溢的新現實主義影片在國內票房慘敗,幾個月後,獲第20屆奧斯卡特別榮譽(最佳外語片)獎,它是雷諾阿的《大幻影》獲最佳影片提名後,第一部獲得奧斯卡獎的非英語影片。是繼1943年《孩子們在看著我們》之後又一部以兒童問題為題材的影片。1948年,《擦鞋童》獲得了奧斯卡的特別獎,奧斯卡組委會是這樣評價的:“這部優秀的電影把我們帶入了處於飽經戰爭創傷的國家中的悲慘生活,它向世界證明了創造精神可以取得對一切災難的勝利。”事實上,正是這部電影推動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設立。兩年後,德·西卡憑借著被後人認為是影史上最偉大的電影之一的《偷自行車的人》,再次獲得了奧斯卡的特別獎。
德西卡是著名的意大利導演,他擅長拍攝社會底下人們的生活,而《擦鞋童》就是一部用孩子為題材來反映二戰後的現實生活。這跟儸西裏尼的《德意誌零年》有著某些相同點,但不同的是,《擦鞋童》是一個從社會的殘酷到純潔的友誼被破壞的過程。而《德意誌零年》就是用黑暗的現實和人心的險惡來腐蝕孩子的心靈。基本上兩片所引出的問題都是一樣的,只是,《擦鞋童》中關於孩子們之間的友誼是最讓我心痛不已的。
因爲貧窮,馬克和朱佩塞兩個年齡相符的小男孩跟其他受戰爭迫害的孩子一樣,爲了生活,他們都成爲了擦鞋童,因爲金錢,他們兩人被人設計而捲入了一宗犯罪案中,結果兩人都被關押在少年所當中。在少年所裏面,很多小小年紀的孩童都流露出比實際年紀更成熟的表情或者行爲,很顯然,大家都是爲了生存,大家都是爲了在這個無政府狀態下鞏固自己的小小地位和稱王稱霸。對於馬克和朱佩塞這兩個單純的少年而言,分離成爲最殘酷的事實。馬克像哥哥那樣愛護著朱佩塞,在當中這個混亂的社會中,朱佩塞可以說是幸福的,他有父母的愛有馬克的愛,不過,他畢竟還是個孩子,小了心眼的他很容易被外界所影響,因誤信謠言,他誤會了一直愛著他的馬克。背道而行的兩人最終相遇在死亡邊緣,馬克誤手殺死了朱佩塞或許真的是最好的結局了。“死”這詞在當時可以說是一種解脫也可以說是另一種生存方式,這只是靈魂方面而已。很多人都說茍而殘缺,這就很顯然了。
影片有兩個最重要的場景,其一是開始兩個孩子在馬場騎馬,然後他們為別人擦鞋,買到馬後在大街上騎馬穿行。外景拍攝,攝影機自由地運動,代表著孩子單純而美好的願望。相信這一幕會感染很多人。後來他們被抓,攝影機通過囚車的鐵窗拍車外的情景。他們已經與自由美好的外部世界隔開了。第二個重要場景也是本片筆墨最多的場景少管所,在攝影棚拍攝,高大的少管所骯臟而陰暗,他們的小囚房則更加擁擠,本來善良仗義的孩子在這裏變得好鬥猜疑和充滿怨恨。此外,影片還展示了擦鞋童的工作場景,酒店門口很多美國大兵和妓女走來走去,這是一個被蹂躪的國家;德西卡拍攝的法庭高大嚴整,一群孩子在它面前顯得是那麽矮小,他們的命運是可以被隨意決定和宰割的。
關於孩子們生存的那個少年所,正確地來説是個年輕化的監獄。這些百分之九十都是無辜的孩子還處於幼童時期就無端端地被關押在這個惡劣的環境當中。片中,那個有肺病的小男孩無意中表達了一種希望,只是,最後他還是死了,馬克心中的希望也跟隨而逝。導演讓很多人間的醜,善,美,惡都附在不同的孩子身上,用他們來表達這個世界上一切的情感和現狀。如果慢慢細嚼這片,很容易會發現每個孩子都有著不同的使命,他們用自己的遭遇來告訴所有的觀衆什麽才是現實。
《擦鞋童》這部影片的一個配角的故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小男孩被關進少管所後天天盼望著自己母親能來探望自己。當他滿懷期待地等來探望的時刻時,卻發現來人不是自己的母親。母親的朋友給他帶來了一個大包裹與一張卡片,小男孩看著這些少管所裏的“奢侈品”卻一點都高興不起來。他抱著大包裹走進牢房大門,邊走邊想著自己母親,想著想著忍不住擦起了眼淚。小男孩委屈的樣子讓人心生憐惜,他在牢友中間坐下來分享了母親帶給他的東西後,看著母親給他的卡片,他想了很多為母親不來看他開脫的理由……
那個曾經跟朱賽佩要錢給他媽媽的小女孩,曾經跟在警車的後面走,在法庭上充當了“皇帝新衣”中說真話的孩子,她罵朱佩賽雜種、惡棍。是導演對童真喪失的譴責。街頭孩子們湧向法庭,仰著脖子看頭頂上的雕像。巨大的空間對比與反差是不公平審判的伏筆。
有靈性的動物也經常出現在電影中,用做暗喻。片中,馬克和朱佩塞的愛馬“狙擊手”轉頭而跑,這一幕讓我想起塔可夫斯基的《安德烈盧夫斯基》中的那匹跌倒在地上的馬。馬的離去,馬的受傷不都是呼應著主人們的處境嗎?不都爲了影片增強了感染力嗎?
《擦鞋童》是“新現實主義”電影運動的一座裏程碑,它的許多創新之處都引起了當時的批評家們的一致歡呼。實地外景拍攝、啟用群眾演員、紀錄片攝影風格的運用……這些出自經濟考慮的革新手段同時也是一種藝術上的選擇。寫實帶來的效果是強有力的,特別是在兩個小男孩被抓進少管所之後,觀眾真切直觀地目睹了監獄內犯人之間的欺壓與屈服以及監獄看守的現實生活。德·西卡自己作為一個優秀的演員,具有一種特殊的能力,能夠引導群眾演員做出完美的近乎專業的表演。那兩個小男孩面對冷酷無情時所表現出來的柔弱和敏感既出自於他們自己對所演角色的熟悉與理解,又深深地打動了觀眾。
《擦鞋童》作為“新現實主義”電影潮流的引發作品之一,它所掀起的轟動效應是世界性的。它是第一部獲得奧斯卡獎的非英語影片,征服了世界上所有還未被戰爭泯滅了同情心的觀眾。
6 ) 从梦想开始,以绝望终局
镜头一:当少儿看守所的副所长向所长抱怨,孩子们恶劣的生存现状时,所长告诉他,“不要把这些‘无谓’的东西想的太多,我们管理的是看守所,不是托儿所,不然的话,你永远只能做副职。”
镜头二:当两个小男主角居塞派和帕斯克里特在看所所内为了所谓“告密”事件互殴时,副所长“苦口婆心”的告诫他们:“不要再闹事了好不好?我可不想因为你们而永远烂死在这个地方!(这位副所长是这部电影中唯一一个可以被称为“好人”的成年人,但他也只是一个“好人”,一个软弱的人而已)。
镜头三:擦鞋童们蜂拥进了设置在某座貌似意大利古老建筑内的法庭里(审判居塞派和帕斯克里特)听审(结果却被赶在法庭门外),他们看着这座建筑内一尊大型的某位古罗马女神的雕像,胡乱猜测这这位女神的身份。(原谅我才疏学浅,我也不清楚她是谁【笑】好像是公平女神。)。这些可怜的孩子们本该是这些古老的文化遗产的主人!但他们现在却被迫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
关于开篇与结局:
电影开篇:居塞派和帕斯克里骑着靠着自己辛苦"工作”买来的骏马驰骋在罗马城的街头,让他的同事们(也让电影观众们)感觉如梦似幻。
电影结局:帕斯克里特在激愤之下,失手打死了居塞派,他怀抱着居塞派的尸体嚎啕大哭,悔恨不及。那匹曾经让他们这对好兄弟为之骄傲的骏马也早已跑的不知所踪。
一个从梦想开始,以绝望告终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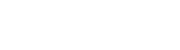




















战后罗马,「贫穷把所有人都变成了罪犯」。「孩子们就没有未来吗?」孩子们在大人们的欺骗、栽赃、抛弃中互相背叛、反目,然后在还是一个孩子时死去,或者长成一个大人。【-你们为什么要买马?-因为想骑。】孩子说,狙击手跑起来就像飞。可马儿终得自由飞奔,但他们留在了原地。擦鞋童,每日拂去脚下灰尘,自己则低入尘埃中。7/10|长成大人的男主角七年后成了「浪荡儿」
《偷自行车的人》前两年,德西卡的又一部最佳外语片;可惜看的时候太困了,最后半小时,基本处于昏睡状态。。。。。。太对不起本片了~~
我是一次次重新燃起希望,希望能看见这两个孩子再像最开始那样骑着马穿过街道,但是到了最后也不可能了。德西卡可能就是用这样扼腕的绝决来质询着现实的残酷。情节推进很有节制,一点点放大,一直到无可挽回的结局。
巴赞说:“德西卡对人物的爱从人物自身反射出来。”而这部《擦鞋童》体现得尤为显著,以其对成人社会多元化的批判视角来“反射”主角朱塞佩与帕斯克里特两名男孩的悲剧命运。走私犯们利用孩子销赃,警察们则将孩子看作破案的线索与工具,不惜使用威胁花招来获取信息,律师也是把诉讼案当作牟利的工具,从本质讲,三者无异。在德西卡的影片中,不存在好莱坞式的代表正义与公平的强者英雄,有赖于影片的新现实主义式纪实风格,死亡正如孩子们被捕般令人意外,这突如其来的惨剧正如“皮娜之死”般还未来得及激起涟漪,就已结束收场,却深植于观众心中,尽管德西卡或多或少也放置了一些天主教的元素用以“拯救”他们的灵魂,但宗教的代表者牧师也并未真正关心少管所的孩子,他们所造成的意外间接导致朱塞佩的死亡。唯一的遗憾可能是淡入淡出稍显累赘。
一个少年犯说少管所有吃有住还有娱乐—电影,简直是天堂。可怜啊。然后监狱放电影时几个人逃狱,朱塞佩和另一个人逃了出去,混乱中一个本来得病活不久的善良小孩被踩死了,帕斯克里特带警察去他和朱塞佩寄马的地方抓朱塞佩,帕斯克里特激动中打死了朱塞佩,痛哭不已。马跑走了。环境造成的悲剧
男孩触石而亡,骏马翩然离去,这一笔胜于后继者幸福的拉扎罗。德西卡比特吕弗高妙多了,他永远能用看似绝对现实的局部,演绎出一个解释所有世代的故事。是成长破灭,是监狱风云,是战后观察,是命运的踪影。
當輕快的主旋律再度響起,童年歡樂的消逝與純真友情的碎裂,正如馬作為自由的象徵,在黑夜中消失無踪。心之所向的神槍手被理性人的利益計算衡量;為友情兩肋插刀被視作精神不穩定的暴亂因子。純真在這年代成為一種罪惡,孩子被利欲熏心的大人拖進作惡的泥潭,又要承受他們所建立起體制的羞辱,接著,告發與背叛的惡行如行雲流水般流暢——就像白紙被揉出難以復原的皺褶,並用墨水潑灑黑漬。這一頁頁殘碎不堪的紙張拼湊起未來世界的模樣。
儿童的友情就如山间的溪水,自然美好纯真童趣,但同时也因为现实而有诸多的可变性,一个弯道,一块石头,一场误会,都会让一切走向不可挽回的局面。少年犯之监狱风云之外的背后是战后意大利的一种现实,两个少年残酷童年悲剧的背后是社会的无奈和成人以及教育的缺失。结局真是太悲惨了。
在87分钟的体量之下能够完成如此复杂精妙的剧作属实令人震惊,难怪威尔斯如此推崇德西卡,更是将这部《擦鞋童》称为“唯一的杰作”,以我看来是因为电影在叙事主题上采取了“隐而不现”的手法,主题始终未被特意点明,一系列事件既有直面现实的冷峻,又保持着含糊的诗意。并非编造现实,而是保留了现实的完整性,使电影成为现实的渐近线,生活本身变成有声有色的场景。正因为德西卡在电影中所采用的有关分立事件的插曲式片段并不遵循严格的因果关系,而是靠情感基调来组织,因此它们形成并表现为一个中心主题的多个侧面。而将所有的侧面集合起来,我似乎窥视到了威尔斯电影中所透露出对“生”的价值审判,德西卡基于新现实主义的纯粹表达将“生”同义为“求生”,并对这一行为进行一再否定,直至抹杀干净。通过抹杀战后儿童求生权利悲观地再现了现实。
让我不知怎么想起大岛渚电影里那个卖鸽子的少年,同样是战争后的土地上发生在一个少年身上的惊天动地的纯真与卑鄙的撞击,同样是难以抑制的难受。最难忘的始终是阳光下骑在马上两个少年的微笑,明媚得宛如冲破黑暗之神。但那匹象征纯真与梦想的马终究是独自跑向了那片雨雾蒙蒙的黑暗里,不禁潸然。
少年版监狱风云,或者应该反过来说,四十多年后林岭东拍的《监狱风云》是成年版擦鞋童。入狱、对立、谣言、告密、暴打、越狱,所有元素都包含了。意大利裔和香港导演可能是世界上最会拍兄弟情仇的两拨人。因白马而起,遇白马而终,用说不出话的动物来目睹命运悲剧。
导演想说的也许正是那句:如果说这些孩子有罪的话,那我们全部人都有罪。友情在变化的环境面前那么脆弱 T T 这让我更爱那个肺结核小孩,疾病和环境都没有夺去他的单纯善良 和对大海的向往。|| 这群小孩被拍得太有型了,而且导演你摸着良心说真的不是在拍基片嘛,还抽皮带什么的真是够了!
成长时期的友情就如刚出窑的白瓷,晶莹剔透却又显得不堪一击。曾经的快乐与友情,曾经的信任与崇拜,因为算计与误会,因为煽动与报复,因为儿少时的那份尚未脱掉的稚气,白瓷被人一撞,碎了一地。再也回不到过去,两人骑在马上,其乐无穷的日子。友情却仅仅只是在社会压制下破碎的事物之一。
德·西卡的这部新现实主义杰作将镜头对准社会底层。看过这部影片我对片中这些成人的所作所为感到恶心,这两个小孩确实没做错什么事,他们被成年人利用来犯罪,那些警察也好不到哪去,利用小孩之间的友情来套话,而那个辩护律师是个什么嘴脸也就不用再说了。他们做的最错的事就是包庇了那群罪犯。
畏难而退 还是不习惯新现实主义
@小西天。被迫成人的儿童:被生活所迫过早地上街糊口、被刑罚所迫失去了纯真和友谊。逃得出牢狱,也终逃不出险恶的人心、惨淡的现实和死亡的阴影。德西卡对希望的表现形式总那么卑微无害,不过是一匹马、一条狗、一辆自行车、一间刚能容下一张床的小屋。纵是如此,亦不可得。
『四百击』一定受到了这一部的影响,但这对好基友比起安托万实在凄惨(狗血?)多了...『战火』里表现过的穷苦的意大利小孩群体的故事,果然只要是小孩子就是有办法在悲惨的时代制造出快乐的气氛,无奈时代太坏,孩子太弱小。
之前有《孩子在看着我们》,之后有《偷自行车的人》,德西卡常用孩子视角的纯真来观看现实世界的丑恶。使之更为突出,“你想要什么的时候得反着说,就像和你朋友在一起,你要说你恨他”,用欢乐——这部里的骑马,偷自行车里父子俩下馆子——来映衬之后更残酷的现实,象征性的自行车与白马都无可奈何的失去了。只是这部还不够成熟,不及两年后的《偷自行车的人》。
首个奥斯卡“特别荣誉奖”(最佳外语片奖前身)
1948奥斯卡荣誉奖(最佳外语片)。1.揭露了少管所(监狱)对底层孩子们的戕害。2.看默片时的越狱行动,硝酸胶片起火同[天堂电影院]。3.死于踩踏的小男孩看着银幕上的大海,绽放出世间最美丽的笑容。4.新现实主义将陷入的死胡同初露雏形:竞相比惨的情节剧模式。5.“狙击手”白马贯穿头尾。(8.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