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M(鲁妮·玛拉 Rooney Mara 饰)和C(卡西·阿弗莱克 Casey Affleck 饰)是一对十分恩爱的恋人,在一场车祸中,C不幸死去,将心碎欲绝的M孤零零的留在这个世界之中。然而,C却并没有真正的离开,他依然以灵魂的形式留在他和M一起生活过的那幢房子里,留在M的身边,沉默而又深情的看着他生前的恋人的一举一动。 C的离开让M陷入了绝望和痛苦之中,她哭泣、抑郁、自闭,仿佛生活在真空里。M决定从房子里搬出去,可是C无法离开,他只能继续的等待着等待着,支持着C的,是M曾经留在墙缝里的一张字条。新的住客来了又走,无限的时间永恒的流逝着,某日,拆迁队将C所在的屋子拆除了,一片废墟之中,C发现,原来被困在无尽的等待中的,并非只有他一个。陌陌影视陌陌影视傍晚她敲开我的门家在阿拉斯加 第一季迷线魔符地球最后的导演雨城故事黑袍纠察队第二季幸福到万家梦游小人国博物馆的秘密第一季她和她的航天员第一季狄仁杰之亢龙有悔世界属于你昌迪加尔爱曲紫红色自由GAMERS电玩咖!风云岁月机械师2:复活(原声版)孤独的美食家第八季千面魔女地藏王传奇沸腾校园无眼杀手我的机器人女友终有一天2019大司机弓
长篇影评
1 ) 他,在等一部合适的电影
导演大卫·洛维:
很早的时候,在我的头脑中,就住着一个鬼,一个穿着床单的鬼。我爱这个鬼,这个穿着床单的鬼,以前,我也尝试着去拍关于他的电影,但是都没有成功。现在看来,他一直在等着我,等着一部合适的电影。
我和妻子的争吵

在拍《彼得的龙》期间,我和我妻子从德克萨斯州搬去了洛杉矶,我又去了新西兰,那是《彼得的龙》的拍摄地,拍完后我又返回了洛杉矶。离开德州对我来说是很心痛的,因为我和我妻子结婚后的第一个家就在那里,我爱那里,所以我和我妻子会在假期的时候回去德州住。在度假的时候,有一次,我问她:“我们能不能在拍完《彼得的龙》后返回到德州?”但是她说:“我不想回德州了,我觉得洛杉矶挺好的,洛杉矶是个好地方。”就是因为这个意见的分歧,我们发生了争吵。我爱德州,那是我和我妻子曾经一起幸福过的地方,我是属于德州的。
就因为意见的分歧,我们开始了争吵,我们坐在在沙地上,画着直线,线条的长度表示着为了彼此我们还能走多远,我们就这样探讨着我们的未来。在争吵时,我似乎一度看到了我们两旅程的结束,我常常回想那个时刻,原来一件如此简单的小事就可能让我们的幸福结束,我感到如此的困扰和悲伤。但幸运的是,我们冷静了下来,并达成了和解。后来我把我们的这段争论的内容写了下来,并且变成了电影的一个镜头。
关于这个镜头的剧本内容,我写了差不多有10页的样子。我还记得那天,卡西和鲁妮在片场要表演这个镜头,而我的妻子也在那里,当卡西·阿弗莱克和鲁妮·玛拉的对话中出现了我们曾经争论的内容时,我看到她翻了翻白眼,哈哈,当然她是不会介意的,她是完全支持我的,她可能在想:“我是非常支持你的!因为你把我们的关系延伸到了艺术创作中了啊。”这个镜头的内容也是其他镜头融合在了一起,按照我们的需要,穿插在了不同的地方。
暖心的朋友;还好我没放弃

当时我还在洛杉矶为完成《彼得的龙》而努力,我在想在这个暑假,我还能做什么呢,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也是最好的时候下定决定去拍这部电影了。
下定了决心要拍这部电影,我就开始通知我的朋友了,真的,我只叫上了我的朋友,他们都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打电话给他们:“嗨,朋友,你想来和我们一起干这个大事吗?”“这个夏天,你们愿意花两周的时间待在德州吗?” 我的摄影师安卓(Andrew Droz Palermo),艺术指导杰德(Jade Healy),服装设计师安内尔(Annell Brodeur)等等,他们都来了。我的团队是很小的,也很团结和紧密。在前面的一段时间里,我必须花狠多的时间待在洛杉矶完成彼得的龙,在周末的时候,我就飞到德州,我们会一起去找适合拍摄房屋。我们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准备过程,一切就是那样的有组织地走到了一起,但准备过程的缺失的确会造成一些问题。。
我是直到完成《彼得的龙》的两天后,我回到了德州,整个拍摄才完全开始步入了正轨。在拍摄中期的时候,我差点就放弃了这部电影,因为那时候,在很多次的拍摄中,达不到我想要的那种方式,但同时我也发现我们的拍摄已经太深入,以至于无法后退。那个时候,我失去了信心,有时候,我都被自己说服了,我甚至告诉自己:这项工作怎么这么的复杂和困难!这完全就是不行的啊。我在那个时候,已经准备好去失败了。但是我有最好的朋友,最好的组员,他们鼓励我,我们一起努力,坚持下去,总会找到解决方法的。
绝妙的方式;我们的幸运
因为我们是自筹资金的,所以一方面在使用钱的方面没有大的束缚,有足够的资金让我们使用而不会造成我们的破产,不需要去敲别人的门去要钱,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资金预算都是比较小的,我们得想一些聪明的办法去用好钱。
大家知道我们拍的整部戏都在这个房子,最后这个房子也被拆了,这个是真的拆,并不是什么模型,或者是什么胶合板的墙。所以如何找房子真是个大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制片人詹姆斯(James M. Johnston)和托比(Toby Halbrooks)就用了绝妙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
他们打电话给了当地的拆迁公司,并且拿到了确定要待拆除的房屋名单,我们就开着车,去看这些待拆除的房子。如果有房子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就打电话给这个房子的房主,问他们是否愿意让我们使用房屋。
后来我们找了一个看起来完美的房子,正是我们想要的那种房子,这栋房子的主人名叫斯库特。在我们的艺术设计师杰德的指导下,我们把这栋房子修复好了,设计了厨房,安装了地板,甚至维修了天花板,最后看起来完全像个温暖的家。然后当我们把它装好了以后,我们又拆毁它,就像电影中那样拆了它。

在这栋房子里拍摄的时候,令我们完全没想到的是,房主斯库特不仅同意把房子交给我们使用,而且在我们拍摄电影的过程中,他还帮了我们超大的忙。他的孙女,那时候正在上高中,在片中成为了鲁妮的替身,而且在片中,她还扮演了其中的一个拓荒者。斯库特也开着一家空调公司,他给我们安装了一种便携式的设备,能把冷空气送进房子里,使得我们能够在德州的酷暑下保持干爽。
我们是非常欢迎他们来到我们的拍摄大家庭的,他们帮了我们很多。当然,他们也来到了圣丹斯电影节来参加我们的首映礼,他们同我们一样为这部电影骄傲。我觉得没有他们,我们不可能完成这部影片。
还有点花絮:
1. 本片拍摄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艾尔文市,本片的资金来自导演大卫·洛维执导的上一部影片《彼得的龙》(就是那部美国动画电影)
2. 电影从一开拍的时候,就是对公众保密的。直到电影拍完了,都过了几个月了,导演才宣布“咱们的电影拍完了,电影叫鬼魅浮生。”
3. 2017年1月22号,这部影片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而早在首映之前,A24电影公司就获得了电影的发行权。
4. 鲁妮·玛拉吃派的镜头只拍了一次就成功了,一次就成功哦!!还有啊,关于鲁妮吃的这个派,导演大卫·洛维说:“鲁妮吃的那个派啊很好吃,那个派是素食巧克力风味的派哦!”
给大家解释下为啥叫素食巧克力派,一般做巧克力派嘛,都要用到鸡蛋,黄油,牛奶等等和面粉和在一起做小面饼,果酱拿来做馅,然后在巧克力酱那里滚一转,就好了。所以素食派意思就是不用到鸡蛋或者不用牛奶来和面,或者不用黄油啊等等。
未经同意不得转载 ,本文翻译整理于2017年8月12号,后面还有2000多字还未整理
有空再整理分享给大家哈。BYE
我完成的其他花絮故事:
《三块广告牌》的幕后以及致敬! 你知道科恩嫂的花头巾是在向哪部片子致敬吗?知道片中的小鹿是谁吗?你知道弹吉他的伍迪·哈里森吗?你知道......
裴淳华和克里斯蒂安·贝尔的新片:关于《敌对分子》你不知道的事
卡西·阿弗莱克、鲁妮·玛拉的新片《鬼魅浮生》幕后故事,花絮,还有很多,还算可以吧
2 ) 对万物的赞美都可以给如诗的你
彼时2018年2月1日凌晨,严寒中颤抖着开始码字的我,已经彻底分不清是受冷的缘故,还是在为一次差点错失的邂逅、后知后觉的喜爱而激动了。
我看了四遍《鬼魅浮生》。前三次观看,每次相隔不超半小时,而我刚刚结束了最后一次。这样的观影经历,在成为影迷的五年来,从未有过。
一刷罢,别说丧起来,我甚至不觉得自己看明白了。而且遗留着对部分情节点的不适(“闹鬼”后墨西哥妈妈的不真实反应、派对上莫名其妙的高谈阔论)。纸条上写了什么?最后余留的新鬼魂拿不到纸条还怎么循环?从高楼跃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是穿越到过去、重启了时间、还是进入了未来?带着这些自惭形秽的疑问,我翻遍了几乎所有长短热评与讨论区,却没有得到任何统一的答案。涉及到本片概念设定的评论,有的模糊其词,有的不成系统,回放对照也均驳多于证...我陷入了对自我和对集体的双重怀疑,是我脑子不好用还是片子本质意识流?强求逻辑却忘记意会?说不定如貌相掌握少数者真理的批评所言,北美高口碑和喜欢它的豆友都是文青日常装逼瞎捧?一片茫然中,我几近选择不再深究,随便标记了事,何苦徒添折磨。

但它那股透着坚定、举重若轻一般的极简主义气质是如此迷人,念念不忘着,仿佛我也中了“执念”的毒,不情愿轻易放下。终于,我决定花上属于午夜的92分钟,带着这些疑问二刷之。
脉络全通的快感在白床单掉落的一刻夺然而出。我不敢马上相信。
而三刷,除了确证自己的想法并非一厢情愿的过度解读外,唯余沉醉。
想不到啊想不到,2017年新片中的最爱诞生了。而这竟是一部从9月份就出了资源、我索然地拖了半年才点开的电影。

如果说经过四重滤净后的它终于能在我心里留下相对透彻的印象,那么是的,这92分钟在我一年来的新片观影里,必定是银幕时间最长的一个半小时。这种“长”,不因四倍的累积,更无关其名声在外的“缓慢”节奏,而恰恰是它太快了——在大卫·洛维那个性鲜明的跳切与出神入化的匹配剪辑里,我感知到了它所承载的成万倍以计的象征时间,体验着光阴在光影里绝无仅有的流逝。
如短评所言:唯纸条内容为开放式,整体设定大巧不工而自洽,感知无力仍可解读,非马力克式意识流,劝雾里者勿弃思之。——我认为本片即便被冠以“意识流”之称,也要明确它和泰伦斯·马力克《生命之树》那样全开放式文本的意识流存在本质区别。它的具体设定或许没有达到滴水不漏的程度(无关bug,而是诠释具有选择性和间接性),但在概念层面上,它是绝对自洽且完整的。
本文从这之后就开始全面剧透了,强烈建议观后阅读。
关于设定
关键词:轮回。

首先,很多人认为《鬼魅浮生》讲的是一个无限循环的故事,我觉得并非如此。在讨论之前,如果一定要以更准确的形容取代之,那么,称为轮回可能是最合适的。轮回包含着生死的重复,却并非没有出口;它有它既定的轨迹,却不同于闭合的循环。这或许是更好理解这个故事的基础。
虽然是一部有着常见环形情节概念的电影,但本片的突出之处在于,它从开篇到落幕所展示的并非循环中某个千篇一律的周期(比如《记忆碎片》《恐怖游轮》),而是一次轮回。
如果要尽量准确地概括,那么:这是一个以主角C的两次生命重演为背景、并聚焦于其鬼魂的故事。

我们可以把主角C的出生视为一切的开始。他的逝去使自己成为了一个依托执念而存在的鬼魂。在失去了爱人M留下的、未经阅读的纸条后,它目睹沧海桑田,最后或有意或无意地选择了穿越时空,回到故土,历经无数春秋,终于迎来了自己作为人的再生、并重新见证了自己与M的感情,直到纸条的再次出现——它抠出、阅读,消失。
如上所述,这个故事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循环(循环需要重复性、闭合性)。如本片英文名所示,它不仅是一个鬼故事,更是只关于一个鬼的故事。只不过因为时空穿越元素的加入,经典的宿命论得到了表现,且在故事的最后,经历过穿越的它看到了未经穿越的自己。仅此而已。看到了太多对本片设定的扭曲化、复杂化阐释与评价,是我决定写下本文的动机之一。

但在落幕时刻,经历过穿越的C鬼魂消失了,而另外那个未经穿越的它将何去何从,电影并没有作出交代。可以肯定的是,故事空间内的一切,从这里开始便不会再和第一个时空有完全相同的发展了。未经穿越的C鬼魂很可能不会再有穿越时空的选择,而没有穿越就没有人类文明的重蹈,更没有角色生命的重复——找不到纸条的它,或许会经历诧异和失落,会把一切再次寄托于无尽的等待中,可房屋总有拆迁的一天,爱人无归,失去纸条的它浮尘旅途的终点,或许也就和那位彻底绝望的花被单鬼魂无异了吧。但显然,那已经是下一个鬼故事了,而导演欲尽的一切表达,在这个故事里已然淋漓尽致、无需多言。After all,this is A Ghost Story.
关于情绪
关键词:寄托。

M:小时候我们经常搬家,我会写纸条,把它们叠得非常小,然后藏在各个角落里,所以如果有一天我想回去的话,那里会有一部分曾经的我在等着。
C:你回去过吗?
M:没有。我没有理由回去。
C:里面都写的什么?
M:就只是些古老的韵文和诗歌之类的。或者我想要记住的,生活在那间房子里的日常和我喜欢它的地方。
C:你们为什么搬家?为什么离开那些房子?
M:因为我别无选择。
这是本片开场时C和M之间的对话。在我们不知情的时候,这段对话看起来是多么日常而无关紧要啊。可它不仅给了C鬼魂跨越上万年的执念,也给了最终无从得知纸条内容的观众无限的怨念。
但它的意义远不仅此。这场对话也是本片的情绪奠基,或浅或深,它包含了M和C鬼魂几乎所有感性逻辑的因果。
这段对话至少提供、阐释了这两个客观信息:
第一,M搬家留纸条的习惯、与纸条于她的意义。
第二,M有回来的可能性。但不回来也很合理。

C鬼魂之所以会在深情的目送中选择留下,而不执意追随,在于它相信M留下的纸条是关于这里的、是关于他们两人的,或者说,关于这段M不愿带入新生活的过去。对纸条的寄托是它继续存在的重要原因,也代表着最大“执念”所在。

这么看,“第二次抠纸条远比第一次抠得快”的问题就显得相当合理了。第一次之所以抠得慢显然不是因为难抠,而是一开始的C鬼魂也并不急于看纸条。回顾那次对话后,我们可以想象,如果M有一天回到此地,那么C很可能就是她重游的原因——那个M自小从未找到的、回去旧房子的“理由”。这对C的鬼魂会是何等温柔的安慰啊。如果这一刻发生,那几乎足以诠释纸条本身所及的等重意义。
此外,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一幕:

对M故地重游这一可能性的惦记,乃至对房屋易手后情感找到新寄托的渺茫希望。这一切都围绕着种种寄托而成立。
可如我们所知,不论是墨西哥单亲家庭或是后来放纵喧嚣的派对,都只喂哺了它无止境的乏味与孤独。在经历了第一次错失(快抠出来房子就塌了)带来的无限遗憾、写满孤独的漫长等待、对命运走向无可改变的彻底失落(撞琴的情节)后,这一次,它决定在M离去时就把纸条抠出。与此同时,门又一次被打开,而它虽然再次报以回首,却对继续打开纸条没有丝毫犹豫——

这个微妙的对位细节意味着,不仅执念即将走向了结,它也失去了任何付出新的爱的兴趣,放弃了假装像一个人一样,重新“开始”的任何希望。
这道跨越万年的情绪弧光,更决定了它于我,是永远值得反复品味的电影。从这个角度看,无论它有多少瑕疵,都不影响它是具有经典潜质的。
关于纸条
关键词:释然。

我理解所有看完感到悲伤的人。
在这个鸡汤求毒、以丧文化为主流的时代,在我们仍未摆脱曼彻斯特的海风时,看到一部这样的电影,真的很难不悲伤。但是否如置顶的热门短评所说:C鬼魂看完纸条,就“信念崩塌”了?
不一定啊。甚至于,我想反对,为这部看似小格局、只仗小聪明的作品挽回它最后的不俗。
我对这个时刻的理解:释然。前面所有的铺垫(花被子鬼魂因为放弃了继续等待“他们”的念想而消失、未看纸条的C鬼魂仍未放下 )都诠释了它的设定:执念即鬼魂之魂。执念一消,无论所感几何,一切都会随风飘散,只余留那短暂的光晕,这个光晕,在我看来更像在诠释着释然的美丽。这种释然,无关喜悲。

导演大卫·洛维在有关本片的访谈里也曾不可避免地被问到纸条内容的问题,对此,他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可见并不想对观众做出任何引导。这部电影就像它那披着床单的主角一样,是一个充满感情和温度的“空”壳,纸条的内容是什么,纸条的信息复杂或简单,纸条的能量是正是负,都取决于尚未被理性吞噬的那个感性的你有着怎样的过去,有什么爱情观(乃至三观),甚至因此,如果你愿意,可能从此以后每一次重看,纸条的内容都会随之变化。

而在我眼中,无论纸条被书写了什么,永远共通也永远不变的,是爱与孤独。它绝对象征着存在主义的探讨,而虚无只是一种结论。存在包含着虚无,所以,请不要狭隘地以虚无否定存在。
杂谈
细节、风格与不足。
所有无法嵌入任何版块的所思所感,我都放在了这一部分。
1.我以为的不足——来自一个脑残粉的指出
我深爱这部电影,但我不会否认这部作品的不完美。很奇妙,第一遍看留给我不适的两个情节点:墨西哥妈妈在“闹鬼”后的反应、派对上那次接近5分钟的长篇大论——到最后一次看仍然没有彻底化解。可能除此之外对其他部分的深沉爱意早已无限冲淡了这种反感,但在冷静思考过后,我坚持认为这是不足,也有称其不足的理由。

关于第一个:任我如何尝试找补,也无法让自己相信冷静地蹲下来收盘子会是一个正常人在“闹鬼”(明明是床单怪撒娇对吧)后的正常反应。即便搬离这里是一个正常的理性选择,但面对桌上的杯子腾空飞起和柜子上的盘子屋子里乱飞乱碎,你竟然不是本能地捎上孩子落荒而逃?虽然这不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但作为一部电影里无可争议的现实部分(环境与人物的现实性),这怎么看都更像一个崇拜卡西、对披着床单的他无法视而不见、跟导演反着来的配角演员在花絮里才会有的反应。
—————补入分界线—————
18.5.5:抛砖引玉,因为评论区一位友邻的提醒,针对以上有了新的看法:对于所谓的情绪反应bug,或许“墨西哥单亲家庭”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设定——
@Anson_Van :“墨西哥人很相信鬼神存在,单亲是因为丈夫死了,她误以为是丈夫的鬼魂所以淡定,这一情节也大约影射了如果C鬼魂随M而去,M会有如何的反应,无非是再次搬离企图开始新生活,毕竟人鬼已殊途。”
我个人的信服度是很高的,而且感叹于和“C若追随M会怎样”形成对位是一个后知后觉的绝妙设计,至于到底能否因此达成自洽,大家见仁见智,也欢迎继续探讨~
——————————————————

关于第二个:对于这段明显带着自我解读性的对白,即便我发自真心地认为它压根就表意不清,但我仍不确定它的正反属性。所谓正反,无外乎是这个角色的话到底代表着“导演所认同”还是代表着“导演所不认同”的问题,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不缺论据——
正:在贝多芬创作是为上帝或为一个人、艺术作品的流传、艺术作品对文明的意义等论述上,我们都能看到故事中相呼应的部分——比如C鬼魂经过穿越后,我们能在那个拓荒者女儿那里听到C所创作的那首《I Get Overwhelmed》的旋律,由此甚至有人得出了“C鬼魂跳楼后进入未来”的推论(但这在故事提供的空间内根本无法解释C和M为什么会以完全相同的面目再次降世、进入完全相同的命运轨迹,至于为什么旋律相同这个细节仍可佐证我对“C鬼魂跳楼后回到过去”的说法,请见下文)。
反:在这段话的前后,分别有对C鬼魂不满、不认同的铺垫与描写。比如变戏法撩妹的玩牌男(这个真的没必要细说了,如果记不清重看一下就能明白),以及更明显的:秃顶男刚讲完,派对还未结束,天花板上的灯泡就又开始“灵异”了,随后便是又一个住户搬离后的破败场景。
是的,对正反属性的深究结果并不能说明这一段是不足。但如果说开篇不久那个鲁妮·玛拉的吃派长镜头表达了导演带有洗“粉”意图的可爱任性,那么这段高谈阔论的话则恰好相反,它仿佛是一种害怕洗光了粉的露怯表现。虽然对观众有所引导、对内核有所提炼,甚至在“鄙夷”式的刻画中实现了某些对立而空泛的表达,但无论如何,比删去也完全不影响和扑面而来的假大空更可惜的是,它终究不可避免地破坏了全片这股迷人的极简质感贯彻。
2.视听
所有杰作所向观众输出的议题,绝不局限于其故事与整体所探讨。我认为《鬼魅浮生》如是。这一段我简直不想用文字表达了,如果可以,我只想带所有人在最好的银幕与音响条件下再次欣赏这部电影,然后关注这些——






3.《I Get Overwhelmed》

先一起通过苍白的言语再次重温这个位于80min处的段落:C和M正在参观这座房子,而C鬼魂已经在这守候已久。C走着走着停了下来,环境音逐渐减弱,充斥窒息感的音效逐渐增强,这时候画面一切,我们得以看到C失神的目光——突然“啪”的一声,观众和他一起受到惊吓,镜头下移,看到了窗外的M。这两个镜头,天啊,就两个,包含了多少内容!既隐晦地强调了阴阳、两个自我(C与C鬼魂)之间模糊的感知,又在感知过后让刚才的漫长瞬间中止于M——对这个故事的情感驱动源再次强调与归结,乃至内在因果的串联,完全是库布里克回魂式的大师级表达啊!第四次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已经无法自拔了。
这也引出了我想用来收尾的部分:可感知——我对旋律可传递的想法正是建立于此。女孩所哼的旋律正是被C鬼魂所记忆,再经过C鬼魂于阴阳与自我之间的感知,在所谓冥冥之中赠予了为人的自己。基于此,我也进而正式确认了对“C鬼魂跳楼后进入未来”这一可能性的否定。在上述这一幕尚未结束的时候,《I Get Overwhelmed》这首歌就响起来了,进而在记录日常碎片的蒙太奇中过渡到C正在创作这首歌的场景。导演的表达意图已昭然若揭。
在感慨过本片中所有关于爱情、时间、存在主义等主题的探讨后,我们把目光投向一个不那么宏大、也相对具体的问题:灵感是怎么来的?
或许我们都不止一次地思考过,对此,显然也不存在标准答案。而我在《鬼魅浮生》里,经过不可避免的自我投射后,找到了可能是观影史上得到过最美的答案。
神秘,有时无迹可寻,有时又真实可感。相信这是我们对灵感这个概念的基本印象。当你问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从何而来?他的答案语意一定无法脱离这两种:无法言说。或者源于某人、某物、某情。
同样的,如果我们问故事里活着的C:你是怎么创作出《I Get Overwhelmed》的?
他能付以言语的部分,一定包括我们在那段蒙太奇里所见的、与M的感情。甚至他会说,这首歌就是献给她的。但他很可能无法言说的部分呢?那正是我们通过影像所得的另一部分答案:关于那个与他阴阳相隔的自己,关于那次等待的所见、关于历史、关于万物、关于更多。
这一部分答案,放到现实里,即是在这个世界所有人类所未及、所未知的一切。所有我们渴望通过科学、通过宗教甚至通过世外外力去探寻的部分。那些言语无法承载、前所未见的迷人事物——当我们触碰到那一切,对习以为常的既有一切才会有更好的理解。无论我们征程的终点属于可知或不可知,不要停止探知。
共勉。

感谢阅读。
3 ) Where are you?
在无尽的时间里还有无尽的等待,当等待化为了执念,等待显得就没那么重要了。花被单说她在等人,但等谁却不记得了,最后花被单说:“我觉得他们不会回来了。”然后化为了虚无飘散了。大家都在猜那张纸条到底写了什么,有人说是“I know you've been back.”,也有人说是“I've been here.”。其实这张纸条也是给了C最后的解脱,他在等待里已经迷惘了,他期待妻子有一天会回来,每当屋子的门被打开都代表着一次希望的破灭,周而复始他的心也只能随着这间屋子坍塌,生前的他就不愿搬离,妻子问他为什么,他说是因为在这里有很多历史啊。这间屋子充斥着他太多的执念,不断往复都不知道多少个轮回了。也许那张纸条是空白的,多可笑多讥讽,一直对着虚空抓着不放。
4 ) 严肃影评#37:毫无歉意的杰作 – 10/10
。
我对此无法进行反驳。确实,《鬼魅浮生》的节奏慢得让大多数的观众昏昏入睡;确实,它的题材似乎是那么的自大;确实,仅仅以一张床单覆盖全身、弄两个黑色眼孔这种小孩子复活节扮鬼作为电影的概念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然而我却只能说这是2017年至今我看过最好的电影,也是近年来极少有的成功的意识流美国电影。在我走出电影院时,我甚至不明白为什么我如此欣赏这部电影,但我却能理解那些中途离场的观众,虽然我为此感到非常遗憾。

前面提到的那个让大多数观众退场的长镜头,当然就是那个已经臭名昭著、长达五分半钟、女主角吃巧克力派的镜头了。它的臭名昭著大概可以归咎于电影在年初圣丹斯电影节首映后影评们两极分化的评语——反面的如“无聊”(Village Voice的影评Melissa Anderson)、“玛拉(女主角的演员鲁妮•玛拉)的表演是老套无用的”(Newark Star-Ledger的影评Stephen Whitty)、“这是一个烂的笑话”(Entertainment Weekly的Chris Nashawaty),而正面的则有“精彩”(USA Today的Brian Truitt)、“玛拉的表演是出色卓越的”(Time Out的影评Joshua Rothkopf)、“这是一个好的笑话”(Los Angeles Times的影评Justin Chang)。
是的,似乎对于《鬼魅浮生》的评价,只有好和不好两个极端,而并没有任何居中的说法。
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在女主角M(鲁妮•玛拉饰)吃巧克力派吃了五分半钟之前都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她跟男主角C(新晋影帝卡西•阿弗莱克饰)讨论着搬家的事情;我们看到她把家里不需要的东西搬到大街上去;我们看到某天半夜房子里的钢琴突然发出奇怪的凄惨声音,但他们却没有发现任何人在房子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回到床上,绵长而充满爱意的亲吻;我们看到某一天C车祸身亡;我们看到M在停尸房里无法接受事实的表情;我们看到C突然醒来,裹着床单变成了一个外貌简单得滑稽的鬼魂;我们看到鬼魂拖着长长的床单回到了家里;我们看到卖房经纪人来到家里留下巧克力派,并叮嘱M准备好之后联系她继续把房子卖掉;我们看到M回到家里,试图做家务来减轻哀伤的感觉,却发现一旦停下来便会被悲痛所吞噬。
M开始吃巧克力派,而回到家里的C,只能在角落慢慢看着M经历这静止、绵长、悲伤的五分半钟。

平铺直叙地讲述着《鬼魅浮生》这前三分之一的剧情,就如同电影中的镜头平淡无奇地为观众呈现它们一般,似乎索然无味,似乎只冲着一个低级的人鬼情未了故事来发展罢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能明白不少观众在这一刻选择放弃的原因。电影开端的这些片段均是冗长而固定的镜头,除了偶有的美丽画面外,实在不能说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无甚特别、缺乏电影感却挑战耐心的画面让观众们感到困惑甚至愤怒,也只能说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该退场的观众终于在此退场,但电影却没有因此而表达歉意。镜头没有变得流动起来,它反而变得更加静止了;节奏没有变快,它甚至像按了暂停一样不动了;剧情更没有变得像《鬼魅浮生》这个题目所暗示的那么惊悚可怕,反而把最平凡的场景展现在了观众面前。是的,我们看到M拆掉包裹的锡纸,坐在了地上,把叉子插进巧克力派里,然后放到嘴里,然后重复。我们不知道她重复了多少次这个动作,只能听到她越发用力地往碗里插,因而发出了叉子和玻璃碗的摩擦声;我们不会数她到底吃了多少口,只能看到她最后实在受不了而崩溃地跑向厕所呕吐;我们没有被告知她当时的心境到底是怎么样的,只能在静止的画面中寻找走进她心灵的线索。而如果你对鲁妮•玛拉的演技在这之前还有任何的疑问,她在这一幕里近乎无声地把悲痛欲绝成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应该可以消除所有的疑问了吧?在这个静止的五分半钟画面里,细心的观众们能在银幕上看到她的泪水滴到了鼻尖上,看到滑稽的鬼魂只能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而无力出手安慰。时间是如此的静止,画面是如此的凄美。我从来没想过2017年到目前为止最让我崩溃地感动的一幕,竟是这如此简单的一幅画面。
“电影应该更像音乐而不是更像小说。它应该是情绪和感觉的积累。它的主题、它所要表达的意义,这些都应该放在感情之后。”对于电影,斯坦利•库布里克曾经这么说倒。
《鬼魅浮生》的前三分之一,恰恰印证了库布里克的这个观点。在看似平淡枯燥而缓慢的镜头和故事里面,导演大卫•洛维为的是给耐心的观众们制造出一连串能让情感得到共鸣的画面。这在美国电影中是极为罕见的,只在欧洲电影中更为普遍,比如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传世名作《潜行者》便是如此。长镜头让观众们更能感受导演所希望营造的氛围,静止的画面则让观众们的眼睛更容易地找到导演所希望表达的重点,或者导演所精心设计的构图。这种意识流的电影创作人,在美国主流制作中大概只有泰伦斯•马力克了吧?他的《天堂之日》以及《生命之树》便是意识流电影中的佼佼者。无独有偶,导演大卫•洛维的前作《他们非圣人》便被诟病太像马力克。但这次,他终于算是走出这位同样来自德州的大师的阴影了吧。

如果说吃巧克力派这一幕是《鬼魅浮生》前三分之一感情氛围积累的顶点而让人感动,那么电影的后三分之二则是更为迷人而值得沉思的主题升华。当我们看到M逐渐走出悲伤甚至终于放下过去离开这里后,故事以及电影情感的侧重点终于落到了这位披着床单的鬼魂上。为了让电影的主题更鲜明、为了让观众们更直观地有情感依靠,大卫•洛维在编写剩下部分的剧本时从鬼魂所感受的角度出发。我们看到它所体验的时间跟正常人不一样,时间不断地跳跃。我们从他的角度看到了M如何一天一天地走出悲痛,重新拥抱生活,却对他来说是那么的残忍;我们从它的角度看到了M离开后的墨西哥家庭以及他的孤独感;我们从它的角度看到了墨西哥家庭之后某次派对的现场,一位高谈阔论者似乎道出了它关于时间、关于存在的意义的心声(以及电影的重要主题,虽然我觉得这段独白非常多余…);我们从它的角度看到了多年以后房子被拆除,而本来的郊野也终于变成了高楼大厦,再也没有它所熟悉的东西了。我们看到它终于忍受不住,决定跳楼身亡。
然而大卫•洛维在这一刻却使用了更妙到毫巅的神来一笔——我们跟随鬼魂,进行了时间的倒退,回到了100多年前房子还没建成的时候,看到了开拓者们在这个地方试图修建房子而身亡。然后我们回到了那家熟悉的房子,然后我们看到了从前的C和M,他们第一次进入这家房子看房的时候,他们搬进来肩并肩趟在一起闲聊,他们坐在门廊开心地喝着啤酒聊天,他们为了是否搬离这里而争吵,C终于决定同意搬家。
鬼魂无法接受这既定的事实,在钢琴旁坐下,使键盘发出凄惨而熟悉的声音。

或许正是在这一刻,我开始确定《鬼魅浮生》是2017年到目前为止最好的电影吧。时间是一个平整的环,我们跟随鬼魂体验了时间的静止,体验了时间的快进,体验了时间的倒流。终于,我们还是体验了时间带给我们的悲伤感觉。在最后,我们看到了C依然遭遇车祸,而鬼魂也看到新的鬼魂站在窗前目送M离去。时间面前,我们的生活显得如此的毫无意义,我们却依然选择坚持重复着似乎是既定的无可避免的事件。但即便如此,随着鬼魂终于找到了M所留下来的纸条,作为电影重要部分的音乐在最后一刻变得更为充满希望,似乎代表着在悲伤面前的大卫•洛维,依然对生命和时间怀有期待。
而他当然应该怀有期待了。在《他们非圣人》后投身大制作成功给出意外地精彩的《彼得的龙》,又紧接着给观众们带来《鬼魅浮生》这部能够如此安静美丽地给观众共鸣、在近年电影中实属罕见的意识流独立电影,更在这之后被传奇好莱坞老影星罗伯特•雷德福钦点执导退役之作《老人和枪》。
大卫•洛维,当然值得期待。
5 ) 看这片子之前,我居然和它的幕后英雄聊过天
这世界很小。
去年六月,我跟这部片子里的一位重要参与者,打了有快一个月的交道。他在本片中的作用,不能说不重要,但是却很容易被人忽视。
当然,这不能怪观众。因为他们这些人对于本片的贡献,本来就不应该被观众关注,甚至发觉。不过既然大家都看完电影了,所以我们也可以来聊聊这些幕后英雄了。
这不是篇影评,只是一个恰好和影片工作人员打过交道的人,过来和大家分享些小故事。
这个工作人员在影片里是有露脸(虽然露脸时间加起来可能也就1秒多钟),甚至有几句台词的。他在片子里扮演自己的老本行:魔术师

Jared Kopf,本片的特效团队的成员之一。
《鬼魅浮生》这部“鬼片”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全片里没有用到任何电脑特效。其中的所有灵异效果,全部是请魔术师过来,用魔术手法完成的。
而这位Jared Kopf,如果你不是在魔术圈呆过一定年头的,可能都不一定听说过。他叫是一个非常低调,但是极为牛逼的青年魔术师。这种人放在网络小说里,就妥妥的是那种绝世少年天才,超级宗门核心嫡传弟子的模板。
去年六月份,我们工作室请了他来中国,做巡回魔术讲座。
这里要纠正一些人可能存在的一种偏见,那就是魔术师都是对秘密十分保守,死活不愿意公开自己的东西的落后人士。实际情况真的不是这样。魔术师不是不愿意公开秘密,只是他们的公开是有对象的。这个对象限定在其他魔术师,以及魔术爱好者这里。换句话说,你如果是混这个圈子的,那你将接触到太多太多的秘密。
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西方魔术师著书立说的现象变得越来越频繁。而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基本上只要是个大师,就会或早或晚地将自己的魔术公开,写进书里,然后交给专门的魔术道具商售卖。至于行外人,对不起,这些不是入门读物,是需要你有一定基础才能看的专业教材,所以别想在普通书店里看到它们。
再后来,又有了录像带、VCD、DVD乃至网络。魔术师们的记录手段,自然也与时俱进。
一百多年下来,作为后辈的我们,面对的是汗牛充栋的,记载了十几代魔术师一生心血的魔术文献。说实话,看,是根本看不过来的。而且你这边看,那边还在不断出新的。
扯远了,聊回Jared Kopf。总之,魔术师除了会著书立说,拍摄教学录像之外,还会做讲座,教世界各地的其他魔术师和爱好者变魔术。我们给他安排了尽量松一些的巡回日程,并且让他可以先带老婆孩子去想去的地方逛一逛。
6月初的某一天,我和团队老大去车站接人。第一眼看到他,我就愣了。因为之前印象里的Jared Kopf,一直是这样的形象:

没想到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他,却发现画风变了太多:

我问他们一家三口之前先去哪儿玩了,他老婆Elayna费了半天劲,脱口而出两个奇怪的音节:
Qiu Fu
我说我去,你们仨挺会玩儿啊,来国内第一站去曲阜。该不会是旅行社给你们安排的吧?
Elayna说不是不是,我们确实对孔子很感兴趣。
细聊下去,我发现Jared真的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看上去有些闷骚,却意外地很健谈。忘了当时话题是怎么拐到电影上去的。他拿出手机说你们看,这是我刚参与拍摄的一部电影。电影中有个一直披着床单的鬼,可好玩儿了。
哦等下,我想起来话题是怎么拐到这上面来的了。
当时,我们正在聊什么样的魔术,才是好魔术。Jared说他觉得最好的魔术,是发生在观众面前,但观众却完全意识不到它存在的魔术。
于是他便举了《鬼魅浮生》的例子。
比如这里:

其实仔细想想,这个片段是有个不合理的地方的。
能猜到是哪里么?
来,给你一分钟的时间思考。
不知你想了没有,无所谓,我揭晓谜底了:
白布
如果是按正常情况来拍,那么当“尸体”坐起时,盖在他身上的白布会从他的头上滑下来。或者就算不掉下来,仍然罩在它头上,那么当“尸体”完全坐起时,他的头部也不应该像片段里拍的那样,正好位于白布的正中央。
可如果真是这样,那不就穿帮,或者没感觉了么?
想让这个鬼魂真的有那么一点“飘起来”的感觉,他的头部,还真的就必须一直处在白布的正中央。
Jared说,他们魔术师团队绞尽脑汁,最后才想出来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
那就是把白布的一头反复折叠(注意看下图红圈里)

这样当人坐起来时,折叠的部分便渐次打开了。嗯,要的feel有了!
可是呢,费了这么老些劲,观众却是基本注意不到这个细节的。但Jared在聊到这些的时候却很开心,因为他们帮导演创造出了一个”明明就是披着床单的人,却时不时会有‘真’灵异举动的鬼“的形象。

这里继续聊一些题外话。
其实,魔术和电影的渊源很深。在早期电影的发展史中,一直贯穿着魔术师的身影。电影的发明者之一,奥古斯托·卢米埃尔,其实便是一位业余魔术师。
卢米埃尔曾在职业生涯的早期,研究过人是如何眨眼的。也正是凭借着这样的研究,他和他的哥哥路易斯·卢米埃尔,才发明出了恐怕是有史以来第一台实用的摄影机。1895年12月,他们在巴黎卡皮欣大道上的"格拉咖啡馆"的地下室里,播放了他们制作的第一部电影——《火车到站》。看完首场电影后,巴黎的一位记者预测了其光明的前景:
“摄影的对象已经不再是静止的物体,它使运动的场景成为了永恒。当它被公众所掌握之后,当任何人都可以拍摄下自己心爱的人的影像、运动、动作、熟悉的手势和口中的话语后,对于他们来说,亲人的死亡就将不再是彻底的消失。”

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拍摄事业随之展开。但是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那就是既然电影才刚刚被发明出来,那么电影院,自然也是个还不存在的事物。卢米埃尔兄弟应该去哪里播放他们的作品呢?
这个时候,身为业余魔术师的奥古斯托·卢米埃尔,想起了自己认识的一位职业魔术师:乔治·梅里埃。梅里埃当时刚刚买下了前辈魔术大师罗贝·胡丹(Robert Houdin)坐落于巴黎市中心的剧院。两人便在这家剧院见了面。卢米埃尔向梅里埃,展示了自己兄弟俩的新发明。
梅里埃几乎是在看到那活动的影像的瞬间,便意识到了其价值所在:如果他能够把自己的表演拍下来,然后投射到一块大屏幕上。那么他每场表演的观众人数,就将不再只局限于区区一两百人而已,而是可以得到数倍的扩增!
梅里埃向卢米埃尔提出,要购买他的机器。可是卢米埃尔拒绝了。梅里埃没有气馁,他找来另一位英国魔术大师大卫·德温特(David Devant),以及一位非常厉害的工程师。三人一起努力,逆向破解了卢米埃尔版摄影机的构造,并打造出了自己的版本。于是仅仅在一年后,电影,便成为了梅里埃剧院表演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现在我们提起乔治·梅里埃,已经不会再提他是一位魔术师了。可是如果仔细想想,这其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毕竟,从梅里埃可以买下魔术大师罗伯·胡丹的剧院,做自己的表演场地这一点来看,他的魔术造诣,绝对也是当世一流的。事实上,梅里埃曾经被选为法国魔术师协会的主席。而今天的人们,之所以会彻底忘记他在魔术方面的功绩,其实恰恰说明了他对电影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因为一桩辉煌的事业,只会被另一桩更为辉煌的所掩盖。
梅里埃发明了一样东西,或者说,一个对于电影的发展来说,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的技巧。
有一天,梅里埃和他的摄制团队,在巴黎的街头拍摄影片。结果不巧的是,拍摄过程中机器出了问题。于是他们只好停下检修机器。过了一会儿,机器修好了,他们继续拍了下去。
回到摄影棚后,他们把胶片冲洗了出来。但在观摩影片时,一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影片中的一辆公共马车,突然间变成了辆运棺材的马车!
一瞬间,所有人都蒙了,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众人想了半天,才终于意识到原因在哪里:因为摄像机在拍摄过程中,停了一次。检修机器前,摄影机最后拍到的是一辆公共马车。然后摄影机停止了工作。而等它被修好以后,有一辆运棺材的马车,正好跑到了之前公共马车所在的位置。而这个变化,被以一种非常直接而又突兀的方式,记载在了胶片上。
如此一来,乔治·梅里埃便在无意之间,发明了“剪辑”。
梅里埃也确实是一位天才,他不仅在看到电影的那一刻,便意识到了它在宣传方面的作用。他还在看到“剪辑”诞生的那一刻,发现了这个技巧的价值所在。他想到,这可以是一种全新的叙事手法。人们在拍电影的时候,其实完全不需要老老实实地把一桩事物从头拍到尾。我们可以用“剪辑”,把不同的场景、不同事物人物连接在一起。而以此为起点,一个包含了无限可能性的新世界,就出现在了所有人面前。
梅里埃从“停机再拍”这件事中,悟出了剪辑这一手法。他接着将这种手法玩出了花,类似于像慢动作、快动作、倒拍、多次曝光、叠化这些拍摄手法,逐一被他开发了出来。更重要的是,凭借着剪辑,电影的拍摄者们,可以真正的开始“讲故事”了(而不用像最早的电影里那样,纯粹就拍拍一个人在喝汤这样的无聊镜头)。
观赏梅里埃所拍摄的电影,你分明能看到一位魔术师的各种奇思妙想:复活的骷髅,凭空消失的演员,被砍下的头却在四处张望,甚至开口说话。

6 ) 《鬼魅浮生》:我瞥见幽深的黎明,我看到古老的昨天
“我将来要当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有那么一群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玩。几千几万的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就是在那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是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做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有些电影,一旦看懂了,就会格外悲伤。 很难概括《鬼魅浮生》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它充满了个人风格和独特的诗意。平淡而缓慢的长镜头,静止的画面,导演大卫•洛维用独特的电影语言讲述了一个略带悲伤的故事。我们跟随着只有眼睛的鬼魂,看见了时间带来的沧海桑田,分崩离析,最终看见的却是时间带来了悲伤和人力不可为的无奈。影片自始至终都在阐述着距离和变化,生与死的距离,过去和未来的变化。 “你在干什么?” “我在等人。” “你在等谁?” “我也不记得了!” 然后在漫无目的的等待中烟消云散。 影片没有复杂的剧情,没有巧夺天工的结构,但整部电影却有一种震慑人心的感觉。大概是因为触及到了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有些疼,有些悲。在时间的洪流之中,所有的等待和爱都是无意义的。死亡和出生之间不过是一段被虚无填充的过程。 “生命的形式是空泛的,但我们却要脚踏实地; 生命的本质是荒诞的,但我们却要假戏真做; 生命的真谛是虚无的,但我们却要信以为真。” 大卫•洛维是一个虚无主义者。 除了爱和凝望之外,《鬼魅浮生》也在探索生命的本质,在时间的流淌中,生命的形态越来越清晰,它热烈、脆弱又短暂。 它由一连串的记忆构成,看似牢不可破,其实转瞬即逝。这种感觉就像要奋力抓住什么什么东西,伸出手,才发现不过是月光中的树影一不小心照在了手心。 大卫•洛维是一个聪明的虚无主义者。 在我以为故事就要戛然而止的时候,他通过那双望向无限的眼睛,看人来人往,看木板的腐败和墙纸的脱落。在这无尽之中,那双眼睛看见的除了孤独,什么都没有。就连曾经真正属于他的东西,也不过是时光中的灰烬。我们隔着银幕看见的其实不是一个无法走出的鬼魂,而是赤裸裸的时间,生命的真相与本质。 影片改编自佛吉尼亚·伍尔芙《鬼屋》,原作延续了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大卫•洛维却让这个故事更有深度和广度。 有转瞬即逝的爱。 有恒古不变的守望。 有分崩离析的不可控。 鬼魂看见了兵荒马乱中的生灵涂炭,看见了工业文明的锐不可当。然而,那又怎样,一切的一切都是无意义的,因为最终都会消逝。在一个固定长镜头中,之前、现在、以后被结实的连接在了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 “小时候,家里经常搬来搬去,我会写纸条,把它们叠得非常小,然后藏在各个角落里,如果有一天我想回去的话,那儿会有一部分曾经的我在等着”。 “你回去过吗?” “没有,你看我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没有理由回去。” “里面都写的什么?” “就只是些古老的韵文和诗歌之类的,一些我想要记住的,生活在那间房子里的日常和我喜欢它的地方。” 所有的爱与恨,欢乐与悲伤,等待与绝望,生与死,过去和现在,自由和禁锢都在时间里。他们已经远去,他们从未远去。 “没错,人人都尽力留下长远的影响,我们一点点地建立成就,或许全世界都会记得你……然后会有一个重大的板块漂移,旅游胜地国家公园会爆炸,西部板块会移动,海洋会上升,高山会倒塌,90%的人会死亡,这只是科学。幸存的人会去高地,社会秩序会混乱,人类会重回拾荒者、猎人、采集者。但也许有一个人有一天会哼起熟悉的旋律,这给所有人一点点希望。人类处于灭绝的边缘,但总能一天天坚持下去,因为有人哼起了熟悉的旋律,耳朵里的物理反应让他们感觉身上不只是恐惧、解饿和仇恨,于是人类生存下来,文明重回正轨。” 在时间里,每个人都是一粒尘埃,是念想让我们的生命有了意义。“我瞥见幽深的黎明,我看到古老的昨天。” 时间无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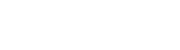




















1. 少见的美国导演可以把握"微妙"这个词;2.孤魂对情的留恋与世间物不断毁灭循环的对照;3.可以跟阿萨亚斯《私人采购员》做double bill。4.5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汤姆·哈迪:“我只露一双眼睛就可以演戏。”卡西·阿弗莱克:“我连眼睛都不用露就可以演戏。”
一头白床单也能拍出惊艳的鬼片。神游八荒,见证沧海桑田,对他来说魂牵梦萦的却永远是一道墙缝,因为墙缝里有她写给他的字条:真是个情深如海的鬼故事啊!鲁尼·玛拉坐在地上边流泪边吃派吃到吐是我今年看过最美的画面。(配乐值得加一星,好听到爆!)
导演一定觉得自己很屌吧。你特么倒是告诉我纸条上写了什么?!心疼吃派的玛拉。
全片自始至终诗意的镜头仿佛在诉说着生与死的距离,在思索灵魂与记忆的分量。当那座幽魂坚守的房屋被拆掉,这具幽魂心中默念”我想他不会回来了”,紧接着瞬间烟消云散,这真的比任何悲剧都让人悲伤。
应该名为《鬼比人孤独》或者《鬼再孤独也不找同类》,又或者《披着白床单的孤独鬼》,应该是史上最有逼格、最安静的鬼片之一,把一个MV就能拍完的故事,活生生撑成一个长片,对话很少,还动不动长镜头,剧本应该很好写,主要看演员,看摄影,听音乐,这个鬼的造型其实很搞笑、很调皮,一点也不惊悚。
前半部的节奏控制得太刻意,跟后半部截然成了两部电影,不喜欢。鬼魂作为旁观者所呈现的虚无,无力,被突如其来的控制电灯和摔碗摔盘子桥段破坏得所剩无几。就安静如鸡做一个鬼不好吗,这么大魔力怎么不去改变世界呢,瞎搞。有很多非常迷人的片段,像小调,或者交响乐,但强行合到一起让人感到厌烦。
不用担心我眼睁睁看着你爱上别人继而搬离这间房子的无能为力,我飘荡在人世间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看一眼你写下的古老诗句。
应该是比爱情更甚的对起源和因果的迷恋,就像经过一个宇宙轮回也想看清墙壁里那张字条的执念一样。在看似深邃而巨大的记忆房间里,每个人都不由自主想加入C,他是有限历史的绵延和川流时间的常量,这种悲情的迷人感或许就是唯物世界意义的一种解答,连达伦的《珍爱泉源》似乎都在对比中相形见绌。
被短评笑死,虽然也不是什么烂片,但真的是尬吹
在Dunkirk的配乐轰鸣后看这个简直洗耳。像MV的部分都是一种享受,出了影院后有种处处有床单的感觉。
时间与情感,细腻的感动
一个男人超越时间的深情。
以为自己心疼玛拉,吃个派看得我泪水一脸,后来才发现至少玛拉还可以搬家可以开始新生活,而鬼魂却只能留在房子里等她回来,世世代代轮回再轮回。还有什么比信念崩塌嗖得一下床单就这么滩在地上来得更让人绝望,那个花床单说我觉得他不会再回来了,泪奔。原来那句我做鬼也要缠着你是句如此温情的话。
据说每一间闹鬼的房子里,都居住着蒙盖白布的游魂。每个游魂都在等人,却从不记得等的人是谁。我的深情是触不可及,我的爱是无能为力。看你木然狼吞、呕吐到昏厥,我只能在一旁束手无策。时光漫漫,时间的轨道兜转,去挖开墙角里的秘密。魂飞魄散前终于领悟,孤独让我有了实体,寂寞却抽走了我的灵魂。
其实看到前面一大半时都感觉虽然很细腻很喜欢,但拍成短片就足够;但电影从时空错乱的时候开始变得有意思,一个孤魂目睹时代的变迁,他在等一个特定的人或是一句话给自己的存在做最终的定义--大卫洛维是个虚无主义重症患者可也真的好浪漫。卡西和玛拉就算演对情侣闲聊九十分钟我也乐意看!
All those moments will be lost in time, like tears in rain
仍是马力克附体,尤以门上光斑与头顶星云表现人类在时间长河的永恒微渺感,近乎默片的表现形式凸显环境音的作用,倒回叙事在结尾闭合,门框的取景构图让这座回环着爱与回忆的废墟呈现出迷宫的质地;日换星移,沧海桑田,万物荣枯有时,时间绵绵无尽,顿悟刹那灵魂委顿扑地,全片最佳瞬间。
Mo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