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让娜·迪尔曼》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呢?它是阿克曼1975年的一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电影,它又是一部著名的“女权主义”电影,它还是一部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极富革命精神的电影。总之,阿克曼这位拍片数极少的比利时女导演凭借她二十出头拍出的这部电影,就足以让无数的影评人、电影史学家为她 树碑立传了。它的独特、先锋已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相信,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如此奇妙的观影体验了! 影片内容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一个中年寡妇三天的日常生活(影片其实是从第一天下午到第三天的下午,仔细算下来也就两天多一点),影片的拍摄手法也十分“简单”——固定长镜头(影片中的机位选择非常严格,比如说厨房是正面、侧面两个机位,算下来全片也就只有十几个机位),影片场景同样十分“单调”——超过90%是在让娜?迪尔曼所住的公寓里拍摄的。陌陌影视陌陌影视天使不爱人间非常营救亲亲坏姐妹飞哥与小佛第五季罪恶黑名单第二季武当少年病房肉欲的42街杨梅洲夏日风暴2004大耳朵图图之霸王龙在行动约翰·威尔逊的十万个怎么做第二季春的诅咒烈火营救蓝色海洋之心国语被不良少年盯上良师难为加州靡情第四季骇人命案事件簿第六季爱情季节夺棍国语地下长城孽欲凶杀牧场趣事第四季妹妹成了女朋友握三下,我爱你
长篇影评
1 ) 香特尔•阿克曼的“妈妈与妓女”
《让娜•迪尔曼》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呢?它是阿克曼1975年的一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电影,它又是一部著名的“女权主义”电影,它还是一部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极富革命精神的电影。总之,阿克曼这位拍片数极少的比利时女导演凭借她二十出头拍出的这部电影,就足以让无数的影评人、电影史学家为她树碑立传了。它的独特、先锋已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相信,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如此奇妙的观影体验了!
影片内容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一个中年寡妇三天的日常生活(影片其实是从第一天下午到第三天的下午,仔细算下来也就两天多一点),影片的拍摄手法也十分“简单”——固定长镜头(影片中的机位选择非常严格,比如说厨房是正面、侧面两个机位,算下来全片也就只有十几个机位),影片场景同样十分“单调”——超过90%是在让娜•迪尔曼所住的公寓里拍摄的。这位中年寡妇的日常生活有什么特殊吗?值得“浪费”我们三个半小时?其实迪尔曼的生活有90%是平常、普通的:起床、做饭给儿子吃、买菜、织毛衣、洗碗、整理床铺……然后电影花了三个多小时的时间来表现迪尔曼起床、洗脸、做饭、吃饭、擦皮鞋……而且全部是“单调、乏味”的长镜头:没有镜头移动、没有景别互换。与其他电影相比,简直就是伏特加与白开水。如果说那10%有什么特殊的话,也就是迪尔曼在每天下午会在家接待一位固定的嫖客。电影在表现这“特殊工作”方面却是“惜墨如金”,影片宁肯花十分钟“完整纪录” 迪尔曼洗几个碟子,而且第二天又洗一次,也不愿在这儿多给哪怕一个镜头。客人按门铃,迪尔曼起身开门,帮客人拿帽子、围巾,然后两人通过过道走向卧室,走廊灯熄灭,一会又亮起,迪尔曼与客人走出卧室,迪尔曼交给客人帽子、围巾,客人给迪尔曼钱,最后开门走人。前后不到一分钟,我们走入了迪尔曼的生活,但她的生活仍然神秘,让人费解,观众以为已经完全了解了这个女人,可她远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简单!影片结尾镜头突然切入卧室,给观众的震撼已足可抵消掉那三个小时的“沉闷”原来导演是想制造悬念,并非刻意抹掉迪尔曼“妓女”的这层身份。相反,影片中还不时提醒观众迪尔曼的“妓女”身份。迪尔曼将嫖客给的钱放在客厅餐桌上的陶瓷罐内。在影片的很多时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陶瓷罐与迪尔曼并列的镜头:迪尔曼与儿子吃饭时,迪尔曼织毛衣时,迪尔曼取钱时……可以说这个陶瓷罐是影片中出现次数最多的物件,而且相比其它频繁出现的沙发、锅、咖啡壶、杯子等物件,这个陶瓷罐具有明显的象征含义。“妓女”身份如果是“特殊”的话,那么“母亲”身份就应该是“普通”了,但电影却将这个“普通”变为了“特殊”。 迪尔曼生活的方方面面均是围绕着儿子,早上起床为儿子做早餐、帮儿子刷皮鞋、去街上为儿子修皮鞋、到处找与儿子衣服上遗失的相同型号的纽扣、为儿子买菜做饭铺床洗碗,影片就不停地描绘着迪尔曼的这些行为。阿克曼不但在影像上细致入微,而且在全片仅有的几句对白中绝大部分是与儿子的对话,其它一小部分与修鞋匠、卖毛线、纽扣的对话其实也是以儿子为出发点的。儿子为迪尔曼朗诵波德莱尔的《敌人》,还有一段带有浓重“俄狄浦斯”情结的回忆录,这是导演设置的隐藏信息,这些隐藏信息(卧室里发生的事以及迪尔曼与儿子晚上的外出)是导演在空间上与观众的“捉迷藏”, 迪尔曼这个形象也就将永远留在观众的脑海中,她永远都是一个谜,如同最后突然杀死嫖客的行为,真实还是虚构?偶然还是必然?
迪尔曼的多重身份:母亲、家庭主妇、妓女在电影中被推至中心位置,这也就是“女权主义”电影的最大特点。女性主义者安奈特•孔指出,在电影中,女性通常被社会结构成男性主导世界的“他者”或“局外人”,女人无法说自己的故事,因为影像是被男性控制,通常女性被视为性客体,惟其美貌和性吸引力才有价值。阿克曼的这部电影可以看作是对传统男性电影霸权的一次挑战。女性作为故事中心不说,那些嫖客,包括迪尔曼的儿子等男性形象均被刻画为女主人公生活的延伸。另外,亡夫通过卧室梳妆台上的照片被完全客体化。在影片末尾的一个镜头中,迪尔曼面对梳妆台,相框位于左下角,镜中是迪尔曼的脸以及身后床上的嫖客。这个镜头中迪尔曼是唯一具有主体(演员本人)与镜像的“双重存在”,而嫖客与亡夫均被“客体化”或“镜像化”。立体变平面,一种全然“女权主义”的视角。“身份扮演”是“女权主义”电影中要极力批判的价值取向。正如波伏瓦的那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变成的”社会给女人加上了“女人”的这一层身份,所以你就必须扮演好“女人”这个角色。迪尔曼的“双重身份”是一种尖锐的反讽。这个社会强加在女人身上的“妈妈”与“妓女”的两种极端的身份对立,她既要演个好母亲,又要做一个性工作者。我们可以在很多电影中看到这样的情节设置。在帕索里尼的《罗马妈妈》中,罗马妈妈出卖身体就是想让自己的儿子过上上等人的生活,这部帕索里尼“新现实主义”时期的杰作不能作为“女权主义”电影的重要原因就是它批判的是阶级问题而不是女权问题。同样在伊利亚•卡赞的《伊甸园之东》中,“母亲”的缺位,“妓女”的在场折射出的是儿子成长的痛苦与迷茫。到了阿克曼这里让娜•迪尔曼这个肩负“妈妈与妓女”双重角色的女性形象才真正被作为一个“中心化”而非“边缘化”的主体,社会与男性角色成为陪衬。让娜•迪尔曼的神秘也打破了以往电影对女性形象的单一、刻板的书写模式。最后杀死嫖客是一种对“身份扮演”的摧毁。这种摧毁是暴力的、极端的。而我们在雅克•里维特的杰作《塞琳娜和朱丽出航记》中看到的反抗是轻松的、游戏式的。塞琳娜和朱丽的几次身份互换(如朱丽代替塞琳娜的魔术表演的工作)非常有趣,更绝的是,里维特还虚构了一个“魔幻世界”,让两位女主人公在“现实世界”与“观念世界”之间来回穿梭,也让这部电影在表现“女权主义”之外,包含着其它深层次的思考。《塞琳娜和朱丽出航记》作为“女权电影”未免将其狭隘化了,但《让娜•迪尔曼》从第一个镜头开始就告诉观众,这就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女权电影”。“妈妈与妓女”是一种“安娜•卡列琳娜式”或者说“包法利夫人式”的女性宿命,这样的教条规则真能像迪尔曼用一把剪刀就能解决吗?电影最后一场戏,迪尔曼坐在黑暗的客厅中,屋外斑驳的蓝色霓虹透过百叶窗铺满房间(突然想起了法斯宾德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里面主人公的房间同样被霓虹所笼罩,只不过是红色的)长达5分钟的静默,是迪尔曼在思考,也是阿克曼在思考。
《让娜•迪尔曼》在电影时间与空间上的实验是大胆且令人难忘的。传统电影想做的是拼命拉长时间,一部电影中的时间跨度通常很大。最绝的是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中骨头变飞船的那个蒙太奇。这是电影领先于戏剧的一大优势,戏剧时间的改变往往要通过幕与幕之间的转场来实现,因为它是“现场的”。 《让娜•迪尔曼》的戏剧风格非常明显,如通过插入字幕来实现时间的改变,其它时候都是按照时间轴的顺序排列迪尔曼的重复、单调的生活。时间被导演放在了一个必须要求观众去体验、去感受的地位(我们平时看商业电影一般不会去注意这件事是在早上抑或是在中午还是在晚上发生的?这件事与上一件事之间究竟间隔了多长时间?这些问题)这部电影将时间放大,并将时间缩短(相较于观众平时看电影时的心理时间)也许你会问,为什么冲杯咖啡要这么长的时间?但实际生活中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是因为传统电影的时间比现实快了很多。阿克曼的这种实验无疑将电影的表现方式扩大了。提到“实时电影”就不能不提阿涅丝•瓦尔达的《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同样是一部女导演以女性为主人公的电影。讲述了女歌手克莱奥去医院领取体检结果(她怀疑自己得了绝症)前后两小时发生的事。《让娜•迪尔曼》比《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走的更远就在于克莱奥的两小时对于观众而言是新鲜的、陌生的;而迪尔曼的三天很大部分是重复的、熟悉的。重复、熟悉不意味着刻板、无聊。迪尔曼的生活中充满着各种意料之外的事情,虽然这些事大部分极其普通(如第三天刷鞋时鞋刷不小心掉了)但这却得以更接近生活的本质。在空间上的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摄影机是固定不动的,有时迪尔曼会走出画框,传统做法是让摄影机跟随主人公,但镜头不动让主人公走入走出,电影突破了那个画框的限制,这已不单单是“记录”那么简单了,这更像是对传统电影理论的一次挑战。
一个个长镜头拼贴出一个普通中年寡妇三天的生活,一部在简单与复杂、真实与虚幻之间游走的电影,一位在“妈妈与妓女”角色互换中挣扎的女性,共同成就了世界电影史上最奇异、最独特的一出神话。
2 ) 偷窥他们进餐,感到无望
《让娜·迪尔曼》是比利时杰出女导演阿克曼的杰作,采用最直白的时间顺序和固定长镜头,描写中年让娜两天半的生活。
阿克曼抛弃花哨的技法和章法,如水平静地将镜头对准琐碎的日常生活场景,让我们产生对真实生活的偷窥感来。偷窥引发一种对生活无望的强烈共鸣——不仅弱势女性让娜·迪尔曼,而且我们每一人都要面临这种无望感。
《让娜·迪尔曼》,是“慢电影”,是需要你投入情绪的。倘若不戒除浮躁,可能不易于体会它:90%的室内镜头,让娜在房间里走动、操持家务、照顾儿子、接待嫖客,生活单调重复,即使偶有波折,也用极其克制、冷漠的方式处理。
比如影片中的两场进餐:
1,儿子放学归来,两人收拾餐桌,让娜细心整理餐布,摆放餐具。先端上两盘汤,两人坐定,拿起勺子喝汤。喝完,让娜走进厨房,盛两份主餐,关灯,回桌,再各自用餐。两人几无谈话,儿子边吃边歪头看书,让娜劝说儿子用餐时不要看书,儿子把书收起。
2,第二天晚餐,儿子仍然看书,被再次劝说后收起。
这两段镜头看起来单调冗长,却让我有莫大感动:对于让娜来说,生活只有惯常的琐碎,细致的晚餐像是一场每天进行的仪式,仪式代表生活的延续,即使漫长、仍将继续下去。或者说,晚餐,意味着给枯乏生活上一次发条,手一松开,新的一天还将继续运转。
对于我来说,生活也是如此,对你来说,恐怕也是。我们都像是自己生活的机械人吧。
但是,让娜选择在第三天晚餐前结束这种延续。如果第三天的晚餐仍照常进行,让娜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就永远不会发生,电影也将不复存在了。
不再上发条了,我们每天都在想,换一种运转方式吧,让娜在重复了千万次之后,发出行动了。在克制冷静的电影语言下,巨大的情绪积压等待爆发。
让娜的另一身份是早年丧夫的妓女,从固定的嫖客那里获取生活所需的金钱。妓女的身份,我认为并非“女权主义”的用意,电影并未着重于这身份,而是同等对待“母亲”和“妓女”两种身份,或者说,这两种身份对于让娜并无差别。
我们能看到,“妓女”让娜并无半点“性”的味道,在她无表情的脸上,只有无欲望的冷淡(对性无欲、对生活也无欲)。她对待嫖客也与对待儿子一样细致、体贴,但冷漠:接过他的衣帽,一件件挂好。
第三天清晨开始,变动发生了。
让娜规律而平淡的生活出现了斑点——给儿子擦鞋时鞋刷掉在地上,咖啡煮坏了,在咖啡馆常坐的位置被别人占据。这些细斑预示着变化。细微的变化,剧烈的腐蚀。
与前两天不再相同,让娜接待嫖客时,并没有如常将卧室门关闭、关灯,镜头缺失了习惯的结束点,无法结束:只能对准卧室内让娜的面部,一段3分钟的特写,让人清楚地观看一张被压制、被蹂躏的,苍白的、无望的脸。
接着,她起身梳头,手边有一把剪刀,仍然面无表情地,她转身将剪刀插入嫖客胸膛。嫖客闷哼一声,没看到多少血,就一动不动了。在克制的冷谋杀下,生活从一种绝望,转向了另一种绝望。
杀人后的让娜回到客厅,呆坐了五分钟。漫长而焦虑。窗外的蓝色霓虹灯映照着屋内的玻璃橱窗,也映照着迪尔曼苍白的脸。我们无从得知,这五分钟里她在想什么,但能想起,在第一天傍晚,让娜同儿子读完亲戚的来信,两人诵读波德莱尔的《敌人》的场景:
我的青春是一场阴郁的暴雨,
偶尔被灿烂的阳光射穿。
倘若没有迪尔曼最后的刺杀,这首诗放在影片里,将失去回音。
看完影片后很长时间,我都将这部影片关联到贝拉·塔尔的《都灵之马》,虽然风格迥异,但我都喜爱的,就是对进餐场景的窥视:《都灵之马》中,马夫与女儿对坐在昏黑的屋内,两只餐盘里各放了一个白水煮的土豆,老人迅速地剥皮,土豆很烫,想必也索然无味,他却吃得很快,神情间透露出一种“完成仪式”的庄重感,一种拧紧发条的决心;这让我感到某种相似的恐惧,与无望。
我们也许要慎重考虑一个问题:当生活的机器久转之后,它将被动地、悲剧性地停滞,还是我们可以主动为其转向?我们对无望生活的控制力,到底有多少?
3 ) 奔溃边缘的女人:现代性/拮据、秩序/失态
如果不是因为第四届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展映单元“女性主义电影:尚塔尔·阿塔曼70”,我可能也不会在《让娜·迪尔曼》这部电影诞生了足足45年之久主动打开它,毕竟我没有办法保证不在影院环境观看的情况下,我是否能够集中注意力整整201分钟,还是这样一部特别的、没有可供辨别的类型元素的所谓先锋电影。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这部电影没有想象中的沉闷,我甚至觉得窥探她房子的空间构造都如此有趣,进门处直走是客厅,右拐进去厨房在右手边,走到尽头是女主角的房间。
实际上这部电影文本精巧、结构有序(三段式),从第二天傍晚烧坏了土豆开始,(此时影片时间差不多过半),接下来的100分钟里女主角的每一次动作都令我屏息紧张。

尚塔尔·阿塔曼如何在24岁就天才般地为她的电影注入女权主义、颠覆电影形式的长镜头、无尽的沉默和女主角丰富的”面孔“表演我便不再赘诉,本篇文章也不过是笔者印象主义式的观感。

一、美妙的放映事故

值得一提的是,在观看这部的“第二天”伊始,我的电脑画面暂停在注目客厅的情况(字幕还在随着音轨而匹配播放),我聆听着女主角在厨房洗洗涮涮,紧接着出门修儿子的皮鞋,遇到了旧友但婉拒她一起喝一杯咖啡的提议。

然后我开始意识到不对劲,重新打开这部影片才发现这几段场景是有运动画面的,我没有重新放映这一段,因为经过了第一天对她的了解,我大致知道了像她这样的女人多半没有围绕家庭以外的其他生活,没有社交也没有娱乐消遣。
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个放映事故啊,我光是闭着眼睛听都知道她在忙碌些什么,我像是成为了她周末放假在家的儿子,瘫在沙发上目不斜视地盯着手中的书,维持一个固定的“机位”习惯性地忽视着这一切。多余的机位没有必要,因为仅是静止长镜头就够描写她的生活了。

她当然是极度孤独的。
二、现代性与拮据

我们很容易发现作为寡妇、babysitter和妓女的女主角生活的拮据,她洗土豆和洗碗的是同一个盆子,儿子每天的零嘴是喝咖啡附赠的,客厅中的折叠床,走到哪都随手关灯的习惯,以及在狭小的厨房餐桌前完成刷鞋和食材处理这两样卫生程度要求大相径庭的工作,衣服和鞋子都需要修理而不是购买...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她看起来依然如此“现代性”:吃牛肉喝咖啡的习惯,总是一丝不苟的头发,法式的优雅裙子,看报纸和听电台的闲情逸致。

让我联想到《我是布莱克》中女主角带着两个孩子领社会福利,但依然穿着像H&M之类的快时尚,戴着欧美大耳环;

《诗》中同样拮据但依旧会被人夸赞衣品很好的老奶奶。

这与我认知中国式观念的拮据是很不一样的,说多了可能又要牵扯到影像“后殖民”的问题。
三、秩序与失态
我甚至可以想象她是多么辛苦地在丈夫离世后摸索着回到了生活的轨道(也或许丈夫本就没有给她比现如今更体面的生活),东西的摆放习惯、边烧水边刷鞋的时间利用、如何规律地安排嫖客、精打细算每一笔支出。

所以电影里没有出现时钟也没有通讯工具,她像一台严密的/没有感情的机器井井有条地安排着生活中的一切,当然也正是这种强迫症般的“秩序”让她的生活瞬间分崩离析,天知道突然多出来买土豆的钱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的生活?

她失态的头发和扣子,忘记打开广播的失神都由儿子来提醒,可是她连喝咖啡时最习惯的女侍都可以暂时“失职”,为什么她还要被提醒着回到生活的轨道上去?


或许她从前也有过片刻的不如意,但她成功地自我调节了。这次她抱着“老娘就不信今天做不好了”的信念冲调咖啡,但她的价值像被倒进水槽的咖啡一样一文不值,她又想起今天种种的“水逆”,怎么连想修补一件衣服都这么难?
十(六)年如一日的隐忍在观众的“凝视”下亟需有个发泄的出口,没有摔碎负累的婴儿是她母性残存的最后温柔了。

她控制不住地高潮了,行为和身体都无法由她支配,杀死男人后的她重新“活”了,我总算与女主角一起舒了一口气。

这就是,一个崩溃边缘女人的故事。
随时都可以成立。

4 ) 香特尔·阿克曼:洗碗和谋杀的强度在电影中是同等的
香特尔·阿克曼早期访谈: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电影创作
1976年,香特尔·阿克曼带着她著名的突破性电影作品《让娜·迪尔曼》(Jeanne Dielman,23 Quai du Commerce,1080 Bruxelles )在美国巡回展映。同年11月19日,她应时任芝加哥艺术学院电影中心馆长B. Ruby Rich之邀来到芝加哥参加放映活动。
当时阿克曼住的Palatine Building客房的楼下正好有两位女性摄影师Kate Horsfield与Lyn Blumenthal正在拍摄一组对女性艺术家的视频采访。她们用当时最先进的摄录一体机Portapak camera记录下了B. Ruby Rich对阿克曼的采访过程。由于当时只有一盘磁带,所以整个被纪录下的采访时长只有50分钟。

在「导筒」为大家带来这篇份采访的翻译整理之前,采访者B. Ruby Rich希望读者了解几件事。
首先,阿克曼当时才刚刚出名,她早期的作品在美国没有被展映过,所以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关注,即使是美国的资深影迷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其次,她在24岁的时候就完成了这部广受赞誉的电影,这部杰作定义了她的职业生涯,也为她许多其他辉煌的成就蒙上了阴影。因此,这次采访是一次对她的了解,因为当时几乎找不到关于她的报道,也没有互联网能够查找信息。

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让娜·迪尔曼》经常被当作一份女权主义宣言,在许多研究小组中被分析,被作为例子来说明激进的女权主义美学在屏幕上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人们强烈渴望定义女性主义电影的审美观,《让娜·迪尔曼》完美地符合这一要求,以至于这部电影在如野火般迅速传播的争论中得到了支持。
可这种对电影工具式的使用最终让阿克曼放弃并终生拒绝“属于”任何群体,她也拒绝她的电影被纳入任何归类当中;但是在一开始,她并不是那么的坚决,事实上她似乎欢迎这样的解释。同样的命运也出现在她的早期电影《我你他她》(1974)中,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就成为了一部“典型”的女同性恋作品,这让她非常懊恼,尤其是她自己主演了这部电影,所以阿克曼很快对这部电影的表演感到尴尬。在这段早期谈话中,她承认了这部电影具有一定的自传性质,并且谈到了她早期写剧本时的不成熟。
不管怎样,香特尔无疑是一位值得推崇的导演: 身材娇小,年轻得令人难以置信,充满激情和才气。
B. Ruby Rich作为采访者,这次采访是为了捍卫她,试图让导演自己解释《让娜·迪尔曼》这部非凡作品的一些含义和指涉,并把将其置于她自身发展的背景中; 对阿克曼来说,诠释自己的电影是她后来一直否定的东西,她的工作是拍电影而非解释电影。但是在这段采访里,她没有那么戒备,会透露一些有趣的信息,有些是后来大家熟悉的,有些则是从不为人所知的。

B·卢比·里奇(以下简称“里奇”):我们从你决定用35mm拍摄自己的第一部影片《我的城市》(Blow Up My Town,1968)这件事开始谈吧。
香特尔·阿克曼(以下简称“阿克曼”):我那时有点疯。当时我觉得,如果能拍部短片的话,我就可以向别人展示,这对我有帮助。
里奇:拍这部片子的时候你多大?
阿克曼:十八岁。实际上,拍摄一部黑白电影而且只拍一个晚上的话,35mm和16mm是差不多的,所以我选择了35mm。当时我正好有机会使用一台不怎么花钱的摄影机。

里奇:你是怎么找到设备的?是因为你在上学还是你认识什么人?
阿克曼:我当时在上学,用差不多10美元一晚的价格租来的。10美元总能在身上找得到的。
里奇:那之后你就拍了《蒙特利旅馆》(1972)吗?
阿克曼:是的,我是1968年拍的,但当时没有剪,也没做声音。一天内拍完要比找到剪辑机和混音机更容易,混音需要跟其他人一起。所以我又等了一年才开始混音和剪辑,我当时住在剪辑室里,因为没钱。两年后,剪辑室打电话给我,要我取片子、付钱。最后大家都是满意的,我也拿到这部片子。
就在那时,我离开了布鲁塞尔,去了巴黎,在那里闲逛,没拍片子,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拍一部。后来有人在在电视上播了这部影片,那成了我后续电影的开始,因为我的片子开始有机会被看到了。

这部片子我不大喜欢。不过第一部短片更没什么形式感就是了……声音部分或许有点,但我这么做,完全是无意识的。制作第二部片子时,比第一部晚了三年,我已经开始思考形式了,但没有整合自己的想法。第二部开始使用长镜头,因为我开始思考剪辑和剪辑带来的操控。但是第二部片子并没有什么安排,演员都是即兴的,我现在不喜欢这样,但是当时并不清楚这会出什么问题。当时之所以会即兴,是因为他们希望表现得“真实主义”一些(注:“真实主义(verism)”,是19世纪末意大利文坛上出现的一种艺术潮流。它属于批判现实主义的范畴,又受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它强调客观地表现生活,通常是下层人民的生活。)你知道“真实主义”吧?就是verité(注:法语“真实”)。
里奇:现实主义吗?
阿克曼:不是的,是“真实主义”。
里奇:自然主义?
阿克曼:(点头)他们想表现得自然点,希望加点什么可以让主题看起来更自然,但这样就会没有核心,你明白吗?我那时并不知道自己必须安排好他们在拍摄中需要做的事,才能让拍出的东西更有节奏感。所以,这部片子非常温和,什么都没有。
里奇:那你的第一部长片是《我你他她》吗?
阿克曼:是的。第二部短片真的很糟,当时我很绝望。我喜欢第一部短片,我觉得我只是偶然做到了,那只是第一次尝试。我想拍电影,想了几年,然后发现自己拍得不好,这很让人恼火。我来美国,在纽约看了一些电影,就是在这里,我明白了电影的张力,类似这些,我以前都不知道。

里奇:你在纽约看了什么电影?
阿克曼:很多都是在 Anthology Film Archives(实验电影人乔纳斯·梅卡斯和几位合伙人一起创立于1970年,专注于独立电影、实验电影、先锋电影的保护、研究和展映)看的:斯坦·布拉克哈奇(Stan Brakhage)、迈克尔·斯诺(Michael Snow)、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乔治·兰道(George Landow),还看了一些霍利斯·弗兰普顿(Hollis Frampton)。然后发现可以拍一部没有叙事和观点的电影,这很不寻常,但却有点如释重负。之前我只想拍叙事电影,所以那时觉得像是解放。所以我拍了《蒙特利旅馆》,说它完全不是故事片,也不准确,因为它具有连续性,从一楼到屋顶,从夜晚到黎明。


里奇:你回巴黎前,在纽约拍了《蒙特利旅馆》?
阿克曼:是的,这个旅馆在纽约。
里奇: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在通过拍这些个人化的影片向拍长片过渡,拍一部能在影院上映的电影?你一直都这么打算吗?
阿克曼:没那么清晰,走步一看一步,没有什么大目标。
里奇:你什么时候拍的《我你他她》?这是部什么样的片子?
阿克曼:我1974年完成了这部电影,根据我1968、1969年写的故事改编的。这部片子很私人,但不算是自传性的,而且结构清晰,有一些部分我以前经历过。这部电影分三部分,讲述了一个女人,也就是我,事实上还是个青少年,我扮演这个青少年……这部片子就像三次不同的旅行。
第一部分是在房间里,第二部分我离开了房间,跟一位卡车司机一起上路了,第三部分我去见我以前的恋人,留下跟她一起过夜。不过,主题没那么重要。这么说吧,这部更像是……我也不知道了,太难解释了,因为它不像《让娜·迪尔曼》那样“观念”。实际上,我拍《我你他她》就像拍第一部短片那样,没有想太多。

里奇:你觉得《让娜·迪尔曼》是第一部让你觉得叙事、形式和情感以你想要的方式融合在一起的电影吗?
阿克曼:是的,没错。
里奇:《让娜·迪尔曼》的主题——家务,她的妓女身份,还有谋杀事件,这些都吸引了很多女权主义者的关注以及女性的大量反馈。这是你之前所期待的吗?还是跟你的意图有所不同?我很好奇。
阿克曼:观众的反应吗?
里奇:是的,对《让娜·迪尔曼》的反应,法国或者比利时的,都可以。
阿克曼:我并不清楚会有怎样的反应。拍的时候不会多想,做完之后,我看成片的时候说:天呐,不会有人想看下去的!因为很难想象,商业影院里的观众期待在电影里看到什么,我不清楚……
里奇:你拍的时候完全没有从社会学的角度去思考吗?
阿克曼:两天前,我向观众解释了这一点。我和玛丽莲(Marilyn Watelet,《让娜·迪尔曼》副导演)写的第一版剧本,会更社会学一点。那意味着更多观点,我们知道自己在表达什么,但不清楚如何结尾,因为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合理的社会学结尾,但不知道该怎么办。过了一段时间,这成了一个道德问题:我们凭什么为一个45岁女人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不住在她的身体里……我们意识到,我们想表达一个又一个观点,所以需要找到场景来承载。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处理,我写完剧本的时候,并不清楚自己写了什么,真的不清楚。我只知道,她会是个妓女,这包含了我们的一些观点,她是个家庭主妇,是个妓女,仅此而已。
还有就是,我写的时候几乎没有考虑要表达什么观点。我只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来自童年的一些形象非常强烈,我的母亲,我的阿姨,所以这不仅仅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表达观点。

里奇:所以,德菲因·塞里格表演的那些每日例行公事更多是来自你的观察而非弗洛伊德理论?
阿克曼:没错没错!随着第二位客人的出现,有些事情开始不一样了,那是一次性高潮,尽管我没有把它表现出来,但是它激发了后面发生的所有事。
这不是弗洛伊德式的解释——因为所有人都告诉我,有过一次性高潮,就还想再来一次。但是对我来说,在她的处境之中,拒绝性高潮就是她最后的力量,她最后的自由空间就是不让性高潮发生。正是因为她高潮了,因为她太虚弱了才无法抵挡……后来一切才都崩溃了。

里奇:所以对她来说,这更像失败的到来而非自由?
阿克曼:也不完全是这样。我不觉得性高潮总是最好的。不像赖希(Wilhelm Reich,心理学家,代表作《性革命》)说的那样:上床(fucking)啊,高潮啊,就行了。我不清楚这究竟是不是赖希说的,(高潮会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快感理论什么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理论,但我就是觉得,很多女人之所以没有性快感,是因为她们无意识地保护了自己的一些空间。
里奇:我喜欢你的解释。导致她开始崩溃的原因是什么,我听到一些说法,“她需要的就是一次好的性爱(阿克曼:)”,这太陈词滥调了,听到就烦,而且我觉得很难证明这种说法是对的。
我发现,电影中的色彩很有张力,房子和生活非常像做过绝育手术,但是色彩却非常感官,你有意让色彩对观众产生这样的效果吗?
阿克曼:我不想要印象派那样的光,我需要非常准确和丰富的光。事实上,光来自上方……
这可不是为女人打光的最好方式,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样打光更好(她指向侧边),她只有一点点补光,所以她不会有黑影。这就是我想要的,因为场景是在房间里,不是印象派那样的。色彩要强烈,我不知道会产生你说的那种效果。

里奇:我注意到电影剧照因为是黑白的而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
阿克曼:那些剧照很差,很便宜,不是拍摄过程中拍的,是从剪下不要的电影负片里选的,但是印得不好。
里奇:我不是那个意思!看到那些剧照,我意识到,如果这部电影是黑白的,会更悲剧、残酷或是更verité(真实)。
阿克曼:那是伯格曼吧!(笑)我看过一些黑白的电影样片,但我有点被彩色样片惊到了。
里奇:为什么?
阿克曼:我不知道,讲不清。一开始黑白和彩色的样片我都看了,我觉得很奇怪,我被彩色样片惊到了,因为它好真实,黑白就有点……
里奇:更柔和?
阿克曼:是的,冲击力没那么强。我没法用英语解释。我不需要那种距离感,电影的风格已经足够有距离感了。
里奇:你是怎么和德菲因·塞里格一起工作的?多少是她自己的风格,又有多少是你的要求?
阿克曼:很难说到底有多少,我们用录像机拍了很多,用来排练。我不想让她在表演里加太多东西,她也的确这么做了。我们用录像机倒放,我会向她解释我想要什么。我说过,一个动作重复一万次会让你觉得这个动作是与生俱来的。

她很快就明白了。几乎一切都写好了。所有通常不会出现在剧本里的动作都写好了。她说:我没什么可发挥的;一切都写好了!一开始,她有点沮丧,但最后她找到了自己的方式,出色地完成了我所写的。这很难!她找到了角色行为举止的方式,她在生活中并不那样。最后,她和那个男人做爱的时候,她和他一起高潮,德菲因找到了自己的表现方式。
里奇:最后一场,和那个男人做爱,我觉得比恐怖片还可怕。
阿克曼:太可怕了,我都没法拍下去。她问:你还想再来一条吗?我说:不!我受不了。当时我的母亲也在片场,她说:哦,可怜的德菲因。
里奇:你的母亲也在?
阿克曼:她来探班,就在拍那场戏的时候。(笑)

里奇:你和你的母亲讨论过这部电影吗?
阿克曼:她很爱这部电影。有一次我们给她看德菲因吃面包片的排练,还有吃肉那场戏,她说:哦,那个可怜的女人,一个人在厨房里。她的感觉很强烈。
里奇:你从你的母亲那里取材很多?
阿克曼:是改编,电影里肯定有我妈的一部分,她也在一些地方辨认出了自己……但我不能说就是她,我不能,完全不能,因为她不再是个家庭主妇了……

里奇:我不知道人们对卖淫有什么看法,在艾德丽安·里奇《女人所生》(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这本书中,她收录了很多十九世纪女性写给失恋专栏的信,讲述她们的婚姻责任,性就像卖淫一样,她们在床上对丈夫的义务,跟在厨房里一样。
阿克曼:是的,我知道,是这样的。
里奇:女性把婚姻当作卖淫,你这样觉得吗?你觉得卖淫是更极端的性描绘吗?
阿克曼:是的,一些女权主义者说,你不可能跟一个男人做爱而不出卖自己。我不太确定。他们还说你很容易被强奸的。这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在婚姻里,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
里奇:看电影的时候,我没有想明白谋杀的原因是什么,多大程度上跟性有关。你还提到过一点,你想让谋杀看起来跟其他行为差不多。你能谈谈结尾吗?
阿克曼:可以。不少人问我关于谋杀的问题,他们说:哦,那是象征,她为了生存杀了那个男人,为了生存,每个女人都必须杀死男人。我必须说,这是他们的问题,如果他们从象征的角度看待谋杀,那我真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他们关于女性的困惑。?
里奇:大多数男人都会这么说吗?
阿克曼:对的,他们觉得受到了冒犯……我想要那场谋杀,我就是那样写的,对我来说,合乎情理,不只是为了完成影片,这部电影就是那样构成的。还有人说:谋杀情节有商业考量,是商业片的主要元素,暴力和性也是。
电影中的确有很多谋杀情节,但不会安排谋杀的女人洗碗。他们会觉得如果电影拍了一个女人洗碗,就不该拍她杀人,因为两者不该联系在一起。我倒觉得把它们放在一起很合适,杀人和清洁的强度是一样的。
如果没有谋杀戏,会像很多电影那样以微妙的感觉结束,那就是个闭环,非常老套……我不想要那样的结尾。我觉得一切都分崩离析了,我不觉得谋杀意味着解放……她希望一切都井井有条,你明白吗?我是这么觉得的。我觉得最后一场戏比谋杀更有戏剧性,如果拍完杀人,电影就结束,这很好理解,可是谋杀后还有整整八分钟,这比谋杀本身更重要。

里奇:是的,谋杀一点也不戏剧化,人们很容易把它跟好莱坞电影联系在一起,习惯看“形式电影”(formal film)的人不会觉得有什么,其他人可能会不太能接受时长、节奏和拍摄方式,也还没学会摆脱对谋杀的固有反应,他们会觉得谋杀很重要,即便电影里不是这么表现的。
阿克曼:电影是有等级制的,亲吻特写在商业片里地位很高,洗碗就很低,但我觉得这些元素都是平等的:亲吻、洗碗和谋杀,他们觉得杀人情节太耸人听闻而不该有的时候,其实又创建了另一套等级制,为什么要这样?我不同意。
里奇:这很有意思,至少在美国,很多“形式电影”有点走进纯粹主义的死胡同。
阿克曼:我也觉得。我1971年来纽约的时候,这些电影完全改变了我的想法,拓展了我的电影观,但现在“形式电影”变得如此学术化,跟好莱坞电影一样压抑,它其实没有那么多受众,但是对于了解这类电影的人来说, 它变得越来越沉重。
里奇:我觉得,汲取“形式电影”的态度,再吸收好莱坞电影的情绪、角色和叙事,把它们重新组合起来,这很有意思。
阿克曼:哈哈,我真的觉得这不是偶然,也不是巧合,我来自欧洲,我带着欧洲电影的自由感来到纽约,我回欧洲的时候,又带着美国结构主义或者说形式主义电影的自由感。
里奇:欧洲似乎有更多在剧情片框架内拍先锋电影的传统。
阿克曼:纽约没有,制片人在欧洲从来没有好莱坞那么重要,导演总是很重要的,有一定自由度,不是说全都这样,但有一些。导演从筹备电影到完成剪辑,都一直跟着。在这里,每个环节都被分割了,更像产品,即便我喜欢一些莱坞电影, 它们多少都有点像“金汤宝” (Campbell’s Soup) 。这跟欧洲不一样。导演会从剧本创作就开始跟编剧一起工作,直到混音结束。不能只是拍了一个又一个孤立的镜头,却不跟剪辑师一起工作。
里奇:《让娜·迪尔曼》是你自己剪的吗?
阿克曼:不是,我跟剪辑师一起,不过我跟了全程。
里奇:有比这个更长的版本吗?
阿克曼:没有。我数过,一共十一卷胶卷,我知道每卷有多长,所以本应该是3小时45分钟,但我用手表计时,发现只有3小时18分钟。所以是一开始搞错了,只有这一个版本。
里奇:你觉得大家对《让娜·迪尔曼》的关注会改变了你工作方式吗?你对此有什么感觉?
阿克曼:很糟!(笑)我觉得《让娜·迪尔曼》达到了某个高度,像个有成就的作品了。从开始拍电影到现在的七年时间,我得到了我一直在追寻的。 我可以再拍一部类似的片子,一直重复,但我不想那样,所以我现在必须找到新的方式,一些未知的东西。我唯一知道的就是,如果我拍一部离自己更近的电影,那样我就能找到新的路径了,而不是困在已有的形式里。
我在纽约拍了部新片,我还想去其他地方拍,这也会是个变化,当你还是个孩子或者青少年的时候,没法开拓世界。现在,我知道机器是如何运转的,这台世界机器。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存在于内心,像我青春期那样。所以我觉得我要走出去。
里奇:下一部要去其他地方拍?
阿克曼:对的。
里奇:你在纽约拍的新片是什么?
阿克曼:跟纽约有关。我不是说这部片子都取材纽约,只是一些纽约的镜头。声音有一部分来自三五年前我妈给我寄的信。这部片子能带我去向别的地方,因为它不像《让娜·迪尔曼》那么有野心。我觉得很好,这部片子没那么有野心,这就是我想要的,没有什么大的抱负。挺愉快的,唯一一点就是我喜欢跟演员一起工作,但这部里面没有演员,混音和剪辑很有趣,不过拍的时候没那么有意思,不像《让娜·迪尔曼》。
原文出处
//www.jstor.org/stable/26413736?read-now=1&seq=1#metadata_info_tab_contents
“CHANTAL AKERMAN INTERVIEW, CHICAGO: 1976/2016”
B. Ruby Rich and CHANTAL AKERM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ilm Quarterly
编辑/翻译/校正:李斯佩克朵
2020年第四届山一国际女性影展「女性主义电影:尚塔尔·阿克曼70」Feminist Film:Chantal Akerman70单元中展映三部风格迥异的香特尔·阿克曼之作。 与此同时山一还复刻了《让娜·迪尔曼》中的一个场景——“我们还原了电影《让娜·迪尔曼》中的餐厅,并放置了一个和电影相同的机位,摄影机所拍摄的内容将被实时投放在大屏幕上。游客进入场景,即为进入电影,他们从“看”变成了“被看”,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毫无剪辑和修饰地展现出来,自拍、发呆、站立、坐下、说笑、沉默,和香塔尔·阿克曼的固定长镜头一样,时间被连贯地呈现。我们看着时间的流逝,时间为我们所有。”



5 ) 场景信息和电影语言
场景信息
《让娜·迪尔曼》以极少的场景构建出一个女人的生活空间,这些场景内部蕴含的信息及场景间的关联无疑是本片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场景为室内的封闭空间,即让娜的家中,包括厨房、走廊(连通家门及各个房间的门)、卧室、浴室和客厅(也是儿子睡觉的房间)五个部分,由这些场景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罗列。以下分析几个关键场景。
(一)厨房
厨房作为全片的第一个场景,也是导演想要突出的最重要的场景,这一点在后面分析电影语言时具体再说。厨房是一个主妇每日庸常的体现,其中发生的事件看起来最反复、最“无聊”,但却包含了女主角的身份核心。除了烧水动炊擦桌洗碗这些家庭杂务外,片中重点刻画了三个场景。一是每天早上起来给儿子擦鞋,这蕴含着一个母亲的细心与爱;二是两次中午自己给自己准备午餐,这是一个单亲母亲独居的孤独;最后一处是尝咖啡。让娜在反复调试过两次咖啡后才决定把咖啡全部倒掉,重新再磨,这一段描写体现出她对待自己的生活是呆滞死板的,并且开始走向一种失常。后文还有一场喝咖啡的戏,这两段均是作者的伏笔。 厨房延伸出去还有一个阳台,在这一封闭的室内场景里,阳台是电影“画框”的“窗口”,不过遗憾的是这一小小的阳台竟然成了本片最为神秘的空间,我们仅能通过厨房门窥见其一小部分,或许这也是导演的寓意所在——在这个黑漆漆的家里,有一扇通向外面的门,但它却在大部分时间被忽视。

(二)走廊-门口-客厅-儿子的房间
当让娜走出厨房,来到走廊以后,影片紧接着向我们展示了她的另一重身份——一个妓女。走廊蕴含的信息主要集中在门口,其余部分则只是被让娜的走动所填满。门口是让娜每天中午迎接邻居、下午迎接客人、晚上迎接儿子的场所,三天内门口发生的事件也很好地折射出了让娜的变化。第一天晚上儿子回来,让娜起身前去迎接并亲吻儿子;第二天中午在门口与邻居寒暄了较长时间;第二天晚上,儿子回来,让娜并未迎接而是呆坐着;第三天中午与邻居仅两句招呼再无其他。让娜的“失语”不是一种偶然,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她与儿子关系的隔阂。这里可以谈到“客厅”这一重要场所了。首先这是一个公共空间,尽管只有她和儿子两人,但他们的谈话并不亲密,而是客客气气的,比如让娜全片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别一边吃饭一边看书。”让娜例行公事般地读信、检查儿子背书情况等,更多时间两人是沉默。而到了夜晚,“客厅”转变为儿子的房间,这也暗示着公共空间向私人空间的转变。儿子睡前的两段对话都是私人的,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母子交流。但这样的交流却也并未显出亲密。在第一段对话中母亲是谈话主体,在诉说和逝去的父亲的当年往事,而儿子却反问母亲为何不再婚,他对母亲的选择没有丝毫的理解;而第二段对话则是儿子滔滔不绝地说着自己的心事,母亲却没有任何回应,直接以“太晚了”搪塞过去。在第二处场景中,母亲站在门口,儿子斜倚在床上背对母亲,这就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同时这一处景深也直观地表现出母子的隔阂。其二,让娜的“失语”归因于她对过去的沉湎。在一场找纽扣的戏里,让娜在与一位店主的谈话中详细地说着关于这件衣服的故事,往日的美好时光仿佛一一在她眼前重现,然而这种怀缅终究是得不到回应的,我们都无法走进让娜的世界。


(三)咖啡厅
还有一个较为重要的场景是咖啡厅。咖啡厅的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二天下午,让娜买完毛线以后来咖啡厅喝杯咖啡,这是她生活中为数不多的闲暇时刻。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场景几乎是(全片中罕见的)完全静止的,除去端起和放下咖啡杯的细微动作,让娜始终位于画面中央静坐,像是发呆,也仿佛是在想什么心事,这个镜头是一次视觉的注目礼,是引导我们认同并走进让娜内心世界的有效方式:
在一幅画面或一个镜头中,相对于一个处于不断运动中的人物,一个始终处于静态中的人物居心理优势,呈现着某种对情境的掌控力。
而让娜第二次来咖啡厅的场景则更有意思。她进门后先是愣了一下,发现门口的位置被人占了——这说明这是她常坐的地方,而当她坐到相邻的座位之后,镜头并未随着让娜转移,而是依然凝视着原来的位置。于是让娜被挤压到了画面的边上(这不是让娜第一次位于画面边上,但是是我们第一次感受到明显的挤压,因为画面的中心是被一个从头到尾一直存在的陌生人所占据的)。这两次喝咖啡的位置的转变(在构图上反映为由中心到边角)正是让娜失常的标志。让娜依然发了会呆,但这次她却没有喝咖啡。她静静地调好了咖啡,手指微微端起咖啡杯,然后猛地一放,收拾东西离开了。原本我以为这里导演又用了一次跳接,像前两次男人进出卧室门之间发生的事,以及第二天吃晚饭的过程,都被略过而代之以前后的两个动作。但我反复看了两遍以后发现,这里丝毫没有剪辑的痕迹,让娜真的没有喝咖啡!为什么这一小小的动作如此重要呢?正如我前面所说,咖啡是走向失常的伏笔,此时的让娜连享受下午这片刻闲暇的心情都没有了,这也正是她在杀人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或许正是在此刻她下定了杀人的决心,这一意外的举动将那种焦躁不安、反复挣扎的心境展现得淋漓尽致。





电影语言
(一)机位
本片采用的是一种客观记录的拍摄方式,即摄影机始终与角色保持适当距离,没有任何特写镜头。以特写镜头主导的电影——譬如去年的《少年的你》,能够无限放大情绪的张力,同时在对角色情感的细腻捕捉中容易让观者产生代入感。而相比之下,我更欣赏阿克曼这种冷峻、克制的做法。这种做法在当时无疑是颇具先锋性的。同时我也想到新世纪另一位擅长这种风格的导演——蒙吉,他的代表作《四月三周两天》完全地体现出了这种拍摄手法的优势,即客观长镜头写实的力量。
本片基本使用远景至中景镜头。最远的一个大远景镜头出现在让娜家楼下,在这个镜头里我们远远地望见让娜从楼里出来走上街,在这个镜头之前用了一个明显的空镜来衔接,展现了让娜生活的街区的冷清场景。而本片最近距离的中景镜头则出现在厨房,这也印证了我之前说的:厨房是导演想要突出的最重要的场景。因为厨房最能体现这位女性的核心身份。同样地,本片通篇都采取一种平等的拍摄角度,且机位几乎与人物保持水平,而偏偏在厨房里机位是偏低的。我们知道,平等也是这部女权主义电影的核心诉求,首先自然要让观众以平等的角度来观看。俯拍代表的是含有审视性质的目光,而仰拍则有提高人物形象的意味——如威尔斯在自己的作品里常用仰拍展现人物的高大形象。而厨房里的低机位也蕴含着同样的意思。这些家务庸常无非是重复的劳作,但它们浓缩了让娜为妇为母的生命核心,也代表着一个平凡女性最撼动人心的能量。在近距离低机位的注视下让娜的形象似乎一下子变得高大起来,成为整个画面的支柱力量。
处于相对小的景别/相对大的银幕形象呈现的人物,较之于相对大的景别/相对小的银幕形象,更具有规定场景中的掌控力或意义呈现的肯定价值。



(二)构图
首先,本片大部分时候采用的是稳定常规的封闭性构图。除少量空镜外大部分镜头都是以人物为主导的。因此我们可以主要从人物位置来解读画面的意义。人物作为画面的重心,并不是说要把人物放在放在画面的中心位置。事实上,导演完全无意将让娜推向观众视线的正中央,在绝大多数场景里,让娜都位于画面的一边,甚至只是偏离中线一点。譬如在一场餐桌戏中,画面把儿子放在正中间,而让娜则坐在一旁。这些场景好像都在说,让娜只是自己生活里的配角,她从来没有为自己做出什么重要的事情(直到最后)。







不过,阿克曼也植入了一些不稳定因素。譬如在让娜与邻居对话的场景中,邻居以画外音的形式出场向让娜抱怨自己的生活,该处构图是对电影“画框”的一次明显突破。阿克曼以“窗口论”的开放性构图指涉画外空间的存在,此举反映出她不仅仅在讲让娜的个人生活,而是在折射所有家庭主妇这种囚笼般的生活,邻居这一角色的介入将这种折射表达得更为明显。

此外片中也有多次对“画框中的画框”的运用。最明显的一处,是在结尾处的性爱戏前后,导演刻意用镜像来展现让娜的动作,增强人物心理的不可捉摸性,而杀人镜头也是在镜中完成。最终画面停留在镜中的尸体上,而镜子旁边还摆放着一张让娜与丈夫从前的合影,这是对生活最无情的讽刺。
人物与其镜中像两相映照,可以借重种种关于镜像的隐喻,构成虚与实、真与伪、真言与谎言的表达,构成关于人物某种内心状况,某种内在冲突、乃至精神分裂症的视觉呈现,构成某种直面或拒绝直面的自我的表达。




(三)视点
本片的视点是本片最为吊诡的存在,也是理解这部电影的重中之重。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看”这部电影?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是“谁在看”。本片对传统叙事的颠覆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其绝无将摄影机隐瞒的意图,但其也并非是摄影机作为一种客观记录方式时的机械注视,而带有明目张胆的窥视意味。而片中对“画框中的画框”的多次运用正是对这种窥视行为的自反:
画框中的画框凸现并强调了此情此景中的人物;同时,它也可能形成一种对画面构成/画框的自指,从而形成一种丰富的视觉表达;它间或暗示某种窥视者的目光或窥视行为的存在。
这样来看,摄影机与人物的关系似乎不那么平等了。在窥视的过程中,摄影机被赋予了超出道德界限的权力(观看人物洗澡、做爱等),其入侵使得人物被死死地钉在了画框里——让娜全片总是以正面、背面、侧面展现在我们面前,其运动并不自由(无法三百六十度地展现在镜头前),而是被限制做出任何“灵活”的举动。
因而这部电影的平等视角,实际上只体现在个别正面机位的段落里,这些也是电影中的高光时刻。比如第一次在咖啡厅喝咖啡的那一场景,再比如电影结尾的长镜头——所有积攒的能量全都在这一段长镜头中爆发出来,在这一静止的凝视中,喷涌而出的情绪终于找到了释放的出口。让娜独自坐在漆黑的房间里,端坐在桌前,边上正是用来存放她的“收入”的钱罐,手上和白衬衫上沾满鲜血,窗外不时响起微弱的车鸣,我们跟随让娜陷入一阵沉思,又或者只是迷惘。儿子即将回家,面对杀人的母亲和尸体将作何反应?让娜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我们只看到她微微偏了下头,画面戛然而止,但这一形象已经永远地留在了我们心中。


最后再说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吧。影片的后半段我是和我的母亲一起看的。作为一位家庭主妇,也是完完全全的电影门外汉,她认为影片中大量的长镜头实在是难以忍受,并且调侃自己说:“原来我的生活就是这么无聊啊,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同时她也告诉我她印象深刻的一幕,是让娜在第二次擦鞋时手一滑将刷子扔了出去,她说:“这个生活细节很真实,我也有过。”是啊,一部四十多年前的电影,至今依然能够触及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以及精神角落,这就足以称得上伟大。感谢阿克曼的这部天才之作。
*文中引用段落出自戴锦华《电影批评》
6 ) 记的一点点,依然只是呓语
心境被最后的突然震碎了,嗯只余留着痛苦和茫然,还有疲惫,说不出什么来了。就把观影上半部分的感受码一下。
感觉看到了很多…宁静,重复,无味,漫不经心,娴熟与疲惫,是被困住了吗?擦鞋的一点点随意,采购的一点点雀跃,捏捏两块方糖慢慢放进杯里,是仅有的乐趣;倦意和疲惫藏在洗碗的背影里,过滤咖啡时的嘴角,瘫坐沙发时的眼底。像是习惯和内化:每天都是这样…没有足够的精力去跳出这一切,琐碎的疲惫和规律的依赖是很重的。发呆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想很多…
停驻在橱窗前,回头一点点的笑意,像是整部电影唯一活力的地方。 还有母子关系,像是都憋着一口气。吃饭时,母亲开口;临睡前,儿子开口。一个累了只想看书,一个累了只想睡觉。
情人…我没想到会有个转折点。(好像全部的全部都连接起来了。)明明还在为好看的衣裳开心。嫣红,麻木,局促,难堪,后悔,痛苦,爆发。我想这是突然涌上来的决定。坐在椅子上茫然的表情,看的人心揪。最后呆愣的笑,又像是解脱。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真她妈难受啊💦。会让我感觉,不该是这样的。该好好的。我只看到了她的疲惫,没想到会是这么沉重的痛苦。我也该预料到的,寡妇为什么有人给她钱?
至于儿子说的那一段话,可能像把刀扎进了她心里。嗯。
像在看白噪,重复但不烦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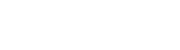




















7/10。阿克曼把家务处理成含有性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含义,第一次嫖客按门铃前,让娜正在煮土豆,和嫖客回到走廊时她很快开灯,紧接沥干土豆上的水继续正常生活轨迹,第二次由于性交的兴奋,送走顾客后忘了开客厅的灯,同样忘了炉子上煮的土豆和盖好盖子,直接去整理卧室、洗澡,重复的情节动作暗示性造成家庭秩序的混乱。汤盆和霓虹灯光成为妓女身份的象征,每当客人离开,让娜把钱放进一个汤盆里,闪烁的灯光打在餐桌后面的玻璃橱柜上,母子吃晚饭一幕也伴随闪烁的灯光,让娜手边若隐若现的汤盆掩饰了母亲/妓女的双重生活。最后一天让娜回家发现姐姐寄来的包裹,接客前让娜从包裹里拿出一件粉色睡袍举到胸前,外在得体的睡袍令让娜厌恶肮脏的卖淫,诱使杀死嫖客,她只此一次放松下来,坐在屋内阴暗的餐桌旁,身后那束灯光保留了内心残存的一点体面。
大学毕业论文的时候为了梳理清楚自己的观点,我还试图用这部电影举例,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会幻想,有没有一座城市的广场会日夜不停的放这部电影呢,这就是女性的存在。这部电影是香特尔阿克曼导演的前期集大成之作,将自己喜欢拍的事物和自己主张的表达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容器盛放,因此十分自然。我很喜欢电影里吃饭的场景,因为它很少被打断,是真实的,比起劳作场景更为难得,现在我们的吃饭场景常常是导演要玩花活的舞台了。
在沉默中爆发的熵增片,现代的强迫症的女性主义的关乎生存尊严的;这要是放以前看大概会觉得冗长无聊,然而现在过着类似居家宅女生活的我却感同身受,静默繁杂的日常routine真是有力量;低机位固定长镜头、略有夸大的环境声;开灯关灯、出门回家、做饭睡觉、卖淫养儿、寄信收件,对生活没期待最残酷。
安迪沃霍尔附体,太考验耐性了;表达空虚无聊的最佳方式,就是直接展现;三个小时无聊的不仅仅是观众,还有主角,但正是这一行为艺术,让片尾的行为变得情有可原。
看了三小时你就受不了了?那她是怎么忍受几十年的呀。
坚持住是看这片唯一忠告
生活是写实的,杀人是写意的。静止与生活的暗流。没有什么“女人的生活”,而就是生活,如果说本片是女权的,也就是因为它把一个女人生活中的三天当成了生活本身吧。希望有一座电影院全天不歇止放让娜·迪尔曼,每个在日常琐碎里打转的人走进去,一眼就看到了意义。
我想为它建个小组叫做“我快进了”
真难想象这部对时间和空间语境超级前卫的电影竟然出自二十岁出头的女导演之手,这部女性电影的特殊性在于除了主角身份的变换之外,还有隐性的故事分支,十分钟的结尾将前面三个多小时的情绪突然释放,平静的震撼。
我们凝视三个半小时的主妇生活如坐针毡,却对自己庸庸碌碌的人生无动于衷。电影不应该只有荡气回肠。
阿克曼说并没想要拍一部女权电影,里面的女性完全可以是个男的。可是我最喜欢看人做家务了。哦维也纳牛排。里面的厨具都想来一套。三小时完全不觉得长。可能因为人美做什么事都好看。
空间通过节奏显现,出神的时刻往往最接近真实,可以对照无家电影,阿克曼永远走进了她眼中的阴影里 #SIFF20#
【上海电影节展映】上影节收尾。长达3.5小时,一位单身妈妈,家庭主妇,兼职妓女的3天日常生活。对白少到几乎可忽略。足足190分钟的枯燥琐碎、反复压抑与隐忍,方汇聚成一瞬间的爆发。中间小睡片刻,其余看得认真。若非在影院真难一口气看完。想到做了20年家庭主妇的我妈及无数如此一生的妇女
焦虑与崩溃在看似琐碎无休止循环的家务劳动中逐渐累积,波澜蕴含在最微小的动作细节里。看完第一个念头是给妈妈打个电话,她这么多年真的太辛苦了。当然这部电影远远不止这些,它说的是我们知道却不屑提起的每一个普通人。被深深地震到了。当年的阿克曼才25岁,天才啊
看了100分钟,快进了90分钟,越到最后反而越好看了,看了最后7分钟,沉寂的生活孕育出杀机。still image,阿克曼果然跟阿彼察邦、王兵是一路人。(论自然光对于转场的重要性。)这部电影属于阿多诺所谓的“抵制美学”,为了凸显当代生活的琐碎以及无意义的重复,导演选择放大并重复它的琐碎于无意义,直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观众在埋怨的同时,也会意识到该谴责的其实是那个使存在变得琐碎而无意义的体制。
「所謂的清醒與否,也僅是一種錯覺。當個體認知的資訊系統夠多,彼此衝突,不斷提出新的問題而且彼此毫不相干,超過他的心智(先不管是不是喝了太多酒)所能處理的時候,他將會在他自身構築的理論之海中,溺水。」(李奕樵〈另一個男人的夢境重建工程〉)
等待晚上迎接白天,白天打扫晚上睡觉,日常生活没有烦恼,做菜吃饭购物接客诸如此类,看完一场电影,没见过谁的微笑,直到最后一个镜头,一起坐着发呆。要不是那个晚上,心血来潮宰客一刀…做菜吃饭购物接客诸如此类,妈妈和妓女,千秋万岁
固定机位,平淡生活;一个女人,开灯关灯。去除了技巧,没有任何修饰,这样的处理特别贴近生活的本来面貌。但如此白描并不等于无节制地铺陈,影像仍然在隐晦地传达着导演的意图,凌厉突然的结尾,瞬时幻化出各种五味杂陈的情绪,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完成了故事的升华。
犹如仪式般的重复场景之间,涌动着日复一日累积酝酿的无数念头,终于一刺解千愁;相当大胆的固定机位长镜头,初看闷,慢慢地会溺水其间。
十颗星。令我窒息想想都要哭出来的,整个人都不好了又燃起无限斗志。天才的、深刻的、革命的。一定要耐着性子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