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本片根据导演自己的童年回忆拍摄,他的父母都是医生。一位女医生在乡下医院里为前来求诊的村民和和尚看病,她和一个兰花养殖场的主人热恋,同时,在一间城市医院里执业的一名医生爱上了她,而在他和他之间,却发生了一段不寻常的情感交流。导演仍以长镜头表现人物细腻的情感,片中不时出现一些幽默的小人物,譬如牙医兼职做歌星,求药的老和尚亦为他人施药,年轻的和尚一心想做唱片骑师等。陌陌影视陌陌影视监狱风云之终身犯遗产2013一代名伎李师师雪山奇迹双手1999潜行者粤语潘神的迷宫最后的疯狂1987飞渡卷云山粤语从海底出击第四季公仆2雾之旗2014宠儿(2018)雷霆行动浔风赤子心闪烁的西瓜纯情罗曼史OAD彼得潘与温蒂血手印国语黄埔军魂丈夫的秘密听风者之歌寻护者热血街区电影版:极恶王好莱坞巨猿风中战士不系之舟人间失格
长篇影评
1 ) 感受阿彼察邦《综合症与一百年》:意识的建筑
意识就像一栋建筑,通道交织,房间众多,结构复杂。随着生命进程,意识不断延伸,不断发展。开辟新的走廊,打通新的房间。而记忆便深藏其中。


当人尝试回忆过往的某个片段,就需要打开某扇门。忘记房号,敲错房门的情况时有发生。记忆中的元素也像鲜活的个体,有时会穿梭于各个房间,引发记忆的错乱,混淆真假。当从某段记忆中抽离,就像关掉记忆的房门和走廊的灯,再穿过意识的大门,进入意识的另一个空间。



人透过自己的意识之窗,看着窗外的一切,让新的记忆不断涌入,不断吸收,也试图抽离出来,融入外界的一切。这些记忆穿梭于意识的通道,与人擦肩而过,最后走进属于自己的房间,或走出意识的建筑,被彻底遗忘。





儿时的记忆,往往藏于建筑最隐秘的角落,毫不起眼,却影响建筑的方方面面。就像人们爱谈起家乡的美食,或儿时时常光顾的路边摊。多数时候,人们会认为这些都是最好的。然而,这些美好有时并非源于食物本身,而是记忆和乡愁。

家乡在发展,更繁荣,更便利,更“现代”。但人们总忘不了过去那些,如今看来有些破旧鄙陋的街景,不愿走出内心深处的家。在我梦中,家永远是那几间有些破旧的小屋。因为家温暖的底色,永远都来自那张熟悉的,儿时的床。

2 ) 狂欢者症候群
发展中国家很幸运,他们有一个永恒的创作主题,永远牵动着西方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和良心。就是西方工业文明对东方传统家园的入侵和破坏。后发国家在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全球化进程中的悲惨遭遇和对田园故乡的无限追忆足够讲述几个世纪。其实不止几个世纪,只要后进国家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一天没有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民族心理得不到伤痕安慰和尊严补偿,这些委屈和苦难记忆就会不停被讲述,成为国族叙事,代代相传。《恋爱症候群》在西方电影节大获成功,更因泰国政府对影片内容的干涉搅起舆论风浪。尽管会触碰泰国社会的禁忌,但阿彼察邦绝不是泰国政府的敌人,他的先锋姿态和边缘状态不过是他扮演的艺术家身份所要求的。他对逝去的故乡与传统得永恒书写无不浸透着他的民族之心。反而是那个被抽象化的西方和他们的文明,才是他在影片里真正批判的。当然现在的西方知识分子不在乎被指责,他们对自己深恶痛绝,对所有清算和取消甘之如饴。
《恋爱症候群》用双联画卷的形式呈现了同一家医院的过去与现在。导演再度大胆启用中断叙事的手法将影片一分为二,前半部分的人物和遭遇被高度对应的移植到后半部分,一切重新来过一遍。虽然叙事被一分为二,但线性演进的时间,不断扩建成型的医院空间让影片保持着高度整体感。而剧中的人物其实也不过是同一拨人的下一世轮回:医生在医院里继续为病人看病,他们仍有各自的感情生活。街市上的人们依然在健身娱乐。人类以极大的弹性适应着不同的外部世界,而导演则用影片发出警示之音,新的文明正将人们异化到恐怖的边缘。
略去不谈前后两部分在细节上如何一一对应和导演的意图,观众单凭直觉就可以感受到两部分中迥异的色彩和空间氛围。前半部分的画面里充斥着绿色的生机,后半部分的画面到处是白色的机械冰冷。显然,爱情更适合发生在前面那个更人性更温暖生动的空间。单恋女医生的士兵求爱不得,在花园里小石桌前像小孩子一样枕在臂弯里听女医生讲述她自己的单恋故事。牙医和他的僧侣病人在夜色的走廊里聊天,他们听得到蝉鸣和风吹过树梢的声音。分手后,医生来到寂静的诊室,他的病人躺过的座椅似乎还留有他的体温,窗外的大芭蕉叶垂手伫立,见证着爱情的忧伤。
后半部分,新一代的医生们在新建的现代化建筑里工作。窗外不再有树木和绿色,而是迷宫般的空间格局和冰冷的白色。似乎是钻头发出的持续低音代替了蝉鸣,不再有兰花,只有被宣告了死亡的愤怒少年。前半部分有腿疾的病人不再对人展示她的腿,她从医院白色的走廊里倏而消失,似乎对现代医学的治疗完全无感和失望。工厂一样的空间里充满各种奇形怪状的义肢,装上了假腿的人正在练习走路,一个正在向后人类进发的世界。这个全新的时空里当然也不再有我们熟悉的爱情,那个有着树下私语,有着体温的爱情一去不回。只剩下人类身体简单机械的勃起反应。
和其他所有阿彼察邦的影片一样,这是一部需要思想和开放的心灵才能欣赏的电影。普通的观众可以隐约感觉到影片要表达的对逝去的幸福无可奈何的追忆,和对现代文明的警惕和恐惧。而喜欢挑战的观众则可以用福柯,德里达,巴塔耶,德勒兹来拆解这部电影。没人能真的了解导演创作的真相,各类访谈也大多是场面上的废话或者故弄玄虚。反而是膜拜者对影片越拆解越阐释越觉得深奥无比,导演作为电影大师的形象越来越呼之欲出,支持者对自己打造出来的神顶礼膜拜。艺术家和他的门徒,将电影带入一个知识分子的阐释比大众直观体验更值得期待的高级境界。
阿彼察邦的电影不是为普通观众制作的电影,而是一种对艺术形式进行自由探索的电影。它属于以制造和引导电影艺术品味的国际电影节,属于不断需要引发惊奇和关注的媒体,属于大学里做文化研究的师生们,属于生活中追求新鲜独特的文艺爱好者。阿彼察邦被奉上艺术的神坛,也许并不意味着电影艺术的收获,而是折射出电影艺术与全球文化环境的危机。在由法国后现代思潮开启的瓦解一切的文化运动中,人们陷入到一方面再也无法找到可信赖的文化偶像,而另一方面又对引领者充满刚性需求的可悲循环。在阿彼察邦的世界里,那些“特别懂电影的人”用各种符号和表征来狂欢。更多的普通人隐约觉得电影好像变了,人类共通的情感在一种新型电影里被一套知识系统所编译,观众再也无法直接感受而是必须用与之匹配的知识储备来解码。在这场思想的盛宴结束里,一套符号阐释着另一套符号,观众在头头是道的阐述里逐渐被启蒙,变得客观睿智,而生活,隔着遥远的距离,变得沉静而美丽。
3 ) 疾病是生命里的派生物
症候是一种机体丧失正常运作的病变,或者是隐藏在意识内核中的某种非知识,当主体与他/她的生活世界的关联发生一定的间隙、裂缝、崩落和中断时,症候就会出现,阿彼察邦的症候是诗意的魂灵,缠绕在环境中,镌刻在时间的肌理间,用一切看似迷离的崩落、间离的抽脱去拓宽现实与梦境的距离,用一切有破坏力但却赋予自然气质的的方式去捕捉无意识的状态——「打破线性叙事、形成陌生化表述、割裂因果逻辑、时间与空间的自由跳转、虚构和真实间恣意穿梭…」最为惊惧的一幕(医院地下房间)莫过于用固定镜头和缓慢的移动让观众与环境签订契约,让运动中的人物变为他者,然后让他者拥有返回凝视的力量:“我们观看的人或感觉到被观看的人,反过来也在观看我们。”两段式的设计更是这种相互观看的返回式凝视的神学的体现,剧中每一组人物,打破百年的时间的线性延续,进而在不断的返回对视中呼应着过去和现今,让观者游离在陌生的熟悉感和熟悉的陌生情境之间,产生一种巨大的、迷离但是透明的张力。
布努埃尔言:“诗歌的发明似乎是为了表现已经深深根植于诗歌的下意识生活。”电影叙事用空间来组成时间,因此空间既能够在蒙太奇技法中构建时间,同时也能借此解构时间,如同诗歌文本本身连续不断的流动意义——“电影将时间与空间结合更进一步,时间因此真正成了空间的一个维度。”(艾利福尔)。电影将编码中的结构隐喻还原成空间状态,在《恋爱症候群》中空间是医院主体,伫立于自然丛林和工业化丛林的二元对立中的呈现,关于爱恋的群体记忆围绕医院/疾病建立,在飘忽不定间勾连。疾病代表着对身体、社会秩序的永恒焦虑,医院空间吞噬着焦虑的个体,如同片尾的通风口的黑洞,吞噬虚无缥缈的烟雾。对曼妙自然的向往和对冰冷城市的怅惘,自然光源下的乡村医院是充满生命力的状态,人与人之间淡泊却亲近的交流,人工建筑下的现代医院白色、冷峻,而疾病则是存于两者之间永恒的且不被治愈的——“疾病是生命里的派生物。”(福柯)
而孤独是生命的永恒状态。
4 ) 镜像反转
承接《热带疾病》的双段叙事,《综合症与一百年》不再如前作一般在粘稠的氛围中陡然坠落,而是建筑了如巴赫平均律般彼此勾连的两段平行时空,通过跳跃的剪辑在复调结构中不断穿插着即兴的旋律,生成了一种镜像反转般兼具均衡与错位的美。
表面上看,阿彼察邦将弥漫着青草味的乡间诊所置换为渗透出石灰味的城市医院,实际影像的运动逻辑也发生了调转。在乡村田园段落中,人物往往处于固定镜头的景深中段,摄影机不断尝试着空间纵深的压缩,俯冲式向外扩散,如即将跳出画幅的限制拥抱外部的未知;而进入城市工业段落,规整森严被笔直线条切割的室内空间让影像更贴近人物,却也止于人物,仅在手持跟拍与推轨移镜中维持着某种气若游丝的挣扎,成为漂浮的幽魂。
人物情感的蓄力被刻意削弱,其更像是附着于建筑装置的零件,传递着所处环境的色彩与气味,而在前后两段中,零件材质的变化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灵动追赶着的对话节奏被迟滞沉闷的停顿代替,前段被表白的女医生视角转换为后段需要以搬家留住爱情的男医生,诉说与倾听的悠闲情调也变为由热吻和汗水交织的激烈情欲;牙医不再兼职歌手,僧侣也不再拨弄乐器;一氧化碳中毒的病人接受了老者的瑜伽治疗,依然僵硬而呆滞;假肢被藏在房间存放烈酒,而失去下肢的病人却在医院过道艰难移动。
科技功能的进化与人物感官的退化同步并行,生成了撕裂的症候,又在固定与变动的拉扯之间营造出一种“相似即亲近”的假象。阿彼察邦的神秘主义也完成了由“震慑”向“迷惑”的变革。标志性的丛林野兽是否缺席?影片尾声的装置艺术大赏揭示了答案。医院褪去道貌岸然的外衣,终成长为巨兽,露出爪牙,将阳光与空气、风烟与尘水尽数吞噬,人物也在封闭狭长的甬道之间彻底迷失。
再次回归俗世,小桥流水、花坛草地、零散锻炼的老者与蜂拥而至的广场舞,人为制造的的现世安好抚平了巨兽潜伏的狂怒。女人希望男人搬去她工作的新址,对男人说:“那里还靠着海。”男人回她:“不要用自然诱惑我。”



5 ) 生长在一起的回忆与现实
现实是以视觉为主的综合感受,回忆是一种抽象的幻想元素。两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公平的影像
同时将现实与回忆以影像的方式再现出来,其实就是抹去了现实与回忆之间的不平等
真实的回忆与虚幻的现在
在头脑中再现了一万遍的回忆比一个身处其中极其苦闷以至于经常抽离并浮想联翩的现实更具有“真实”性。
影片当中那个乡村爱情故事就是个“真实的回忆”而现代医院的故事就属于“虚幻的现实”
为什么两个故事那么像?
因为“回忆”是“现在”的回忆,它注定会有“现在”的影子。既然“回忆”已不是真正的过去,现实又那么虚幻。那到底哪个才是真实??
生长在一起的回忆与现实
种植园主向人推销兰花时说“你看它们纠缠在一起多漂亮,可是人们不太喜欢认为看起来像缺陷“ ”也许生命本身就像这样”
看到这里导演拍这部片子的初衷逐渐浮现出来。
6 ) 形式素养太好了
第一个吸引我的镜头是片名出来的时候,叙事突然一分为三,一个人被扔在屋里,女医生和别人走了,但声音一直在场,镜头却一直在凝视空旷的草地。
片中还有几处重复的叙事,对白基本上一样,镜头角度相反,对话的对象也换了。这种似是而非的时间循环的错觉很奇妙。这种基于重复的渐变和极简主义音乐的感觉也很像。
和音乐配合最好的一段是地下室那一段,烟雾缭绕的室内,抽风口那个黑洞在画面中越来越大,音乐和视觉的形式感相得益彰。
叙事方面,那种“走着走着就走岔了”的感觉特别好。女医生给老和尚看病,说着说着,老和尚倒给医生开起药来。叙事内容不重要,形式好。
每次看阿彼察邦,都会叹服于其形式素养,不得不服。
至于以前比较看重的精神议题,现在觉得也不是那么重要。当然也还是要的,就像个篱笆,远远地围一圈,把要紧的东西都框在里面,不让它跑出去。真正让人玩味的,还是语言上的那些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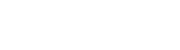




















1. 我基本上就没看懂。前三十分钟节奏缓慢,再30分钟趋于平静,60分钟左右,突然发现,这很蔡明亮啊,最后三十分钟节奏突变,镜头给了地下室的管道,机械,大型的抽油烟机,让你开始思考着所谓的现代化是为什么?我们究竟在哪个阶段?面试医生的问题那么可笑,不靠谱,但是还是有人来求医、问药。
93/100 #第6300# 叙事被减弱至仅仅是人物来来去去的时刻,连交谈也很短暂,而仅通过氛围,产生一种无法解释的力量。音乐是工业化且空灵的,指向对现代世界温和的批评、带有讽刺意味的冷,隐隐让人不安。虽然在电影里大量显现的是外部的结构,如建筑内外的结构、人的关系结构,但更关注的是各种内部的存在状态,接近人类内心的困境。而邦的电影总是在治疗观众,如溪流冲洗身体,到结尾“邦的父母”终于在公园里坐在一起,阴阳平衡了,现代世界也与自然融为一体,这样美妙的共存开始让身体充满活力,勃起了,起舞了,似乎在现代化过程中唯一的幸福来自爱的自然联系。虽然后半段梦的质感更强,但到结尾似乎梦和现实已经分不太开了,越来越多“确凿的迹象”,似乎预示着邦后来的作品,不再进行严格双段的结构,现实与梦境的融合实则更为有机。
A / 阿彼察邦的“日蚀”电影。镜头收拢光线,折叠的时间被逐渐展开,医院成为回收能量的巢穴;镜头被光线/视线“驱逐”,欲望的时间被固着于错乱的雕塑/阳具之凝视中——这时它真正成为了飘移的幽魂;日常装置成为反向捕获镜头的黑洞,电影在黑洞中重新睁开双眼,一个“世纪”的时间停留在何处?
大师大师大师!阿彼察邦的神秘性不仅在于拍摄客体的飘忽多义,更源于主观意识的赋魅难测。自然田园段落的影像自上而下,俯冲式的向外扩散,场景是跳跃而自由的,人物内心的悸动却始终紧密勾连;工业城市段落的影像自下而上,在挣脱之力的驱动下,空间被机械切割,形成垂直闭塞的区块,直至医院长成真正的巨兽,将阳光与空气、风烟尘水尽数吞噬。爱情是一种病症,被培育、被传染、被变异、被治愈。
又是JOE惯用的上下两段式,前一部分拥有自然、爱情、生命。后一部分充斥机械、严肃、冷漠。刻意的对比,用意显而易见。
第二次看,不是“建筑”而是“场所精神”,是人在其中的活动赋予场所的情感和人格。幽默感是场所的个性派生出的(小镇石凳上谈起的兰花,城市医院的瑜伽疗法,广场“粗俗”的健身操…)啊啊啊啊真的想不出还有别的导演能拍出这样的电影
非常喜欢的故事,并无夸张的奇技淫巧,仅仅通过运镜以及空间的营造便将现实的故事渲染出超现实的美感。摄影风格非常统一,缺少直接的特写使得整部电影仿佛在一个旁观者角度凝视情人间暧昧的波动。该“旁观者的眼睛”(即摄影机)在每个场景的始末通过巡视察觉周围的环境,也使在那个场景中的物种——人与周围这至少存在百年的地貌发生关系。爱是荷尔蒙驱使的产物,但人与其他物种的区别是常常会通过理智制定规则,为了维系社会的稳定抛弃低等社会的那些情况,掩饰潜意识,所以说常常是踏入爱河而不是坠入,但内在的感情终究与任何动物毫无差别,所以最后一段终于达到了我心目中最满意的高潮——动物本能,近距离特写的眼神交换将暧昧流动于方寸之间,旁观者不复存在,本性主宰了自己。流畅的叙事中,关系终得搭建完成,最后的毛坯房暗示了新的希望
这片最牛逼的地方在于把写实电影拍出了超现实的味道,阿皮查朋的电影总有些神秘主义的味道,可能是那些如有生命的运动镜头,以及神秘且宗教味的配乐,或者是有些神奇的故事。闷是闷了些,但绝对是种全新的体验,所以他被热捧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神奇的观影体验。开场五分钟之后就昏睡过去,醒来之后发现电影又重新回到最初的位置,女医生又开始向男主角发问和做心理测试。只是时间发了推移,而电影的视角也发生转变,而我也不再是睡着之前的我。
伯格曼的孤立式对白和复现,费里尼和安哲的人像,安杰依瓦依达的储藏室地下室堆积的人体和其他废料,布列松的画外元素……阿彼察邦并不神秘,他恰恰是能把前辈精髓吸收到自己电影中的优秀后辈,再融合一些泰国特色元素,加入自己对声音的不同用法,因此对于电影没有一定积累的人来说,就显得有些神秘。他的长镜头对比安哲,显得有些呆板,但静止镜头没有到罗伊安德森那种强迫症程度,用得算不上一流,但跟孤立式对白和复现的手法形成一定的内在关联,空镜头就比较随意,没能达到小津那种克制减省有种画龙点睛的味道。看阿彼察邦,应该看他怎么把技法用到自己电影里,而不是人云亦云,附庸风雅,说空话。说难听点,去国际上闯荡,你主题深度没有达到惊世骇俗的程度,谁要听你讲大道理,作为一个导演,还不是拼技法加民族特色。
7/10。空间构图上医院体检的学生排列成与医院长廊相平行的队列,佛像雕塑被建筑物交错的几何线条所压迫,氧化物中毒的网球少年(指代文艺界)害怕军装父亲(泰国军界的审查),地下室的换气筒仿佛吸走人类的灵魂,城市医院象征现代病,而乡村静静流淌的吉他声和谈话时镜头转向绿色稻田象征恢复美好的人性。
果然TMD没看懂。结构绕得挺好玩的,著名的两段式哈。但是总觉得装逼的成分大,阿比察邦欠点诚意。这方面贾樟柯比他实诚。另外BW出的碟,字幕是亮点……
剪辑和对白太神奇了,完全创造了两个相似的世界,相似的情节和人物确是完全不同的细节和人物关系,大量的神秘空镜和长镜头使电影蒙上一股超现实的味道。导演几乎创作了一种全新的叙事模式,加上一些泰国独特文化的对白,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力量。★★★★
镜头是间离的,摄像机后的眼睛审慎着“症候”。但它同时又是先验的,这是流动感来源之一,流动感来源之二是情感,人物试图用“爱情”画出一个圆,却跌入永恒轮回的困境。灵动的空间从缥缈地建立,被压缩,到最后的坍塌,引领一切走向虚无。舞动着的人们为什么如此快乐?或许陌生的摩擦永远比亲密的汗水更温暖。
故事其实很简单,改成《医院物语》就好解释多了。记忆互相缠绕,人在时间长河中游玩。
1/女醫生跟蘭花養殖男在陽台聊天後接了一顆隔著窗戶看日落的鏡頭,這時候放起了牙醫唱的歌,在兩個時空交錯的瞬間,突然想起小時候在鄉下經歷過的一種感覺,不是想起,是感受到了,遺忘已久的一種感覺。2/最後集體廣場舞,音樂好像超級馬里奧,不小心眯了一下,夢到了自己飛進去變成了其中一個舞者。
阿彼察邦的又一神秘之作。1.两段式结构上承[热带疾病],聚焦前现代-现代过渡时期与当代的医院图景对比,女性-男性的视角转换(两段开头的面试镜头也正好构成一组正反打),自然与后工业的冲突+共生。2.两段间不无微妙的【差异与重复】,一如两次系鞋带,牙医不再兼职歌手也凸显出专业化分工的趋势,还有向绿色自然开放的敞亮门窗与封闭而惨白的室内空间,还有佛像与铜像所处环境的对比。3.前半段几乎均为远景固定长镜,后半段摄影机则常常摇移推拉逡巡。4.后半段更可细分为三节:医院地下室为插入段落,亦由全片唯一的手持晃镜跟拍导入,漫溢着假肢、机械与施工的味道。5.最后的空镜蒙太奇让人想及安东尼奥尼[蚀],而日蚀的过程与吸纳烟气的管道黑洞也暗自构成对照。6.口述告诫人们不要贪婪取财的奇幻寓言亦见于[热带疾病]。(8.3/10)
阳光下,人们每天唱歌、健身、栽兰花、生病、治病;地下室,悠长的通风管道深入的是最隐秘的内心,那里的人失语,试图记忆和回味什么,却已然陷入百年的密闭空间综合症。
医院与广场——一组对立空间,医院不仅是功能性建筑,也是宗教空间与情感空间,时间的绵延凝固在空间之中,它的神秘也是时间的神秘,在“医院”空间中,不同身份的存在滞留,相爱,离开,身份关系将随时滑动,犹如剧场,在日食的渐变中,观看者获取关于时间的经验主义,而广场同样是驻留的空间,但它的主要功能在于“释放”。正如同身份关系的变异,在《恋爱症候群》的两段叙事中,结构在一种差异化重复的空间—景别中发生转变,全新含义来源于人物与空间(语境)的全新互动,阿彼察邦在进行着一项观看实验:如何在室内制造与“日食”相同的语义?答案是通风管道。所以这两段究竟是以如何关系连接起来的?正如同对于王家卫《重庆森林》两段式的思考可能产生一种空间意识,对于《恋爱症候群》这个悬而未决问题的多重答案也将开启一种神秘主义。
阿彼查尔的闷片系列。超级闷。但是超级好看。一般的闷片都是知道它在讲个什么故事。但不知道导演要表达些什么。但这部属于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但依然觉得无比好看。一百年前的部分有些闷得受不了。一百年后的部分出现了一些微妙的雷同。很有爱。最后是十多分钟的毫无对白的长镜头。类似于{咸豆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