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秋仪(王姬 饰)和小萼(何赛飞 饰)本是青楼女子,解放后,她们“这样的”女人被送往了劳动营进行劳动改造,忍受不了劳动营里辛苦的生活,秋仪翻墙逃跑了,身无分文走投无路的她决定投奔自己的老相好蒲家伟(王志文 饰)。 在蒲家伟的家里,秋仪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发现本来对自己一往情深的蒲家伟在压力和利益面前,也开始变得言不由衷了,最终,秋仪负气离开了老浦,出家当起了尼姑。让秋仪没有想到的是,蒲家伟竟然和小萼走到了一起,他们不仅结了婚,小萼的腹中亦怀上了蒲家伟的孩子。遭到了昔日好友的背叛,秋仪却并不愤怒。陌陌影视陌陌影视季风季节羞耻 第一季天地姻缘七仙女2024浙江卫视跨年晚会神探狗笨吉国语无形杀戮9/10:悲剧前夕航班蛇患(粤语版)寻龙之发丘天棺青蜂侠报告老板之豪言壮旅秀吉疯狂星期一(普通话版)欢喜大逃亡来自谁的启示齐木楠雄的灾难孔雀王子60天,指定幸存者斯诺登你的样子孙悟空大战盘丝洞(普通话版)警与囚第一季五朵警花爱很美味神探南茜 第三季打卡吧!吃货团
长篇影评
1 ) 墙头
去年曾在苏州陆巷古村的一间木楼上随手拍下一张照,日前看李少红根据苏童小说拍摄的电影《红粉》,见片中有些许外景颇眼熟,又看到秋仪翻出去的那间木屋,拿出去年照片来仔细比对,果然是一处。
李少红1994年拍摄《红粉》,曾在陆巷古村及周边借景。04年我去时村中古居尚未对外,07年再去时业已开放了,从照片看与十三年前的影像有五处明显修缮:秋仪翻过的窗原是长方形的,后来向左挖成了正方,故而窗与左墙距离较之前窄,并加了木板;右旁八角小窗亦加上了六角形木框;右侧整排窗都已换过;屋顶与墙头结合处也向下加了木板,位置接着大窗;左墙上曾有木柱,后被拆除。又,电影中机位于房间偏左后角所摄,我们进房间时门在右,站在靠右后角,因此照片同影片中窗外墙头风景有很大偏移,照片中偏左,影片中偏右。
我记得当日在窗口向远处张望,但见连墙接栋,阳光朗朗。未知与此地相关还有这样一个令人怅然的故事。而昆剧《墙头马上》中,李千金与裴少俊私自结合的结局就不至于那么悲凄,虽有波折却终得破镜重圆。我小时候趁父母不在,曾以手撑墙翻过门上副窗到他们屋中偷连环画《墙头马上》来看,佳人小立粉墙,才子马背相望,印象极深刻。直看到结局一句: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去年看到戏剧频道有放早期录制的老片《墙头马上》,才知此剧是昆剧。曾看过的连环画,想起来正是剪此剧分镜头编辑成册。
李千金在墙头找爱人,功成名就。最可怜是秋仪,她后来叹道:早知道命运还是让人走投无路,倒不如那时不跳墙头了。
或许在墙后的都不是些想规矩做人,屈从现实安排的人。曲曲折折的廊,高高低低的墙,有太多故事在此出演。墙头又总有诱惑,譬如《拍案惊奇》的二刻卷三十四中,权臣杨戬的馆中门客任君用被捉奸墙头,甚为狼狈,又说“一枝红杏出墙来”、“路柳墙花”、“逾墙窥隙”,可见墙垣难以阻挡那些不安分的心,反倒还添增了半遮半掩的情色意味;或“隔墙有耳”,墙这边事为那边的有心人所窃取;或人事浮动“祸起萧墙”;或软弱如泥“扶不上墙”;甚至窝里相争“兄弟阋墙”;自招灾祸“引水入墙”;见风使舵“墙倒众人推”——无一不是人心作祟。今过苏州,频见吴中以为特色之一的墙头和落在粉白壁上的影子,恰似人心弯弯直直明明暗暗,一时间想起许多墙头轶闻来。
照片地址:http://xiaoqipao.ycool.com/post.1880799.html
2 ) 云袖之中,寒光一凛
我大学时候,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跨世纪文丛正好如火如荼的出版。对那年代的文艺青年来说,如获至宝,阅读如饥似渴。
苏童的《少年血》因其暴力扭曲的青春期描写,配以芜杂隐晦的江南小镇香椿树的芸芸底层市井生态,一下子就击中了少年的我的阅读G点。
之后就开始遍寻苏童的小说,第一时间狼吞虎咽。从少年血系列到城北地带,香椿树街的系列狗血市井与热血中二少年们,到当时正蜚声影坛的第五代集体导演的著名女性三部曲,分别由小说《妻妾成群》,《妇女生活》,《红粉》,各自成,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侯咏的《茉莉花开》,还有就是这部李少红的同名电影《红粉》。其实他当时还有个小长篇《武则天》,据说电影没拍城,小说我也买了,那个真心一般。
我当时觉得苏童的才华驾驭中篇恰如其分,游刃有余,写长篇就有些力不能逮。那些灵动的,腾挪的,闪耀的文字和段落,放到长篇结构里,就显得浮华,轻佻,猴急,压不住,抻不起,轻飘飘没质感。后来他又出了一部长篇《米》,黄健中执导电影《大鸿米店》,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都不怎么样,小说2流,电影还一度被禁了7年,2012年才公映,结果大失所望,还不及小说的那种粗粝感和压迫性。
女性三部曲里,《妇女生活》写的最好,祖孙三代妇女,原生家庭原罪宿命与基因里的叛逆性,爱恨交织,时间太久很多情节已经忘记,就记得这几个女的在家里撕起来,真的是夹枪带棒,句句机锋。比那些宫斗剧过瘾得多。苏童特别善于捕捉人性中的闪念而过的小邪念将它放大,落地。就好像《红粉》里,小萼与老浦结婚那天,秋仪莫名递给小萼的那把雨伞。三部改编电影里,《大红灯笼高高挂》无疑最佳,超越了原小说。尤其是美术置景的设计,从江南小镇搬到北方乡镇的一个大院落,一下子那种封闭的肃杀感就铺天盖地了。大红灯笼挂起的仪式感,老谋子玩仪式感,天下无对。什么时候都是。
《红粉》电影的美术还原性做得相当好,解放初期的江南水乡的小城。木结构的小阁楼,邻水而起的脏的几乎看不出是黑瓦白墙的斗拱建筑,拾阶而下倒马桶的妇女,雨色中弯曲而去的青石板路面的小巷;以及解放后贴的可哪都是膏药般的标语、三俩的黄军装的正气凛然不断审视你的眼神、氤氲评弹软语中,突然爆出的大嗓门口号、一本正经的关怀,呵斥的口吻,从岸边上船时,秋仪伸手要解放军战士搀她一把,解放军小战士一言不发,给他搭了条木板。像这样的细节,太精彩可惜真的太少了。
红粉小说仅是个短篇,但电影应给为它赋予更多新旧时代在划时代的瞬间的差池感和撕裂感。无论是秋仪小萼这样的JI女群体还是地主二代的老浦,他们都是旧人物,面对新时代一下子破门而来,惊慌失措,完全没有适应能力。老浦之死就是一场与旧时代中产恬适生活的告别。整个生活中,除了床笫之欢,大概最快乐的时候就是他打扮成黄世仁的地主装的时候,他好像还还原一些精气神。结果还被低下一顿山呼海啸的口号给吓得差点尿了。
三个主人公演员找的都极其精准,表演都脱像入骨。王姬的妩媚、坚韧,决绝如刃而柔情似水,气场强大,霸气侧漏,真是大青衣的首选。何赛飞真的是江南妖娆小女子柔情化骨,一口吴语软腻得,虽然明明恨得让人牙痒痒,TM的还是我见犹怜,感觉比《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三姨太还演的更传神。作为旧时代的寄生者,她已经习惯于用肉体依附男性,习惯于依赖周边环境的供奉,根本没打算适应自力更生的新生活。这个原型的当下意义仍然熠熠生辉,美女都习惯于被拥戴和供奉,习惯被备胎舔狗包围,没办法,她气场就养成了。导致你不是她备胎和舔狗,有时候也会不自觉迫于淫威顺从她,好像怕打击她自信心一样。这真是奇了怪了。这种人只会自恋,不懂爱他人,她还以为她的爱是施舍。说起来是气人,不过有时候,男人还真就吃这壶。至少我觉得,年轻时候,没找个能作妖会撒娇,一天不给你找点事就没存在感的美女谈一次虐狗的恋爱,人生还有点小缺憾。哈哈。
王志文演的老浦真的太帅了,我几乎忘了我读小说时候是怎么想象的老浦的外形,现在想来,老浦就应该是王志文那样弱不禁风又帅又有魅力又不负责任的样子。如果他不是雅痞帅,他不是风度翩翩的有点病态的浪荡倜傥,他不是又不在乎钱又肯服低扮软,潘驴邓小闲哪样都占着,阅人无数的大姐大秋仪怎么会看上他,每次都不要他的钱(而且明显,老浦并不差钱,所以也并没太在乎你要不要钱,老浦还真就时喜欢秋仪),秋仪怎么敢断定,自己逃走到老浦那肯定就能投奔终身有靠?至于小萼,小萼大概从来就没爱过老浦,她只爱她自己,而且她设计追求老浦,也仅仅是因为她崇拜和依赖秋仪,反正要投奔一个男人,那就找自己偶像的男人吧,终究不会大错。如果错了,那也是秋仪的错。
电影给了他们三个扎了舞台,他们仨演的都本儿好,本儿卖力气,电影的美术做得也很好,置景服装美术都到位,也有时代的一些背景音色。大概可惜就是,好像插些时代交织的更鲜明更锋利更具有隐喻性的冲突,不管是情节的还是内心的,还是寓意的。老浦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悲夫”,如果他仅仅是流连秋仪和小萼肉欲的缠绵者;如果他仅仅是因为曾经富有豪宅良田而今蜗居斗室;如果他仅仅是当了个会计,入不敷出,被坛慕虚荣的懒媳妇每天唠叨而郁闷;这些会让他给儿子取这样的名字吗?乃至还最后走向贪污公款,枪毙了结?
悲夫者,不过是逝者如斯罢了。一个旧时代被绞绳送走,拖起满天烟尘,甩出个绳头,老浦把自己也套进去了。悲夫,告别者,变成了殉葬者。
秋仪,历经红粉风尘、怀孕、梯度出家、流产、还俗、嫁人,渡劫后,就如所有从旧时代翻涌过来的国人,其实说悟了什么,也没什么悟的,只不过把孩子的名从“悲夫”改为了“新华”。
所谓了悟,就是不过如此。
苏童小说,即使短小篇幅中也能突然给你抖个番儿,云袖之中忽然寒光一凛。
2022年12月27日
3 ) Self-negation and the Redistribution of Body
The logic of self-negation is for all, who and which are relegated to the remnants of the dark old society but are still retained the chances to regenerate, partially for the evocation of a reshaped subjectivity, and partially for the demonstration of a promiseful de-oppressive regime. The “labor camp” for the prostitutes is one of the apparatuses of this logic. In a closely watched space, former prostitutes are deprived of the right to live as before and even, the right to die, yet are endowed a self-supporting and dignified future life. The enforced space itself has already indicated that these women are taken as corrigible vermin, although they are ironically taught to ascribe their “sins” to the brothel madam or social mechanism other than the degrading fate during the pedagogy of “speaking bitterness”. In other words, the labor camp is designed to erase the structural inscriptions of the feudal or capitalist society on the body and spirit of the prostitutes, but at a cost of implicitly duplicating the prejudices to them and negating all their past, their personal history except a good nature that hasn’t decayed totally. I’m not denying the seminal impact of this discipline, especially the redistribution of body, from the haircut, physical examination, regular routine and factory labor—every motion, every form or sign is politically considered--, which transforms the objectified body “for play” or “for sale” to the autonomous body for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deed, life is not so bad for some of these reformed women. Nevertheless, I have to point out two problems remained. First, how can we really distinguish the transformed body, the labor in the factory with the capitalist production that reduces human to machine? The great will of working for socialism or the bright scene in which these seemingly free women are running through the rape flower fields cannot explain all. Second, the pedagogical apparatus and public opinion push the former prostitutes to thorough self-negation, which reduces their past to nothing or dirtiness. For instance, in a scene Xiao’e is irritated by a forewoman who suggests the money she made before was “unclean”, and as a counterpunch Xiao’e declares that money is all the same and call her names later. That’s how the traditional discrimination for prostitutes slips into the conjuncture of the new logic of self-negation. “Unclean”, this is a too rough generalization for the complicated situation of subjectivity and feelings of the prostitutes. To some extent, strategically, it is precisely this kind of thorough negation that leads to the impossibility of the reformation, because no room for the past, no empirical agreement for the future.
Back to the specific details in the movie, I want to future stress the bifurcate of Qiuyi and Xiao’e: For Xiao’e, does the labor camp really change something? (Also, we don’t know whether the former prostitutes are married to the former clients.) Or rather, is the self-negation effective on her? For Qiuyi, escaping from the negating process of the labor camp qua an entrance to a new social life, what is left for her in the society? We see another direction of redistribution of body— To take tonsure, give up her hair that is cherished as a feminine character (versus the haircut of the disciplined ones) and become a nun. But where she comes back to at last is still the symbolic position of Laopu’s embrace, the only position having something to do with an acceptable past.
4 ) 第34名:《红粉》——影史50部平民史诗
《红粉》 年代:1994年 / 国家:中国 / 导演:李少红 / 主演:王姬、王志文、何赛飞
有一部电影叫《中国最后一个太监》,讲的是在清王朝结束之后,那些被赶出紫禁城的太监如何过普通人日子的故事。片中有个场景是已被阉割的来喜,遭到戏班的伙计们捉弄,到妓院里跟一个妓女共处一室,那女人一摸就心里有数了,为了不折他的面子,故意在屋里叫床给屋外的伙计听。其实妓女跟太监一样,肉体的残缺让他们的灵魂也被浸染了俗世的偏见,往往在社会转型期,这类边缘群体总是会率先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红粉》当中的转型期是1950年,从旧社会向社会主义新时代过渡时期,这“新”体现在新制度、新思想和新作风上,旧社会的糟粕都将被全面清洗和摒除,就连喜红楼的妓女们也都被划入社会主义改造的行列里。解放前靠身体挣钱的妓女,如何在新时代里寻找自我认同感,社会又将如何接纳她们,这是我们好奇的地方,不过影片在后者问题上只是轻描淡写地略过,但对于前者,则是把重点放在了两个比较极端的个例身上:秋仪和小萼。同是女人,她们却各有各的不幸。
从秋仪在影片中出现开始,就带着一种自命不凡的自傲,在解放军面前,她还不慌不忙地提丝袜,披着呢子大衣,买块烤红薯,上船前还要让人搀,一副没褪去的大小姐气。如此娇惯的她,怎么受得了人民军队对她“收编”呢?。所以她逃走了,找到了她的旧情人老浦。两人一见面就干柴烈火,不用说,日后在老浦家,秋仪就继续用她的肉体,来换悠闲安逸的生活。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秋仪做的跟解放前的事并无异。按理说这也是门不错的买卖,可秋仪养成的公主病,让她不作就难受。老浦为了服从老妈的安排,只能打算把秋仪安排到外面住,秋仪一听立刻炸了庙,她绝不能被撵走,除非是她自己走!走投无路之下她只好剃发为尼,皈依佛门,然而此举也不能帮她超渡困苦。她怀孕了,又流产了,又因为老浦,跟好姐妹小萼分道扬镳了,还俗后的她几乎失去了对生活的热忱,如行尸走肉一样毫无生气。
同样是No zuo No Die的小萼,从进入教养院起就陷入巨大的不安中。她尝试过自杀,也试图逃走,但都没有成功。然而出了教养院,也不意味着她从内心全盘接受新时代的事物,她心里还惦记着吃西餐,听留声机、喝咖啡这些早已消失的洋玩意儿,对于同志也不太友好(比如跟“马脸”吵架,还扬言报复)。她的大小姐脾气也同样不小,在老浦家不但用脸盆当尿壶,还嫌自己没有戒指,骂老浦没有良心,一吵架就一哭二闹三上吊。坐月子的时候,还做着阔太太的美梦。为此两人彻底闹翻了,老浦几乎绝望地喊:“我自己作死!” 秋仪和小萼的作,归根结底是妓女在旧时代被老鸨压迫,卑微的身份和自命低贱,让她们自己都无法接纳自己。一旦条件变好了,她们就要变本加厉地得到那份原本得不到的关爱。但这却往往是饮鸩止渴,越陷越深。
身在其中的男人也难逃悲剧的命运。老浦其实就是个妈宝男,老妈不让他跟妓女同居,都得照听不误,除非是像小萼这样肚子被搞大了,才只能勉强奉子成婚。老浦对秋仪不是没有爱,只是实在身不由己,资产被没收、秋仪头发剪了,让他只能把爱转向更容易得到的那个人:小萼。可是在婚姻里他又被嫉妒和失去耐心折磨到濒临崩溃,不仅喟叹:“拿你们这些女人真是没有办法!”周旋在姐妹俩中的男人难免被骂“渣男”,但有的渣男也有良心发现的时候,他为了补偿秋仪,给她送去了一大笔钱。不过,这钱却是贪污公家的,挖一个坑来填补另一个坑,后果只能是自掘坟墓。为了贪图一份不亏欠的爱,他甘愿搭进一条命,难怪秋仪在老浦临死前专门赶去见一眼,神情凝重且复杂,眼里满是责问:这样,值得吗?
时间是前行的,人也被时代往前推着走。从前是过着富庶生活的阔太太们,到了如今是人人平等、劳动致富的普通人,身份的转变带动心态的转变,如果不能及时适应这个社会,将会被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压在下面。有的妓女改造成功,进入工厂工作,有的还已经进入了婚姻,然而秋仪和小萼则是在倒转历史,逆时代而行,结果只能是太、惨、了,就连秋仪都说:早知道就不跑出来了。
这样一部以女性悲剧命运为题材的影片,由一位女性导演执导,她就是李少红。在这部影片中她一改之前《银蛇谋杀案》直接、凌厉的影像风格,转而变得富于诗意。还有一些人认为,李少红在这部电影中有意效仿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两部电影同为改编自苏童的小说,编剧也都为倪震,且都有何赛飞出演,两者自然有着暧昧的联系。从效果来看,很多场景都采用了远景,并且画外音和入镜角色的不对等,的确很像张艺谋的处理手法,并以此来营造疏离冷淡的氛围。后来李少红也把这种疏离感放置在了《大明宫词》《橘子红了》《红楼梦》等电视剧中,树立了她独特的女性风格。
5 ) 中国女性导演风格变迁:从李少红到李玉
一、中国女性导演求索之路 中国女性导演的诞生应该追根溯源到20世纪初,谢采珍作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导演在一个绝对的男权主义时代开辟了一条前无古人后途茫茫的大道,在那个连电影拍摄都难以维继的动荡社会,女性导演的声音弥足珍贵。 新中国成立后,女性的社会地位在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压迫下得到重塑,但意识的形成的核心始终是文化,在围绕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新生主流社会价值观的笼罩下,女性对自己身份的认知与对女性意识觉醒的挖掘深度始终逃脱不开时代的桎梏。封建帝制之中形成的男权意识已经在男性与女性的自我认知之中根深蒂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家庭,几千年的文化与意识渗透把关于中国社会共性的话语权全权交予男性主导。建国初期代表女导演王苹、王少言的作品大多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其核心价值观或多或少都逃脱不开男性权柄的约束,即使以女性生活为主导也没有能够有意识的去找寻女性本身的价值和意识,比如“永远忠于党”“永不消失的电波”“柳堡的故事”,尽管影片里不乏优秀卓越的新时代女性,但是花木兰式的女英雄实际依旧是被束缚在男性价值观下的女性人物。导演是以男性英雄在复刻女性英雄,这样的表现形式并没有尊重以女性为本体的女性意识觉醒,而是以一个男权主义者的身份替女性思考女性意识的觉醒。时代的悲剧性决定着女性导演要以男性导演的视角“重塑”女性,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畸形与病态。 在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动乱后,改革开放的文化复苏之风干柴烈火般席卷着整个中国文化产业,加之社会主义特色经济的发展,导致经济与文化的双重接纳,来自于西方甚至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思潮冲击着中国女性导演被束缚住的思想,更多的女性导演加入了影视化作品的拍摄工作。诞生于那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人鬼情”“山林中头一个女人”“谁是第三者”等作品均不约而同的对女性社会地位有着发人深省的思考,同时对两性关系中的不平等进行批判和求索。这一时代女性导演的独到之处在于她们既是女性又是导演,在双重身份的影响下,女性导演渐渐开始以女性本有的细腻和柔软在电影之中表现她们对于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所思所想,她们开始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在黄蜀芹的“人鬼情”中,女主人公是在京剧中扮演钟馗的女老生秋云,在一个男权社会扮演男性角色的女性,影片里多次出现秋云与脸谱虚虚实实觉的结合与其中意味深长的自白,表达着一个新时代女性服务于男权社会与男性角色后在新社会中无法找到女性自我意识的矛盾与恐惧,刻画着在以男权意识为主导的社会里,女性在命运中沉浮飘零去坚持找寻自我意识的心路历程,做鬼容易,做女人却艰难。第四代女性导演替被中国传统价值模式所湮灭的女性意识发声,在倡导对女性本身的关注时也认同了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导演、一个女性的身份。 在20世纪末80年代初,对女性意识的探索迎来了一个漫长的缓冲期,以胡玫、李少红、史蜀君为代表的第五代女性导演的问世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第五代女性导演更多的将时代的符号与对女性社会性质的历史重塑融入在自己的作品中,渴望从男性主导的发声中逃离去创造属于女性自己的视角,从“他诉”转化为“她诉”。在“大明宫词”与“红楼梦”等作品里,女性导演们通过对历史的重新解构去赋予历史女性角色新的生命与意识,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打造着属于女性独有的历史主义观。但是,单就女性意识的探索而言,第五代导演的女性电影始终延续着第四代导演的女性题材和女性解构,很难找到自己对于新时代女性角色的把控与创新。对女性命运的消极预言在她们的电影中潜移默化的形成,不难看出,对于女性自身发展境况与社会对女性的兼容有着属于那个时代独有的焦虑后遗症,这样的不自信成为了限制她们想象力和创新力的枷锁。 随着千禧年的隆隆报鸣,诞生于新21世纪的第六代女性导演以全新的面孔和主导社会主流思想的精神力量重新掌舵新时代中国女性电影巨轮。在日益强大的中国走向世界开疆拓土时,以WTO为首的大大小小的贸易组织争相向中国抛出了橄榄枝,以资本主义为价值核心的文化产业对于中国电影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震荡,以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为首的导演迫不及待地向全世界展示属于中国独有的五千年华夏文化,资本与艺术的完美结合逐渐演变成新时代导演不可磨灭的时代勋章与电影艺术追求。以李玉、徐静蕾、马俪文为代表的新一代女性导演不断的在作品里尝试新时代的女性元素,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在招商引资的国家政策指导下特色化的结合,21世界女性的工作条件与工作岗位更加的多元化,很多属于男性的岗位逐渐被女性取代,社会模式的变动在为女性本身的发展前景与机遇带来颠覆的同时也激发着新时代女性导演创作的灵感源泉。在数以万计日益递增的女性岗位中,女性导演随波逐流的成为了电影届独树一帜的流派并且在国际影坛掌握着极有影响力的话语权,女性题材的多元化与个性化不可阻挡的统治着被资本入侵的中国电影市场。徐静蕾自导自演的“杜拉拉升职记”作为艺术片转型商业片的跳板有其独具一格的表达和信念,讲述着一个新时代女性如何在属于男性职场中凭借自己辛勤的工作与敏感独到的处世智慧在爱情与事业中找到平衡并最终融入社会改变生活的成功独立女性,影片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证明了徐静蕾替新时代女性发声的能力与她能够在资本与艺术中找到契合的悟性。通过徐静蕾的成功,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电影与女性导演风格的蜕变,相比于过去执着于家庭女性的第五代导演,她们更多的找到了属于女性内心世界的追求与渴望,而不是倾向于塑造传统女性在社会压迫中如何苦心经营家庭如何费心养育自己的子女。她们为女性诉诸更多脱离于家庭和传统女性贞守的需求,结合着时代的本身赋予的多元化题材去开拓女性电影的新视野,对女性角色不断的解构。第六代导演在塑造新时代女性时代的同时,也平衡着两性之间几千年来的强弱之差,不断的强化女性自身的独立、坚强和自爱,接着弱化男性在社会中的统治、权力和威严。 从20世纪到21世纪,女性意识的觉醒在社会意识的转变与社会资源架构的转变中走过了将近100年的漫漫长路,中国女性导演更是背负着中国三千余年封建统治文化下女性根深蒂固的社会形态负重前行,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束缚。我们可以在女性题材电影的发源之路上发现一个浅显的规律:但凡社会在进步,女性的地位便会被拔高;但凡女性在社会拥有话语权,女性的自我意识便会更健全;但凡有女性在社会里崭露头角,女性导演作品便越来越具有唤醒女性意识的魔力。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是辩证统一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应,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而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何欧洲的女权运动甚至女权革命能够拥有如此庞大的拥簇,而中国从古至今竟然没有过一次有革命运动实质的女权运动?这来源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家国情节与孔儒礼学,女性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她们的意义被与家庭和国家的羁绊重新定义,女性不能“自私”的为自己考虑,而应该优先考虑自己的做法会对国家和家庭带来怎样的后果,这样宏观的理念和思维早已扎根在所有中国女性的心中,什么三从四德,什么忠孝廉耻,对女性意识的觉醒形成了强大却无形的阿克琉斯之踵。所以,文化的觉醒才能带来国人整体意识的觉醒,而国人整体意识的觉醒是让国人去了解女性意识觉醒的大前提,只有先进文化在社会里得到传播,女性导演才能够用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唤醒一个更大的群体对女性意识的了解与认同。 二、李少红:从女性视角诉说属于女性的的历史重塑与悲剧情结 新黑格尔主义代表人物Bendetto Croce最负盛名的理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史并不是指狭义的近期发生的过去事件,而是指人类在完成过去的活动时对已发生活动的自我意识附加,所以,历史是活在人们心中透过自我意识棱镜反射出的心灵影像,当代是对历史做出叙述时所出现的一种思考状态。胡适在北京大学讲授实在论时这样给学生说: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中,由我们雕成了什么样。书写历史的人所了解的历史是实在吗?真实存在的客观历史是否能与我们主观创造和接受的历史所契合呢?历史就是过去与现在无休无止的争执,所有我们未曾经历的历史都是不断由每个时代的强权统治者一笔一画书写的当代史,不是每一个史官都有勇气与信念写下“崔杼弑其君”。记载历史、研究历史的学问往往随着人类主观意识的变化而发展完善或歪曲捏造,思想的现代化和当代化才是才是历史形成的真正奥义。 李少红将新历史主义观与效果历史完美的融合进她所创作的电影与剧集,新历史主义观认为历史不是大写的单数HISTORY,而是小写的复数histories,历史本就是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连接着虚构、隐喻和想象的历史,带有明显的批判性和颠覆性。而效果历史认为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存在着历史的实在性,理解历史本身就是对效果历史的诠释。在李少红的大部分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中,她诠释了自己对于历史实在性与艺术创造性的理解,以自己对于女性历史角色的重新解构去重新阐释属于李少红的历史天空。李少红勇敢的用效果历史讽刺、粉碎着以男性权力和欲望为核心构筑的概念框架,不断地挑战他诉历史在人们潜意识中的统治性地位,更多的站在了女性的视角为以她诉的历史为替代品篆书立作,以推陈出新的方式一点一点撼动着男性虚妄自私的历史怀旧情结。李少红在历史本体论中基于自然、神、人、生产力的思辨下,巧妙的利用着时代的符号与文化形象还原着更加客观、公允、合乎情理的她诉女性人物历史,在塑造宏观现实的基础下,依然倾诉着对女性在社会中所经历苦难的悲伤和关爱。 我们可以在李少红执导的古装电视剧“大明宫词”中从她对武则天一角颠覆式的表达来探究李少红对于历史重塑的敏锐嗅觉。在李少红看来,武则天称帝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历史因素提供的自然动机,另一个是武则天对于天下危局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无数的“他诉”历史中我们不难透过男性的主观镜头描摹出一个残忍无情、欲望滔天的女性暴君,然而,李少红在证实自己对历史主观性怀疑的同时将自己对于女性的期待与理解投射于银幕中的武则天。李少红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的匹夫不光是男人,也有女人,武则天和其他所有的权力争夺者都有责任与义务去关心天下的兴亡、去承担君临天下的重担,这样构造人物设定的目的无疑是李少红追求男性与女性两性权益平衡的跳板。通过赋予武则天与男性君王同样的、甚至更加先进的政治诉求与执政动机,以极具戏剧性的历史人物作为媒介直勾勾的指向“他诉”历史中潜移默化形成的男权至上主义思想,间接地在属于自己的历史世界中向所有的男性宣告以武则天为代表的女性完全有充分的理由与资格在统治阶级占有一席之地。在李少红的历史剧中,比起对于宏观历史事件的思考与探索,她更加渴望通过消解历史在群众心中的刻板印象来表达她对于当今女性自我价值实现方式的引导与祈愿,不仅用一种极具女性本我态度的创作理念贯彻了她的历史解读,也同样用她充满辩证意义的历史哲学观点突破了历史剧作者单一复刻的文学概念框架。 同样在“大明宫词”当中,李少红对于太平公主一角同样有着属于自己对于女性角色的琢磨与考量,她省略了太平公主因在权力旋涡中斗争而死的悲情结局,转而在太平公主对于爱情、自由的追求上留下了大量的新历史自由创作空间。李少红对太平公主的两次婚姻进行了大篇幅、大幅度的重新解读:在第一次婚姻中太平公主失去爱情是因为母亲对权欲的把控害死了薛邵的妻子,在第二次婚姻中太平公主失去爱情是因为遭到不顾一切奉献心血的爱人背叛,李少红在太平公主角色中灌注的是太平公主在爱与被爱中彷徨挣扎但坚定不移的态度,太平公主的爱被净化掉了权力、金钱、血脉与谋略等一系列可能影响爱情纯洁性的指标,成为了一个为了爱情与自由勇敢的向宫廷权势宣战的具有新时代女性特征的历史人物,李少红用她笃定而坚韧的镜头语言一次次呼吁人们去感受和尊重中国女性遗失几千年的精神文明。所以,当太平公主死于李少红所塑造的“真善美”人设下时,李少红所希望营造的对于“真善美”女性的怜悯、悲伤、同情、惊惧便会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油然而生,显而易见的伤痕式的文学情怀能够在人的心中留下对女性悲剧命运成因的深刻思考与主观批判。李少红的悲剧情结相比于她对历史重塑的倾向更加不具有题材的限制性,甚至可以在李少红所有的影视作品里找到她那一抹独树一帜的悲剧色彩。 无论是“生死劫”中的燕妮【拼命挣脱父权家庭的控制考上大学后,因为平庸但浪漫的小镇青年木玉而怀孕并辍学,最后却发现自己仍旧被以爱情为糖衣炮弹的丑恶男权主义彻底侵蚀后沦为生育工具,看清真相后毅然坚强地选择继续自己的未来】还是“红粉”中的秋仪【在被深爱的男人与姐妹背叛后,毅然决然的选择撇清关系,皈依佛门,还俗后依然选择庇护曾伤害过自己的小萼】,在李少红看来,她们都曾经是男性的衍生品,因为衍生品的特性而注定了她们悲剧的命运,李少红赤裸裸的将男性对女性充斥着占有欲和利用欲的爱情以她作品中独有的冷静与理智一点一点的披露与展示。在“恋爱中的宝贝”和“四十不惑”中刻画的宝贝与段京华与燕妮、秋仪一样,她们都是这个时代出色的女性,经济实现了独立,人格实现了健全,摆脱了家庭的束缚,但她们的结局却不约而同的毁灭在对爱情的幻想之中,因为带入她们堕入无边黑暗的原因也不约而同:每当遇到困难都毫无防备地寻求男性角色的帮助,当她们将掌控命运的钥匙交给男性时,她们的命运也戏剧般的急转直下。李少红通过影片中不断重复的女性悲情故事,不仅是要告诉女性暂时的经济独立和人生自由并不代表人格的完善与思想的解放,女性应该努力的在这个社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属于自己的意义,这样的定位与意义需要撇开或削弱男性角色的存在,在将男性变量确定后仍然能够实现独立自由的女性才是李少红通过悲情情节的渲染所要推崇的,女性绝不能成为男性与家庭的附属品,不要将自己的理想与目标是实现的前提与男性虚妄的、随性的爱情挂钩。 无论是在李少红不断重塑的历史题材还是浸染浓烈悲剧情结的社会题材中,李少红的作品中都饱含着她对当今女性的发自内心的希冀与祝福,以及对两性关系失衡下女性社会状态的求索与反思,用自己充满人文关怀的解读克制而激动地为女性意识的崛起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李少红塑造的众多悲剧女性人物也同时反映着她对女性未来发展前景的消极和悲观态度,一种贯穿始终的创作思路在深度剥离后其实是李少红对女性自身的不自信,认为女性会自主的为男性牺牲而不会有改变,这样的不自信则来源于时代意识的束缚和物质条件的限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时代的印记是女性意识觉醒不可磨灭的枷锁。 三、李玉:以后现代主义思维的人文诉求表达女性本真之态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从理论上难以精确下定论的一种概念,它产生于现代主义之后,意在宣扬人类应该去超越习俗、挑战权威、批判真理,后现代主义没有明确的中心思想与意识,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是随着现代主义衍生而来的附属品,是现代主义的影子和另一面。后现代主义用敏锐且敏感的怀疑和抗争态度去评判甚至颠覆约定俗成的社会理想、人生意义、家庭伦理、传统道德,所有被定义的真实和正确在后现代主义下都是相对模糊和虚无的,后现代主义的表达将逾越了物质本体的辩证和统一两性之平衡平面,打破了宏观社会语境中的无法被互相割舍取缔的顽固观念。 后现代主义电影有着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引用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的观点来进行延伸推导,后现代主义电影是指能够反映后现代社会时代特征的艺术风格的电影类型,这种艺术风格是无中心的、无根据的、拼贴的、戏仿的、模拟的、多元主义的,它模糊了高雅与世俗、艺术与生活经验的界限,往往是与消费社会的商业逻辑和高度发达的科技媒介联系在一起的;狭义上则引用了中国学者伊鸿的“后现代文化学说”进行了比较,后现代主义电影指的是对后现代社会的时代特征进行反应和反思,它具有知识分子精英的怀疑气质,不再相信真理的存在和可追求性,不再相信人类解放的宏大叙事,也不再相信主体人的伟大神话,它是对崇高感、悲剧感、使命感的疏离和拆解,在具体的电影摄制上它往往把这种思想气质融入到电影的表现内容、反映视角、框架结构和镜头语言上,这使得电影往往能显出一种强烈的实验性质和前卫立场。 李玉的后现代主义首先体现在她的光影世界下,在李玉的光影世界中,时代化和人性化的拟人符号滴滴点点在李玉的作品中涌现,以抽象的隐喻与象征化手法制造视觉的冲突,将女性人物的性格与命运记录在她极具锋利棱角与批判精神的的镜头下,多以短时间内拍摄场景及摄影角度不断的切换与镜头和焦距不断的放缩为主要镜头语言。李玉在东京国际电影节获奖的作品“观音山”中,影片在她的剪辑手法下,以一定频率间歇闪回来体现人物行为与思想的迷茫和煎熬,以手持式的摄影机在真实的拍摄环境下随着酒吧摇曳的霓虹灯、列车高速运行的颠簸、破车蜿蜒蛇形的摇晃而有共情感官的表达,将李玉自己崇尚追求女性本真与自由的信仰在她充满怀疑和反击情绪化的镜头语言里以极具力量的方式诉说了出来,以人物近景的写实感镜头也恰好契合了电影人物本身带有的焦虑和忧郁气质。同时,李玉对于水这一元素在她作品中的象征性立体化描绘做出了具有后现代主义人文化的处理,在与范冰冰合作的第三部电影“二次曝光”中,李玉用水在不同环境中的形态去勾勒人物内心情绪的变化和戏剧情节的转折,用浴室喷头中淅沥沥喷薄而出的液柱去赋予女主角宋其精神和人格在虚拟与现实中杂糅不清的矛盾情绪,用宋其与河流的结合象征着宋其回归到了自己舒适区:一个无法让自己走出自己构建的虚妄的思想迷宫转而去接受需要掩盖和埋葬的不幸记忆的舒适区,在影片的最后,宋其在秦皇岛外的大海之中褪去了用以掩盖青年白发的痛苦记忆标识,李玉再次使用以水为基本单位衍生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母性情怀暗示着宋其终于逃脱除了自己在液滴中的分裂矛盾、在河流中的自我麻痹的象征意味符号。在“红颜”和“观音山”中也依然少不了极具李玉电影标志性的液滴、河流与大海,通过记录云姐曼妙的胴体在水中洗浴的情节给予人物圣洁的重生与洗礼意味,通过追随南风、常月山四人乘船在平静如镜的湖面中穿行的镜头表达人物与自然随遇而安的契合和从容,利用水无定性随境而适的特点发掘多层次的象征和解离使水能够刚柔并济的呈现在李玉的作品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李玉用自己对自然元素犀利且不羁的拟人符号化表达独辟蹊径的将女性人物本身具有的的戏剧性和多面性相当形象的、三维的塑造了出来。在李玉看来,展现女人意识最好的表意手法就是以水为媒介展开的,从后现代主义思维视觉去打破客观现实和宏观社会语境所定义的电影写实手法。爱因斯坦说:更简单的理论,涵盖更多不同内容,具有更广阔的应用,这才是更令人信服的理论。李玉打破了观众传统的观影习惯于偏好,突出了对于后现代电影的自我意识和主观精神的补强,她用一种即兴的、无序的、创造的、虚无的影视拍摄手法来表达影片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的思想:本真。 在李玉对于电影情节走向的把控与设计中也体现出她后现代主义式的反抗和怀疑精神,李玉有意识的将自己电影情节创作倾向于对普世价值观下女性形象的颠覆,多次涉猎中国文化中所明文批判的禁忌话题,希望在西方女权主义兴盛的意识积淀里中找到可以用于表达中国女性意识的媒介。在“红颜”中,云姐因为意外怀孕而被迫退学,多年后重新进入小镇正常生活,并和自己认为未曾出世的儿子小勇发生了一段名为姐弟恋的母子不伦恋,在李玉的视角下,她并没有去批判这样在中国传统爱情观中因该被批判的“罪恶”关系,而是选择去给予了小勇和云姐一个美好的结局,去赋予了这段爱情一个名正言顺的两性关系。在“观音山”中,三个在社会上混迹的流氓无奈式的人物和一个老年丧子的京剧演员常月山在一个公寓里从互相斥责警惕的租客演变成互相关怀理解的忘年交,李玉通过书写像南风与常月山这样女性之间相依为命的真挚友谊来展现出一个没有男性爱情所包裹的两个女性角色是如何在坚持自己濒临崩塌的梦想与活下去的信念,以一个奇特的视角去稀释男性角色在传统女性题材影片中从始至终的存在感,从而让人们看到女性在两性关系中除去男性之后的命运可能性,李玉在观音山下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设计中体现了她对女性在社会角色与生活信仰中的更深层次的思考。在“苹果”中李玉消解了婚姻的忠诚与不忠所带来的社会与家庭效应,在“今年夏天”中,李玉更是大胆的尝试了非常敏感的父女乱伦和同性三角恋题材,并以小群逃脱父权的性控制阴影与男友的平庸无能转而在同性之间产生的爱情中徘徊并坚持的行走为结局。 李玉的女性题材电影在向所有的中国男性、女性传达一个讯息:女人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女人不需要男人也可以拥有幸福的生活即使它破烂不堪。以这样的假设为前提,我们可以在李玉的电影中发现一个共性,那就是对男性权威的不断消解和丑化。“今年夏天”里小群已经去世的父亲、无能而没有存在感的男友;“红颜”里云姐失踪的父亲、同样没有责任感的少年男友与两位有妇之夫;“观音山”里丁波毫无廉耻心的再婚父亲;“二次曝光”里畏罪潜逃的父亲和自私自利的哥哥。在李玉的电影中男性要么是处于一个空缺和单薄的地位,要么是他们没有资格和能力去保护女性、帮助女性、尊重女性。李玉的电影在消解男性权威的同时,也塑造着一个个有思想、有灵魂、独立自主、自尊自爱的新时代女性形象,李玉以后现代主义的人文诉求表达了她对女性未来发展前景的自信与积极,并且在资本需求与人文情怀中找到了时代框架下的平衡。 结语 李少红与李玉,一个人用悲情故事告诫女性不能相信男性的所谓爱情与承诺,一个人用消解男性权威的方式告诉女性男人不是生命中的必需品;一个人用新历史主义观重新塑造历史女性形象,从而表达自己对女性人格完善的辩证性希冀,一个人用后现代主义观彻底颠覆传统女性形象,从而传达自己对女性人格完善的批判性思维;一个人对女性群体的发展前景悲观而怜悯,一个人对女性群体的发展前景积极而自信;限制李少红的是时代思想下匮乏的想象力,限制李玉同样是时代思想下崩散的创造力。她们都同样渴望女性意识的解放和觉醒,她们都站在了女性的立场去替女性发声,她们都在同样的希冀女性能在这个社会拥有真正的话语权。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文化是社会意识的一部分,文化的提升需要经过一代代电影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与大胆探索,只有文化进步了,国人的整体文化意识才会完善,一个完整的国人文化意识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充分必要条件。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还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衷心希望中国女性导演可以锲而不舍的追求更加完善更加先进不受束缚不受限制的女性意识,并且一代一代的传承这样的精神。 [参考文献] 葛黎明 新时期中国女导演共性研究 庞守贵、范映雄、李艾蓉 绽放在银幕之中的女性之花—李玉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探析 刘智焕 “效果历史”女性凝视下的新历史主义—以李少红影视作品为例 胡玉洁 李少红影视作品中的悲剧意识和男权批判 2010年9月“中国女性”杂志 用影像探索人生—中国女性导演群体访谈
6 ) 来自歷史學家贺萧(Gail Hershatter)的評論
原書396-8頁,翻譯本《危險的愉悅》409-11頁。
Moving into politically more volatile territory, the 1994 film Blush (Hong fen), by the renowned woman director Li Shaohong, offered an oblique comment on the limited success of the 195os campaign to reform prostitutes. In the film's opening sequence, Qiuyi and Xiao'e, two Suzhou courtesans, are rounded up for reform. Disdainful of the entire process, Qiuyi stops to purchase a sweet potato, commenting that "even a condemned man gets a last meal." She escapes from the reform institute immediately upon arrival and goes to live with one of her customers, a gilded youth named Lao Pu. Xiao'e remains incarcerated. Frustrated by the hard work of bowing cotton in the institute factory, she tries unsuccessfully to hang herself.
In one of the film's most interesting moments, Xiao'e's political instructor urges her to tell her "classmates" that she attempted suicide because she was worn down by the oppression and exploitation of her past life as a pros- titute. Without directly contradicting the instructor, Xiao'e makes it clear that it is not the past that troubles her: rather, she is afraid of the future, exhausted by the work, and uncomfortable because of blisters on her hands. Undaunted by Xiao'e's refusal to draw the proper political conclusions, the instructor then goes on to tearfully recount what is apparently her own story. She is the daughter of a prostitute who sacrificed to put her through university, yet it has taken her many years to get over her shame at her mother's occupation and to appreciate her efforts. Communist reformers are not pilloried or satirized in this account-in fact, the reform campaign is treated sympathetically--but it is clear that the attempt to impose a single narrative of oppression on a heterogeneous group of women is doomed to fail.
The remainder of the plot (which is based on a story by the popular young male writer SuTong) is worthy of a first-class soap opera. Like SuTong's story Raise the Red Lantern, which became a prize-winning film by Zhang Yimou, Blush contains enough inconsistencies and problems to annoy feminists, historians, and assorted other viewers. Qiuyi's liaison with Lao Pu during her stay in his family's house is incoherent: the two use each other mercilessly in an exchange of protection for sexual pleasure, then suddenly and inex- plicably discover their undying love for each other long after the liaison has ended. By that time Qiuyi has left Lao Pu in a fit ofpique, become a Buddhist nun, discovered she is pregnant with Lao Pu's child, miscarried, and mar- ried an older teahouse keeper whom she does not love. Meanwhile, Xiao'e is released from the reform institute, works briefly in a factory, quarrels with a woman who implies that she is still a prostitute, and marries Lao Pu. In the process she metamorphoses rapidly from petulant prostitute to sweet young worker and back. Xiao'e and Lao Pu are unhappy together; they fight continually about money, and Xiao'e exhibits what the reformers would undoubtedly call an unreconstructed courtesan's mentality, demanding material goods and throwing tantrums.
Ultimately, Blush is not a story about reform at all. Rather, the author and filmmaker regard the 195os reform efforts as a safely distant treasure trove oflong-ago times, to be mined for interesting dramatic material rather tha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lessons. And the film's success-it won the Silver Bear award at the 1995 Berlin Film Festival-suggests that such material will find a receptive audi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tistic realm as well.
In these late twentieth-century reconstitutions of the past, prostitutes were multiply deployed: as figures in Republican China's interconnected social ills, as important historical figures who contributed to the nation's cultural heritage, as worthy subjects of elite male observation and writing, as exemplars of traditional female virtue, as sites of nostalgia and popular entertainment, as subjects incompletely reformed by the state. But perhaps something more was promised as well. As the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the reprint of Hell on Earth explained, "Through this book, longtime Shanghai residents can arouse their childhood memories; young people can see the bizarre and motley character of old Shanghai, and sense the health and prosperity of new Shanghai; social historians can find material they need; psychologists can rely on it to research the particular states of mind of the people who were active in those circles; linguists can make use ofit to investigate changes in Shanghai dialect."18 The reissue of courtesan novels was meant not only to facilitate research, but also to restimulate individual memories that might well have been buried under the state's master narrative of twentieth-century history. At the same time, although the introduction expressed the pious hope that young people would appreciate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bad old days and the healthy present, the book itselfaimed to make available to them a textured and colorful body of knowledge about the past, one that they might well use to fashion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so fold Shanghai, of their own heritage, of their own Chineseness. Prostitutes were important figures in this reach for a new and improved past, making it likely that the meanings of prostitution will continue to be re-created and negotiated in China as elsewhe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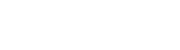




















秋仪出家,是想寻求一个心灵支撑——她的生活倾覆了,以为可以依靠的男人也退缩了,她无处可去,想要留在寺庙。然而寺庙也不留她,幸好她一直是坚韧的,最终在红尘中找到栖身之所。可惜小萼没有认清形势,虽然经历了劳动改造、工厂做工,她始终如菟丝花一般无法自立,最后毁了老浦,也毁了自己本可拥有的平静生活。当然,是老浦选择了小萼,而不是秋仪。因为小萼柔弱又可爱,他的男人气概可以在她面前展现——相比之下,秋仪略显刚强了。既然他选择了“傻白甜”,就要为“傻白甜”买单。
豆瓣的劇情簡介寫得太糟糕。秋儀是大女人,在現實中大女人總是被男人“犧牲”掉的那個。老浦去拍庵門,大雨沒傘;秋儀辦完父親喪事拍庵門,大雨沒傘,他們都是沒有庇護的人。傘出現三次:慶婚、送刑、片尾秋儀給小萼送熱湯——她完成了自我建設,足夠強大,甚至成為他人的庇護。
6/10。充满意味的空间造型来达到集中展现矛盾这一目的,曲径通幽、封闭的天井楼厢限制了女性生存,开头解放军搭在船与岸之间的木板象征她俩无法改变命运道路,阴雨和伞的意象铺设了情感悲剧,给老浦侄子画胭脂水粉、削发为尼两场戏显露秋仪心软和决绝两面;硬伤是旁白未能准确结合影片情绪又弱化冲突。
如果我没看过黄蜀芹版的红粉我可能会打个四星。扣掉的一星是过于浪漫化的处理,遮蔽了“历史”的暴力,另一星还是过于浪漫化的处理,使本该特立独行的女性陷于与一个原著中本是懦弱无能却被改写成痴情的有担当的男性的情爱世界里。任何改编小说的电影都多多少少会加上一些罗曼蒂克色彩,毕竟是资本操控。和教授讨论的时候,我说我更欣赏小萼,即使她好吃懒做,但是她从来不否认自己的好吃懒做,不掩饰欲望,管它世界翻天覆地怎样的发生变化我只追求我的,什么伦理道德抚养后代对她来说不是义务,不是枷锁。在女性依然被父权伦理道德,母性神话束缚的今天,不得不说她是一种意义上的女权。
比上一年相似题材的《红尘》好太多。用空间和构图反映人物的境遇。很工整,处理得也老练。几乎每个场景都有言外之意。妓女解放后进的是弹棉花的工厂,背景音和团团弹起的棉花照应内心的不安;何赛飞在工厂往竹架上挂折扇,摇摇欲坠的画面感暗示接下来的命运;秋怡跳窗逃跑,给的是层层叠叠的屋顶的远景,只有薄薄的瓦片,没有路;地主老宅的前景走过蹒跚的老妪;两个女人在高墙下的窄巷子会面;秋怡结婚的话外音配的画面是秋怡走下台阶到水边倒马桶。王志文演得真好。
《红粉》电影的美术还原性做得相当好,解放初期的江南水乡的小城。木结构的小阁楼,邻水而起的脏的几乎看不出是黑瓦白墙的斗拱建筑,拾阶而下倒马桶的妇女,雨色中弯曲而去的青石板路面的小巷;以及解放后贴的可哪都是膏药般的标语、三俩的黄军装的正气凛然不断审视你的眼神、氤氲评弹软语中,突然爆出的大嗓门口号、一本正经的关怀,呵斥的口吻,从岸边上船时,秋仪伸手要解放军战士搀她一把,解放军小战士一言不发,给他搭了条木板。像这样的细节,太精彩,可惜真的太少了。电影给三个优秀的演员扎好了舞台,他们仨演的都本儿好,本儿卖力气,美术做得也好,置景服装美术都到位,也有时代的一些背景音色。大概可惜就是,好像差些时代交织的更鲜明更锋利更具有隐喻性的冲突,不管是情节的还是内心的,还是寓意的,差拱火。悲夫者,不过是逝者如斯罢了。
南方湿漉漉的,风情万种,拍得蛮好,普通话配音也不影响,如果是上海话配字幕应该更佳。。直到90年代中期国产电影都还过得去,到了现在,一年也出不了两部佳片
想必李少红心中有更合适的演员,但这三个人应该是当时最红的明星了。看小说的时候我带入了一下十年前的郝蕾和霍思燕,现在的倪妮和周冬雨,还蛮有趣的。
喜歡小說多於電影。女性角色耀眼,但男性角色更能突出中國人的特性:軟弱,長期在父母權威下不敢自己做主,只能通過女人和一時激情去做出看似果斷,實際逃的決定。面對無法處理的局面,依然選擇逃避式的選擇,所以命運是導向死路一條。
唉,人啊!反射弧太短,反应太快,很可能走错路;反射弧太长,反应太慢,更可能走错路;随大流吧,看运气漂吧,鬼知道会混成个什么德行?脑回路奇特,来一次跳跃式发展,又很可能摔死。主动些吧,很可能自作自受,自找苦吃;被动接受吧,很可能掉进陷阱,永不超生。出世吧,尘缘难了;还俗吧,无立锥之地。怎么就是瞎折腾,不能好好过日子呢!
王志文老师的声音是真好听啊!没有刻意拍江南,但是那一口吴语,不经意的评弹,却比现在刻意为之的江南更江南~何赛飞老师年轻时真的是娇憨,太喜欢了!王姬老师攻气啊攻气,啊最后一起奶孩子好百合!彩蛋是第一编剧是倪震!旁白娓娓道来也好听!
每一次都感慨,中国再也拍不出这么好的电影了。扎实的原著,牛逼的剧本。三个那么优秀的演员,和李少红导演的正当风华时。故事节奏取舍大胆,细节又丰沛,情感的收放和表达都很戳人。而对于历史和人性的还原鲜有批判,但力道十足。
鉴于李少红的导演记录 看下来这算她比较靠谱的片子了 很浓的吴地风情 也基本忠于原著 变化多在于场景与禁忌台词上 所以讲完全没小说味也大可不必 毕竟文学作品不是剧本无法复现 在改编上 最后让秋仪与老浦见面 以及老浦的补偿 比原著多了份人情味 也少了哀戚与凌冽 主演们都不错 加分
赛人正巧今日话了《红粉》,还是引用他一段吧;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还是李少红的这版略好些,假不假江南水乡的韵致还是出来了。苏童写了那么多女人,但写得最好的还是男人。又或者在他笔下摇曳生姿的女人,只能在男性的目光里才能展现欢颜或暴露愁容,这些女人很少有独处的时候。而苏童笔下的男人往往一个人就能去寻欢作乐。我的建议是,《红粉》要重拍的话,还是找男导演更合适一些。那点小猥琐带来的小可怜,女性很难体会。《红粉》要说的是什么呢,妓女这一古老的行业,除了阶级压迫之外,还有些不易总结的内容,在驱使着这一职业女性花自飘零水自流。时代在变,但总有些事物,像苏州小桥下的流水,自顾自的蜿蜒,谁也控制不了它的流速,也不知道它究竟会流向何处。
同时期,国内有很多佳作登场,本片却只能算是一部徒有其表的佳作,虽然忠于原著,但删减和修改了神韵,就没有了灵魂。……大量的留白,导致3个演员越卖力,却和原著所表达的渐渐偏离。就如《亮剑》小说和电视剧的区别,小说看的痛哭流涕,电视剧看的热血沸腾。……如果是姜文和刘晓庆来拍,又会是如何?……王姬的秋怡太作了,反而王志文和何赛飞很出彩。……导演李少红,她拍戏一直都有她独特的表达方式,“鬼”气太重。好在本片没有。突然想起了她导演的《红楼梦》和本片一样,也是剧情+旁边,第五代导演当中,也算是个另类。……苏童的原著可能受到日本电影《望乡》的影响。
故事好,拍的也好。冷静得不像女导演,这就是李少红。故事可大可小,大的方面很深刻,小的方面人性方面更深刻。男女关系真是亘古不变。女人的爱分两种,一种爱到深处说不出口,一种为了生活机关算尽。三位主演都太好太好了。王姬有一种贝蒂·戴维斯的冷静果断,王志文声音也太苏了。何赛飞美!
大约二十年前,买过《红粉》的正版铁盒VCD,不想碟片不能播放。念念不忘二十年,终于看了。老浦小萼吵架一场,太有感触,若是二十年前看,肯定是无感的。王志文演得真好,优雅而懦弱,被时代迫害的良好市民。
太好看了,红粉—女人的一生!镜头真美,王志文演得真好,让人开始反思话语体系和权力体系下的个体:一夜取消昌既行业,她们的生计成了问题,全部转入棉纺教养;一夜转变规则,没收土地,按成分处理;刚结放,需要你们的田产支持,你们需要自力更生;家伟,秋仪和小萼的命运令人唏嘘,权力和规则转变,小萼柔韧的适应,秋仪倔强的碰撞,家伟的求取生存;艰辛生活下的个体挣扎,家庭争扰,互相埋怨,外部压力转为家庭战争——人的生存压力,是家庭争吵的主要来源,只要能解决掉个体的生存压力和家庭的生活压力,那么家庭问题一定会少很多;人的一生事就那么多,也就那么几个,两个人里有一个有问题,那么双方关系就会承压,问题也会接踵而至,确保双方能承受和化解各自的压力不抱怨和归咎对方很重要,爱必然是在此之上才能维持,不然就是无尽的争吵和不安
这真是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婊子有情,男有义,没有太多的矫情腻歪,在情色、利益之间,处处闪烁着温柔动人的光辉,这不是爱情,什么又是爱情呢?相比于《姐姐妹妹站起来》的旧社会妓女改造,此片没有把这帮妓女们往苦大仇深里刻画。事实上,高级妓女的生活其实很好,尤其是过惯了纸醉金迷的日子,一时劳动改造,反而不适应,甚至会怀念从前的时光。毕竟她们年轻,经历过“五陵年少争缠头”的风华正茂,却尚没经历“暮去朝来颜色故”的郁闷。秋仪逃离了,本来她可与蒲家伟成婚,可是因为是真爱,所以较真,而这一较真,将蒲家伟拱手相让于小鄂。小鄂是典型的婊子形象,无情无义,只谈利益,当蒲家伟无利可图时,便怨声载道。蒲家伟死于多情,死于善良。电影意欲告诉我们,这世间的真爱往往徒留遗憾。
想不出谁比何赛飞更适合这个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