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侯麦著名系列作品“四季的故事”之一。菲利茜(夏洛特·海瑞 Charlotte Véry饰)和查理(费德瑞克·范丹狄德夏 Frédéric van den Driessche饰)在海边浪漫相恋之后,因为一时不留神留下了写错的地址,而导致了二人再也找不到彼此。菲利茜生下了查理的孩子,但5年来却再也没有查理的音讯。 生活还在继续,菲利茜遇上了喜欢她的一些男子,他们也不失为好男人,足够爱自己。比如成熟体贴的马桑(迈克尔·瓦雷蒂 Michael Voletti饰)和才华横溢的路易(Hervé Furic饰)。然而,在菲利茜的心中,查理却仍旧是个挥之不去的至爱之人。她不是不爱他们,只是无法爱到能和他们一起生活。她和路易一起看莎士比亚的歌剧《冬天的故事》,为里面的人物悄然落泪,也许她和剧中人一样,也在坚守着一个信念。 终于某个冬天,菲利茜和查理竟然在公车上重遇,执着的梦想等来了实现的一天。陌陌影视陌陌影视落凡尘人民公仆第三季滴答屋五个女儿世上只有爸爸好2021西雅图寻爱记美的统治德云社德云三队小园子天桥站故宫里的大怪兽之莫奈何的谜题萌犬好声音国语失控的布朗森半仙半死降伏魔女的手段亲爱的麻洋街BanG Dream! 电影演唱会2兄弟情人百万新娘之爱无悔太妹刑事救世 第二季大人的防具店 第二季爱就爱了赌棍解锁鬼应用伯爵2023
长篇影评
1 ) 《冬天的故事》——侯麦对爱情最本源的探索
写在前面:
我相信看这部电影后,部分男性可能会感受到一些不适,反而女性可能会更加偏爱这部电影,尤其是女性意识越发觉醒的今天。
警告、警告、警告⚠️:以下内容涉及剧透!!!
故事一开场,便是女主角菲莉茜与一个帅气的男人在一起,那个帅气的男人是个厨师,两人一起做饭吃饭、一起赤身裸体在海滩上嬉戏、一起做爱,俨然如同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情形。
分开的时候,菲莉茜留下了地址,故事来到了五年后的巴黎。因为菲莉茜留的地址是错误的,两人期间再也没有见到过。
菲莉茜有了一个女儿,她此时斡旋在两个男人之前,一个满腹经纶的文人,一个美发店的店长,这是极具代表性的两个设定,一个代表着内在精神,一个则代表着外在展示。文人非常爱菲莉茜,但是菲莉茜却一点都不爱他,原因是文人受过太多教育,她不喜欢别人在精神上控制她,反而更喜欢在肉体上被控制,他更爱那个刚离婚的店长。
美发店店长:
当店长决定去另一个地方开分店时,菲莉茜决定跟随他前去。做这个决定,菲莉茜其实是深思熟虑过的。她先来到那个地方实地考察,店长向她描述着接下来的美好愿景,这让菲莉茜渐渐下定了决心。
最终,菲莉茜不顾身边人的反对,带着女儿来到了店长这里,但是第二天,她就决定返回巴黎。因为她发现,自己并没有太爱这个男人。
菲莉茜的心境变化,经过了三个方面。
第一,当菲莉茜带着女儿抵达的时候,店长并没有来接她,反而是忙于店里的生意,当见面的时候,店长要求菲莉茜的女儿亲他一下,被拒绝了;
第二,抵达当晚,店长和几个朋友坐在餐桌边,而菲莉茜在厨房忙着切火鸡,而脸上的表情则是闷闷不乐;
第三,当菲莉茜为了让女儿开心,带着女儿出门散步,因此耽误了工作,店长对她发脾气,同时提议要给找保姆照顾女儿,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实在菲莉茜在前来考察的时候,侯麦已经通过一个细节铺垫了这段故事的走向。当时卧室里墙上有一些小天使的铜像,店长说要把那些铜像扔掉,而菲莉茜看到铜像是丘比特后,却一脸欣喜的表情。这是两个人的根本矛盾,店长想过柴米油盐的生活,而菲莉茜发现这样的生活会消减掉他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的时候,她果断地选择离开了。
文人:
回到巴黎的菲莉茜,找到那个文人朋友,文人对于见到她非常吃惊,因为在菲莉茜离开之前,两人已经摊牌和平分手。菲莉茜告诉文人她已经离开了那个店长,文人想要提出恢复到以前的关系,但是菲莉茜深知自己不爱这个男人,坚持他们只能做朋友。
两人相约晚上一起去看莎士比亚的戏剧——《冬天的故事》,在观看过程中,菲莉茜被戏剧深深地感动了,而文人却有些无动于衷。两人经过了一番思辨,最终菲莉茜慢慢感受到两人之间可以产生一些共同点。
菲莉茜与文人之间的感情开始升温,由一个细节可以看出来,菲莉茜主动帮文人泡咖啡,这与之前给店长准备晚餐时的闷闷不乐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说明她在向文人靠拢。并且当菲莉茜带着女儿来见文人的时候,女儿也很主动地亲文人的脸颊。
但是紧接着发生的事,再次让菲莉茜重新燃起的希望开始破灭掉了。
第一,当文人带着菲莉茜和女儿游玩的时候,文人不自觉地独自走在了前面,把菲莉茜和她的女儿甩在了后面。
第二,礼拜天,他们来到一个教堂附近,信仰天主教的文人在到底是去做弥撒还是陪伴菲莉茜之间犹豫不决,并且想要劝说菲莉茜和他一起去做弥撒,这遭到了不喜欢被人精神上控制的菲莉茜的拒绝。
这两点,让菲莉茜再次意识到自己与文人之间的鸿沟,最终回到住处,当文人向菲莉茜发出性暗示的时候,菲莉茜果断拒绝了。而两人的分手则是在文人送别菲莉茜和她的女儿的时候,以女儿拒绝亲菲莉茜。
厨师:
在故事临近结尾的时候,菲莉茜和女儿在坐公交车的时候,因为巧合遇到了之前那个帅气的男人,当她看到那个男人和其他女人在一起,因为担心带着女儿跑下了车,男人紧随其后追上了他。两人简单地交谈后,男人得知,菲莉茜的女儿也正是他的女儿。
菲莉茜带着男人回到了家,交谈了解到各自的近况。两人互相坦露还彼此深爱着对方,菲莉茜哭了起来,男人关心地询问,菲莉茜说自己是喜极而泣。
就这样,一个对爱情有着偏执理解的女人,她也曾犹豫,彷徨,放弃,最终重新找回了自己所坚持的那段爱情。菲莉茜作为一个人,她一直跟随着本我在追寻自己的爱情落脚。
联想到海报是菲莉茜牵着女儿的画面,在我看来,这是侯麦的一种隐喻表达,女儿是菲莉茜对于她所坚持的爱情的一种希望。
埃里克·侯麦,对于细节的把控,精准到让人赞叹,他用思辨主义讲述了一个浪漫主义故事。侯麦在展示这个故事的时候,只有开场让菲莉茜与厨师之间有做爱的一些画面,与店长只有亲吻的动作,而与文人之间更多的是言语交流。
在西方世界,亚当与夏娃,也是从吃开始,才有了后面两人被逐出伊甸园,经历过数次分离,但最终仍旧长相厮守的爱情故事,这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对情侣。而更深层的内容则是,作为亚当的肋骨出现的夏娃,在爱情中,也在努力争取与亚当平等的地位,这在菲莉茜的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最终,菲莉茜重新遇到了作为厨师的男人,让我想到了李安的《饮食男女》中的一句台词——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焉!
2 ) 语言。洒脱,等待,与日子的灵光
侯麦和戈达尔一样自然不相信语言过于强势的符号化功能。“把血还给红色”似乎表明在他们看来真正抵达缀合的,或许是那些片刻的灵光诗意,碎散中萌发的奇迹性的完满。而绝不是一个给定的真相,一种先验的锚定:忽隐忽现才能唱出歌谣,而一套秩序内部的东拼西凑和角逐互换,或许只能无限靠拢向空转的呓语。但在同样的创作路面上,两者生成的步伐却并无太多吻合,方法论上的两人有着本质区别。戈达尔将情绪斩断,将因果玩弄,所有语言在他这里只是身体坚实同时又“似有若无”的累赘,洒脱的扬弃间,只留下身体的探戈作为一种不可知性的引线,为随机流泄的把玩,热情,诗意,提供共谋与机关,在他这里身体是一种增殖而具有扩散性的场所。如果说安东尼奥尼的漫游者意志最终导向一个虚无的闭锁的机器按钮,那么戈达尔就是和空气同生共死的游戏爱好者:可能造访的死亡不会呈现一种超我律令的侵袭,散漫并可能被随机的隐患没收的,一线之上的反义词生命,才是构成了诗意与死亡并肩齐驱的中心调和,这不是本体论式的,僵硬的生命,而是从幻光与玩闹中反射出的富有动感的气体性生命。 ———而侯麦则不选择对语言有任何的压抑,亦不打算进行某种靠近戈达尔的调和-占领。在他的电影你可以看到人物无可辩驳的叙述,唠叨,纠结乃至躁动不安的多舌。但这并不代表侯麦“承认”语言,更不表示语言有某种奇妙,活跃的地位。他表明的反而是在这种语言上的想象性描绘,传输中,抵达的一种“真实”反而是“越描越黑”的,南辕北辙的。由此从中掌握现实的宏观辩证。你会发现他们看似时刻抛出了理直气壮的观点,文学性与哲思性两者都固执地并存在内,而这既不能以某种建设性指向身体,提供弥合;也不能消化矛盾。反倒是在情感的浓度中愈演愈烈:他们很少能和解,拉拉扯扯中语言就像多余的小动作一样,成为一种微观的症结。很多时候他们并不会认可彼此,反而是一种诗意的,自我的,不服的苟同。他们善用语言,但同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从来又不相信语言中任何一套公理,这种不自知的反叛在微观上击碎了语言的完满论,那些灰溜溜的缝隙由此产生微妙的对撞与错位,故事油然生发而爱与死亡从来不能互相抽身。 由此抒情气质便成为一种奢靡,只有严谨的场景刻画才最好地能够把握这种张力与运动。因此我们看到侯麦“粗暴”的一镜一人,“粗暴”的让角色信马由缰的抒发。他们时刻主宰,或者增添一人平分景框而已。同理都是一种精巧到极致的认真。由此我们看到侯麦似乎很少有肉体的切出,时刻与环境,地景绑定似乎既是表明角色的一种压抑而需要抒发的态度,同时他们又是空间的工程师,用表情与语言结构场所。但同时不可忽视的他们又会被这种跟踪、限定,赋予着现实性的凝视与掣肘。如《春》,似偶遇却更接近宿命,事件的流转指引角色,这是春的意志;如《绿光》一个随机而细微的自然动作,却让女主深刻痴迷,哭泣;如《双珠》,世界的镜像学深深烙印在我们众多的命运之上。 由此《冬》里那种优雅而含混,抛洒而超脱的奇妙触感,似乎是我感受的不同于侯麦其他作品的珍稀而宏大的共鸣。开场的空镜,海水灰蒙的呼吸弥散出苍凉而无孔无入的冷感:冬季是生命的下行,软弱,乃至于匮乏残破。由此萧索的诗意氛围既奠定了心理叙事的笔法,同时起到了淡化地景强度的作用——香榭丽舍大道来回的小情小爱,在低温中触动向了世界化的错位,哀伤,淡化了风月而强化了眼眸。因此侯麦不同于其他作品的克制,果决的调度,这部赋予了更多闹市,车站的刻画,用这种“嘈杂”,随意的生活化的表露渗透进文本的深刻,与氛围,与低温契合。正是在在这种嘈杂,萧索的洒脱中,一切仿佛都不会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剧情上的尖刺。仅仅是过往与现实凝望中不和的因子,心理与现实错位中荒唐的一点冲动的生发,而不要太过体现,只是粗略的表明。于是查理也好像只是菲丽西一个坚实而只稍微伤感迷恋的手印,委身于血缘的拉力;那些男人也不过是一个个场所的封闭的守夜人,“绿光”还要自己找寻。 ———而确实也是一到精致的等待,那从心灵提现到现实的灵光。日子里破碎而短促的遇见,却时不时新鲜在生命孤芳自赏的循环之内。 在纠结,反复与认定又推倒的陈旧日子中。查理还是出现了,“终于”出现了,不带一丝使命只是忧郁的,怀旧的灵光。于是菲丽西色一切纠结,往返以至于冲撞,苦泪,都在一个精致的片刻化作了回溯性建构的诗意等待,等待日子重复——或许在重复中会有讶异诞生的奇迹生发吧,她无心插柳地相信。而他的回归也即将证实,他正是她熟悉而隽永的绿光。她等到了,我也哭了。冬天于是落下完美的帷幕。故事终结。 冬天用尽本来就不多的体温,成全了一次完美而感动的相遇。而春天要做的,或许仅仅是添一双碗筷吧。
便又是一种错位。
3 ) 爱情的不同面相,生活的偶然与必然

爱情常常不知所起,也不知所终。爱情的面相太多,以至于我们会视而不见。
这部电影,侯麦谈了三种爱情:热烈的爱,过日子的爱,仰慕式的爱。
菲丽希与查理的爱偶然而热烈,很多人都希望来一场这样的激越之爱,可这样的爱可遇不可求。一个小小的口误造成了无异于生死相隔的悲剧,无法忘记,也无法挽回。有人一辈子都没有体会过这种燃烧的爱,有人遇到了这种爱也留不住。难道只有偶然的爱才会热烈吗?还是我们就喜欢被命运的偶然击中,这不是另一种受虐心理吗?他两短暂相遇、炙爱过后离开,由于没记对地址,五年过去,谁都没有找到对方,这五年活生生的隔绝是上帝对他们忘乎所以的惩罚。
菲丽希与马桑的爱是一种过日子的爱,平淡而庸常,乏味且真实,这是大多数人的爱。没有那么多激情的东西,匆匆忙忙过一生。如果是一般人,大概也就这样了,但女主浪漫而热烈,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别人,她选择等待那个错失的白马王子。
菲丽希和路易的爱是仰慕式的爱,他教给她知识和见解,他是启蒙者。这样的爱有有一种隐形的不对等,就算努力弥补,菲丽希还是敏感地看到了他们之间的裂痕。女人凭直觉生活,男人靠理性判断,都很好。
电影中有很多菲丽希在车站间转换和行走的场景,疏离而割裂,她行走在偶然中即是对现实的无奈、绝望与希望并存的混沌状态,也是在孕育着相见的必然性。
相遇还是发生了,正如一段作者佚名的诗句写的那样:
相遇的那天,
一切都像平常那样,
楼顶飞翔的群鸽,
街上走过的行人,
都没有丝毫改变,
平淡的像一杯水……
菲丽希本能地制造偶然性的时间与空间,她的穿行就是一种本能的寻找,她终于必然性地与情人重逢了,喜极而泣。查理说要去远郊的小城定居,菲丽希再一次跟随,但这一次她犹豫了。她的却应该犹豫,她还是要去当老板娘,她还是要去面对琐碎的日常,厨子的日常并不比理发师的日常更美好。
或许,这是导演留下的悬疑,她们也未必会幸福下去,生活还会有新的偶然与必然,不一定会以你我的意志发生,一切都有可能。
侯麦电影中的爱情,出现的时候,猝不及防,消失的时候,也不一定有征兆。
爱情有着不同的面相,你不能说过日子不是爱情,也不能说激越的爱才是爱,我们都各自选择着各自的幸福,命运也还会给我们安排新的必然与偶然。生活啊,生活,这才是生活。
侯麦的电影平常如水,也如深渊。看《双姝奇缘》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电影是日常而唯美的。看《夏天的故事》,我知道他把寓言融入日常。看《冬天的事故》,我发现他淡漠而热烈,如同上帝一般极端。
城市和乡村,侯麦都处理得很好,不经意地把我卷入他的法国日常,他的情感戏剧漩涡,他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游戏。在类型片看够了的时候遇见侯麦,是我的幸运,不期而遇,淡然开始,深入骨髓。他的电影不是烈酒,但会让人不自觉地开始思考自己的生活。法国的片子貌似都有这个特点,或许与他们多次革命有关,彻底的弑父带来了真正的自我主体性,让人开始作为主体的、有意志的人而生活。
我相信侯麦拍摄的是法国人的日常,和他们相比,我们的生活啊,真的仅仅是日常。

4 ) “我只能和我疯狂爱上的人一起生活”
侯麦“人间四季”系列的第二部,有独特的冬日气质。
片中上演了一小段莎士比亚的传奇剧《冬天的故事》,特意找来剧本看完。这部剧在剧情发展上和电影形成了互文——结局都是找回失去的恋人,不同之处在于莎翁的剧带有更多救赎意味,强调宽恕与和解,最后的相逢是西西里亚国王弥补了年轻时犯下的过错后换来的,“十六年前破裂的夫妻关系、父女关系、朋友关系,经过当事人在肉体与精神上都经受了时间和生活的考验之后,终于完满地修复了,并将剧情引向团圆欢乐的结局”。
而侯麦的电影讲述的则是一个发生在城市巴黎的、两个无错的年轻人的爱情故事。菲利茜在与查理分别时因口误而将联络地址说错,两人就此失散在人海,菲利茜独自生下孩子,将她抚养长大。“冬日的”侯麦将信仰与宗教放进故事中,隐忍与等待总是与寒冷又漫长的冬日相配。结尾两人在公交车上相遇,菲利茜的祈祷有了回音,孩子在查理怀里甜甜地喊了一声“爸爸”。
从剧院离开回家的路上,路易问菲利茜:“国王的妻子为何以雕像的形态复活,她原本没有死吗?”菲利茜回答:“你没有看懂这个故事,她复活是因为信仰。”



5 ) 最不可靠的关系
【埃里克侯麦 冬天的故事】
文、坏蓝眼睛
人生所有关系中,最不可靠的恐怕就是爱情关系了吧。
我们能够用一个念头爱上一个人,也可以用一秒的决定离开一个人,爱的时候有无数借口和动力,甚至人为地添加上各种神圣的渲染,离开的时候只需要一个理由:没那么爱他。
埃里克侯麦试图用一个平凡的故事来诠释爱情的意义,他用动了宗教,挪动了哲学,甚至涉猎了一点神学以及旁门左道,他只是想给爱情和人生一个精准的定义,但是众所周知,在我们所有能够掌握的技巧和学术中,惟有爱情和人生是根本无法定义的。
于是,众多的门派,各路的人马都为此进行了疲而不止的探讨,研究,反正是无解的,高级的解释和低级的理解的差别也不会有隔着太多道门,只要你肯想,愿意探索,任何人都可以。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冬天的故事中的故事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这只是一个关于女人的选择的问题,侯麦试图意念,意识和宿命来解释“感觉”,而“感觉”决定着选择,选择又决定着结局。
故事起源于一场艳遇,俊男美女,年轻的身体,甜美到不现实的浪漫,美景和美好恋情合二为一,女主角在那一刻也显得格外好看——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进入正片的女主角表情沉滞,衣着邋遢,甚至连气质都算不上特别——当我们沉浸在罗曼蒂克的爱情中的时候,所有人都似乎容光焕发,进入了一个神奇的舞台,大家都是浓妆艳抹的主角,而一旦神坛落幕,当我们走下来的时候,个个都是面目平常的路人,连表情都可以copy,百人同面。
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讲,我们的人生总是灰扑扑的,只有偶遇爱情的时候,才会像被施展了魔法一样,南瓜变成马车,灰姑娘穿上了水晶鞋,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孜孜不倦地盼望和追求“爱情”的根本原因吧。
但是爱情稍纵即逝,短的像夏天,进入冬天之后,一切都回到了现实,女主角菲力西因为一个荒诞原因,把地址搞错,导致她和浪漫情人夏尔勒失去了联络,而不幸的是,她怀孕了。
女主角勇敢地生下一个漂亮乖巧的女儿,却失去了此生的最爱,“失去”让夏尔勒当之无愧成为她的“最爱”,她无法跟命运讲条件,只能郁郁寡欢地自责和等待,盼望出现奇迹的那一天,她能够和夏尔勒重逢。
五年中她的生命里出现了两个男人,一个是知识分子,喜欢从书中汲取知识和经验的天主教路易斯,另外一个是粗壮鄙俗身材臃肿的中年市井男人马桑。面对生命中这两个男人,她从来不掩饰她对夏尔勒的爱,而且她很精准地对每个男人的感情做着一个判断,她不喜欢高深无趣的路易斯,她认为自己更适合粗壮平凡的马桑,但是她对他们都说爱,偏执的她强迫他们接受他们在她心目中的分级,俄日且接受她所有的决定,哪怕是错误的。
马桑为了她抛弃另外一个女人,打算和她一起生活,菲力西二选一认为马桑更适合她,于是不顾母亲的劝阻,执意前去,但是仅仅一天的时间,她便改变了主意,她认为一切都不对劲了,而她不愿意浪费时间去做不喜欢的事,所以她立刻决定回巴黎。
回到巴黎后,她找到路易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自己的离开,路易斯快要被菲力西的变幻搞晕,他试图发作,最后还是控制住了,菲力西问他:你怎么会对我大喊大叫,然后又沉默?路易斯反问:那你要我们怎么办?威胁强迫,跪地求你?谁都改变不了你的决定。
一切都是一个念头决定。
爱的关系是多么不可靠。
反过来说,失去一个爱人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写错一个地址,说错一句话,甚至五官长得凑巧不可爱,这都可以成为她离开你的理由,在爱情关系中,勇于选择的都是强者,他们不念顾旧情,不拖泥带水,不优柔寡断,只听从自己的意志,他们决定着爱情的存亡,而那些被选择的弱者,那些心地过于善良的人们,注定只能在这场决定中被宣布,受伤害。
这里也可以延伸出一种讨论,到底是看重感情好,还是不看重感情只注重感觉好?看重感情会顾及他人感受,而注重感觉则只服从内心的感受,一个是利人,一个是利己,但是从自己的层面来说,注重感觉更实惠。平凡如我们,高尚始终得不到眼前的快乐,要说终极的快乐,大部分人还不配谈。
不信仰宗教,却尊重个人信仰的菲力西在教堂里冥想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必须要尊重自己的意愿,完全没有必要去做任何不愿意做的事,这就是正确的“选择”。
莎士比亚的戏剧【冬天的故事】,让菲力西看的浑身颤栗,泪流满面,她在这幕戏中看到了信仰的力量,信仰可以令人复活,而她的信仰不用于大众所定义的信仰,这种信仰其实也就是一个执拗的念头——要不要坚定自己念头,为自己的选择买单?就像她坚持五年认定夏尔勒是她的最爱,那么,就算夏尔勒永远不再出现,至少她的念头可以支持她带着希望活下去,而且因为她心里最爱的位置有人占据,她可以更冷静,更理智,更无情地做各种决定,这无疑对她来说,是好事。
注重感觉,崇拜个人信仰,利己为先的菲力西迅速离开马桑,又回到了路易斯的身边,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和路易斯交换着自己精神方面的心得体会,并为自己的行为找到足够多的论证和哲学观点,在某一瞬间,路易斯认为菲力西已经真正地回归,至少她愿意探讨那些从前她并不愿意探讨的东西,他认为她在逐渐接近他的世界了。
当然,这完全是路易斯的错觉和误会,菲力西在感觉中早已经给路易斯定了位——她说她从精神到肉体都不喜欢路易斯,包括他的五官,她都讨厌,但是这不妨碍她说爱他,甚至在各种情绪波动的时候投奔他,最后她说:我们可能在某一世是兄妹,甚至我们可能是彼此养的宠物。
平凡的马桑没有能够留住菲力西,哪怕他背井离乡,哪怕他抛家舍业,刻板的路易斯也只是菲力西的一个避难所和风景台,她从马瑟那里获取肉体的安慰,在路易斯这里收获精神的提升,但是没用,这俩人跟她的“爱情”都没关系,她爱他们,却没有疯狂到“可以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这就是她最终下的结论。
正当我们所有人为女主角菲力西的命运和未来担心的时候,侯麦突然安排失踪了五年的夏尔勒和菲力西在公车上偶遇,两个人欣喜若狂,在得知双方都没有多余的状况的时候,俩人迅速拥抱亲热喜极而泣,这个结局更像是一种美好的假象,如果没有遇到夏尔勒,菲力西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在不断的审判中否定一切男人,还把一切归结为轮回和注定,一辈子活在自造的阴影中,为一个艳遇后失去联系的男人耗费终生的情感,郁郁寡欢,落寞无比,满脸愁容,惟靠信念的力量说服着自己,直到满脸皱纹,摸着情人的相片泪流满脸……stop,侯麦让这一切都在魔法中结束,他们相遇了,重逢喜极而泣,我们理所当然地相信他们会生活在一起,但是侯麦又留下了一个悬念——夏尔勒决定在一个边远的城市生活,他虽然很英俊,但只是一个厨子,我们的菲力西会跟着他一起走吗,再次投奔,再次体会生活繁琐,再次在教堂中冥想,下一次她得出的结论会是什么呢?
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
做一个残忍的假设,如果夏尔勒的失而复得让菲力西发现“真爱”不过是这么回事,他根本不是她想象中那么完美的话,菲力西那强大的心理建设轰然倒塌后,该如何面对和如何支撑。
重逢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尚未得知,影片已经结束。
那些我们孜孜不倦固执已见追逐的爱和捍卫的爱人,真的是值得爱的人吗?我们为之疯狂又愿意屈尊一切在一起的人,在褪去“爱情”光环后,还能够让我们坚持并坚信吗?为什么我们对某一些人只有好感无法加深到“爱”,而有一些人让我们忘乎所以一见钟情,牢牢钉在爱的十字架上宁愿让我们自己为之受折磨呢?爱情确实是一门玄学,是一门哲学,是一门神学,这是灵魂的事,答案无解,于是我们上下求索,乐此不疲。
保持希望终究是好的。
侯麦代表上帝奖赏那些心存希望的人,虽然他还告诉我们,这只不过是赌注。
2012/12/17 3:02北京。
6 ) 与自己的神性立约——《冬天的故事》
友人相聚,难免聊到看过某部影片,某某人公开表达喜欢某部影片,再寻常不过。记得我曾经和朋友表达过喜欢《三块广告牌》,多聊几句后,友人洞若观火指出我是出于“智性”的喜欢。对这句判词,当时做节目,我赶着输出各种观点,一晃而过。两年间,只要看到喜欢的影片,下意识地就问自己——难道是“智性”的喜欢?我是影迷也好,是从业者也好,这一问,已成自我审视的一类应激反应,直到我在银幕上看过了《冬天的故事》。应景的圣诞节后,钻出散场的人潮,只顾了兴奋,竟忘了自问。过了新年,再回想这个故事,自觉已经不再需要这个问题,不知道从哪部影片开始,喜爱出于智性还是本能,已经无从区辨。
对《冬天的故事》,我喜欢到生理的程度,就好比下雪天带孩子出门,盯着一片往下飘的雪花,眼巴巴看它沾到我儿子的眼睫毛上,感觉自己心尖儿化掉,那一刻的狂喜。打动我的大概有两处,一是女主角草率地带着女儿去投奔发廊老板,她为了陪伴孤独的女儿而无法分身照看生意,被情人兼老板挑剔,尽管老板当众给了所谓的名分,她还是在偶入教堂之后决心离开,当她陪女儿吃过早餐后断然离开,随后在火车上两人一起看绘本,那一时刻,女主角的率性而为让我产生一种快意,这是看所谓的艺术片难得产生的快意。
另一处,是女主角与爱人重逢。在街头,她听到爱人单身未婚,显露出一种将信将疑的退却,那种微妙的神情令我忍俊不禁。她对重逢一直都有一种不确定的期许。直到去过教堂之后,这份期许被祈祷加持为履约的奇迹,当奇迹降临的时候,女主角的进退拉锯,露了人之为人的局限,因此可爱,进而可信。
这两个处理,让我始终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之下,好比看到雪花飘下来的时候,你期待着它落在自家孩子眼睫毛上,瞪着眼睛追视,你通过它的轨迹预测到一定会落,当它真的发生,尽管是意料之中,依然会感到震颤。
影片散场,从人群中往外钻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句北城女孩的京腔,大意是看侯麦每个片子都会觉得他脑子有包但就还挺喜欢他这种有包的人。这句话我分成两层去理解,首先是通过自己的认知习惯而判定久别重逢的设计太过荒谬,这是从她往上数几代人信仰缺失而在血液中形成的惯性判断——超越了你所能理解的,就是有包。但还有第二层,即便超越了她的认知层次,她还是喜欢,这一层值得干一杯,因为她坦诚了自己本能的喜欢,而且这份喜欢是凌驾于她的所谓理性判断之上的。
细说一说为什么会觉得有包?
《冬天的故事》,有两层含义,表面上是女人辨认自己爱情观的过程,这是开出来给人看的花和叶;另一层,是土里深埋的根,是一个女人展露自体神性的过程,它从宗教的哲学辩论以及仪式中生长出来,进而超越了宗教观念。两层含义包在一个故事之中,故事的讲法,是圣经式叙事。整个故事可粗暴分成三段:立约——守约——履约。
言语的失效
先说说女主角的约。约,诞生在女主角和爱人暂别的时候,嘈杂的车站,女主角留了住址,约定等对方来找她。这是最寻常的爱情故事开端,男女暂别,立约相守,接下来无外乎是花样繁多的考验甚至试炼,最后终成眷属,比如《金玉盟》。立约的时候,说错住址也不少见,毕竟这是试炼的由头。可是,候麦把说错当成是人物的一种惯性,那就别有意味了。
影片中不止一次表现女主角用词不当,比如在跟母亲辩理时把"fruste(粗鲁的)"说成“frustre",在跟发廊老板逛街时词不达意,后来甚至自认一贯嘴瓢。这构成了说错地址这一故事前提的合理性,同时也给出了女主角的教育程度或者说文化素养。她说错住址,致使与爱人失去联络,后悔却不自怨。
因为口误造成长别离,这只是寻常逻辑,不妨碍她和他的约定,地址顶多算个线索,约定则高于一切。言语在“约”的面前不值一提,立约之后,关键在守约,守约靠的是行动而非言语。
谁是约的监督者?或者说是约柜?女儿。
女儿卧房摆放着生父的照片,见到父亲说的第一句话是自己的名字,第二句话看似回答了父亲的问题——“问她你叫什么?其实,她叫的是”父亲“,父,不是名字,不是言语,是契约关系的见证。女儿,也是重逢时刻男女视线的中转站。男人是先关注到了这个女孩子,才进而瞥了一眼旁边的女人,因为有女儿,才有了履约的契机。
那么,问题来了。这到底算不算一种“约”?分别时刻,女主角是无意识地立约,只留了地址说定了要在一起,这是顺理成章的行为。它不像《金玉盟》,在帝国大厦前约定再会,有通天建筑物作为地标,“约”的仪式感被无限强化。以至于《西雅图夜未眠》几十年后还在致敬。
忠于自性的立约
相较而言,《冬天》的“约”只是随口一说。
可正因此,女主角才有一份可信。她的约,是一种私密的情感辨认,认定了爱人,进而在情感世界给了对方一个至高的无可取代的位置,是一种少女本就具足的执着。个人的情感辨认不需要浮夸的形式去张扬。举个并不高级的例子,《倚天屠龙记》的殷离,认定她爱的人是咬破她手背的少年无忌,无可取代。凭这一笔,她就是金庸笔下最为动人的女性形象。
如果说立约是下意识的,那么守约是否有自觉?
女主角跟任何人谈及她的守望,并没有多么笃定,她只是懵懂地认为或许有一天他能够来巴黎找到她。她甚至一度离开了巴黎,几乎彻底断绝这一微乎其微的可能。因此,当爱人突然出现在她对座时,他对身旁的女人谈起五年前他和她的遗憾,他对未果的完美爱情流露出一种随意得近乎调侃的态度,这一切都令她心生疑虑。她仓皇的逃脱,将信将疑的询问,都是她作为人的最真实反应,因为她守约是忠于自己的情感判断,而不是忠于一个符号化的男人,她从未神圣化这份约,只是把它当做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她也在教堂祈祷,也请图书馆员帮她祈祷,可是祈祷归祈祷,她并未流露出半点对重逢的渴望。
由此,因其生活化的质感,因其自我负责的情感抉择,因其作为女性的独立和果断,这个女性形象瞬间高贵——我立约与你无关,我守约也与你无关。无论是立约还是守约,都是她自己的私密行为,甚至与宗教、与神祇无关,消解掉神圣感的同时,一个真正的独立的令人尊敬令人爱惜的女性由此成立。
立约不张扬,就不会在守约处做刻意的功夫,女性就不会因为守约而显得“痴”和苦,像《金玉盟》的车祸卧床,做作地夸大守约的难度和凄苦,进而凸显对爱情的信仰,这是简单的加减乘除公式思路,令观众的认知能力停留在乐于被洗脑的程度,好莱坞恶意地滥用了圣经叙事。
女主角守约的懵懂与天真,让女性的神性在生活中显形,从而脱离了信仰故事的套路。冥冥天定的重逢,也并不是她守约的果,是生活的果。她信仰的是自己对爱情的认知,这就能让观众避开守约者必得圆满的浅薄逻辑陷阱。
结局的重逢,并不是《金玉盟》式的守约者终成眷属,而是基于现实考量的生活之歌。只是她懵懂的守约,暗合了圣经式叙事立约-履约的过程和仪式,其间关于信仰的论辩和启发,也是基于最基本的包容和爱。
比如她为了分手去找图书馆员,在他家里旁观了一次关于信仰的辩论。妙的是,图书馆员以其情人兼友人的立场,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们关于宗教哲学的辩论会令“不学无术”的女友觉得无聊,他是贴心绅士的做派,看似是担心冷落了女友想要尽早结束论争,其实他的行为是对女主角的一种偏见。更可笑的是,他自己的哲学认知根本无法说服友人关于转世的信仰观点。反而被无意中插嘴的女主角问得张口结舌。
再如,偶然被拉去看舞台剧之后,女主角反而比图书馆员更加沉浸在舞台剧传达的核心观念里。而他则停留在这出戏的情节设计不合逻辑的常理认知程度,这跟北城女观众说候麦“脑子有包“是何其讽刺地相似?
再如,女主角说服图书馆员去参加周日礼拜,从而帮后者接续上他已经习惯缺席的宗教仪式。这一神性的启发,看似闲笔,其实含义深刻。你的信仰源于理性?源于你的教育程度和思辨能力?还是源于你对神、对人的爱的信心?女主角最终得以说服图书馆员去参加礼拜,不是理性地说教,而是请他“为她祈祷”,祈祷图书馆员爱的她能和她最爱的男人再度重逢。
情感辨认
某网站的《冬天》条目下点赞颇高的一条评论,居然把一切归为巧合,并认定女主角到最后也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这是粗暴的误读。首先,这是一出喜剧,喜剧的前提之一就是善用巧合,形成宿命对凡人的嘲弄。这出喜剧虽然利用了巧合,却也消解了巧合。落点,是一个女人忠于内心而自然生发出的女人本具的神性,最终神性得到验证的一次显形。
其次,简单谈谈女主角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感情?
女主角仓促决定跟随发廊老板兼男友搬迁,在做决定的同时,她有着清楚的自省。她知道自己是为了决定而决定,因此在和母亲、图书馆员男友、姐姐的三次论辩场景中,她表现出了绝对强势。非理性的决定,但并不是冲动的决定,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最关键的是,她在第一次去实地“考察”时,清醒地指出,她希望自己能够再多爱发廊老板一点。言外之意,她知道自己对发廊老板的爱远远不够支撑着走完全程。
再说她果断分手,离开发廊老板,是尊严受损。她尊严被冒犯,是因为她在乎女儿,要陪女儿还要兼顾发廊生意,分身乏术,而被老板挑剔。她感觉到自己身为母亲的独立性,或者说陪伴孩子的权力正在被男人剥削,尽管男人给了所谓的“名分”,可她毫不在意。由此可见,她对这一段情感关系清楚明白,从头到尾看得人神清气爽。
至于她跟图书馆员,这段情感关系她早就点破,在对方面前更是直言不讳。她巧妙地“拿来”转世理论,用来解释她心目中跟馆长的理想关系,是一种胜似兄妹的亲密关系。她用馆员拒绝认同的宗教观点去说明她们的亲密关系,论辩那天她只是心不在焉听了两耳朵,到了分手的时候她就能准确地应用,智慧不是读书读来的,她与对方的悟性差距几乎可以概括为降维的差距,这一设计令人对候麦由衷佩服。
由此,无论是哪一段情感关系,女主角都可说是当局者清。每一次的情感决断,并不是随性的,也不是为了实现某种信仰或者概念而做的,都是出于情感现实的。她决断的依据正是她对自己情感的清晰辨认。她要求一种纯粹的、对等的爱情状态,然而这种状态无论是跟发廊老板、还是图书馆员都达不到。
女主角的一系列决策转变之快,令人猝不及防,刚开始会认为这是位作女,她的行为难免显得盲目。而这一切都是候麦的骗术,当她和女儿走进教堂之后,神性的主题音乐响起,只有两个乐句,这是候麦对配乐的克制,也是守约的一种仪式感体现。
说是骗术,可如果你的认知真就停留在这一层次,那就太看低侯麦了。其实这是整个故事真正戏剧化的设计,当你开始质疑女主角盲目地所托非人的时候,你的担心很快应验,直到去教堂前,你都会同情女儿的遭遇。教堂以女儿为支点,她是动机,她也是接引,把母亲牵到教堂里坐下,碰触自己内心深处的神性。而后,女主角的果断大快人心,你在女儿开怀的笑容里松了口气,从而推翻了作为情节剧老观众的担忧,开始佩服起这个女人来。
景片式场景
电影中的场景,和女主角的情感一样,表面上呈现出一种随性状态,然而并非如此。侯麦的大多数场景是为了论辩而生发的,情感的、哲学的、宗教的、道德的,他在用影像去实践他的戏剧观念。
他的场景并未承担厚重的空间意义,除了开头的男欢女爱,其后有多回合对话的场景,都如并不重要的舞台陈设,让位给高光下的关于爱情、选择、伴侣、轮回、信仰等宏大命题的论辩。而最终,男性纷纷显形,尴尬落败,而以女主角的睿智果决收场。
过场戏多为街景实拍,女主角独自穿梭在巴黎的人群车流之中,构成一种生活的常态,她的长距离通勤和拜访情人的奔波路程,让她显得更加独立,沉淀在生活之中的从容,脚步更加果毅。
果毅,还体现在侯麦的剪辑上。
影片后半段,女主角在大街上走路的一连串镜头,看似是交代空间的过渡镜头,实则并未真正指认空间。以视觉习惯而言,好莱坞的场景交代最为舒服,在不同场景的开头,以一连串的空间交代镜头,每一镜约2秒左右,根据节奏有长短区别,观众通过这些镜头认可了空间的转换,逐渐入梦。而候麦的剪辑,以女主角的动势为依据,长则一秒,短则半秒,眨眼间女主角已经行走完半个巴黎,干脆利索,以步伐的迅捷传递出她精神上的果毅。侯麦此处的动势剪辑,跟东方的大师成濑四喜男暗合,都是建立在女性步态上的动势,不禁感叹他们都找到了女性的神性,不只是剧作上,也在视觉上。
而重逢的场景,更加不具备空间表现力,甚至消解了神性。三人就那么随意一站,街头噪音的真实感冲散了仪式感,回归了生活本身。彼时的女主角,她难以置信的表情和将信将疑的闪躲,赋予了她可信的美,而不是神性的美。
最后说说场景里的场景。
当女主角果断离开发廊老板之后,很快就去找图书馆员,刚好赶上一场话剧,看似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其实是含义深刻的互文设计。
在影片里,图书馆员和女主角去看莎士比亚的《冬天的故事》,注意不只是同名!该剧的舞台场景被极大扁平化,甚至彻底取消了纵深感,横向调度的进退有撕扯张力,是凡夫俗子对神性的信仰和怀疑的拉锯动线。台下则又取消了纵深,女主角和图书馆员的表情变化是唯一的反应,她突然抓住馆员的手,激动不已,馆员不明所以,她才是唯一活着的观众。
《冬天的故事》舞台剧的初始文本,讲的是怀疑者的悔恨和自我惩罚,他以相反的方式履约,哀悼亡妻和夭儿达16年之久,对其愚蠢的怀疑和一连串的嫉妒衍生出的罪行负责,当救赎来临的时刻,他在挣扎,对神性的怀疑,也是对自己恶行的直面。
请注意,前去看戏之前,当图书馆员告诉女主角当晚有莎剧的时候,女主角脱口就问是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男人会心一笑,意思是莎士比亚不只有这出戏,还有更出色的喜剧。然而,什么才是喜剧?愚人对智慧的视而不见。谁是蠢人?是“不学无术”的女主角?还是饱览群书的图书馆员?
信仰的血脉
故事的终局,并不是女主角和她一直苦守的爱人幸福地在一起了,这时候镜头离开了她俩,而是跟着女儿到了起居室,她说我“喜极而泣”,这是一句超验的台词,但又在小孩子复述妈妈原话的经验范畴以内。而她说出这句话的意义,其实是给履约的母亲盖棺定论。此后,全家团员,应和了履约之后获得的美满。尽管在故事里,女主角言明自己不是基督教徒,而且认同东方宗教的轮回观念。可她坚定地捍卫自己的约,这份信,胜过口头上的皈依,她信得懵懂,也信得宽容,她不质疑那位东方神秘主义论者,而且还最终把饱览群书的图书馆员推回到了礼拜日祈祷的习俗仪式中,尽管他也只是位不自觉的懵懂信众。
最后必须要指出的是,《冬天的故事》,两个说故事的人,无论是侯麦,还是莎士比亚,他们对“信”的思辨源于他们的本能,是长在那一片土地上的习性和血脉,因此他们提笔落笔就自然是圣经式的叙事,无论其故事中的人物是否超越了宗教,但都是以“信”作为依归。人的信仰是其自身神性的根基,若抛开了信仰的依归,人就只能陷入到“有包没包”的二元判断里,活在主动扬弃“信”的土壤和空气之中,连理解大师的作品都存在先天鸿沟,就遑论诞生出大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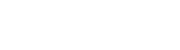




















[冬天的故事]像是女性视角的[夏天的故事],侯麦给女主角提供了务实的、知性的和旧情难断的三种男生,涵盖的类型已足够多,让这种选择成为了一种“爱情哲学”。女主采取的方法论是一个一个试,朴实但也最有效。最后戏剧化的结局温暖了巴黎的冬天,电影感变强。人间四季,至此结束,春冬夏秋。
这女人出奇的忠实于自己,出奇的不会让自己受委屈,她离开马桑的时候开始喜欢上她,哈哈~~小艾丽斯非常可爱~~因为同样的情绪,给五分~~
莎翁歌剧中的雕塑王后,你相框里的一纸爱人。信者真,得新生。
灵肉统一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开端,同时也是人间四季里真正短暂而迷人的尾声和前奏。然而这种和谐的爱却随着时间的流转而暂时性的一去不返,侯麦借着两性之间的游戏抑或冒险拉开了《冬天的故事》的大幕。正如莎翁的名言——凡是过去,皆为序章。自此人们生活在一个灵肉分离的后爱情主义冰河时期。幸或不幸的是,在这旧物速死灵魂复生的冬季总是蕴含着挥之不去的春意。春天适合讨论康德,冬天则宜批判柏拉图和笛卡尔。恰如女主角分析的那样,柏拉图式的爱与机械唯物式的爱都不是真正的爱。但相对于务虚的知识分子女主角更倾向于务实的企业家,然而二者关系的本质却是支配与被支配主奴关系,这让不堪忍受的她走上了内省和反思(辩证唯物主义)之路。结尾的久别重逢真是令人喜极而泣的冬春交接呀,因为拥有历史而非回忆的二者永远无法忽视女儿(真理)的存在。
#060#长达一百分钟的两段关系都成了最后十分钟的重聚最漫长的前戏,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柏拉图、帕斯卡的哲学也统统为这场相遇背书。教堂里的冥想、剧院里的落泪,让她明白了自己真正想要的爱情,是宿命与轮回,是灵魂先于肉身存在,是命中注定和他会再遇见。
四季里最喜欢的一则。“For me the dream was reality. An absent reality. ” 春天的开头,女人下车,离开男人。冬天的结局,女人上车,遇到男人。最后Elise也学妈妈喜极而泣实在萌到心都化了!2021.1.8 其实冬天的故事是从夏天开始的
现在的豆瓣还有多少人能静下心来看完候麦呢。
最后只能算是一种巧合吧,看似圆满的结局,其实这女人根本不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一直彷徨着,如果继续,那么最后这个男人也不会是最后
浪漫主义有的时候很荒谬。
侯麦的去世几乎意味着一个电影物种的灭绝
相信爱情,真好。女主角真惹人爱。哲学、感悟、文化在法国深入每个角落。在中国似乎只是小部分文科学者的专利。这就是差距呀。
侯麦电影里的主角从来不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他们永远都不满足现状,哪怕失去现在的幸福,也会让爱情牵着自己的鼻子走
“人间四季”之冬从某些方面看,侯麦其实和伍迪·艾伦很像:他们都热衷于琢磨男女之间的各种关系,将真实的道德选择展现在观众面前。故事中的菲利茜将全部的男女之爱在冬日里冰封,她迷茫地游走于两个男人之间,而结尾查理的出现就如同《春天的故事》中项链的寻回一样巧妙——如果不知如何抉择,就把一切交给命运吧。
打败了春天成为我最爱的一部,选择在电影院看太正确了,强制的集中注意力,让人在前面一个半小时的铺垫里充满了期待,最后几乎有与女主角同样的喜极而泣。如果你赌赢了,虽然胜算很小,但回报却很可观,就算你赌输了,抱着信仰去生活也会更好。
8/10。侯麦将女主角安排在物质(身体强壮)和精神(博学多识)的两极男性之间,从而形成她不适应两者的张力。颜色和空间暗示人物的现状:图书管理员体现了知识影响着人爱的方式,连卧室都与书店融为一体,夏季恋情的结束和失去爱情憧憬、枯燥地同居约会的白色严冬。教堂圣像表现出上帝对坚持所爱者的眷顾。
爱一个人就跟看一场电影一样,完全就是图个感觉,无法解释,没必要解释。。
雕像复活,是信仰的力量。恋人重逢,是爱情的执著。不喜欢讷威尔,不是因为那里没有花园。不能与你厮守,也不是因为这里书籍太多。有的爱人忠诚可靠但不足以支撑生活,有的爱人学富五车这不是我要的生活。下雪的街头,告诉你虽然没有妻子,但不代表你没有女儿。会为你的幸福祈祷,哪怕那幸福与我无关。
侯麦作品序列中与众不同的一部,首先是探讨信仰,不再怀疑踌躇彷徨,虽有曲折试错但最终坚定难移,教堂冥想与领受启示段落亦是侯麦难得在电影中展示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其次,片头欢悦恋爱蒙太奇里有不少裸露镜头或造爱瞬间,而侯麦极少在作品中置入大尺度场景。另一方面,你也能看到导演不少贯穿职业生涯的母题及偏好演变:从前期男性中心渐次转为以女性为主视点,甚至讲述女性之间的故事(有的人不喜本片女主,我倒尤爱她的坦诚与对原初认定的爱情的执著信仰——尽管浪漫主义式的恋爱并不一定比另外两个男友分别代表的智性引领或柴米油盐式情爱要优越或走得更远);侯麦灵感源自同名莎剧,故片中也有相应戏中戏段落,雕像复活的奇迹也与失联5年又偶遇且闪电复合的童话结局相得益彰;讨论柏拉图与帕斯卡尔哲学则似[绿光]与[慕德家一夜]。(9.0/10)
看有人短评里说侯麦死了是一种类型的终结,这种类型如果真有的话大概就是电影语言不靠任何形式感就讲了所有事;男主最后只出现那么短的时间我觉得讲的是并不是命运也不是选择而只是困境的结局穷举中最特殊的一种,结尾完全是照应莎士比亚的;居然看哭了妈的
不是言情剧,结尾甚至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皆大欢喜,其实是侯麦在表达“爱情宿命”论。女主角朝三暮四令人反感,但侯麦的用意并非是塑造她的性格或爱情价值观,所谓爱情本没有理由和条件,她只不过是突破了世俗对爱情的限制,让自己服从了宿命而已。很多人“认命”,其实不是服从命运,而是屈从了世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