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本片是导演安德烈·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一部自传体电影。幼年的塔科夫斯基随着母亲(玛格瑞塔·泰瑞柯娃 Margarita Terekhova 饰)去亲戚家借钱,他独自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发现了一面镜子,并通过镜子审视自己,在巴赫的音乐中,塔可夫斯基的回忆慢慢带出了一系列的事件:电视上在播报一个口吃的年轻人通过催眠治痊了自己;一个被家庭忽视的妻子遇上一位迷路的乡村医生,两人之间产生若即若离的关系;一个未曾露面的叙述者与前妻在争吵;一个早熟的年轻人备受军事指导员的呵责。这些毫无关联的片段式回忆通过镜子串联起来,展现了导演对时间、历史、生活、土地、梦境等意象的哲学思考。 导演的母亲在影片中扮演艺术家的母亲;他的父亲,一位著名的俄罗斯诗人,在画外音中朗读自己的诗作。陌陌影视陌陌影视上班族妈妈第一季动态漫画·六宫风华第二季复活岛治愈系恋人海底两万里铁证悬案第六季舒克贝塔 第二季天职2009时间管理局 第三季珠光宝气2013无路可走1950新朱门恩怨第一季数码宝贝大冒险tri. 第5章:共生布道家庭第一季我们恋爱吧第六季壮志雄心中世纪考古发现精灵梦叶罗丽5义胆群英鬼夫2013明月的暑期日记老爸老妈的浪漫史第七季馈第一季圣女贞德1948巨鳄2
长篇影评
1 ) 愿理性的光辉指引我穿越镜子的迷梦
或许是字幕的原因,当然更可能是出于我可悲的艺术鉴赏力,我在漫长的100分钟里看到了一些拼凑出的象素运动,耳边充斥着梦呓般的诗篇。这真是久违的观影体验。看完后我立即想起了王小波在《欣赏经典》一文中提到的那个美国外交官,他从初次看到芭蕾舞剧《天鹅湖》到第三百遍欣赏该剧,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你听到的是音乐,看到的是舞蹈——简言之,你是在欣赏艺术。在第二个阶段,你听到一些声音,看到一些物体在移动,觉察到了一个熟悉的物理过程。在第三个阶段,你已经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最终体会到芭蕾舞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不过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而已。从艺术到科学再到哲学,这是个返璞归真的过程。”
与《天鹅湖》不同,塔可夫斯基的《镜子》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能让你在看第一遍时就直接进入第三阶段。在影片营造的无边的空虚和迷雾中,人总是不由自主的寻找一个踏实的落脚点。我不断的自我安慰:啊哈,至少我看到了一些很美的影像,至少我看到了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怀念,又或者是一个男人对童年的追思,当然也许这些都不大靠谱,反正它们都是物质存在的形式,世界并不神秘,只不过是从一个状态跃迁到下一个状态,至于它们为什么会到下一个状态,或者这些状态是什么,非我所能理解。只要接受上帝的恩赐就好。
通过一些对该片的影评,我发现一些人经历了与那位美国外交官完全相反的过程。他们第一遍看到了哲学,然后看了一遍又一遍,他们把电影当成科学研究的对象,孜孜不倦的揣摩和分析,了解塔氏的童年、爹娘和他的癖好,研究俄国的历史和创痛,学习先进的电影理论,剖析每一句台词和每一个镜头,从杂乱的电影枝头收获仅存的逻辑果实,把它们捣碎了砸烂了,加上个人的猜测与冥想,直到用浩如烟海的鸡毛蒜皮拼凑出一个新的经典。当他们看到第三百遍的时候,他们大彻大悟,终于到达了第一阶段——欣赏艺术——看一遍《天鹅湖》式的经典就能达到的阶段。
我承认对影片的破译是通向审美快感的必经之路,可假如一部电影的密文是如此的晦涩,以至于绝大多数人都只能困惑的猜着蠢笨的谜,纵使它包藏了海洋般浩瀚的容量,又如何能称为经典?如《镜子》一类的电影,需要远超过影片本身、也远超过一般观众认知的额外信息才能欣赏,那么它的价值何在?
电影是助人造梦的,但每个人都有自我造梦的能力。放一块超宽白布,上书一个“悟”字,告诉一批人这是一部伟大的经典电影,强迫他们看两个小时,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也能在寂寞的冥想中,由自己的经历,不知不觉创作出属于自己的电影或者梦,达成和欣赏电影类似的体验。可白布是电影吗?创作的责任更多的属于电影人,而不是观众。电影也不是巫师手中催眠的魔杖,或是毒贩手中的迷幻药。魔杖和迷幻药也可以帮人造梦,但它们造梦的方式与电影是根本不同的。
电影是一种艺术,而艺术并不是独白。它总是要附丽于时代与人性,引起群体的共鸣。正如一些电影人宣称的那样,电影是可以超越时代的,部分电影是为了契合未来的某个时代而生的,故而今天的观众无法欣赏,并不能说明一部电影之低劣。但至少在这个时代,在中国,作为一个没有预先作任何功课的观众,我无法给予《镜子》任何赞许。因为当我欣赏它时,我彷佛闯入了他人的迷梦,只听到主人可怕的独白,彼时我唯一的念头,就是尽早从这个迷梦中逃出来。
2 ) 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也有人类的气味
——保罗-策兰《羊齿草的秘密》
毫无疑问,和全人类一样,艺术家正处于一个极度尴尬的时代。只不过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生存中的尴尬所在(即使他们意识到了也不一定清楚那种感受实际上是什么)。站在一般性的角度上看,尴尬本身无处不在,但有个布局广泛的、来自前人警诫的声音告诉我们,尴尬大多源于人的意欲与现实之间出现的断裂。意欲可说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心理动力,但同时,它也是距离事物的柏拉图式的理念最远的东西。因为意欲对智力与能力会产生绝对控制,从而使人们失去直观认识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的缺乏必将造成人类对生活的误解,并且让他们以为能循着功利主义的方法论摸黑走到底,却被另一副凌驾于现实之上的利齿咬住了脚踝。叔本华的哲学便十分强调“直观”这一概念,他本人认为,认知能力被意欲操控与否,即是区分凡人与天才的关键所在——“我们在天才创作的作品里经常见到并非蓄意的、不带目的的、甚至部分是无意识的和直觉的成分,这是因为原初的艺术认识完全脱离和独立于意欲,是一种不带意欲的认识”。
这话不得不让我想到俄国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以及他的代表作《镜子》。作为继爱森斯坦以来最伟大的俄国导演,也是瑞典电影大师伯格曼口中那个“掌握了他永远也无法进入的房间的钥匙”的人,塔可夫斯基拥有极为独特的电影美学和浓烈的个人化视野,是自我的光影世界中的绝对独裁者。事实上,在世界级导演的殿堂中,塔可夫斯基的可研读性早已远远超过一位电影作者,而成为了一种现象,开辟出数条幽径,直通向种种不同的意境。以《镜子》为例,这是一部自传性的作品,讲述一位艺术家的童年体验与成长。其中的画面语言象征主义极强,在结构上则全然拒绝线性叙事,而带有无与伦比的诗意气质。它的形成更多是基于直觉上的体验、心得和个人感受,而摒弃“理智”的作用,在这部电影里,只有直接地、纯净地面向自然与精神的感官才是有意义的。
塔可夫斯基本人认为,艺术决不能将概念之间的互动作为终极目的,形象是具体的物件,但却沿着神秘的途径延伸到超越精神的地带。这种纯粹的认知力所达到的柏拉图式的理念,在《镜子》中主要存在于三种表达层面,它们分别是:从生活中平凡的细节与时刻中捕获意味、对自然和人物庄重的追随凝望、以及沉郁优美的诗歌旁白。影片始于通过催眠治疗口吃的男孩的电视画面,接着在片头字幕之后切入一位妇人坐在篱笆上抽烟注视远方的背影,其后的片段还有舔舐一滩牛奶的黑猫,孩子的手不断翻动的书页,着火的木屋,一只鸟撞破窗玻璃的一角飞出,桌上滚落的玻璃瓶,下雨且坍塌的房间,母亲在镜中的老去瞬间,木桌上缓慢消失的雾气印痕,雪地中枯木下站着的男孩一把抓住停在自己毡帽上的鸟。这些画面都呈现出了一种静思默想的本质,是从意欲世界截然分离出来的纯粹表象世界,换而言之,它们并不与任何实际的价值或用途相关联,却可在思想之中有无穷无尽的指向。它们是出于“无用”而被人们忽略的真实时刻,这种真实又在画面的构图与光线中被赋予了审美意义。塔可夫斯基吟咏这一切,且他的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镜头,而是代之以大量的推拉镜头以及巧妙的轨道车运动。他的电影语言中的凝视感十分别致,镜头的移动和对焦具有一种朦胧与无意识的特性,像孩童一样天真和无目的的视角。如镜头长久地对准狂风乍起的树丛;又或者从吃饭的孩子平缓移向发呆的母亲,随母亲移向放有枯萎花束的窗边,从窗边移向外面被雨点拍打的铁罐;再或是在破旧的房间内缓慢摇动,接着沿走廊向尽头的蓝色窗帘前行;还有从台上的凸肚瓶的花纹特写拉远,并突然把焦点转向后面奔跑的孩子。这些场景与长镜头调度的不可知性,及其所处的跨界、中和、不拘的特殊状态,共同造就了塔氏电影中最主要的两大因素——梦境与回忆。
同样,使本片步入晦涩难懂的电影之列的原因还有它的复杂结构。其中大致可分为创作者的童年回忆和当前经历这两条基本线索,但却穿插着许多梦境与幻象,还有新闻纪录片,构建出个人体验之上的时代现实,形成了全新的时空组接。在塔可夫斯基看来,艺术可以再造时间,而回忆使生命得以重访过去。不拘于线性顺序也是塔可夫斯基对事物直观理念的体现。若想要以最纯粹的方式观照一个客体,我们必须忽略它在时间、空间上所处的位置,即关注它的个体性。这是因为唯有当时间和空间——这是我们认知的主观和形式条件——被抽走之后,这一客体才可以成为理念。因此伯格曼才会说塔可夫斯基“创造了忠实于电影本性的语言”,他始终坚持的原则就是与生命保有纯粹的联系。
除了精神维度上的神性之外,某种程度来说,塔可夫斯基在影片中所表现出的美学思想往往带有一种痛切的破碎和衰颓。塔可夫斯基非常珍视弱者,尤其是小孩、女人和疯子,他认为痛苦之后的疯狂恰恰是精神的高级形式。与充满自信力量的躯体相比,他更偏好探索伤痕累累、犹豫不决的生灵。这就应和了波德莱尔观点中“美与忧郁、不幸、理想的缺失有关”。在塔可夫斯基眼中,个人的学识与能量都无足轻重,他如同虔诚的僧侣般坚信唯有信仰决定生存的意义。也只有通过牺牲和受苦,人类才能获得拯救,走向重生。
平常人沉浸在纷乱、骚动的生活里面,由于意欲的缘故,他们隶属于这种生活,他们的头脑充满着生活中的事物和事件,但却又一点都不曾意识到这些事物、甚至生活的客观含义。而塔可夫斯基则始终在以博大深邃的目光凝视着大地、雨水、着火的灌木丛、人类的缄默和孤独。在艺术的漫漫长廊之中,他已像片中的殉道者一样直抵人类的尽头,然后慢慢地,慢慢地,转过了身来。
3 ) 淺析塔可夫斯基的《鏡子》
跨度長達四十年時光的《鏡子》,紀錄了自我個體和對母親、家庭的追述。在本片中,演員Ignat既扮演了主角的兒子,也扮演了少年時期的主角;而主角的前妻Natalya和他的母親Maroussia,又是以同一個人來飾演。塔可夫斯基的這特意選用,除了將人物命運泛指化之外,亦形成了一種鏡像反映,他為本片樹立著一面鏡子,不但令角色相互地對照,更令故事中的現實和夢互為地影射。虛實交錯的《鏡子》,很容易教人想到費里尼的《八部半》(連《鏡子》第一個夢中,母親容顏變老的一幕,也跟《八部半》內古依多母親出現的一幕有點相似),儘管它們都看似非常之混亂或很難理解,可遵循了人的意識、回憶總是跳躍的,和突然切入之事實,指向著那超越表面存在的內心世界。
一直都比較執著的塔可夫斯基相信,電影作為藝術的一種形式,自有其相當於散文的可能性,他提倡要展現電影的「詩性」,但需剔除鏡頭所有曖昧的,那些為作品變得更加藝術化而矯揉造作地加上去的「詩意」標記。正如本片內引入達文西畫的肖像畫,既代表了一種超越時間的元素(影片著力打破時間的限制),亦強調了女主角惹人憐愛又討人嫌惡的特質,兩者的二合為一,已經無法從中分離,以致我們在Maroussia迫不得已地要幫貴婦人殺雞時,會將她混合著冷漠、高傲和憤怒的神情,和這幅肖像畫聯想在一起。塔可夫斯基的《鏡子》,雖縈繞著超現實的氣氛,然而這氣氛並不是刻意營造的藝術手段,而是導演實現自身觀念的目的;他製造的一系列夢境,並不在於想暗喻什麼或象徵什麼,更重要是向觀眾表達自己的潛在體驗。所謂人做夢的動機能量(motive-power)是由潛意識提供,因此,夢境很多時是人在自己內心中真正看到的東西,塔氏將沒有概念和符號化的夢,代表了一種內在的意識流動,令電影既帶有「詩性」的藝術形式,又體現了對心靈上的最真實紀錄。
曾被定名為「自白」的《鏡子》,以一個女醫生幫助一個有口吃毛病的男孩開口說話的片段,打破了一種「閉塞」的狀態,也反映了導演塔可夫斯基終解除了某些枷鎖,勇敢地抒發出內心中的情感。這些情感或回憶,因為夾雜著很多的痛苦(如父親的離去、戰時的艱難),令到塔氏於拍攝《鏡子》之前,總很不願意地去提及、回顧(儘管《星球索拉羅斯》有談過自己和父母的關係);他在本片的一段戰時回憶中,讓人有點摸不著頭腦地插入了拉掉手榴彈手環的孤兒,和表面冷漠的教官這兩個角色,正正是說明塔氏自己跟他們一樣,都有著揮之不去的傷痕。
塔可夫斯基的《鏡子》,借影片開始不久出現的一個陌生男醫生之對白,指責了人們沒有時間去關注內心或本質的問題;隨後,主角跟母親的通話,又說到自己患有喉炎(為後面其病危作出鋪墊),三天沒有和人說話。主角的沉默,除了表示著語言的蒼白、不足以說出一切之外,也暗示了現實的邏輯未必能表達到內心的全部(所以之前有一段想象的場景出現);而《鏡子》通過無定的思維、和混亂的夢境,開啟了一個缺口,使到心裡面潛藏的東西能放飛出來,以便更容易地貼近「本質」的方位。對象徵主義不以為然的塔可夫斯基,雖於《鏡子》中放進了雨水、火,以及靠草叢、樹木、窗簾、或印刷廠內女角飄逸的頭髮、衣服所表現出的風的畫面,但這些看似富象徵意味的元素,如我在《星球索拉羅斯》那篇提到,只是大自然常見的現象,塔氏強調它們的目的,有可能只希望突出自然和人類的「本質」主題,而不是某些評論所過份解讀出的深奧含義。
至於電影內的新聞片段,雖然跟前面之情節有一定的聯繫,但我認為它們的作用更多在情感的傳遞上,並非是著力去進行對政治或其它的影射(即使它們表面上將影片觸及的範圍擴展到蘇聯甚至是本世紀的現代史)。好比軍隊橫渡錫瓦海什海的片段,就像塔可夫斯基說到的「讓我們產生一種錐心刺骨的痛楚,因為鏡頭中出現的軍人如此地平凡又渺小,他們在泛白蒼茫的天空之下,勉強拖曳著自己的軀體,穿越一片延伸至地平線彼端無止盡的沼澤,幾乎無人倖存。」這一場景所呈現的痛苦,結合塔氏父親關於「不朽、永恆」的詩句,營造出「如英雄般犧牲」的意象,和非比尋常的情緒強度;而它的拍攝方式(持續地以鏡頭觀察著單一的事件),亦啟發了塔可夫斯基對《鏡子》採用很多長鏡頭的想法,以及將表演部分和紀實素材有機結合的構思,令到本片只靠影像的呈現,便足以俱有撼人心魄的力量。
情節不斷穿梭於夢和現實之間的《鏡子》,給觀眾一種飄忽不定的感覺,而導演塔可夫斯基加上的一些漂浮意象,更強化了這「不定」的狀態。在影片中,有點「突兀」插入的西班牙家庭故事,透過後面新聞片段裡出現的半空漂浮汽球,暗示著他們因戰爭被迫離鄉別井生活的流浪者心態,而類似的漂浮或不能著陸之感,亦被藏於主角的內心。當少年時的「我」,於貴婦人客廳內等待母親時望著鏡子的那一刻,仿佛意識到自己的轉變、自己的覺醒,如此之簡單又有著豐富意涵的一幕,也令到「我」獲得了自主的意識,或找到能夠著陸的地方。因此,這之後再出現的漂浮意象,也多了一層「釋懷」的意思,像Maroussia懸空於床上的漂浮狀態(使人想起塔氏《星球索拉羅斯》中的著名失重時刻),既帶著思念,又想從過去中解脫出來;而病危的主角放飛那受傷的小鳥(小鳥的飛也是一種「漂浮」),亦都表示「我」終於能抱著輕鬆的心態,去面對自己脆弱的生命和往日留下的「傷痕」。
在影片即將結束之際,年老的母親背著我們吸菸的畫面,令人回想到她第一次出現時的姿態(也是背著鏡頭吸菸),而這,又彷如一個循環,反映出電影對不斷流轉之時間的探討。那奄奄一息的主角,把小鳥往上一拋之後,時間又回到美麗的從前,初次懷孕的母親Maroussia,正凝視著遠方蜿蜒的小路,而田野那邊,隨著巴哈雄壯的《勃蘭登堡協奏曲》響起,她已成為年老的母親,並牽著稚年的兒女,走過毀壞的家園。《鏡子》這樣神奇的結尾,彷如將三個斷面重新剪接、融合於一起,導演塔可夫斯基自由地用鏡頭進出不同的時空,使分別困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三間「房間」內的「氣流」,得以流通。
喜歡以較為俯視的角度拍攝的塔可夫斯基,常將攝影機對著廣闊的大地,他借電影的開端,那陌生男醫生與年輕「母親」同時由欄杆上跌落地面的一幕,明顯地傳達出他對大自然景象的關注。不滿於當時政權的塔氏,即便用了印刷廠的一段來表現出史太林政府的高壓統治(校字錯誤這樣的過失,在那個時代也可能導致嚴重的後果),但歸根結底,塔可夫斯基仍是深愛著他的祖國,深愛著這片土地。好比《鏡子》內曾引用的那封普希金致查達耶夫之信函內寫道:「無論給我世界上任何的東西,我都不願意把我的國家換成別的,我也不要任何不屬於我祖先的歷史,因為這本來就是上帝的所賜……」
在拍攝《鏡子》之前,常被童年夢魘折騰的塔可夫斯基,總相信要經歷過心靈危機才有治愈的可能。他在《雕刻時光》內寫道:「心靈危機乃是一種冀求發現自我、重獲信念的誘因,當靈魂渴望和諧而人生卻充滿紛擾,這一對峙反而是刺激行動的動力,同時亦是我們痛苦和希望的源泉」。嘗試走入「禁區」的塔可夫斯基,決定不再把自己收藏起來,他靠著他對藝術的觸覺和跟心魔的搏鬥,不但排走了其童年記憶的困擾,並且成功地釋出自己的心靈深度和潛能,促使了這部如此純粹又誠實的電影之降生!
4 ) 给予电影一种空间描述的尝试
开始
影片 15:45 儿童时期的主人公躺在床上,被火烧的噼啪声覆盖而过的钟摆滴答作响的声音再次响起,鸟叫一般轻微的声响过后①,孩子从床上起身往前看去,镜头转变成户外黑白的草木②,再次的鸟鸣声,风吹过。 又是沉睡中的孩子,”爸爸”,鸟鸣声,起身下床,镜头是持续的黑白颜色。走到门口位置,再次出像鸟鸣,滴答声渐止,一件白色的衣服从墙的背面飞过③,孩子停在了门前。所有和现实有关的物象在这里停止(或许从黑白的画面的开始一切都只是儿童的梦境)
一个黑暗潮湿的房间,远景上有燃烧的小簇火焰。父亲俯身替母亲浇水的镜头,父亲从画面右侧离开,镜头往下是母亲洗头的画面,母亲起身,水的滴答声,镜头开始往远处拉④,出现母亲及画面的全景,脸盆、父亲消失不见,母亲独自赤脚站在房间中央,长发盖住面部,只看见肢体活动。房间的左侧放置了一个带有镜子的大衣柜,母亲身后的墙上有几扇大窗户,窗与窗之间的小柜子上的煤气灶火苗燃烧,右下角定光明灭不定,母亲的头顶是一盏破败的吊灯,地板上有积水。
镜头再次切换是母亲背后的景象⑤,天花板的墙皮开始大块剥落,落在木地板上溅起水,灶台上的火越烧越盛,背景音也相应紧张,镜头往后拉去,母亲已经从原来房间中心的位置消失⑥(或许是走开)
镜头切换,母亲在行走⑦,天花板不停掉下碎屑,人物近景,从场景上判断应当是由原先处于身后的小柜子的位置开始,经过窗,在房间转角处停顿抬头,经过大衣柜的镜子。摄像机到了母亲的前面的墙,停顿,一个影子从似乎从墙上闪过⑧,站在原来的角度镜头再往前转,墙上装着滴水的龙头,龙头下面是一面镶在墙上的小镜子,再往前出现一面砖墙,(应该是一个窗洞)母亲再次出现在镜头中,身上及头发却干燥⑨,围了一块披肩,背后是一大束花朵,似乎是倚靠在窗台上向室内张望,镜头转往母亲张望的方向,一面巨大的半透明的玻璃似乎靠在房间的某一面墙上,玻璃反射了在前几个镜头中出现的两扇窗,及炉火,隐约还可以看到绘画的云彩和一颗树。玻璃上出现了年老母亲的面孔⑩,同样披着一块披肩,母亲望着模糊不清的影子手抚过玻璃。
房间的场景结束,母亲的手,在手后燃烧的火焰。 影片19:08
结束。
鸟叫一般轻微的声响过后①
塔克夫斯基的电影中经常出现一些提示性的符号来预示一件事情的开始或结束,如影片开头医生转身的场景便以一阵风作为回头的理由,而在这里,鸟叫一样的鸣声成为孩子醒来、起身、风吹过以及房间门口衣物飞过的提示反复出现
镜头转变成户外黑白的草木②
第一个转折
影片中黑白与彩色画面的转换并没有限定在某个时间段,如梦境与现实、现在和过去等,而是随着每个情绪的变化自由转切,但在影片此段中,黑白画面由房外的树木开始直至最后到母亲的手和火焰的出现结束,贯穿在这段超现实的片段中,成为梦的颜色。当镜头从户外转到室内时,再次出现了孩子沉睡的镜头,而这种镜头的反复在影片接下来的场景中也以其他的形式频繁出现,这种手法使一个梦境得以意外而又超越合理的完整呈现。
一件白色的衣服从墙的背面飞过③
第二个转折
场景在这个画面后完全由卧室转向一个不属于这个屋子的另一个房间,这也这个段落第一个不合常理的开始。孩子站在卧室的门口观望了自己梦境的全过程,他在梦境的开始预感到自己父亲的出现,却无法穿过门去参与其中,梦境的内容属于父亲、母亲、一个陌生的房间而没有他自己。
镜头开始往远处拉④
第三个转折
这个效果突出的镜头伴随着渐响的背景音,成为一个梦的小高潮。也让我们得以看清房间的真实模样。这是一个潮湿破败的房间,右侧的墙上有一个带镜子的大衣柜,母亲背后的墙上有两扇窗和一个小灶台,母亲头上有一盏灯,发展至此我们似乎可以描绘出房间的大致平面图了,但镜头却又是不诚实的,父亲、水瓶、都在镜头移动的过程中消失了,母亲孤立无援得独自站在房间的中心,(父亲冷漠的表情似乎从开始就预示着离开)
梦发生的主体似乎发生了一点转移,这已经不是一个孩子所能看见的东西,而是母亲的心理状态,关于独自生活的无依靠感,对丈夫的思念,潮湿寒冷。
镜头再次切换是母亲背后的景象⑤
第四个转折
镜头再次出现虚假的景象,天花板的粉皮剥落和地面上溅水的激烈响声,或许是画质的原因(?)这组镜头似乎脱离了整体的段落,颜色生涩不真实。
镜头往后拉去,母亲已经从原来房间中心的位置消失⑥
连接上一个转折
母亲在行走⑦
第五个转折
人物出现在镜头当中,行走的路线与上一个转折发生了冲突,从母亲身后的场景来看应当是由原先处于身后的小炉灶开始经过一扇窗户、墙角转折、带镜子的大衣柜。而人物移动之前的路线的交代缺失了。
停顿,一个影子从似乎从墙上闪过⑧
母亲再次出现在镜头中,身上及头发却干燥⑨
第六个转折
影子的出现预示了后边不同寻常的场面,镜头走得比母亲的速度略快些,在行走的人物前面的墙体上出现了晃荡的影子,一闪而过,接下来又是水、一面镜子。接着往前移动,母亲以完全不同于之前的状态又出现在了镜头的前方,背后的花束和肩上的披肩显得柔和安详。
在这里,房间的平面图又向前明晰了一步,右边墙体上除了大衣柜还出现了一个水龙头和镜子,再往前是一个窗洞。
玻璃上出现了年老母亲的面孔⑩
随着母亲张望的目光,所有之前的平面都被打乱了,一切在逻辑上成立的景象都成为假象。母亲的目光看向的或许是自己倒映在玻璃上的影子,或许是看着站在房间另一角年老的自己走向那片玻璃。
玻璃应当是靠在与大衣柜相对的那面墙上(成斜角映出两扇窗和小炉灶)但是同样映出的天空与树的画面却来源不明。母亲抚过玻璃的苍老的手也难以说明房间中站立的究竟是谁。这个梦境的高潮没有解开所有的谜团只是将一切封闭在一个更大的假象当中
第一次观看影片时便被塔可夫斯基的造梦方法深深吸引,事物都是合乎常理的但组合起来却化为虚幻,梦境本身就无逻辑可循,我试图绘制的平面最后也模糊不清,而导演的手法却渐渐明了,摄影机和人物一次次的“错过”,两次的重复、一次的存在和下一次的不存在构成了所有幻觉的始末,镜头的停顿、放缓、拉快都使得一些物象消失了,或者是一些不合常理的现象发生。这种弱的叙事手段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剪接得以站立。
5 ) 《镜子》:记忆或悔恨的方式
1974年,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凭借科幻电影《索拉里斯》的成功,终于可以自由选择拍摄题材。之前几年,由于(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的反对,他的多部剧本遭到拒绝,一直处于停工状态。而这一次,人到中年的塔可夫斯基选择了自传性题材,回顾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和父亲母亲。这就是后来被伯格曼盛赞、哈内克称为“影史奇迹”的《镜子》。然而,在《镜子》上映以后,相当一部分观众与学者表示不解。塔可夫斯基则屡次强调“《镜子》没什么看不懂的,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线性叙述的故事,每个人都可以当作自己的经历来看待。”然而,存在于声音和画面之间的断裂感、镜头剪切遵照的情感逻辑(而非简单的理性逻辑)、以及极其个人化的时间感受,依旧带给初次观看电影的观众相当程度的迷惑。这是一部需要观众不断调动自己人生经验和情感知觉去浸入其中的电影,在外部“观看”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镜子》定义了电影作为艺术能做到的事,并非提供视觉奇观、娱乐体验,而是扩展人的心灵的觉知。这也是塔可夫斯基对诗歌的认知(“诗人的使命在于激起心灵的火花,而不是培养偶像崇拜者。”——《镜子》中主人公的台词),以及终其一生在电影事业中的追求。而《镜子》作为一部自传性的电影,尤其特别,它几乎是那种拍给自己的电影,看似随意的各个片段中实际上精心散布着暗语、私人隐喻、以及仅作用于个人的记忆辨识物。于是,只有通过重看《镜子》,我们才能够记住这些暗示,将这些片段的隐秘联系构建起来,理解塔可夫斯基所表达的“记忆”。事实上,《镜子》的不可思议之处就在这里,它尝试表达每个人一生中都必将面对的记忆问题,却触碰了个人精神世界的终极秘密:人类如何尝试准确地言说记忆这种不可言说之物,以及,记忆作为被时间抛弃的现实,它是如何渐渐侵入人的梦境、现实与想象,又是如何隐秘地作用于人类语言及人类意志的。
1.记忆的三种叙述方式
电影正片的第一个段落,年轻的母亲静静地坐在一截树篱上,远处的田野上,一个男人的身影由远景走入近景。母亲的台词暗示我们,在望着田野的时刻,她曾一度把这个陌生人错认为归来的父亲。目送陌生人离开以后,镜头回到母亲的背影,并且追随母亲的脚步、经过一个倒在地上的小孩(保姆把小孩扶了起来)、另一个小孩在餐桌上吃东西,牛奶和食物凌乱地撒在桌上,而母亲失魂落魄地走过这一切,对生活中的混乱不闻不问,画外音是父亲在朗诵一首情诗:
每次我们相会的时刻,都当作主显节来庆祝。
整个世界只有你和我。
你敏捷又轻盈,胜似鸟儿的翅膀。
急匆匆跑下楼梯,一步踏过两级。
你拉着我,穿过潮湿的丁香树丛。
来到镜子的另一边……你的领地。
……
正直的神啊,你是属于我的。
你醒来了。改变了人类尘世的语言。
我的喉咙突然充满新的力量。
当我说出“你”字,发现它有了新的含义“王”。
恍惚之间,一切都在变幻。
繁琐的事,笼罩着我们。
寸步不离。层出不穷。
我们被牵引着,不知去向何方。
奇幻的城市在眼前飘过,如海市蜃楼一般。
野薄荷为我们铺路,
鸟儿们为我们护航,
水中的鱼儿逆流跟随,
天空为我们拉开恋慕,
命运正循我们的足迹而来。
像个疯子一般,挥舞着剃刀。
这首诗始于恋人相会的甜蜜日常场景,音调不断拔高,恋人的“你”成了“尘世的语言”,成了“王”,最终,止于不可思议的境地:万物仿佛围绕这段恋情而展开,甚至“命运也要循我们的足迹而来”,从而抵达了精神的宏大、崇高之境。而通过下一个段落,我们知道,主人公的诗人父亲在1935年抛弃了母亲和孩子。这段情节完全取材于塔可夫斯基的童年经历。父亲阿尔谢尼伊·塔可夫斯基离开家,留下一座乡间府邸、形单影只的母亲和许多诗稿。童年的塔可夫斯基则沉浸于父亲的诗歌,也许就包括这首写给母亲的情诗——这构成了塔可夫斯基的一重童年回忆(这些诗歌形成了塔可夫斯基对父亲的精神认同),而另一重回忆则是母亲孤独地等待父亲的现实场景。父亲的诗歌越是甜蜜、崇高,他本人缺席的现实就越是刺痛人心。尤其是当母亲把陌生人错认为父亲后,这期待成空的失落感达到了顶点。于是,在这一片段末尾,当诗歌的情感攀升至顶点,母亲终于打破隐忍,对着镜头哭泣。我们看到语言的力量发生了偏移和失效。
接着,屋外传来起火的呼喊,母亲冲了出去。餐桌前的两个孩子听见母亲说房子起火了,也朝外跑去。这时,塔可夫斯基运用了违反常理的场景调度——镜头并没有追随小孩的身影去往起火的房屋,而是停留在凌乱的空餐桌前,直到一个奶罐从桌面滚落在地。之后,镜头缓慢环绕房屋的内景,对准了两个孩子站在门口影影绰绰的背影,透过孩子的背影,我们能够看到依稀的火光。当燃烧的房屋最终正面出现在画面里时,这个场景却是平静的、景观式的,而不是混乱的、灾难性的。这种奇异的视觉再现,无疑是经过理性修饰后的回想,是基于记忆的再创作而非直接记忆。过往的记忆通过回想被构建起来,加入了现实的日常秩序。这回忆和回想的混淆被主人公后来的独白所印证:
“我经常做一个梦,梦里我回到了我最心爱的地方,祖父盖的房子。四十年前,我就出生在那房子里的餐桌上。每次我想走进,总被什么阻挡。这个梦,我做了一次又一次。当我看到那圆木围墙和幽暗的存储间,尽管是在梦中,我也能意识到我只能梦到它。于是快乐消失了,因为我知道自己定会醒来。有时,一点声响把我从童年房子和松树的梦中惊醒,我便伤感不已,盼望着再做这个梦。这个梦使我又回到童年。重温儿时的欢乐,让我感到一切尚在前方,一切皆有可能。”
梦的重复使梦境本身变成了一种记忆。现实对记忆的回想虽然模仿了记忆中的场景,却夹杂了失去的伤感。唯有通过入梦,才能找回现实中失落的东西:记忆中的情感。
于是,人物通过回想而入梦。梦的段落是黑白的,梦中的一切失序,变形,夸张。比如父亲在给母亲洗头,突然水缸消失,母亲站立如鸟,而房屋开始剥落、瓦解,年轻的母亲走向镜子,镜子中却映照出一个老去的母亲……这并不是主人公期待的那种快乐的梦,而是充满危险和不安的梦。中年的主人公从梦中醒来,接到业已年迈的母亲的电话。主人公提到自己的喉炎,谈到不再信任语言,也回应了前两段场景发生的时间——1935年,父亲的离去和起火的房屋。接着,在台词中,主人公暗示自己和母亲之间始终无法解决的沟通障碍,母亲则提起一桩发生在现实维度的事:以前一起在印刷厂工作的同事丽萨死了。
电话结束以后,下一个段落自然衔接到母亲年轻时去印刷厂校对书稿的段落。镜头追随母亲从室外一路走进办公室、抵达印刷机器所在的房间,通过镜头运动、和他人的互动,塑造了紧张、人与人互相不信任的政治高压氛围。母亲怀疑校对错了一个词,我们通过另一个女孩的哭泣和母亲拒绝对同事解释的态度而侧面推测出事情的严重性。而“那个词”的始终没在电影中被揭示,使得恐惧不安的情绪在沉默内部收紧,无法向任何词语的意义散逸出去。这个段落发生的背景是大清洗运动时期。我们能感受到母亲感受到的这种无法表达的紧张和压抑,尤其是,恐惧并不指向具体事件,而只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会在任何时刻随机降临。
检查过后,校对并没有出错。母亲缓缓走出房间,我们看到母亲精疲力竭的面孔,几乎是遭遇了一场内心浩劫。这时,随着镜头长久地凝视着母亲的面孔,父亲的画外音再次出现:
昨天,我从清晨就开始等待,
他们猜到你不会来了。
还记得那是多么美妙的一天吗?
晴朗得像节日!我外套都不必穿。
今天,你来了,可天气却是
悒郁而昏暗
落着雨,且天色已晚,
冰冷的树枝上,雨水流淌,
言语难以抚慰,方帕也无法拭干。
这依旧是一首情诗,但情感远不及上一首诗那么自信。这首诗中,“我”虽然等待着恋人,恋人到来以后“天气”却是悒郁而昏暗的。“昏暗的天气”可以解读为恶劣的社会环境,恋人本想分享美好时光,此刻却遭受了环境的考验,只好共同承担时代昏暗的一面。这里,恋情不再转向对万物的慨然高歌,而是转向相互依恋的二人关系内部。于是,诗歌和画面的并置再一次产生了反差:政治高压环境下,母亲独自经历着精神的恐惧和压抑。在接下来丽萨对母亲的攻击中,又一次提到父亲抛弃母亲这一事实,丽萨认为,父亲之所以离去是因为母亲的性格缺陷,母亲因此陷入了更佳无助的状态。
这个片段中,主人公显然无法参与母亲的记忆,只有通过母亲后来的转述,主人公才能知道母亲那一天的经历。于是,这段画面将他者诉说的记忆转化为对他者记忆的个人想象,故事虽然来自母亲的真实经历、细节却属于主人公的虚构范畴——也唯有通过虚构,主人公完成了对母亲迟到的理解。
2.跨时间的三组镜像关系
结束对童年父亲的回忆之后,电影时间再次回到现在。画面变回彩色,镜中是年轻母亲的脸,而通过主人公的台词“你真像我母亲”、以及接下来关于教育孩子的对话,我们知道,镜中的女人并不是母亲,而是演员玛格丽特·捷列霍娃在影片中扮演的另一个角色:现实中已经和主人公离了婚的妻子。这大概是塔可夫斯基刻意制造的混淆效果:不仅迷惑了观众,似乎也迷惑了主人公,以至于后来主人公说:“每当我回忆起童年时的母亲,想起的总是你的脸。”
一方面,回忆被现实入侵了,同时,当主人公凝视现实中的妻子,现实仿佛也有了回忆的质地。回忆中的母亲和现实中的妻子,本应分属两个不同的时空,却因为相似而成了同一个人的实体与镜像,共存于同一时空中。而妻子多次提起主人公和母亲的关系,责备主人公对母亲疏于照顾,母亲的诉求附着在了妻子身上。而主人公和妻子无法交流的关系困境,也就是主人公和母亲的沟通障碍的延续。
与“现实中的妻子与回忆中的母亲”这对女性镜像同时存在的,是“童年的主人公与现实中的儿子”这对男性镜像,主人公不希望儿子像自己一样,在父亲缺席的状态下成长。而主人公面对的离婚现实却无奈地模仿了记忆中的童年,作为父亲的自己被动地缺席于儿子的童年。时间像一个漩涡,将现实中的“我”置于童年时“我的父亲”的位置,至此,第三组镜像结构被揭示出来,即“我童年的父亲”和“如今作为父亲的我”。
另外,我们注意到电影对主人公的处理,他的成年形象从不曾正面出现,而是代之以对话、独白、电话里的声音,这和主人公父亲的画外音相似,可以说,现实中的“我”成了回忆中的父亲的声音的模仿,这一次,对称发生在两个声音之间。
3. 历史的三种面相
《镜子》中的画面在黑白和彩色之间切换。至此,梦是黑白的,虚构是黑白的。现实是彩色的,现实中对记忆的回想也是彩色的。而接下来出现的历史纪录片则是黑白,似乎暗示着官方记录的历史和梦、虚构是同一类事物。而历史,在电影中的呈现又是多层次的。
在妻子拜托主人公照管儿子这一情节后,镜头直接切入妻子和西班牙裔朋友的聚会,一些西班牙战争纪录片的片段交叉剪辑于西班牙移民的日常生活中。一边是具体的人的日常生活:男人模仿斗牛表演、年轻女人舞蹈、断断续续的谈话;一边是是纪录片中的人民:救济队伍、轰炸后的街道……并且,历史和现实都通过快速跳切,如同梦境般快速、吊诡、失真。
这便是被历史裹挟着的人,沉浸于细节、瞬间、场景而无法看清历史的来龙去脉的人们,只能拥有情绪而非情感,体验而非意义。
与此同时,儿子被安置在主人公家中,他在餐厅看见了一个陌生妇人。老妇人交代儿子读一段笔记,笔记则摘自普希金写于1936年的书信:
“教会的分裂造成了我们与欧洲的分离。震惊欧洲的每一次重大事件。我们都是局外之人。但是,我们有自己特殊的命运。俄国,以其幅员辽阔,吞没了蒙古国的入侵。鞑靼人也在我们的西部边境,望而却步,最终退回了他们的荒原。于是基督教文明得以保存,为完成这一使命,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保持了我们天主教徒的身份,又把我们从天主教世界孤立出来。您认为我们的历史毫无疑义,我不能同意。难道今真的找不出一点能够令后世史学家心动的价值吗?我热爱我们的国君,但我并非对身边一切都满意。作为一个作家,我也感到屈辱和烦恼。但我可以发誓,世界上的一切都不能使我抛弃我的祖国,或者抛弃上帝赐予我们祖先的历史……而别无索求。”
当儿子被敲门声打断后,出去开门再回来,发现老妇人已经消失,只有桌上一团正在消失的雾气证明她曾存在过。这个诗人的幽灵——老妇人的形象明显参考了白银时代著名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一个同样忠诚于祖先的历史、忧惧自己所处的时代、一生饱受精神摧残却坚持写诗的高贵形象,对应于普希金“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地位,阿赫玛托娃被俄罗斯人称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用诗歌照亮了她置身的黑暗年代。或者你可以单纯把这个消失的老妇人看作一个历史的幽灵,历史的幽灵通过文化——历史的沉积物——向我们发声,而那些留存下来的话语、话语中求索的高贵信念,虽然微弱而短暂,却有着穿透历史的力量。电影在其他段落则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第六病室》、屠格涅夫《贵族之家》……这些文化记忆虽然始终镶嵌在个人生活记忆中,但却并没有阻止整个人类历史走向战争、屠杀、疯狂。
在儿子读的另一句笔记中,塔可夫斯基表露了这种担忧:“对于科学和艺术能否影响人的道德的问题,卢梭的回答是:不能。”
在这一片段的末尾,主人公的声音出现在电话里,和儿子提起发生在自己少年时代的恋爱,唤醒了对于历史的回想——
画面是冬天的射击场,少年时代的主人公听到教官的口令,却坚持做出俄语对应的动作。这里,语言作为人为制定的规范,不再是绝对真理,而只是一种对民族身份的认同。通过台词,我们知道,这是列宁格勒被占领后的某段时期,主人公的父亲死于列宁格勒围困战役。主人公的不惜触怒教官,依旧坚持认同俄罗斯语言。在经过充满冲突和对抗的训练、一桩有惊无险的意外之后,主人公最终孤身一人离开了射击场。战争纪录片再一次出现。主人公的父亲开始朗诵另一首诗:
……
世界上并没有死亡,
人人皆不朽,事事皆永恒。
不论你是十七妙龄,抑或七十暮年。
都不必惧怕死亡,
世上只有真实与光明。
没有死亡或黑暗。
最终我们到达了海滨。
我是其中一位拉网人,
守望不朽的鱼群。
在一座永不倒塌的房屋中,
我要召唤所有世纪,
召唤它们进来,共建我的安居。
于是,在我的桌上,
你们的儿女与妻子同座。
曾祖与曾孙共聚一堂。
未来已在当下注定。
面对你我轻轻举起手掌,
留给你的将是五道光芒。
以肩骨为支架,我擎起逝去的每一天。
我用一把折尺,把时间丈量。
我在其中漫游,如同在深山穿行。
比照自己的生命,我截取了其中一段。
我们向南行进,
草原扬起盘旋的尘土。
长草堵塞了去路,一直闲游的蚱蜢,
用触须轻叩我的马蹄。
……像个僧侣一样,它预言了我的死亡。
我接过我的命运,系在马鞍上。
我将策马驶向未来。
矗立在马蹬上,我依然像个男孩。
我的不朽已然足够,因为,
我的血液已流过沧海桑田。
我愿付出我的生命,换取一个永恒的角落,
安全而又温暖,不再任生命的飞针,
牵引着穿过世界,像一根丝线。
这首诗回应了个人和时代的关系。前半段恢弘的口号式金句表现了追求不朽、不惧死亡、构建家园的伟大信念。但诗歌的后半段渐渐从口号式的呼喊转向对个人生命处境的忧虑,直到感到即将降临在自己身上的不详命运。在诗歌结尾,诗人展现了某种追求崇高信念过后的疲惫,比起成就伟大的事业,诗人愿意牺牲生命,换取死后一个安全的角落,而不是终其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战争、民族、被宣扬的伟大事业。
而诗歌的声音对应的纪录片画面,从涉水行进的军人、变成了希特勒之死、珍珠港空袭、中国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历史以不断推进的大事件加快着自身步伐,取消了一切细节。与纪录片交叉剪辑的画面则是:少年在雪地上俯瞰着远处的人来人往,无限趋向静止,突然,一只鸟飞临少年的帽檐,比起冰冷、浩大、无情的历史进程,个人生命显得何其生动、脆弱却珍贵。
再一次,父亲的诗歌给置身于历史洪流中却不知所措的主人公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和安慰。这直接引发了主人公对父亲的怀念,电影画面也转到了父亲归来的场景。父亲归来的一幕一定让童年的“我”记忆深刻,以至于“我”不仅记得扑向父亲怀抱的瞬间,记得父亲闪亮的军装,还记得在这之前发生的场景:童年的我和妹妹在树林中争吵,突然听见父亲的呼唤。这是主人公等待了整个童年的声音,也必将在他此后的人生中反复回响。
4. 语言,记忆或悔恨的方式
对照于充满情感张力的童年,主人公成年后的现实却深陷泥沼,这时,主人公似乎已虚弱到失去了修补生活的力量,在和妻子进行过一段短暂而无力的交谈后,他再一次陷入了童年的梦境。这一次,梦中的景象开始变得衰败、破碎,一只鸡打碎了窗户玻璃,童年时的餐桌被置于荒野之上,大风把桌餐上的东西吹倒了——往事彻底成为无法复现的过去。在这段令人不安的梦境的末尾,幼小的“我”走过童年家屋残破的风景,一扇“我”无法拉开的门忽然自动打开了,母亲就在那里。可以说,母亲作为“我”童年时的情感核心,支撑起了“我”全部的童年世界。虽然,也正是这样的关系延续到了“我”的成年以后,直接造成了我和母亲关系中始终无法弥合的创伤。
在最后一段对记忆的回想中,母亲带着童年的“我”去邻居家。母亲卖给邻居一副耳环。而“我”坐在客厅里等待的时候,看见桌上的牛奶撒了。牛奶罐、以及倾洒的牛奶在《镜子》中反复出现,似乎对于塔可夫斯基而言,无疑是某种引发个人情感记忆的标志物。(多年后,摔碎的奶罐又出现在塔可夫斯基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牺牲》中。)这之后,“我”看向客厅中的一面镜子,镜中的我也对望过来。镜头向着凝视镜像的我推进——记忆望进了现实中的“我”,而“我”则审视着记忆。
之后,母亲带着童年的主人公回家。河畔边,母子二人各怀心事地走着。父亲的诗歌最后一次出现。诗歌集中处理了灵魂和身体的关系,灵魂从想要挣脱身体的束缚,自由飞向苍穹,到诗人意识到“没有肉体的灵魂是有罪的”,长久被忽略的身体终于被诗人置于和灵魂同等重要的地位。在主人公的童年生活中,父亲通过诗歌声音存在,代表“灵魂”,而维持日常生活的母亲形象则更亲近“身体”,在这里,诗歌的声音不再代表语言的断裂,而是通过诗歌,主人公完成了某种对父母的和解。
然而,我们明显感觉到记忆、梦和梦想的边缘更加暧昧模糊,切换更加突兀和强硬。在梦中,童年的自己穿过空荡的房子,抱着牛奶罐凝视着黑暗中的镜子。在梦想中,童年的我又回到了那片宅邸和那片原野。母亲坐在那儿,却已然老去。塔可夫斯基模拟了死亡之前人的记忆的速度和密度,作为我们生而为人的最后一次生产活动,这段记忆的影像几乎像是人的一生的情感结晶体。
与此同时,在主人公躺在病床时,医生在门外诊断他的病情: “并非因为喉炎,而是因为记忆和良心。”
喉炎只是病情的外在表现,而归根结底,生病是由于由记忆塑造的现实的沉重。由于现实无法医治,主人公只好在内心一次次重返记忆之地,对其进行反复的回想和改造。塔可夫斯基则说,“试图通过自己的过去来解决问题,这是一种悔恨的方式。”虽然在电影中,这种通过回到过去来自我治愈的尝试失败了。自主人公死去的病榻上,却有一只神启般的鸟在创伤后展翅。
这隐晦地道出了《镜子》的秘密:塔可夫斯基通过审视自己的过去而完成了某种自我疗愈,再次确证了对于电影的信念。正如影片一开始那个医治口吃的画面,它和电影本身没有任何情节上的联系,而是单纯展示了语言神秘的治愈性力量。这段影像也是一面镜子,是藏在电影《镜子》中的隐形的镜子。只不过这面镜子指向人类的语言。而语言,在塔可夫斯基的世界里,同时也就是电影、镜子和梦境。
而今,距塔可夫斯基拍摄《镜子》已过去近半个世纪。影像从未像今天一样泛滥、快速传播、并充斥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文化从未像今天一遭受消费和娱乐的冲击。电影也早已不再追求诗歌的质量和密度。然而,当我们一遍遍重看《镜子》,依旧会为它深沉的情感和梦幻的影像着迷。这部回应时间主题的电影,最后成了时间中的奇迹,一座纪念碑,它记录了世上最困难也是最惊心动魄的工作:人如何珍视自己注定失落的记忆,以及人如何艰难地抵御着绝望去救治自己。
2018.6.1
6 ) 《镜子》——世界是一面镜子
有几次惊讶的睁大了眼睛,有几次忍不住流下眼泪,有几次实在无法再看着屏幕,但是一种矛盾的心理又吸引着我迫切地想看到那些被时间掩盖的角落。
是什么让我如此着迷却又如此惧怕?
艺术不能说明只能讲述,正像塔科夫斯基说的那样,他在展现生命,而非讨论。他给人的不是一个结论或者一个需要讨论的细枝末节,而是一种看待自己的方式。
电影由散乱的镜头拼接,很多时候是模糊的,让人置身云雾,但是又有一只手一直坚定的拉起我顺着这条路清晰的走下去。
《镜子》中的世界
塔可夫斯基曾经这样谈论《镜子》:“不要把《镜子》想象的太复杂,它不过是一条直线式的简单故事,没有比这更易读的了。”
塔可夫斯基在《镜子》中讲述和回忆了自己生活的很多片断,这些片断彼此关联,相互渗透,以至于让我们难以区分,深感迷惑,人们在说到《镜子》的时候,也往往称之为“非叙事性”的。毕竟那些故事不是我们的经历,甚至和我们的经历大相径庭,但这并不会阻止我感受到这部电影的美,以及这种美传达的力量,信念,以及探索的勇气,这也让《镜子》有了被读解的可能。
塔可夫斯基曾经为《镜子》辩护说:“如果两个人能够经验同样一件事情,那怕只有一次,他们也将能够了解彼此,即使其中一人是生活在旧石器时代,而另外一个则是成长于电化时代。上帝赋予人类能力去了解、体会人类共同的冲动--包括自己的,也包括别人的。”
虽然我们的经历如此的不同,但是我们还是以不同的方式经历过很多同样的事情,这些事情,正是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必须,我们在其中思考,生活,感动,而塔可夫斯基则用他的镜头,把他的思考,生活和感动凝固下来,成为他的“时光的雕刻”。
《镜子》是在讲述导演塔可夫斯基自己的故事,从童年父母离异,到他现在的情感矛盾,从30年代苏联相当严酷的社会环境,到战时的混乱,亲人的离去,再到他拍摄电影的当下。塔可夫斯基故意使用同样的演员来扮演不同时刻的不同角色,他的母亲和妻子的角色都使用了Margarita Terekhova作为扮演者,他自己儿时也和自己的儿子使用了同样的演员,加上其中很多明显的幻想段落,都使得这部电影具有了更多梦的意味。
*主要角色
母亲Maria,她的同事等人也称她为Masha,Marousia;
主人公Aleksei;
妻子Natalya;
主人公的少年时代Alyosha;
主人公的儿子Ignat。
在这五个角色中,母亲Maria和妻子Natalya的主要形象,以及主人公的少年形象和自己的儿子都使用了相同的演员,而主人公自己则始终没有正面出现,也就是说,这五个角色,实际上只有两个演员。区分Maria和Natalya几乎只能依靠Maira抽烟这一点。另外,母亲Maira的老年形象,则是塔可夫斯基自己的母亲塔可夫斯基娅亲自出演的。主人公幼年的形象,则是一个可爱的小孩子。
此外,在电影中不同场景中重复出现过的人物还有父亲,也就是Maria的丈夫;主人公的妹妹Marina;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明显是在模拟50岁左右的阿赫玛托娃的形象;一位医生。
在电影中只出现一次的其他一些人物,还有母亲的同事Lisa,一对西班牙中年兄妹,主人公少年时的军事训练教官以及一些一同接受军事训练的少年,其中有主人公初恋的女孩子,战争时期主人公家人的一个邻居。
在电影中大量出现塔可夫斯基父亲的诗作为背景声音,这些都是诗人自己朗诵的。
《镜子》被一些研究者分成14个段落(不算片头的字幕),时间上一般分为战前,战时,战后三个时期,分别对应30年代,40年代和60年代,更为合理的区分方式则是以主人公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两个时间段作为标准,另外加上一些想象的场景和纪录片段落,总共有16段。
1. 治疗口吃
战后,现在;真实的场景,彩色
Ignat打开电视机,是一部治疗口吃的影片,医生通过暗示和引导的方法,治疗一个高个年轻人的口吃毛病,最后那个年轻人流利而响亮地说出:“我能说话了!”塔可夫斯基似乎是在以这一段影片来表达自己打破长久的失语状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的心情。
2.片头字幕
塔可夫斯基仍然使用了巴赫的音乐搭配片头的字幕,使用的是管风琴小书的第16首"Dasalte Jahrvergangenist",“旧日时光一去不返”,BWV.614。
3. 着火的房子
战前,过去;回忆的真实的场景,彩色
母亲Maria和一个医生在田野中谈话。画外音是主人公自己,此后主人公一直以画外音的方式出现。A.塔可夫斯基的诗也第一次出现。
镜子第一次出现在几个小孩跑出去看烧着的木房。那是儿时老房子的内景,母亲Maria和幼年的主人公,以及主人公的妹妹。
镜子中的影像逐渐清晰。鹅黄色的光晕笼罩着房间,两个小孩站在门口,一高一矮,玻璃储水罐静静地站在地上,门旁的桌子上堆放着杂物,墙上挂着两个锅。
整个场景安详地让人不安,孕育着一种爆发,在暗示战争的来临。
战争一如那所燃烧的旧房,没人能挽救,没人能逃离,没人能反抗,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灾难的降临和束手无策的去经历。
镜头静止在火焰窜升的木房,仿佛隐喻战争的永无止境,就算结束也要以燃烧殆尽作为高昂的代价。
[着火的房子]
4. 母亲梳洗头发
战前,过去;想象的场景,黑白
幼年的主人公睡在床上,彩色的场景转入黑白,风掠过灌木,鸮鸟略显孤独的鸣叫,孩子呼唤着爸爸从床上坐起来,父亲帮母亲梳洗,黑白的影像明显带有梦的气质,水的声音和环境的声音异乎寻常地大。
母亲湿淋着头发直起身,在坍塌的房子中走过,她走过镜子,水滴不断从上面落下。她双手按着身上的毛巾,当再次出现在镜中时,容颜已瞬间衰老。
时间总是在我们不注意时以飞快的速度流失掉。
一天中,钟表上指针的转动圈数描绘了时间的轮回,那是它的宽度,而在人身上则显示了时间的长度。母亲面孔的变换是时间的速度,也是孩子心中对母亲衰老的惊诧。
如果有人留意看看自己母亲的手,也许就会想到自己紧致的皮肤有一天也变得松弛,渐渐长出老年斑,血管突出,像树根的脉络,深深植入身体。
人也有轮回么,我不知道,如果有,我一定是母亲的轮回。
回忆,想象,梦境,在这一场景中交织在一起,坍塌的房子似乎在暗示一种崩溃,而母亲过去和现在的样子相继出现,也暗示着主人公的一种困惑。
5. 电话中的争吵
战后,现在;真实的场景,彩色
以主人公的第一视角拍摄房间的内景,墙上挂着《安德烈•鲁布廖夫》的海报,是他那幅三位一体画像。主人公和母亲在电话中交谈,主人公提到自己三天没有和别人说话,似乎是暗示与1之间的联系。主人公说自己梦见儿时着火的房子,问爸爸何时离去,这显然是在承接上面的部分。
他接着说:“为什么我们总是争吵?如果我做错了什么我道歉”。“我总是说你像我妈妈。”
妻子仰着头看向镜子中的世界,是一种高傲的神态,似乎对丈夫的每句话都持着无所谓的态度。主人公始终没有在镜头出现,仿佛在念一段旁白,让妻子兀自悲喜。
这样的安排让女人带着孤独无助的哀怨与矜持,两个无法交谈的人,只能通过镜子中那个虚幻的世界沟通。
她一直不肯正视镜头这边的他,说话像是一种自言自语。
她从镜子走向窗子,看向更远的地方,玻璃倒映出她疲惫的脸颊,与刚才倔强冷笑的神情完全不同。几株褪了色的红色植物衬得她的脸更加美丽而脆弱。
两个如此接近的人却隔着千山万水,就算登高眺望也无法看到对方的身影。这样的疏离来源于他们看待世界的态度,一个在镜中,一个在镜外,其实他们都想靠近彼此,但是男人与女人有时候就是无法沟通。
谈话间提到母亲在印刷厂时候的同事Lisa死了,引入下面的回忆。
6. 印刷厂
战前,过去;回忆的真实的场景,黑白
母亲以为在印刷时出了一个错误,据说是把斯大林的名字Stalin错误地印成了Shralin,俄语里面“大便”的意思,她冒着突然出现的大雨赶去印刷厂核对,塔可夫斯基使用了手持的长镜头拍摄,黑白的影像显得压抑而又焦躁。
当最终发现并没有错误之后,母亲告诉了Lisa原委,两个人大笑。可是后来Lisa指责母亲过分独立,甚至有些专横,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魔鬼》当中的李伯金上尉的姐姐,两人争吵。
母亲去洗澡,水却突然停了,她在浴室里面笑。
在母亲确定印刷没有错误后,她穿过一个两面都有窗户的长廊,光线交错着。长长的镜头配以A.塔可夫斯基的诗句,有关于相遇,等待,天气和命运。无论是突如其来的大雨,还是突然停水的淋浴喷头,以及那仅仅因为一个错字就可以让人恐惧的力量,都是一种像天气一样我们无法掌控的存在,我们生活在其中,就好像生活在命运的蛛网上。
这样的场景一直缠绕在我的幻想和梦境中,如今出现在了电影中,着实让人讶异。这里,母亲比任何时候都像达芬奇画中的人物,一个被命运掌握的人。光亮的走廊让人看不到尽头,充满了美好的期许人生,不过没人知道尽头的门后是什么,是黑暗,还是另一条走廊。
这是我一直的困扰,我的想象中没有尽头。
这一段结束于一个大火熊熊燃烧的镜头,暗示这同样是一段回忆。
[母亲跑往印刷厂的路上]
7.主人公与妻子的争吵,西班牙邻居
战时或战后,现在;真实的场景,穿插纪录片段落
妻子第一次出场,她在照镜子,主人公说他看到妻子的时候经常想起儿时母亲的面孔,两人争论主人公的性格。主人公说他同情母亲和妻子,而妻子则说主人公无法和人正常相处。
一个西班牙邻居说着西班牙语,模仿电视中斗牛士的动作。1939年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共产国际曾经将一批西班牙儿童撤离到了苏联,此后他们就在苏联生活,长大,乃至结婚生子,他们既没有办法真正融入苏联人当中,又再也不可能回到祖国西班牙。谁又能够想到,15年后,塔可夫斯基自己也成为了一个这样的乡愁满腹的异域旅人。
镜头随着那个西班牙邻居的回忆开始出现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纪录片,人们在街上奔跑,飞机投下炸弹,亲人们吻别即将撤离的孩子,哭声和告别的声音,最后在一声长长的火车汽笛中,一个小女孩转头面对镜头,脸上快乐的表情突然换上了惊恐,迷惑,大大的眼睛里面全然是不解。残酷的战争不仅仅造成了死亡的伤害,更让无数人失去家园,妻离子散,让许多孩子幼小的心灵蒙上了阴影,这一段纪录片使用在这里可以说是极为深沉而巧妙的控诉。
下面的纪录片片断可能是整部电影里面最美妙的瞬间了,一片寂静之中,是一只充满整个画面,硕大无比的同温层热气球慢慢升起,两只小一些的气球从两旁缓缓降落。
人类操控着这个比自己身体大了千百倍的庞然大物,飞向高高的天上,在夕阳中,镜头缓慢的跟随着辅助气球,这时响起了佩戈莱西《圣母悼歌》的终曲合唱,我的身躯终将腐朽,我的灵魂因着主而在天堂中永生。
这里是电影感动得我第二次流泪。
第一次记事的时候,这个世界给我无比庞大的感觉,那时候,什么都高不可攀,什么都没有边际,什么都不可预测。
也许长大了就好了,长大了可以不用再踮着脚够东西,不用叠个床单还要跳来跳去,不用总是听大人说这个小孩子不懂。
随着时间的变迁,这种渺小感却与日俱增,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愈发的强烈。命运钳制我的力量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开始学会相信。相信有些事情需要放弃,有些时候需要随遇而安,有些过去需要忘记。
还记得有一次同母亲外出发生车祸,第一次,死亡的念头扼住了我的喉咙,眼泪完全不受控制,血从腿上淌下来却没有任何感觉。
第二次,父亲做一次性命攸关的手术,事前他什么都没说,手术成功后才告诉我。当时我什么都没说,静静走进屋子里,不住颤抖。
而我看到电影中那个大气球时,眼泪就是这样掉下来的,那是种面对生命的无助,死亡的恐惧。
经历过才能体会。
在一段欢庆成功的纪录片之后,镜头回到了主人公Ignat那里,他正在翻看一本关于达芬奇的书,达芬奇曾在1550年左右提出过关于热气球的构想,书中有圣母和她的母亲圣安娜的油画,以及一些中世纪宗教绘画中常出现的手势。
[漂浮在空中的热气球]
8. Ignat读笔记
战时或战后,现在;想象的场景,彩色
妻子碰翻了包,Ignat帮她收拾好之后她走了,Ignat转身却发现刚才空无一人的房间中有两个女人,一个老年的仆人端着盘子离开了,另一个看起来像是50多岁的阿赫玛多瓦的女人请他读一段普希金1836年写给朋友的信,其中探讨了俄国和西方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异同,表达了作者虽然同意俄罗斯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历史地位,但是对于自由等等却有着相同的权利的观点,读信的时候,Ignat的身后,是另一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照片。当Ignat读完信,一个老年Maira形象的老妇人敲门,他去开门回来之后,却发现那个阿赫玛托娃一样的女人不见了,桌子上她放过茶杯的地方还留有印记,而这印记迅速的蒸发消失了。
主人公给Ignat打电话,回忆起自己的初恋,引入下一个场景。
[茶杯印迅速蒸发]
9. 军事训练
战时,过去;回忆的真实的场景,彩色
镜头中首先出现的是主人公初恋的女孩子,一个红头发,嘴上总是有水泡的小姑娘,音乐是普塞尔《印度女王》第四幕中的“他们告诉我你强大的权力”。一个始终认为向后转应该是转360度的孩子拉掉了手雷的拉环,他是一个战争造成的孤儿,就像塔可夫斯基镜头中的伊万一样。表面上冷漠的军事训练教官扑向那颗手雷,用自己的身体试图保护其他人,心跳的声音中镜头逐渐拉近,战争留在这位教官头顶的伤痕清晰可见。
那个孤儿孤独的走上山去,穿插进了苏联红军渡过克里米亚的西瓦什湖的纪录片,人们拖拽着物资,水面上漂浮着纸片,泥泞的浅滩上留下无数的足迹,远处苍茫的地平线映衬下,响起A.塔可夫斯基的诗句,“世上没有死亡,一切都是不朽的”。
那个孩子伸手抓住停在他头上的小鸟,纪录片变成了二战中解放布拉格的苏军装甲部队,拍摄战犯的尸体的记者,1946年比基尼环礁的核试验蘑菇云,1969年珍宝岛事件中冲突的中苏双方,海洋一样高举的拳头,紧攥毛主席语录的无数双手等等。
10.父子重逢
战时,过去;回忆的真实的场景,彩色
伴随战争和冲突的喧嚣的噪音突然消失了,父亲回来看望少年时代的主人公和他的妹妹,本来妹妹正在说要把哥哥偷拿7中出现的那本关于达芬奇的书的事情告诉大家,两个孩子一下子忘了这些,跑向父亲。父亲抱着他们,音乐响起,巴赫的马太受难曲当中的咏叹调,"Undsieheda!Der Vorhangim Tempel...",看哪,圣殿坍塌了!这是基督受难之后,上天的愤怒。镜头中接着出现达芬奇的画"Genevrade Benci",非常像刚刚出现的Maria的脸。
11.争吵
战后,现在;真实的场景,黑白
主人公和妻子争吵Ignat该由谁抚养,以及他的未来。妻子指责主人公不与母亲和解,窗外,Ignat在烧一些树枝,这是片中第三次出现熊熊的火焰。主人公和妻子忽然说到天使像火一样出现在矮树丛中,引导摩西,这谈话很快就引入了主人公的回忆。
12.童年的梦
战前,过去;想象的场景,黑白
这一段开始于主人公的自述,这里还是彩色的,他讲述自己总是重复同样的梦,然后出现黑白的水罐,幼年的主人公走过树丛,走向自己出生的房子,黑暗中突然出现孩子的声音,“妈妈”,正和4中开始一场梦的“爸爸”的呼唤相对应,玻璃破裂,一只公鸡飞了出来。和4中一样,风掠过矮树丛,布帘翻卷,树枝颤抖,树干弯曲,雨毫无预兆地落下又消失,环境的声响显得十分不真实。孩子试图打开一扇门却没有成功,门开了,母亲正在收拾土豆,一只狗走出屋子。
13.卖首饰
战时,过去;回忆的真实的场景,彩色
Maria打算把首饰卖给邻居以补贴家用,那位邻居显得傲慢而且相当的不友好。少年时的主人公Aloysha独自坐在客厅里面,看着镜中的自己,音乐仍然是9中的普塞尔。
孩子盯着镜中的自己,年轻、清澈的双眼,镜中出现了那个嘴上长着水泡的女孩。水嫩的脸颊,柔软的头发,手中拿着燃烧的树枝。
他们说小孩子不懂爱情,但是为什么那个童年喜欢的女孩总是不断浮现在眼前?第一个人让他有特别的感觉,即使是战乱,他都能在黑暗中想起她嘴上那粒水泡,连同着这样的不完美构成了童年美好的回忆。
接着,灯熄灭了。镜头中出现了牛奶滴在地上的场景,呼应着3中主人公幼年的回忆。
那位女主人在镜子中傲慢的试戴首饰,带着主人公母子去看她自己的孩子。母亲Maria显得有些不耐烦,女主人甚至提出让Maria帮她杀一只公鸡晚上做饭用,Maria试图拒绝,因为女主人说的恶心她也一样会感到,可是那位傲慢的女主人却一直是一幅高人一等的姿态。在恐惧和厌恶中,Maria接过斧子,按住公鸡,抬起头,那幅10中达芬奇笔下混合着冷漠,愤怒和高傲的神情再一次出现在她的脸上。对比邻居的女人在镜中傲慢的脸,,让母亲的坚强与不屈饱满起来。
母亲带着主人公愤然离去。画外音是A.塔可夫斯基的诗。
14.一系列的回忆场景
战前,过去;想象的场景,黑白和彩色
第一段是在13之中,他们离开邻居家之前,首先出现父亲的面容,然后是母亲浮在空中,巴赫的众赞歌前奏曲再一次响起,父亲说:“冷静,没事的。”母亲则说:“我想见你,不仅仅是我生病的时候。……我终于飞起来了……我爱你。”
在后面A.塔可夫斯基的诗里面,我们再一次看到风掠过矮树丛,那诗关于梦,关于记忆和遗忘,关于生命,关于探索和希望。风掠过矮树丛的段落和12里面并不完全相同。很多关于那座老房子的童年的记忆也都瞬间苏醒过来,镂着花纹的白纱飘动着,一束耀眼的光在黑暗中闪烁,走过去,是一个小孩抱着满罐的牛奶。
还记得,小时候喝的牛奶大多是装在玻璃瓶中卖的,倒出后残留的牛奶让玻璃透着乳白色的光,再慢慢从壁上滑到底部。
和平的时代,满晃着快要洒出来的牛奶,小猫舔舐着泼洒在桌子上的牛奶,战时就只能靠瓶底白色的印迹回想。
黑白画面一下子变成了彩色,幼年的主人公在游泳,年轻的母亲在洗衣服,老房子里面满是美妙的春光,12里面那只狗也以一种幼年的形象出现。
那是童年的木屋。富士屋顶,宽大的走廊,开阔的视野,屋外的荞麦花和风晃动,让整个童年都充满了纯洁的颜色。
塔科夫斯基曾为了让屋前长满白色的荞麦花,大费周折。但那便是他的童年。
曾经我的童年也是在充满了木头腐朽香气的小楼中度过。
从里到外都是木制的房屋,推开窗户的时候总会掉下很多木屑和沙土。几个孩子疯闹着跑上跑下会让它禁受不住一样吱吱呀呀地呻吟。偶尔还会有几只老鼠在杂物间夺路而逃。还有残破的椅子咯吱作响,炉子冒着热气,收音机里传来的音乐夹杂着噪音,有两只麻雀探头探脑地衔食着窗台上的馒头渣……一到夜晚,就有蝙蝠在低空下无声地呼啸而过,走近一些还能听到它们的翅膀拍打空气“扑扑啦啦”的声音。
我喜欢在高大的梧桐树下仰望天空,浮云翻腾着飘过,直到看得眼睛刺痛得睁不开。每到石榴结了果实,就趁那个厉害的婆婆不在的时候偷摘下来几个尝鲜。
那些笑声与房屋一直都在我的回忆中摇曳生姿。
就这样,在影片的结尾我才第一次看到阳光,从窗口斜斜地照进来,幸福的暖色,小狗在柜子上爬来爬去。
所有的梦,美梦,恶梦,结束了,都是清晨,结束了漫长的雨季,都该有这样的光照进来。
窗台上有被风翻动的书,幼年的主人公走向母亲,可是这时的母亲却是老年的形象。
[回忆场景]
15.主人公之死
战后,现在;想象的场景,彩色
一件想象的屋子里面,主人公躺在屏风后的床上。医生认为这只是个普通的病例,8里面那个阿赫玛托娃一样的女人提到5当中的喉咙痛失语,医生则说到了良心,回忆,另一个女人说到了内疚。是导演的良心在为自己的回忆而内疚吗?主人公说,我只是想快乐。他轻轻的抓住床边的一只小鸟,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把小鸟托起,让它飞了起来。
16.田野中的结局
战前,过去;想象的场景,彩色
接近黄昏,静谧而安详的田野中,响起了巴赫《约翰受难曲》的开场合唱,母亲温柔地趴在父亲的胸口,当父亲问她,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的时候,母亲什么都没有说,她低头,笑,眼泪却又似乎要流下来,她转头看向远方。
这时合唱队进入,开始了壮丽的合唱,“上帝,我们的主,你的荣耀遍布四方,广大无比”。场景也猛然转到了密林当中,年老的母亲带着年幼的孩子穿过树林去洗衣服,镜头拍摄林中的树丛,断木,弃置的废井,水罐。年老的Maria拉着两个孩子出了树林。镜头又切回到母亲,她转头回来,仿佛从对未来的想象中回到现实,她笑了,又继续转头看着远方。Maria带着孩子继续前行,回头看到年轻的Maira正孤独地站在如同十字架形状的电线杆下,广袤的原野,远处的森林,一切都笼罩在落日的余晖之中。合唱结束,孩子呼喊着。镜头退回到了森林之中。
[田野中的结局]
记忆——镜中的梦境
叔本华说:“人生的效果如同粗陋的镶嵌画,近看产生不了效果,在这上面几乎找不到任何美妙之处,除非拉开一定距离。”
如果一次只听一种声音就像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自然的声音,沉静的镜头,只不过记忆比电影还要来得真实、动人。不用建造,不用摄影技巧,不用现场的调配,一切都是瞬间的美感,稍纵即逝而又承载着不可替代的永恒。
记忆是《镜子》的主题,而回忆是塔科夫斯基表达的重要手段,属于童年的回忆,属于昨天的回忆。“唯有瞬间才是现存的”,于是我们常常渴望回复那段生命,只有那些不再可能倒流回来的时间,我们才能开始正视,开始珍惜。
可以抛弃时间吗,塔科夫斯基认为当所有人得到幸福时,时间便毫无用处了,它只不过是一个概念。
但是现实中,时间不是一条长河,而是一把刀,会留下伤痕,这些伤痕终身都会陪伴着我们。
*梦境一
孩子从睡梦中转醒,风压过灌木,父亲看着孩子,母亲在洗头,在母亲起身时,只剩下了她一个人,她努力拨开头发走向镜子,剥落的天花板开始坠落,雨从上面落下来。
第一次,我看着斑驳掉落的天花板,哭了。不忍看。
你见过世界坍塌时的样子吗,我见过。一如这样的梦境,安静得像是一片唏嘘。只是低头的功夫,世界就变得全然不同了。
同样的梦境曾缠绕在我的梦境中,那是不安的,惶恐的,辨不清方向的,连噩梦都不是。喧闹的叫喊声在我耳中嗡嗡作响,最后变成尖锐的耳鸣,整个空间都向我挤来,从四面八方,身体在一瞬间就可以消失了,成为一粒尘埃。
然后是夏日吵闹的蝉鸣刺入我的耳朵,是个太阳毒辣的日子,我在空荡荡的楼里穿行,整个院子里都没有人,没有声音。疼痛侵袭了我的全身,让我失去知觉,胃仿佛在熔化,穿透四肢百骸。
很多人在我脑袋中旋转,最后成为空白。
[梦境中的坍塌]
*梦境二
风压倒了灌木,孩子穿过树丛,走向木屋。长长的窗子上,帘子摇荡着像是忍受不住什么。屋檐上,雨似乎又开始下了。那扇孩子没有打开的门,忽然开了,母亲在削着土豆,狗走出来。
记忆有时会向我紧闭大门。我会忘掉电话号码,刚背诵过的文章,朋友的长相,要做的事情,像一个突然被扔出屋子的人,那时的我仿佛没有身份的游魂不属于这个世界。
而那些我一再想要记住却总是忘记的事情,会在一个闪念涌上心头,不分地点,不分时间,就那么硬生生的挤进来,让我久久失神。
记忆中镜子里的世界更像一种幻觉,发生的事情可以消失,不存在的事物却能瞬间充满画面。
镜子是虚伪,镜子是幻影,
镜子是逃避,镜子是毫不掩饰。
镜框中的方寸却能容下整个世界。
电影中的镜子无处不在,悬挂在墙上或是窗户上隐约的倒影,像是让人逃遁,又仔细地审视着人们奔逃的身影。电影记录了我们的记忆么?也许《镜子》正是塔可夫斯基对于自己记忆的审视。他在问自己:究竟哪些是记忆,哪些是梦境呢?
我们的记忆是如何保存的?我们是否必须借助一些别的什么来唤起自己的记忆?主人公回忆自己母亲当年的容貌,想到的都是自己妻子的样子,达芬奇笔下的样子。记忆穿过时间的河流,把我们和我们的过去联系在一起,我们是否因此永远无法逃脱自己的过去呢?
主人公一次又一次地梦见儿时的房子,牛奶罐,风掠过矮树丛的景象,开始的梦中的镜子,以及最后的场景甚至混淆了自己母亲年轻年老时的面孔,这一切都来自于我们记忆的不精确。我们的记忆是一种感觉,而不是精确的复制,就好像我们不会记得某一天刮了6-7级风,脑中只有那天风掠过矮树丛时,树枝摇动依次倒伏的景象。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记忆逐渐变得模糊,就好像逐渐发黄的报纸,退去颜色,最后,甚至无法和梦境的不真实加以区分,变得如同那些久远的梦一样动人。
记忆甚至会以类似于幻想的情况提醒我们,就好像在影片中Ignat看到的阿赫玛托娃一样,正是这一幻想的经历,暗示了我们导演对于阅读阿赫玛托娃和普希金的经历。
这些不精确,不真实,也正是记忆,梦境,镜中幻象的美妙之处。我们并不会和塔可夫斯基拥有同样的经历,但是我们可以分享他的感觉,分享他看到风中树枝摇摆的景象,分享那些温暖的,酸楚的,内疚的,愤怒的时刻,正像一位女士写给塔可夫斯基的信里面所说:“在那间幽黑的戏院里,凝视曾被你的天才所燃亮的那片银幕,那片刻,是我此生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并不孤单。”。
爱与牺牲
母亲在塔卡夫斯基的记忆中占据了很大的部分,使得电影很多时间都在讲述母亲。
也许只有像电影中的母亲这样的女人才有力量度过那样艰难的岁月。她的同事抱怨她的脾气,说如果什么让她不如意,她就会当作没发生过。母亲零乱着头发,惊讶的说不出话,像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人。这样的脸我如此熟悉。
接下来,母亲去洗澡,中途水停了,她笑了。
当一个女人在崩溃的边缘走了太久时,她的神经总是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非常敏感,身体像上满了发条的闹钟紧绷着。断了的水就像身体那根弦突然断掉了,那样的心情“言语抚慰不了,手帕揩拭不掉。”
在影片中,母亲总是在等待,坐在围栏上等,却总是空等,从窗户望出去,长板凳上放着个瓦罐,雨水滑落进去。
最后,她的爱变成屋前的荞麦,她的牺牲犹如最后放飞的那只小鸟。
世界是一面镜子
也许对于《镜子》每个人的讲述都会不同,就像不同的人站在镜子前都会有不同的光景。世界正像一面镜子,反射着人们的回忆和幻想,反射着人们的丑陋与卑微,反射着每个角落的悲伤与欢笑。
转载请注明作者:九尾黑猫
http://www.mtime.com/my/LadyInSatin/blog/5478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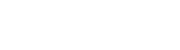




















火与雨,雾与光,温度与湿度,绿色与红色,彩色与黑白,缓缓而来。
黑白与彩色的闪回代表了战争与真实的残酷也有如彼此镜像之影~世界是镜像的也是虚幻的。矛盾的螺旋,心结的未解。没有人带你回到过去,没有人陪你老去,镜子里重重悲哀。
叙事结构与色彩转换都自成一派,不过诗意影像本身比条分缕析的阐释尝试更具直击心灵的力量。风吹草浪,气球,消逝的热气,崩落天花板,小鸟抛上;浮空,火屋与奶罐倾倒同[牺牲]。| 老塔惯用元素总结:长镜,极慢推镜(常至特写),巴赫,骤雨&漏雨,水沼&水草,燃烧的纸/叶/房子,马,狗,苹果,镜子,神迹。(9.5/10)
我认为这是最美的电影,像诗集,可以常常拿出来翻看。
诗性往往是表达未经言明的状态,所指越含糊、复杂、抽象,能指就越丰富、开阔、无定。已知意义的镜头语言就是死亡的非诗性语言。关于童年,关于母亲,我们无法在塔可夫斯基的镜子里简单的找到幸福、慈爱、坚毅、牺牲、善良、含辛茹苦等等对应的公度和通约的预设意义,它的表达在寻常理解之外。而这些提炼过的、很不日常的、无指向性的对话、情绪和画面,恰恰塑造了电影的诗性。
前苏联语境下塔科夫斯基的自传性电影,有些人做事就得有更多的人害怕,然后镜头就转向了墙上的斯大林。历史即镜子,水与火碎片似的不同时间黑白彩色交织的影像梦语,中国的片段也是一种对照,何况还有好多后世作品被影响对它参照的影子。北影节资料馆胶片版,每一部分的色调都不一样,巴赫的曲子配乐。2021北影节深影4K修复版改五星。
一切景语皆情语,一切情语皆景语。观众离内容愈远,便离影像愈近。一个终极的梦,无法诠释。
#重看#水的气息,火的热度,神秘扬起的风,犹在镜中,如在梦中;个体成长与历史进程的同步,撑起广袤时空,雨滴里的微观世界映照无垠宇宙;世事纷纭,时空迂回,只愿梦回童年木屋,打翻牛奶,目光流转过的静物储藏了父母相爱的时光。
4.5。草场那一幕太美了,仿佛风与心之所向,不同身之所往。当记忆、梦境与此刻交相互文,灵魂得以充当唯一的真实,而自察就是这首以镜为题的诗。—“语言无法表达一切感知,它们太苍白无力了。”—是啊,所以你需要电影,所以我们需要你的电影。【在豆瓣标记的第2000部电影】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这部电影,那就是诗意。老塔把父亲的诗转化成了影像诗,其实和「索拉里斯」讲了一样的主题,时间与记忆是人类永恒的命门,在人生有限的时间里,人类还要做很多错事。可回首一生,与自己生命相交的一切组成了一生的记忆,这记忆无论清晰或者模糊,终究如同镜子中的一切,可望不可即。所以可以笑着流眼泪,所谓悲欣交集。
同样拍记忆:伯格曼的介质是意识,是由内向外的。浓重的混沌感,灵魂出窍,情绪是受感染的;塔可夫斯基的介质是环境,是外界本身。流水、烈火、镜面,氛围澄澈,光影绝佳,情绪却是难以捕捉的。我能欣赏美,但美并不都为我所爱。这类电影就像窥看他人的记忆,我能产生耦合感,一样也能产生排斥感。
你说不复杂可我还是很费解.
電影中老塔的自傳元素並不能輕易地被按圖索驥。相反,這些自傳元素在疊加,交錯等穿越手法中,宛如鏡子的碎片一樣,需要觀眾去拼湊。另外,蘇俄前衛派Edward Artemiev的音樂跟電影中風起林響的場面結合得太完美了。PS:電影里有個穿幫鏡頭,難道老塔沒注意到?
与黑泽明最后一部《梦》一样,这是一部极其私人的电影,它是拍给自己看得。乡村随风起伏的树丛,城市公寓破败渍水的墙壁,镜子中一张张沉默的脸庞,被塔氏的诗歌和配乐晕成一幅幅如油画般的镜头。我们只能从中找到极小的一部分关于自己,剩下的属于千万影迷。
又看了一遍。伯格曼所言“宛若奇迹”,通片均是此感。依然只能仰望的作品。看到第三遍,终于明白了大概,忏悔的基调,伟大如斯!
镜子映照女人和少年遁去的第二面,镜头揭开创伤的同时也治愈了它。看完第一部塔可夫斯基,说不上被折服但是有几组足帧的空长镜头确实够惊艳!在随风荡漾的草波中踟蹰不定的侧影、在疾雨中奔跑跳跃的动人身姿、桌面上依循自身节奏而收干的水印、放射状路景带来的的视觉至心理撞击以及几处为缓冲激烈情绪而短暂停留的慢镜头都让我有一种被吸到画面里去了的感受。还有触动我的是塔的面部特写,说话者所说的内容被接收者全部置换到了脸上,主角光环立刻放大了数倍,从而对角色的内心世界能产生快速且主动性的共情,掐断观望喘息的间隙,一定程度上也减淡了晦涩成分。很喜欢穿插在首尾两处的诗篇型旁白,似一个第三视角的阐述,增加了影片的厚度。/能表现出自我与个体的关系,使个体分裂出的另一个自我保持独立存在:一个是“镜子”,另一个是“摄像头”。
父亲死于35年的“大清洗”。大火象征戰爭。成年后的“我”始终没有露面和父亲的缺席不谋而合。片头少年失语和片尾我的吶喊相呼應。风代表父亲,無形卻強大,聯係之後父親的夢中歸來,凱歌高奏。母亲是水,聖潔,卻被玷汙。西班牙内战,悲涼的苏联飞艇暗示社會主義理想的破滅,二戰,核爆,文革……
自然是一座神殿,那里有活的柱子。行人经过此处,穿过象征的森林——波德莱尔
第一次看,很懵,场景的切换和情节的演进是遵循塔可夫斯基私人的体验行进的。母亲淋湿长发从水盂中抬起头,天花板的白灰在暴雨中扑簌簌落下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尽管还不太理解,但这一幕给予我内心很大的摇颤。影厅里有个傻叉大声叫嚷让别人闭嘴,他最应当闭嘴,傻叉如果你是豆瓣用户的话,看到这记住下一场闭上你的嘴。
大家都在执着于把一部电影“看懂”,用一种贯穿始终的逻辑去解释它。但老塔本人其实是反对破解他的作品的。在他看来:<镜子>=艺术品,既无思想、寓意、情节、发展、结局,也不该滥用象征。观众离内容愈远,便离影像愈近。因此任何对电影的解读,也不过是一种自我投射。情绪直觉的触动与接近就已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