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演员过日子,举手投足就是一幕幕川剧,癫狂、苦涩、地道,烟火气刺鼻。百年的生活史,大大小小,就这样在舞台上下踉跄展开。陌陌影视陌陌影视游戏大作战疯狂大家庭休假2016极限17羽你同行伊丽莎·施莱辛格:去掉面纱说你爱我2007风云岁月黑暗自然荒唐小混蛋奇遇记萨拉尔海上乘客爱是美好的,生命是美好的满月酒 滿月酒洞穴客德古拉的新娘拣选第一季下一个就是你1998橄榄树之恋阿朵拉和她的朋友们SPECSaga黎明篇~慧的爱恋迪迦奥特曼:最终圣战 普通话版万圣节传说衡阳会战犯罪现场调查:纽约第三季太空堡垒卡拉狄加第三季什刹海手术室的故事第四季存身
长篇影评
1 ) 艺术为人民服务
#三刷 #TGC 04/12/2022
三刷达成,不能再看了,剧情上没有更新的感受了,细节上这次注意到给男主祭酒烧钱的时候,祠堂下的小辈儿拿着刘师长的小板凳出现,依然体现人物的一次次轮回。新中国成立后墙上的作画,之前也没注意到,这次发现是随着中国一起长大的,意义颇深。结尾人员表上注意到了片名字体设计和书法都出自导演的父亲邱志敏,真的是艺术世家。之前二刷有个点忘记了说,一个是老丘改造时砌的“向右倾斜的墙面”,后被砸掉了。还有…唯物主义财神和相信科学的牛头都够我笑一壶了!
继续吐槽…屏摄的太多了,坐第一排同排就有两人。
#二刷 #TGC 19/11/2022
二刷更关注细节,感触最深的是很多人物先出现在阴阳界中,再出现在回忆中,再搭配上牛头马面在回忆中大量的出现,让整部影片带有浓浓的宿命感,其实这也很符合导演在Q&A环节所回答的问题,影片对费里尼的作品进行了致敬,还有对很多默片时期的电影致敬,扔砖致敬的卓别林还挺有意思。
之前也没有注意到驼子和刘师长的死亡,照相之后马市长就接管了新又新,而刘师长应该就已经死亡了,随之一起走的还有驼儿,以喊驼子来打麻将开始,到最后在麻将桌上将他喊醒,整场戏拍的非常美,超现实感很足。
其实在一刷时候就有一个疑问,关于“吃人”的画面展现,视觉冲击感很强,这也引出了这次Q&A也非常想问个问题,但是还是苦于没有机会,希望下次有机会吧,标记一下问题:“整部电影在视觉上对于暴力和死亡都采用了非常戏谑和荒谬的处理手法,但是吃南瓜那里展现的残酷还是非常赤裸的,非常想知道这么处理的原因” 。
非常感谢伦敦场的组织者帮我问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得到导演的正面回答。
再感谢杭州场的小伙伴帮助我再次问了一下这个问题。
导演答:影片也只是在口述中阐述了吃人的清洁,南瓜被吃本身与吃人无关,而更多的是想表达大家对于这件事的和解。

#一刷 #OLWE #LEAFF 22/10/2022
影片整体表现非常不错,以小人物视角带大家走过那些时代,带有强烈的《霸王别姬》《活着》和《香蕉天堂》的那种大时代感。
影片风格上非常独特,可以说结合了舞台剧与电影,大量的舞台剧布景让我想起了木下惠介版的《楢山节考》,而且布景非常用心,一直存在的那墙上的破洞也一次次的陪着观众一起欣赏洞内的风景。浓雾一次次出现不光用于烘托阴间气氛,还在很多时候被作为过渡专场,还有水流般的布料,童趣的设计,唯美中透露出那种戏谑和荒诞。
叙事上以男主死亡为开始,牛头马面出场就基本奠定了影片的基调,死亡轮回之意明显,而且牛马记得次出现也都一次次的把死亡表现的更加平淡且戏谑,男主的宿命感就不说了,各个人物的塑造也是非常鲜活的,感觉这种解构还是非常有趣的。整体以倒叙形式回忆男主的一生,中途会在不同时期利用定场诗的形式转场效果非常好,而且各个把握得也很“巧妙”。而且四川的方言可以用于避免母语羞耻,让台词听起来更舒适。
视觉上,大量的使用侧跟镜头,让舞台剧效果达到一种空间上的扩展,深焦镜头的使用也带来了很大的信息量,变焦镜头对于角色的塑造也起到了很大帮助。还有几次推焦,虽然使用不多,但每次都很惊艳。构图还是非常棒的,不论是室内的对称构图,还是前景遮挡时的空间把握,都挺美的。印象比较深的是驼子看照相机的视角,去除了环境音后带来的紧张感还是非常爽的。
听觉上,可以说是传统和现代的一次次交融,出现了川剧的配乐到后期钢琴,手风琴的转变。
不喜欢的点就在于后期的配音了,很多时候口型对不上还是有些难受。
当然,要说影片的核心嘛,那当然还是,“艺术为人民服务”了。
最后确实需要吐槽一下候场时间,1个半小时,整整1个半小时,早知道去隔壁看场电影再过来了。而且场内还有屏摄的,请大家文明观影。
2 ) A counter-history of Opera
直接搬过来我在别的地方先写的英文感想了:
Those who are familiar with Chinese cinemas and theatres may easily spot similarities between A New Old Play and the 1992 film Secret Love for the Peach Blossom Spring at a first glance. Both films focus on individual experience under massive political turmoils in China from 1930s to 1970s and both directors make use of theatrical elements as well as distancing/alienation effects with great dexterity. However, as the title suggests, Director Qiu isn't ambitious to create a new play ( "Secret Love" is a milestone for contemporary play). His true intention is to bring the spirit of old play back to life in a new form.
Qiu reinforces his disbelief in Stanislavski's system, an approach imported from Russia into China that trains the actors utilising their conscious thoughts and experiencing the role emotionally, in a scene that sarcastically shows the playwright reading a Stanislavski's book in toilet while doing his business. Here, again, we can draw another interesting comparison between the farce-centred traditional Chuan Operas and (cultural) Revolutionary Operas that aim to instil nationalism and loyalty towards the party. The two represents diametrically opposite philosophies.
Like what is depicted in the film, the protagonist Qiu Fu first learnt to sing without quite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lyrics. Chuan Opera is more of a "bodily awareness and awakening" as mentioned by director Qiu. As time goes by, Qiu Fu eventually becomes an embodiment of clown-figure in his real life, displaying optimistic and frivolous attitude in the thick of every hardship.Revolutionary Operas though require spiritual loyalty and faith of the actors, fails to help its followers to find truth and navigate their lives, as seen from Ah Hei (Qiu Fu's son) and his friends' failed trip for truth in Beijing.
3 ) 名为《椒麻堂会》,实为浮世万千
《椒麻堂会》(9/10) 上周有幸在杭州看的点映,时至今日仍然回味无穷——在《霸王别姬》与《活着》之后,我们终于在银幕上再次看见描绘小人物与大历史的杰作。借用一句影迷的话,“电影”又活过来了。不仅是座无虚席的影院活过来了,在这片土地上隐匿已久的创造力、对“美”与“真”的追求似乎也活过来了。 邱炯炯导演将手工布景、川剧元素与他的写实而魔幻的画作融为一体,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独属于自己的影像美学。在剧场式的逼仄空间中,他借助简洁的摄影机运动和介于布莱希特与梅兰芳之间的表演风格,实现了一种“间离”与“沉浸”的平衡,让人在观影(或者说是观剧)过程中能够清醒意识到环境的荒诞与诙谐,但又始终维系着与角色的共情。 在惊艳的视觉风格之下,本片的文本同样卓越。影片以川剧丑角“丘福新”(原型为导演的祖父)视点展现了民国到文革六十余年的历史,对于不同时代的态度相当纯粹,既无政治谄媚也无苦难消费,无愧于“小丑精神”的自谓。在一百八十分钟的时间里,镜头跟随“丘小丑”游转在生死两界与往昔现实之间,将亦真亦幻的世界与悲欢喜乐的个体共同绘制在一幅长篇画卷中。这画卷名为《椒麻堂会》,而实为“浮世万千”。
4 ) 《椒麻堂会》:神话的灰烬,或少不入川
《椒麻堂会》是一部惊人的作品,“惊人”既匹配作品整体的呈现,也在其潜藏的野心。
考虑到导演及团队拿起画笔把片场变成了挤满绘画和手工艺制作的洞穴,影片就不能因为预算不高而被简单归入低成本制作,其中“惊人”之处也并非“花小钱办大事”。

形式感的惊人是一目了然的,在前述美术展级别的布景搭建之外还有很多:
无限趋近于平面的浅透视空间没有桎梏眼睛,偶尔还拍出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悠远意味。
演员站位如排兵布阵,任凭频繁横向运动的镜头点兵点将。全员素人演员本来是个难题,放弃同期声、全部后期配音却意外带来了“有声默片”的奇特效果。
一人逗众人捧的对话处理方式借自戏曲舞台,一方面降低了表演难度,一方面强化了“做戏感”,放大了导演预设的“间离效果”。
云遮雾绕暗淡无光的“阴间美学”并未止于阴间叙事线,人间情节的画面质感也如出一辙……

有意思的是,近乎溢出的形式感——大概也就是导演多次提过的“生造”——没有喧宾夺主之感,而是让命意暗流涌动、青筋隐现,两者充分互文。
《椒麻堂会》不是神话,而是神话的灰烬。
它荒凉、腐败、华丽、丰盈,充斥着怪力乱神的灵光。故事发生在导演故乡四川乐山,结束于主人公剧团老少在黄泉路上共饮孟婆汤的镜头,这个诡异的全家福时刻,使得剧中人的命运和长达三小时的观影皆如大梦一场,那句俗语“少不入川”又上心头。
从来只知,见“少不入川”即可想象川地丰饶,却极少乐意再进半步:朝日初升下的丰饶并不会腐蚀土地和黎民,反而会清泉汩汩,使少年成长为元气沛然的勇士或开拓者。
而每当临近历史时间的漫长尾声,一切丰饶惟有徒然化为腐烂败坏的红尘万丈,淌着黏液蚀穿时人心智体魄,让他们貌似圆熟实则弱小,其中佼佼者也只剩下仅够自我消解或自我旁观的力气。

有时我们会在“幽默”“讽刺”“达观”或“荒诞”诸词间择其一,去形容那些末世中的灼灼其华,主人公丘福新(以导演祖父为原型)正是这样一位人物,他是舞台上的新又新川剧团担纲丑角,也是一生悲苦不改笑颜的川地遗孤,戏里戏外共同的禀赋都是抽离于自身的苦难之外。
其实,乐山人鬼穿越、阴阳共处的世俗生活世界,本身也是一个灵魂出窍、自我抽离的结构。
在这个丰富依然而根底日消的天府之地,阴间不是地狱,而是人间的增生,人间的内爆。就像黄泉路上丘福新感叹的那样,纵然此刻他已死,“戏还没有唱完”。这种“人生如戏”,不是人在建构他的戏剧性,而是人只能服从施加于他的巨大而静默的命运。
乐山是川地的马孔多,川地则是神州的马孔多。贫瘠而匮乏令人安心苟活,丰饶而徒然则使人颓然难平。“少不入川”的晦暗一面,只可况味,不可言说。

祖父离世数十年后,导演终于着手面对创作命题,此时川剧的世界消弭殆尽,只存在于他幼年浸泡剧团剧场十载的记忆里。当然,影片要呈现的并不是川剧的灰烬,而是关于川剧风行水上的那个民间世界。
影片叙述始于1980年代主人公丘福新之死,面对牛头马面的“邀请”,他全无准备,诸般未了。现实中,从国共更替到改革开放,时隔四十年后川剧一度热度重燃,丘福新(现实中姓邱)此时正欲东山再起,却戏剧性地死于意外。
对于丘福新的艺术生涯来说,抑或于川剧的自发命运而言,1980年代的短暂热闹都只能算是回光返照,余烬最后一闪继而彻底湮灭。
实际上,主人公丘福新(包括他的同事们),他的艺术家生命在某个节点——确切地说是在剧团的创始人、出资人和保护人旧军阀麻儿消失无踪——之时,就“功能性灭绝”了,此后不过行尸走肉、炉火余温,历次运动、饥荒固然跌宕起伏,“毛将焉附”的艺术家丘福新无非一再神经反射、自我旁观。

影片尾声,丘福新饮完孟婆汤退出画面,镜头渐次展露满座剧团故人,众人皆饮孟婆汤。随后镜头回位,此时登场的是丘福新的孙子,也就是导演自己,他落座饮汤,全剧终。
不难看出,《椒麻堂会》是导演邱炯炯的告别,也是出发。现实中的他早已远离家乡乐山,多年漂泊在北京等一线城市。惟有离开,他才有机会把自己的先祖故园做成一部电影、一碗视听惊人的孟婆汤,让远达瑞士卢加诺的今日之世界,也能甘之如饴、饮而忘忧。
5 ) A New Old Play,一种犬儒式的奇观狂欢
一个小丑的严肃产生了这篇严肃的短评。
对于粉墨登场的“旧”历史,形式之间是平等的,因为几乎很难从形式之中得到除了美学之外的更多的内容。就像椒麻堂会,这部电影并没有任何新的地方,它就像是用新瓶装旧酒,这种相悖,新颖和保守,也形成了这部片子的感受。作者从当代观念艺术汲取了他所需要的形式,而不管在电影叙事还是文学理念上面都极其保守。由此漫画般的历史登场跟样板戏的区别并没有那么大。比如说对作为一种“电影技术”的平行剪辑的频繁的使用,一个为了控制电影时间以及观众注意力而产生的电影技术(与“工厂大门”和“火车进站”相比的“火车大劫案”),可能对另外一些严肃的电影人来说,这一技巧纯粹是多此一举:电影-图像的意味乃是激起内在的时间——新的时间-图像。
对历史的美学形式化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莫名其妙地映射在一种庸俗的历史主义之中。也许作者并没有对这一历史的划分有多么以为然,只是将其视为天然存在的结构划分而去强化它,这也许不能说是历史意识以及文学素养的缺乏,但却是对历史的无激情以及悲观(这是一部奇怪的没有引起任何欲望的电影)。这可能也导致了为什么在极端形式化包装下仍然是极度保守的历史观,这两者的对比是那么的强烈,以至于作者以尊重已然存在的观念为借口(甚至将怀旧视为是神圣的,这一敬意让人佩服),丝毫不在意其平庸性;而观者,自然还是为这部片子隐匿的历史的平庸性而感到困惑,而削弱了为其形式主动辩解的宽容。顾全叙事和形式比较完整的评论是困难的。
所谓的个体关注则虚有其表地分布在集体-私人回忆以及主角化色彩功能(比如说一种聚焦写作:“主角”可以看到来自冥府的使者)的一些情节之上。而事实上呢,个体私密被集体-个体书写中想象的“观众”扼制在所谓时代洪流的波动中(传记写作之中的读者)。于是记忆的幽灵变得更加的虚渺,真正的的个体历史在这一新的历史样板戏中,既缺乏力量又难以为继,不得不笼罩在历史连续性的阴影之下。
如果不将这部电影视为艺术上的犬儒,可能只是因为“历史”这个词语已经不再敏感。不过也是由于这种不敏感使得这部电影失去了一个重新涂抹history的机会,因为它的制作、美学包装下的隐晦以及营销方式保证了它难以可贵的自由。我仍然怀疑这是否也是作者如此浓彩重墨地去描述小丑的严肃想要达到的,这意味对过去的“改变”————这种改变就像是《信条》中通过“回到过去”重新认识过去来改变过去对现在的影响——正是通过真正的对个体历史的刻画以及神圣化,通过对其踪迹心无旁骛的跟踪(并由此产生叙述的形式,而不是将其归结在“时代洪流”中)产生解体历史叙事的描绘。对历史的描绘认识可能是断裂,而不是延续,因为只有断裂历史这一巨兽的脊骨,才有可能将某一个时刻所发出的微弱(几乎无法抵达前方)的光与自身联系起来。
当然也可以说作者意不在此,不过难以辨识的是,此种介入是否因为意识的阉割而导致的(稍显洋洋得意的)躲避游戏:带来了这一深陷视觉奇观狂欢的新样板戏。
6 ) 时代一粒沙:评椒麻堂会
“新戏从来演旧事,周而复始话沧桑。离合悲欢忘川渡,生死不外两茫茫。”——《椒麻堂会》
故事
《椒麻堂会》的故事,初见感觉很像《霸王别姬》,但随着电影剧情的深入,我个人倒是想起了波兰斯基那部《钢琴家》。
由阿德里安布劳迪饰演的波兰犹太裔钢琴家,在德国闪击波兰后,随家人一路流离失所,从最初还能在占领区的酒馆里弹琴补贴家用,到最后只能在炮火摧毁的城区里觅食维生。
片名虽叫《钢琴家》,但钢琴曲并没有奏响几次;就和《椒麻堂会》里的丘福一样,虽然贵为川剧“大艺术家”,但全片中丘福并未唱过几段戏。
钢琴家和川剧名角一样,都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颠沛流离、命如草芥。
影片开头就是打扮独特的“牛头马面”来到人间,把命将休矣的丘福带上黄泉路,剧情也由此开始,回忆起丘福的一生和国家历史的大变迁。
其中一段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丘福与妻子去茅坑偷屎的段落,几乎是理解全片剧情的最佳注脚。
偷屎当然不是为了吃屎,是为了找出屎里的蛆,烤熟了吃还能补充蛋白。
除了这一端偷屎找蛆的段落外,片中丘福自己还说,国共内战时期,由国军刘师长支持的新又新剧团必然式微,缺了戏台的丘福染上大烟,天天抽个不停,活得像个蛆一样。
人物自比为蛆,其实是形容主角从未脱离底层的生活状态,更是在时代洪流下像蛆一样寄生、苟活。
年幼丧父,又被母亲抛下,丘福偷偷地在剧团生活,受尽霸凌;成为名角没几年,战争来临,改朝换代,丘福一家只得随着时代潮流“浑浑噩噩”地活着。
因此,丘福先是被当做“戒除鸦片”的典型对象,在全剧团人面前“示众”;十年W/G时期又被打成“文艺黑帮”,必须服从命令接受劳动改教。
历史无情,人生薄命。
就像文章开篇所引用的那段诗句一样,历史就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而个体的命运总是免不了离合悲欢,甚至在动荡的大历史面前,人的生与死可能都无足轻重。
美学
在《椒麻堂会》的一场映后交流上,邱炯炯导演特别提及,电影中的美学灵感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祭坛画。
祭坛画全名为《根特祭坛画》,是由15世纪的凡·埃克兄弟创作的尼德兰绘画代表作,也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幅真正的油画作品。


邱炯炯导演说,由于自己是画家,他的影片是通过一个风情长卷的感觉来展开,让观众感觉自己是在看画。
同时,邱炯炯还在映后交流中表示,由于《椒麻堂会》是有关戏曲人的作品,所以选择了特别贴合舞台的表现方式。
在观影时我们也能感受到,影片采用了舞台剧式的布景,大量的远景都采用“假”道具或背景画来呈现,甚至很多可以用实景拍摄的部分,也用舞台道具来替代。


除了电影本身是有关戏曲的原因之外,导演选用舞台剧式布景的一个重要,和他想呈现的间离效果密不可分。
“我把握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沉浸到某一个个体里与它发生共情,而是希望通过一种间离,让大家达到一种观看的立体的效果,就是观众是可能会跳出来的,然后真正地意识到一个观看的存在。”邱炯炯说。
强调观者的角色,让观众意识到自己在观看,而非共情体验。私以为,这背后是导演想强调的一层隐喻:即超脱现实本身的戏剧感与真实悲情,就是对那段历史最好的诠释。
全片虽以真实历史为背景,但无一处呈现历史大事件的起因和影响,而当一团云雾升起,丘福和丘福的儿子都曾飞向天空,这些超现实的场景继续强化间离效果,提醒观者的观看属性;同时也在反复强调着那段历史的荒谬与可笑。
就像丘福的儿子升上天空,看到不同的两派青年剑拔弩张,他们不会去问派别形成的原因,只为了划分阵营、党同伐异。
在这里,故事的张力与美学浑然一体。
年代戏
从第五代导演开始,拍那段动荡历史的电影并不少,但我认为,没有一部能超越《椒麻堂会》
《活着》《蓝风筝》《霸王别姬》的故事都非常具有张力和冲突性,但《椒麻堂会》有一种来自底层的悲悯真实感,比如丘福和妻子去茅坑偷屎被发现,稽查人员认出丘福是名角,最终“丘艺术家”不得不用一场戏,换来一泡屎。
讽刺与苦痛尽在不言中。
不仅是故事,邱炯炯考究的、体系化的布景美学绝对技高一筹,这是第五代导演在相应作品中所不具备的。
最后的最后,导演在片中设置的小细节无处不在,比如那樽新又新剧团最开始祭拜的祖师爷像,在战乱中被迁走,又在新的政权上台后,被两位小鬼送去归西。
超现实的表现手法背后,新神赶走旧神,历史仍在继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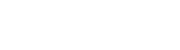




















在这样的年代仍饱含着对过往两朝历史洪流中人民日常生活细节的追溯,且以极为稀缺独特的艺术工作坊式的方法完成。历史大舞台下的他方唱罢尔登场,民间传说中的阴阳神鬼孟婆,以及随波逐流于期间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堪称精妙的历史群像画卷。而献世诸多霸占着的主旋律票房大户们在如此影像映照之下就更显其小丑之态,当下这样的年代是配不上这样的电影的。
年度华语第一,不过分吧。
非常幸运能在大银幕看到这部片子/当中国近代史的洪流穿过邱福的身体 溅出的是一代艺术家的绝唱
从《痴》《姑奶奶》到《椒麻堂会》,一路证明,邱炯炯是天才。
老又老,新又新。
下沉年代,喝下孟婆汤之前——肉体与魂魄一俱消失,记忆彻底蒸发尽遭遗忘,来自冥河忘川畔阴曹地府中途,主人公的一次次回眸,精神顿首。这部电影,是破译时代密电码的通天塔图书馆——而非单一实体书的密码本。旧时代成长的川剧名丑,努力唱新戏,交错于大烟梦与批斗喷蛆大会,被豢养、阉割、毒打,啼笑皆非。不插电、艺术家手工做派的摄影棚,时刻笼罩着掩盖真相与欺骗自我的团团迷雾,同一套班底不断串场,永世轮回,台词风味绝伦,素人演员朋友们实力镇场,小演员尤其机灵出彩。卸下所有、轻装上路当然是个选择,但那并不意味着今生没有虚度。《椒麻堂会》的巴蜀,是你看完电影,才惊愕察觉其存在的昨日世界。舞台还在,但很寂寞。人间犹存,却很荒凉。
没想到看到了目前今年华语最佳,心满意足了~
“韦斯安德森式霸王别姬”。作为四川人完全无法理性评价的一部电影,充满鬼气,看完手脚发凉。
"新戏从来话旧事”,一句话非但不指向新生,反而给大陆电影下了死刑判决,仿佛第五代的阴霾还不够窒息,第五代的叛变不够近在眼前,仿佛重写历史仍然是唯一的出路,而我们的观众又究竟要沉迷于陈旧的集体叙事,沉迷于咀嚼和反刍一成不变的窝囊到几时?导演的风格无疑是成熟且自洽的,但或许正是因为太自洽了,他和自己的世界一样一劳永逸地活在了阴间,不需要质疑自己在说什么,拍到了什么,他的人物又意味着什么:场面调度成了唯一的内容,但可供调度的素材又是几乎不存在的,因为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人的游戏。 A New Old Play演的究竟是什么戏?一个中国文人一脉相承的春秋大梦:想用一个集体叙事盖过另一个,最终发现无非还是同一个。
能在影院看到这样的华语片是一种巨大的幸福。 #SGIFF
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灵气有余,但导演很明显还不足以把控时间线如此之长的叙事。沉浸于自我表达,填的太满,会把电影变成形式大于内容的流水账。只有画面是不够的。3.5
看完这部影片会短暂失语,兴奋与惆怅同时涌现,你固有的审美秩序似乎变得失灵。只想说,我想再看一遍。
三个钟头过去了,旧时代也就过去了;年轻导演青胜蓝,中国电影新又新噻。
绝对五星,名副其实的华语年度最佳!荒诞的艺术,光怪陆离的社会变迁,《霸王别姬》的隔空对唱,模糊舞台和荧幕的扑面而来的丁达尔效应,极具个人色彩和地方特色的空灵的戏梦版的表达,文革时期向右野蛮生长的水泥砖墙,屎里找蛆的桥段。细节和记忆点很多,非常大胆,导演也极具野心。在釜山电影节看的,179分钟,中途走了几个韩国人,亮灯后也有几个韩国人昏睡在座位上,只有我和个位数的同胞在诺大的影厅里鼓掌到人潮散去
新戏从来演旧事周而复始话沧桑离合悲欢忘川渡生死不外两茫茫里面这几句印象深刻。
2021洛迦诺主竞赛-评委会特别奖+青年评审团二等奖。邱炯炯电影第二阶段开山作。「霸王别姬」做到的,「椒麻堂会」大部分做到了;「霸王别姬」没做到的,「椒麻堂会」做了很多。#年度十佳Mark#
伶人泛舟遙啊遙,遙過軍閥割據時,遙到蔣公掌權年代後,為溫飽,為屋頂,彷似在這個地方生命都只輪迴到兩件事上徘徊,再問不到究竟,只有苦,沒有悲。真正的悲劇是在自覺,意識下看到命運和絕望。又為何在這地方,大歷史下的伶人藝術生命都只求生存,而沒有藝術追求,一門手藝任由掌權者擺佈。這場百人大戲佈局了追求的正常生活仍在遠方,它還沒有向人們招手。新又新,只是重複又重複的命運,確實看著有種似層相識的感覺,也不是第一次看過類似的故事,比如我就想到張藝謀拍的《活著》,但邱炯炯甚至比張藝謀更接近余華原著表達方式,相似得要問,為何還要老調重彈(那英文戲名,new old play),是大歷史下的小人物們故事總是相近,還是有重說一段老話的必要。《椒麻堂會》重要,是2018年後的中國電影環境裡難得地出現了一部具地方色彩和作家主義作品。
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里说过:“暴风雨结束后,你不会记得自己是怎样活下来的,你甚至不确定暴风雨真的结束了。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早已不再是原来那个人。”
完全放弃景深的舞台剧呈现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但前景遮挡(?)的布置又成功拉出了纵深。其实好几个孩子的镜头似乎是回到电影场景给出了正反打,而不是像全篇这样保持观看的距离,但正是这种戏谑又苦中作乐的距离反叫其所书写的更加震撼人心。去成为眼睛,去成为摄影机。
这片土地上能拍的很多,能上映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