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刑满释放的洪忠都(薛景求饰)出狱后,家人对他横加排斥,而他之所以被判入狱,只是为了顶替哥哥的罪名。之后心冷意凉的他,来到车祸死者的住所拜访家属,遇到死者的女儿韩恭洙(文素利饰)——一名重度脑麻痹患者,面容扭曲、手脚抽搐。但忠都却被她吸引,并在冲动下做出大胆之举。 但在意外事件后,两人彼此都萌生了情感思念,孤独的心灵就此渐渐靠拢。他们看似身心不甚健全的非正常人,却遭遇着赤裸裸的现实不公。不过,命运并没有就此放过戏弄他们的机会。陌陌影视陌陌影视小姐全美缉凶: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通灵之六世古宅穿越时空的少女不结婚别惹流氓兔马修 第三季狂野之河(粤语版)海角惊魂深蓝即是黑和前任的第二次恋爱罗西塔风度中国孤独的美食家:笑料加量!当五郎遇上搞笑艺人范·德·沃克第四季宠物英雄巴瑞 第三季五彩神箭大都会传奇阿尔卑斯:自然的巨人新网球王子:冰帝VS立海约翰·木兰尼:J宝宝香水第一季网上鬼妻孤独的美食家 第一季假面骑士01 日语版甜蜜的家乡
长篇影评
1 ) 一个锯树疯子的自白
那幅画挂在她房间里,上头绣着几个洋文,我认得字母,O-A-S-I-S,不过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一见到那幅画,就知道它叫“绿洲”。真的。就像我那天提着水果篮上她家道歉,一见到她就觉得她特别漂亮那样。那天第一次见面,她拿镜子来晃我,我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不过我还是看得到她,她很漂亮。而且她不认得我,不会和她的哥哥一起来赶我,不知道我撞死了她当清洁工的老爹。
只有我和我的哥哥、弟弟知道那个车祸其实不是我干的,是哥哥干的。反正我也觉得坐牢没什么,我就顶上了。坐牢我不怕,里面有人骂我打我,没人瞧不起我。
我不怕再坐牢。我这次被逮进去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心里也难受,可能真的是做了坏事吧?第二次见她的时候,我想强奸她,她死命挣扎,可见她的次数多了,和她一起,那感觉反而淡了,我只觉得两个人说说话聊聊天出去溜达溜达是很美好很美好的事,和她在一起我心里就很安静,所以昨晚她不让我回家,要我留下来和她做爱,我一下没反应过来。我没有指望我能够得到那么多。我有点像小孩子那样不好意思了。但她问我,我不是觉得她美丽吗,我就没多考虑把衣服脱了。做爱的时候她像上次那样死命挣扎,好像很开心又像是感到痛苦,我有点害怕,可能我真的是冒犯了我和她的关系,我会得到惩罚,所以要我坐牢我也不辩解,反正他们不会相信我和这样的女孩会存在一种也许叫做爱情的东西。
我脑子很混乱。神父说,我是迷途的羔羊。
就在他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就冲了出去,警察在后面追啊叫啊我都不管,他们真以为我要逃走呢!其实,我不过是在神父说我是迷途羔羊的时候一下子决心把特想干的一件事给做掉,那就是坐牢之前先把她家窗外的树枝锯掉,让那幅叫绿洲的画在晚上的时候不会有阴影投到上面让她害怕。
哈哈!站在树上是多么开心啊你们没体验过的一定要体验一下我实在不懂你们在树底下怎么这么着急这样大呼小叫呢?我不过是把这棵树的枝枝丫丫锯掉让它们晚上不要晃来晃去拿影子吓人她会感到害怕的但是她又没办法自己去锯或者告诉别人去锯反正也没别人会想和她说话听她的话那些人还真当她是个手脚一直在抽筋话都没办法说的残废女孩呢!锯掉了这些树枝她就可以安心睡觉因为你们不知道那幅画上有一个印度女人一个印度小孩一头大象和像她的心灵那样干净的树林和草地我甚至有一天晚上还梦见我和那个女人那个小孩那个大象在一块一切都像真的那样哩!
树枝快锯完了我听见她在窗户里面给我放的收音机了。那是音乐那是她想对我说的话但是她爬不起来说不了话。
晚安,公主!将军已经完成使命。
2 ) 看一场绿洲
镜子的大碎片是鸽子
小碎片是蝴蝶
阳光晃眼
树影玄秘
我们的愁苦有所不同
看着我,当你残缺的时候
看着我,当你幻想的时候
“一个罪犯不可能真爱
一个病人不可能健全”
他们以为有资格评判别人的一生
人世苍凉
眼光鄙夷
内心呐喊换作轻淡笑过
真的,我也喜欢白色
并善于隐忍
善于等待
3 ) 《绿洲》:天真的人们能够爱
我想了很多天真的事情
它们全部都昂扬在生活的边缘
——臧棣《玉树,一小时的骑手》
李沧东倾向在他的电影中呈现粗粝、市井的现实世界。无论是街头、室内(家和公共空间)的取景,还是演员(主演以及群众演员)形象的选择,都非常靠近一般市民的日常生活。那几乎就是现实世界的复刻,想在电影里寻找浪漫和幻想的观众可能要铩羽而归。
《绿洲》拍摄于2002年,是李沧东的“绿色三部曲”的终曲。这一次,李沧东选择了最具浪漫潜质的爱情题材,虽然,是两个残障人士相爱的故事。男主角洪忠都,很明显有智力缺陷(因此主动顶替哥哥肇事逃逸的罪名而入狱服刑)。而女主角韩恭淑是车祸中身亡的受害者的脑瘫女儿,因为身体残疾而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只能在哥哥嫂子的照拂下勉强度日。这样两个人的相遇,始于洪忠都的天真善意——出狱后,他要带着礼物去探望死者的家属。类似这样莽撞冒失的事他已经做了不少,我们看到周围所有正常人的反应(陌生人的冷漠和愤怒,家人的厌弃和无可奈何),而洪忠都始终不为所动。他的残疾在于缺乏对他者情感的感知力,他不被他人劝服和打击,依旧遵循他的情感逻辑,执着于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
于是,在这样一次不合时宜的探访中,洪忠都遇见了被抛弃在搬家后空荡的房子里的韩恭淑——另一个同样天真的人。她出场的镜头十分梦幻,虽然面容因残疾而扭曲,虽然每一个动作都颤颤巍巍,但她却执着于摆弄一面镜子,使它在天花板上反射阳光。追随她的视线,我们看见一只雪白发光的鸽子在空中展翅飞翔。一瞬间,残破、混乱的现实空间飞升至不可思议的纯洁之境:身体被困,精神却能够在想象中自由飞翔。
然而,无人在乎、也无人愿意去理解一个脑瘫女人的精神世界。她的哥哥和嫂子接受了韩恭淑的残障住房补助,抛下韩恭淑搬进了新家。目睹这一切的洪忠都再一次发出了不合时宜地询问:“你们搬走了,你妹妹怎么办?”
没有答案,于是洪忠都本人提供了答案:他自己的电话号码。你可以说他被韩恭淑吸引了。也许是始于身体的吸引,但却更像一个孤独的人被另一个人吸引。洪忠都虽然身体健全,家人却同样拒绝接纳他。于是,他只能独自在黑暗中等待着一个电话,一个来自同类的讯息。
一场不可思议的恋爱似乎就要开始了。但李沧东的冷酷面就在这里——他从不塑造单纯的童话,而致力于还原现实的真实。二人关系依旧始于一场未遂的性侵,始于洪忠都失控的身体欲望(前有伏笔,后有照应)。之后,洪忠都仓皇而逃,之后,又怀着愧疚回来,承诺给她应有的尊重,这才开始建设二人之间的情感。
这几乎是笨拙的孩子的爱:一段段天真的谈话,为爱人彼此命名(一个是“公主”和一个是“将军”),在被遗忘的房间里跳舞(挂毯上的大象和印度女人也加入他们的舞蹈),他推着她的轮椅上街去,坐地铁、去餐馆(被拒绝后去他住的修车厂点外卖一起吃)。他做了一切自己所能想到的事,为了使她快乐。而在她的想象中,她拥有健康轻快的身体,能够和他舞蹈、玩笑——那是她真正的快乐。说来不可思议,几个飞升于日常生活中的奇迹桥段有着令人窒息的张力,而达到这种张力的全部梦幻不过是她拥有了一具健康的身体。于她而言那注定无法实现的梦想,却恰恰是正常人从未意识到的事。然而,就是这样被世人视为残缺的两个人却轻易地完成了爱所能达成的最艰难的事:构筑一个属于他们的世界。这也是世间最卑微最崇高的爱。卑微,因为他们对爱的需求竟如此天真简单;崇高,因为不计后果,不求理解。
他人对这样一份爱的误解是注定的。两个世界注定无法弥合——不是不能弥合,而是强硬、冷漠的现实世界全面倾轧着另一个边缘、脆弱的情感世界。人们对一切早已草率地下了定论:一个是智力缺陷的强奸犯,一个是毫无防御能力的脑瘫女人。在正常人(包括主角的所有亲人)的目光里,残疾人已经异化成非人,以至于他们无暇在两位主角身上无法看到一丝美,更无法想象两位主角具备任何符合人性行为的可能——而造成这一状况更深层的心理原因是:当人们居高临下时,他人的痛苦是不重要的,他们自己的世界才是一切。他们根本不愿意做出任何弥合两个世界的努力,他们宁可选择看不见另一个世界。
在电影结尾,被判强奸罪的洪忠都突然疯狂地逃出警察局,他来到了韩恭淑的楼下。那儿有一棵树,树的投影落在韩恭淑房间的墙壁上,墙上挂着一副画。画上写着:绿洲。韩恭淑曾说,在夜晚,墙画上闪动的树枝的阴影令她感到害怕。而洪忠都爬到树上,为了砍掉每一个树枝,为了毁掉这现实世界的绿,让树的阴影不再打扰那面墙上的“绿洲”。虽然,这只是一个被遗弃在破旧房屋里的“绿洲”象征物。而在人心荒芜的世界里,依旧有天真的人愿意相信它。
借此,李沧东审视着我们的所谓健全的人的社会:冷漠自私的洪忠都一家,唯利是图的韩恭淑一家,以及所有无动于衷的看客们(也包括屏幕之外的我们)。电影中被判定为犯罪的“性侵”案件,出于一份纯洁的爱。而正常人合法的性爱(邻居夫妇在韩恭淑家发生的性爱事件)却因压抑而显得分外病态。最终,这两个世界的善恶颠倒——以残疾人艰难构建的边缘世界的轻轻崩塌结束——却以这崩塌之力发出了对健全人的世界的反讽。
选择讲述这样一个故事的李沧东,更像是一个叙事诗人,只是他写诗的材料并非晶莹、洁净的词语,而是生活中一切被嫌弃、被遗落的事物:一碗豆子饭、一副艳俗的墙画、一个丑陋的微笑、一曲平凡人的歌谣(“如果我是诗人,我会为你歌唱。”)。这位诗人的确为它们歌唱了——而且以超凡的技艺将这一切沾满了尘土的事物净化为诗歌的结晶,这首诗极其细腻极其锋利,它几乎像出现在电影中的镜子的碎片。它们刺痛你,但你因此看见最纯洁的事物——所有镜片反射在墙壁上的光。
纵观李沧东的电影生涯。他在拍第一部电影《绿鱼》时已经43岁,因此,电影几乎没什么青涩的过度状态,而是一开始就已经具备成熟的风貌、之后只是不断走向辽阔和深邃。他带着一个中年人打量现实世界的目光:他看到世界是泥沙俱下的,其中,丑陋、世俗、恶是构成这个现实世界的主要部分。他从不回避和美化这现实世界,但他却更执着的是观察肮脏事物里的纯洁部分——他以全部的专注催动它在电影中奇迹般的生成。或者,不妨说,李沧东以电影重新定义了纯洁:纯洁不是人类童年时对于世界美好的误解,不是作为奇观和风景的某个远方,甚至不在人类过往的文明里,而是就在此处,它挣扎于无尽的鲜血、眼泪和泥淖,它脱身于令人绝望的庸俗生活,它尝过无数次人性的黑暗和恐怖,但它的内部依旧保持(或者幸存着)一份人类童年式的天真——这是李沧东的纯洁,《绿洲》的纯洁。
恰如黑塞在《悉达多》里说:“天真的人们能够爱,这就是他们的秘密。”
4 ) 剽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它讲述一个因为行为鲁莽,思想不成熟的社会边缘人和一个脑瘫女的爱情故事。
老罗曾经说过,剽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并进一步阐释说,只有两种情况他会解释,一是好友亲朋的误解,二是涉及法律,而这部电影的男主,连这两种情况下的解释都放弃了。本片就是讲述一对男女如何在巨大的社会误解中开始爱情故事的。
洪忠原这个人,28岁了,仍然保持天真,往好处说,他善良,热情,是个保持赤子之心的成年人;另一方面,他拒绝长大,拒绝接受社会的种种规则,不愿意或者学不会用『正常』的方式在社会存活,想要钱就偷(虽然这是他应得的),为了带脑瘫女出去兜风,就无证驾驶,还驾驶弟弟修车店客户的车出去一整天。他是个只顾眼前,不顾后果的人--在正常人看来,智力也不正常。
从一场未遂的性侵犯开始,他爱上了脑瘫女--后者他们能够心意相通,或者他觉得他这样的人,也就只配爱上一个残障人士。然而,他对待爱情和对待其它事情一样,是儿童式的。心智不成熟,一心对她好,用自己的方式去爱她,完全不顾世俗的规则(其实正常的爱情又何尝不是如此),最后在一系列因为他不愿解释或者觉得解释了也没人信的误解中,二人的爱情开出花来。
最后他们终于像正常的恋人一样,经过数次的约会,情到浓时,共赴云雨。这也变成他们爱情的巅峰,几分钟后,便急转直下。
电影的结尾是开放性的。悲观的结局可能他在监狱中被折磨致死(自己的家人有可能疏通警方,不让他再出来了),乐观的结局则可能他出狱后,和脑瘫女在一起,直到她死---但这个结局也不乐观,他们要如何在整个社会的巨大误解中生存下去呢?几乎毫无可能。
李沧东是作家出身,作家电影当然就是用平凡的事表达宏大的主题。
所以,从这部电影,难免让人想起一些哲学问题,Norm,社会范式和人性的冲突,是最先想到的。作者也许想说,在韩国这个社会,是不允许这两个人生活下去的,不能包容他们的幸福。他们想活下去,只能接受社会范式:即,洪忠原要好好工作,勤勤恳恳赚钱养活家庭,养活自己。而脑瘫女恭洙则要继续孤独的活在房间,看着墙上的绿洲挂毯,度过一个又一个绝望的日子,直到死去(她甚至没有能力自杀)。
社会范式是强大的,并且总是以『我是为了你好』为借口,将各种不合理强加于每个人。尤其是韩国这样的传统亚洲社会,并不承认人生的多样性,人性的多样性。这种社会先的人,首先『自阉』以适应社会(当然,官方的话叫『成熟』),然后对于任何有意无意不遵从或者挑战社会范式的人(这种人天然JJ大,不愿意自阉),不遗余力横加打压,必欲除之而后快。通常,前一种人虚伪,麻木,凶狠(以洪忠原的兄长为代表),而后一种人则天真,热情,单纯。中间的(洪的弟弟)处在阉割过程中。会有一点残存的人性--这就是为何两次去警察局保释他的,都是弟弟。
这部电影中的人,从各个主角,到一个小火锅店的服务员,莫不如是。
导演特地拍了几段脑瘫女幻想自己是个健康人时,和洪忠原的爱情场景。其实在他们心灵上,这种美好是存在的,仅仅因为她是脑瘫,这些美好就变成了嘲笑。这几段拍的凄美浪漫,对比现实,让人落泪。
5 ) 《绿洲》:关于被剥夺了语言的人
有人说这样的爱情是不可能存在的,我则要辩解说,如果人类本就是一种生来残疾的物种,那么这样的爱情只会是世间唯一可能的爱情。
我对于《绿洲》的基本理解是,这是一个关于被剥夺了语言的人们的故事。
无论是智力低下,还是脑瘫,这些都是呈现失语现象的疾病载体。也许非要选择一个脑瘫患者,更多是出于对影像奇观的需要以及为演员的发挥提供条件,甚至可以指责为一种取巧的做法(文素丽对脑瘫者的再现太有说服力,以至于我忍不住不断把电脑屏幕推远,仿佛那种残酷要冲破屏幕刺伤我)而这两种疾病的共同点,是他们对于自己境况的不可言说,因为这不可言说,他们的大脑被视为没有思维生成的封闭体,最后,连他们的生命本身都变成了没有生命存在的,任人处置的客观物。
在最后警察局那场令观众难以在伦理上难以忍受的戏份之前,李沧东已经展现了不能说话者被如何对待。女主人公的公寓是一个没有任何私密性的场域,钥匙被放在楼道的花盆里,可以随意当着陌生人的面拿出,任何想要进入这间房子的人都能轻易得偿所愿,因而她不能预测何人、何时、因何事会突然闯入她的房间(这也酿成了最后的悲剧)对于所有的闯入者,她只能被动接受,因而她对于强奸这种极端事件也是完全敞开的。残疾所带来的限制并不仅仅在残疾本身,比如不能自己吃饭,自己洗澡这般日常生活之上,它会修改整个生命的代码,改变每一个层级的运转方式。对于女主人公而言,并不是在事件发生之时,她没有力气抵抗,她的生命的实质,是已经被限制得只剩下某种被榨干的形态,心脏的机械跳动或者持续的呼吸。毁灭必然会发生,她只是在等待它而已。

邻居家的负责照顾女主人公的女人和情夫在她的房间里交欢,证明这里变成了一个合适的偷情场所,免费、便利,而偷情最需要的条件,则是无人知晓,很显然,女主人公虽然存在在这间屋子里,但她并不被视为人,偷情者无须担心她会告密,甚至无须担心她是否可以理解眼前事情的意义。当女人(也许由于平时那最低层次的照顾,虽然是连喂狗的精力都不及,但她尚且知道这一团扭曲的持续抽搐的肉体里有生命存在)略带迟疑地告诉情夫,“她在看”时,他以无法理解为什么需要担心这件事的口气回答“没关系”。在很多的电影叙事中,动物的目光都常被作为使偷情者(甚至是正当的情侣)羞惭的存在(比如《华尔街之狼》,我看的太少了一时只能想起这些,但应该有更多)而这里的脑瘫者是连动物都不如的,她没有令人羞惭的能力,她被降格为类似于一件家具一样的存在,不动,无声。她的观看不能转化为言说,观看就变成了只有输入的过程,输入的内容被大脑如何处理如何理解,因为出口被封闭了而永远不能被人知道,因而观看本身也失去了意义。
男主人公对于女主人公的意义,他作为“绿洲”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是唯一想要去破解那一连串毫无意义的能指碎片,在正常人所不能理解的语音中,主动去拼凑出一个连贯的句子的人,他带有鼓励意味地重复女主人公的话,因为她没有能力一次说太多的词,他作为一个补充的大脑,帮她存储那些已经费劲说出来的东西,使得她可以安心地接下去说,而不用为上一句话不被理解而焦急(在警察局的场景里,我们可以看到失去了男主的辅助,女主的话语如何不可能被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他意识到女主的理智存在,又或者说,他从来就没有质疑过这份理智。令我惭愧不已的是,她对于历史的了解,她对于爱的渴望,她最原始的性欲,她虽然缓慢,但是仍旧能清楚表达自己需求的能力,这些事实都在某些瞬间里引起我的惊奇,“不是所有的脑瘫都是智力低下”,这对于我来说是个新知识。
如果说女主人公的失语是直观的,男主人公似乎有非常好的语言能力,很多时候我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有智力上的缺陷,因为至少在现实中,我知道有很多的人只是因为坦诚和率真,只是因为不愿意去按照所有人都生活的那套规则去行事,就被视为怪人,甚至被认为是有某些精神上的疾病。从男主弟弟的口中我们得知,替哥哥顶罪是他自己的主意,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怪异的举动,因为它违背了人本性中的利己倾向,这是人们怀疑他智商不高的充分理由。当然,家人们是不需要理解这种行为背后的原因的,因为这种话语的施事结果正好符合他们的利益。在男主的话语和思维之间的关系上,家人们判定有一种智力的缺陷和精神的疾病造成了扭曲,因此男主虽然可以说话,但是不被相信。

在男主把女主带到母亲的生日宴会上,若无其事地告诉大家这就是哥哥车祸撞死那家人的女儿时,他毫不在意地反应使得众人的惊诧和愤怒达到了极点,似乎他只是带来了一个无关的人。如何可以在阖家欢乐的日子把整个家庭推向愧疚的深渊,而又不在语言上体现这种恶意呢,这是他的家人们所不能理解的。他的哥哥,也就是那场车祸的真正肇事人,无疑是最为不安的一个,因为男主人公不仅帮他顶罪,更替他愧疚,这是一种令人抓狂的僭越。事实上,男主人公本不应该有任何的愧疚,反而是哥哥,不仅理应对车祸的一家人愧疚,更要对主动顶罪的男主愧疚。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模式,男主应该表现出愤怒、痛苦、冤屈等情绪,然而他却反而同情别人的受害者,他的话语无法展现他对于含冤顶罪这件事的任何态度。为了使自己摆脱这种愧疚,将男主判定为智商低下的未成熟的儿童显然是最方便的做法。只有那个弟弟,尚存理解的企盼,尽管他根本不可能理解,他问出那句不会有答案的话:‘솔직히 말해 봐,지금 무슨 생각하고 있어?(老实说,你到底在想什么?)’其实男主人公在想的,他都已经说出口了,可无论是哥哥和弟弟,都坚信还有一些没有说出的东西,他们一面寄希望于男主是智障的的事实来消除自己的愧疚感,另一方面怀揣着男主装傻寻求报复的阴谋论,活在持续性的良心不安中。
在故事的高潮部分,男女主人公显性的失语和隐形的失语终于合流,他们无法告诉所有人他们恋爱的事实,无法让这种爱被众人认可。而对于众人来说,不能相爱,仍旧有活下去的希望,而对于他们来说,爱情的悲剧则等于人生的悲剧,一个再度入狱,另一个则失去了生的希望。
当看到有人在评论区询问为什么女主人公不解释自己不是被强奸的,我怀疑他是不是放了二倍速并且跳过了无数个段落,以至于他刚好理解到了情节的彻底反面。李沧东所展现的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女主人公如何声嘶力竭地想要表达自己,说出真相,她的理智是多么努力地想要冲破那扭曲的躯壳,被人听懂。她的焦躁却使得她陷入了不被理解的恶性循环,由于她的亲人早已放弃从具体的词语,而是从肢体语言上去理解她,因而她越试图说话,表现在肢体上的躁动就越会被她的嫂子理解为是经历了强奸之后的PTSD,并自以为是地帮她诉说她认为的真相,而女主就会更加着急,仿佛被堵住了嘴的人。情况就变成了:越想说话,就越被视为不能说话,越不能说话,就越想说话。对表达无望之后,女主人公遂用自己的身体砸向桌子柜子,试图自杀,或是用这种方式表达她对现状的否认,然而即使是这种尝试,都会被理解为是因为无法忍受被强奸之后的耻辱,因此她甚至被剥夺了选择死亡的正当理由。这是何等深刻的绝望。

男主人公又为何不解释呢?答案也很显然,只要他要辩解,他和脑瘫女孩是自由恋爱,是女孩主动想要和他做爱的,人们就会更把他当傻子,尤其是在他有强奸前科的情况下。傻子可以干的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声称自己不是傻子,男主人公似乎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没有做任何的辩解。他的越狱也只是想要和女孩子打个电话,在破碎的声音能指中再度确认她的存在,帮她砍掉树枝,消除绿洲上的阴影。他对于辩解之不必要的清醒认识,似乎说明他的智力也许还要超越常人。
有人说这样的爱情是不可能存在的,我则要辩解说,如果人类本就是一种生来残疾的物种,那么这样的爱情只会是世间唯一可能的爱情。它使用一种排外的语言,绿洲国的绿洲语,不需要他人的理解,只需要彼此心领神会。然而正如残疾人是少数群体,绿洲也是那些快要消亡的所在,它们不断被侵蚀,缩小,直至消失,总有一天,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绿洲,也不会再有少数人的爱情。
绿洲是相对于沙漠而言的,在这里,所有人理解所有人,或至少,所有人试图去理解所有人。只有当绿洲和沙漠不再有分别时,我们才可以承认,每一种爱都没有分别。可是,那样的世界是无差别的绿洲还是无差别的沙漠呢?我不得不以悲观的口吻似诉说这个现实:我们似乎离后者更近一点。

6 ) 公主殿下,等到我下次给你写信的那天
你知道所谓悬念吧,某学院文学系那帮教授们写了无数本书,无数的笔记教案,就在于教会课堂里那帮梦想成为大编剧的痴儿们,可惜不知道是痴儿们功利心太强还是教授们功力不够,学不会也没学会什么。
一个刑满释放的将军,一个脑麻痹的公主,外人看来这样一对太诡异了。一个被人认为品行不端,另一个是丑陋的代表,怎么会在一起呢?
将军的兄弟。公主的哥哥。其实他们才是真正品行不端+内心丑陋的集大成者。不过这些表面现象掩盖下的事实必须慢慢揭晓,所以就耐下性子来慢慢看吧。
公主说:
将军,其实你不知道,我多想像别的恋人一样,依偎着你,和你逗笑,唱歌给你听,和你跳舞。在家跳或在高速公路上跳,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只要我能像正常人一样体面地站在你身边。
文素利演得太棒了,原来她是一个那么好看的姑娘。
将军说:
殿下,我把那些吓唬你的树杈都砍掉了,他们以为我疯了,那有什么,我听见你的收音机广播了,我知道那是你的回应。等到我下次给你写信的那天。你想吃什么,列一个单子,我出来的时候给你买。
薛景求演得也相当好。一开始看到这么个吊儿郎当的混混,我实在讨厌,但接着往后看,想想也是,导演也够讽刺的,这个世界上,轻度弱智的人才具有真正的善和爱。不被世人所理解的感情与行为是最大的悲剧。他没有错,所有人都认为他错了,怎样说得合理?你们好好学学吧。
中间,公主在地铁站里给将军唱歌的那段,太感人了。如果她真的能给他唱歌该多好,他们该是多么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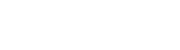




















那個,可能是我敏感,熱評第一的「連殘疾人都有人愛我還不如殘疾人的」言論也太刺耳了吧,無心無情無同理心。minimize harm什麼時候才可以成為common sense.
从两个单一的弱势群体的纯洁爱情来映射现实世界的残酷。女主人公的家人甚至都从不去关爱她,唯一真正关爱她的男主人公却在正常人眼里成了肮脏的强奸犯。原来真正丑恶的是这个世俗社会。
觉得电影里喜欢抓无辜的极端男女来爱情里报到。不是疯子就是绝症,不是犯人就是残疾。
打了五星的朋友们,如果我有暴力和强奸未遂的前科(撞人逃逸不算),第一次见到你就威胁,强迫你,然后拿着花去找你,说我爱你,你会歌颂我吗?(最后被突袭抢手机的女人真惨,不知道心理阴影要留多久。)
与之后两部片相比,李沧东还是太过倚靠演员,尤以这部最为明显,文素丽和薛耿求抢去所有风头,以至于一度对影片传达的内容失去兴趣,事实是,并非每个导演都能在头三部片邀来演技派助阵。倘若将李沧东作品以三部为界分开的话,后几部则在文本方面做的更为出色,当然,这话得留到《燃烧》看罢再做定论。
连残疾人都有人爱。我还不如残疾人。
忠都是蹲过监狱的边缘人,同时也有疾病在身(可能是多动症或者脑部缺陷),所以他看到恭洙的那一刻就像看到了自己。这是两个边缘人抱团取暖的故事,时而残酷如恐怖片:被亲人利用,被现实璀璨,被社会抛弃;时而浪漫如童话:蝴蝶、小象、恭洙的三段遐想非常浪漫,最感动的是高速公路跳舞和结尾锯树。
文素丽应该在想象中作为正常人健康一次,可李沧东让她正常了四次。这种重复不是加强,反而削弱了影片的力量。
生命中哪里有绿洲,只有沙漠和沙漠间的空隙而已。李沧东太残忍了。
极端的美丽爱情,女主突然从轮椅上站起来跳舞的一段简直美翻了,女人一生最美的时刻始终是在最爱的人眼中。。
他们是世人眼中的怪,却在互相的慰藉中活的逍遥自在。他是她身边高声歌唱的将军,她是他怀里美丽起舞的公主。他为她去砍社会恶意的枝,她为他盛放温柔的想象。可叹绿洲只能活在彼此两人的世界里,人性的荒漠最终把它覆盖。扮丑成这样,文素利的演技让人膜拜。
砍树枝的行为深深震撼了我,很难说是爱情,人类渴望摆脱孤独的需求强烈到超出身体的残疾智力的缺陷
以前在网上搜oasis相关的时候老搜到这部电影,搁置了几年今儿终于看了……怎么说呢,虽然认为这样的爱情不大可能存在,但电影却因两位主演出色的表演而极富代入感,试想,我们在怜悯电影里孤独可怜的男女主角时,自己在生活里又何尝不是个自私冷漠的角色呢。PS:男主角太像糕叔了吧!!!
薛景求、文素利的精彩出演。最卑微的人生开出最美的花。爱情最单纯、纯正的一面,感人至深。
房子后面的不是麻雀而是科鸣鸟,我的祖先不是将军而是叛国贼,如果这些都能搞懂,你便知道我不是强奸犯而是她的英雄,她不是智障女而是我的公主。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起舞,在绿洲里欢歌。若我给你变出消失黑影的魔法,或许你就不会害怕。可你为何要害怕黑影,我怕的是把撒谎当成熟,视相爱为耻辱的世俗。
6.5 最深情的一部李沧东,人物依旧出彩。他有擤不完的鼻涕,她有聚不拢的目光。男欢女爱,自然而然,只是社会容忍不了他们的自然——所以最后没有了阴影,也没有了绿洲。
看完这个感觉四肢健全而不能去爱上某个人简直是犯罪了
薛景求,文素利。炸酱面,豆子饭。(字幕翻译是东北人吗?薛景求长的像张艺谋)
1.高速上的欢舞;2.房间里幻想的舞蹈;3.努力割断的树枝;4.稀罕的情愫,傻子与脑麻痹患者,哪一边正常了,情愫也就消逝了,这便是现实;5.不满意邻居的“太不关心”和做个爱就突然被发现。
最近看了几部李沧东的电影,这一部给我很多期待,但最终是我很难喜欢的片子。生命的绿洲,蝴蝶的光斑,飞舞的白鸽,残缺的爱情,命运的讽刺,确实让人唏嘘不已,但是无论多么优秀的演员表演以及细节的处理都无法抵消三十分钟左右那场强奸未遂给我带来不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作为女性体会到的并不安全的生存环境,这种男性视角下的爱情和感动,连道德感有些薄弱的我都只能感到担忧,下班走在街上的女人,上一个强奸未遂的女人,我眼里满是这些无辜的人,已经无暇去顾及你们自顾自的,脆弱而灿烂的爱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