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照
剧情介绍
长篇影评
1 ) 找到樱贝壳的人
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作者:萌(来自豆瓣)
来源://www.douban.com/note/835960818/
孟梨看到那个典故时,有时是在白天,有时在外边她那个院子,这时她母亲有时在,有时就找不着,孟梨在使劲拔笳子了,就放宽点心。
这个典故是在说日本的一座故桥,孟梨又会想到芥川,他有一句话,原话是这样说,他行走在黄昏的一个铁桥,也可能早错了。那时,她记得她母亲就在右边,她躺着,背出来,外窗接近秋天,孟梨欣慰,这又是母亲感受不到病痛的一个正常天,外边也正巧刚下雨,来日方长,秋天滋味,酝酿无边,孟梨极致地去想, 那个男人,一点优势,一点点担心,最后舒出口气,朝天花板子伸直胳臂,她早在那座铁桥下边等着的了,母亲蜷成个美猫,白白净净,偎守床边,听见,听完,也没说出什么。那时空气真甜。
这桥下一直有人。
她想念中的桥,和这里的一个枯桥,极其相似的埋没,孟梨每回看都在拨开一种雾,在知道些底细下,故意隔绝,这种她自己造的忏悔,要不开一开,她就总看不到这样座桥。大体上说,是一个小僧,戴着大的菇帽,在桥底下等一双鞋。
还是专门为人送鞋而等人,孟梨这些年记不着,就混混噩噩地,就那么想进去。后来有了个行人,走到这桥下,大雨天啊,他没有雨鞋,小僧奉上,说,给他等天晴了,一定再送过来,不然……他就一直在这里等,等着。等下去。要是下暴雨呢,漫天大雪啊,要死人的!脚上没得鞋子,会直接冻掉,你也还在这等!?……就是。所以,所以你得守信。
小僧和行人告别。
由小僧负责看,行人匆匆远没背影,心念他刚才话,他绝对不会忘记,他也相信,因为亲眼见的就是那种眼神,绝对赤诚。
就这么过下去,一下就是数十年。
行人有了女儿,鞋子倒也没扔,可是主人是谁,谁也不知道了。有天,女儿大了知道打扫房间,看到了这里,扔前保险问了父亲,他一眼过去忽然记起点东西。他在这些年,他这一整个家庭,都不买这种穿在雨天里的鞋,最后才想起小僧。
整整20年的小僧。
他还会在那里?等着?他想起来都笑,但是有一天,他还是决定去,24年,小僧变老,站在洪水中,不走,行人他一眼认出来,他还站在那个大桥墩子下边,看到他以后,脸上终于不是闲适。
行人这时感觉手中鞋,已无多大意义。
我等你,一直就在下面,你怎么给忘了呢。行人有一时许多冤话,再说下天来也是他错,大错,时间铸就的,坚固、凝固,永远不给机会,改变不过来的失误。惩罚也将会是生命所给,小僧说不上几句,也接了鞋子还是没接,这里孟梨就记不住了。
行人接受一生悔恨。
当看见一种鞋,桥底小僧脸上从容,布施过来,路过难民般的行人,在俩方之间,孟梨就看那枝小木香长点。木香喜水但不能饱水,孟梨最害怕的是,一天大雨完了,出不了太阳,她就在根部撒点干土,培一培,木香花白,像鳕鱼肉,不好形容,但是她母亲会出现,她挑选那件典型白绸衣,印暗玫,走两步显现在枝丛,白木香上绽出月楼子。孟梨现在都放在橱子里边。
她也干过剪了麒麟再捏土的事。
孟梨认为她就是医生,看着窗下麒麟她就想以前,她很不能容忍,用剪子绞,把那些刺都干掉,所有挣扎向天的,连上绿色躯干,也像那些叶子,烟花喷射状的细叶,外缘变成光滑,就算看上去有些秃,孟梨觉得一切都还像她母亲原来样子,该是的样子,身体健康,圆润、齐整。然后补就,她往伤口上培土,椭汁样的鲜,汩汩滚在绿干,就是上了土,有些洇下去,接着流布。
这时从不让看见母亲。
孟梨做完了,就好看天,向着阴处,就又落后担心,她不是已经绞掉不该有的么,看来母亲还是不能如愿。听到耳朵小鸟声,时间已经过去六年,就有时追得回,有时她做的好,也不回来了啊……啊?
她母亲出现的时候,往往都是她出错时,就有一次来早,孟梨在祭拜,一张陋桌子,她没摆牌位,相片两张,点了柱香。
孟梨约好那天,她俩个姊妹要回来,就提前上敬,请柱芸香。拆纸盖,她闻着又在那年,和她母亲在四里山,在买假沉香。底座还是用的个莲花,小的,描蓝边,余烟刚开始拖不开,她就有点害怕,是母亲不高兴,用细镊子夹夹,一线灰蛇就出来了。
她听到古琴,就不想那年,为姥姥上香点开手机,是忆故人,现在觉得是形式,害人不浅。
形式。
幽兰气,冒出蓝烟,烧过母亲脸,母亲在冬天笑得变样,就变成了白的,正走到小小牌位四周,孟梨从不看,她一直认为,母亲——那里不是母亲,是有一个名字,但那不是母亲。今天圈住了,怎么不走,孟梨不得不额外看,再装作什么没发生,擦擦相框,摆摆苹果,那股烟还不散,孟梨发上恨来,用手摆了摆,烟接着就离开,牌位上,那个名字不得不落进眼中。
一块巨石,再次压到心头,孟梨闭上眼,平复身体上刺痛,但是她听到一个桶声,传在条长巷,没人要的空桶,被摔到砖地,蹦了两蹦,巷子传音,很荒凉。
她好像也看见有个人,被她短发遮住,孟梨人在祭台前转头,那截头发消失净前,她明明看到了母亲,她没脱小木香丛里那件绸绸衣。倒是温柔,可孟梨全回了头了,刚才是梦是真?后边是那个墙,挂着圣母像,护童男童女过桥,还好好的。
这时孟梨的大妹,三妹就进了屋。孟梨觉得她们应该没看见。
她们总有她们的事。大妹梳上头发来,盘着高头,气质有了,说话还是直,就是她问的孟梨,龙宋岳回来了么,孟梨回答被三妹盖住了,她嗓子结完婚更壮,最后姊妹三人都记住的,是她有喜了,最好应是个女孩。
大妹偷看了孟梨一眼,叹了气,孟梨看着桌上摆的,有奶油蛋糕,巧克力蛋糕,咖啡、苦咖啡,还有些酒心糖块什么的,微微笑着,感激了一番,不用说出底细。
吃饭时,大家拿出各人手艺,三妹蒸了条鳗鱼,孟梨特地跑到厨房,害怕它这种面相,盯着看好,总觉得鲤鱼会从锅里,和蛇样再钻出,等到三妹盖好,才走回到小厅。这时见到大妹,她看着母亲呢,一动没动,孟梨打断她,扶着肩膀问你做的还有没有,三妹已经快上菜了。她被吓一跳,不小心滴到孟梨手背上泪,彼此说不了什么,就又看回母亲。像野间炊烟,孟梨听见了,大妹说,她正给妈做着爱吃的,一块绿豆沙糕。
孟梨接着就想哭了,笑着回身,大妹身子朝前摆了摆,大姐那只手就离开了。
孟梨暂时回到小屋,床上这时可看窗,升起了点暮色,很奇绝,她想到育秧二字。这种豆糕好吃啊?以后孟梨再也没见这种绿豆糕。假暮色中有树,远树,母亲那个嗓子,越来越淡掉,孟梨往右习惯性歪头,这时倒没头疼,她看见一种厚糕,像个超大象棋子,里边尽是馅,绿的。绵延的甜气气,孟梨啊了声,把手拽一拽床单,四围很静,又想到吃这种糕的下午,她在看汪曾祺的书,早上是看的爱伦坡小说。母亲每天午休结束,4点左右和朝圣般的,到冰箱拿出红豆沙糕,绿豆沙糕,那时她俩已出嫁。
大妹怎么知道,母亲爱吃这种糕?
好了——!孟梨来到饭厅,才一会功夫,有薄鸭肉,有鲈鱼,有炒仁子,有大对虾,有红烧肉炖蛋,有白斩肉,有豆腐丝,有切瓣的松花蛋,有大肠子,有……吃那种做成火腿的松花,还是和她姥姥,姨姥姥的一席呢,老屋哪有厨房,她大姨夫赞妹妹贤惠,要是换个个,可没有吃苦精神,孟梨母亲笑着,在个写字台板上切这种肠。做下了她问大妹三妹还记不记得,之后就渐渐没了声音。
有的记错了,三妹说二姨姥姥那天穿白衣,大妹坚持那天她没在,孟梨记着没说,那天她穿上她母亲的,一件红花绸,巴洛克花饰,走街串巷,无头无尾的典雅,以后她姥姥去世第一周,她也穿。
大略就和今天这席面,欢声笑语的,但是比那次静点,后来想不起来,是谁先看的那个门帘。
三妹叽叽喳喳,犟是她帮忙母亲,还好留到了现在,大妹夹着口嫩肉柳,孟梨耳边陆续听到盘子声,门帘那就有了母亲,她还在40几,穿着夏天的胶鞋,实际在下边扶住梯子的,是她大姐孟梨。
是啊……妈妈说,嗯,这里,是说的……是,往右一点,啊?
嗯——不是,是我,她说我最聪明了,唉……是左,是左!我闷头想事,记着呢……
那天刚下过雨后,空气明亮,母亲是画的个娃娃,非要踩着铁梯子,挂好那扇子竹帘,最后到底出丑,这种事都得让父亲干,母亲也没让人叫,光线——雨后,北欧那种冷对,压上母亲的胳膊,叶子突兀张开,更茂盛了,干净的绿和白的皮肤,母亲稍一改变动作,孟梨这屋里就暗一阵,是十月金秋,云彩厚的,煞一阵开一块,人在底下心旷神怡,还有好多时间。雨汽不断,母亲在檐下按帘,孟梨在屋里。
姐姐既然想他,就跟了他。
这竟是小妹妹说的,孟梨一下子回到桌前,一盘煎鱼,现在调到她跟前来了。她继续听,有时是大妹在说,有时小妹就钻进,最后淹没在小妹的细嗓子边。孟梨嚼到那块细肉了,鳕鱼,母亲在时她不跟她去集,现在她经常从集上挑选。屋角的电扇呼呼转,小妹的头先转到的那边,大妹这一边,就更静,摆在她身子后边的松树,发出清香味,孟梨刚闻到外边就起了阵风,打捎的帘子咵咵的,鱼盘上有了大叶影子,接着下雨了。
母亲在雨天里,伸着白胳膊努力挂帘子。姊妹三人都看见6年后的妈妈,都以为是自己在帮忙,大妹就在铁架子右侧,是个简易拉梯,她亲自拿出来,倚住檐墙,下边凹道里,是那棵矮的无花果。小妹在母亲够檐时,终于憋住嗓子,怕她母亲紧张好再掉下来,手里托着个盆,里边是剪子、小镊子、螺丝刀什么的,小盆清蓝,底上是俩个小象洗澡,她说她和妈在2元店买的,实际也是孟梨跟着去相中。
孟梨在屋里。
她没帮忙,也在帮,用眼,她看见母亲一人,从头到后都是她一个,倒是伶俐,爬上去了,就是真正订帘时,往屋里问,是这里么,斜不斜?哦啊?歪了……?!孬了,歪了,啊。
最后母亲在竹席子外头,挂了匹字,丝的,上边写着,绿酒一杯,歌一遍,底下就没有了。孟梨在屋里。外边白布招摇,在绸边蹭下个小的东西,孟梨在屋里,看着像是个樱花瓣。
大姐?那张字呢?
这是大妹问的,小妹回答了,说这都多少年了,就有也变黄了,不如卸了。是吧姐?小妹回过脸,只孟梨在吃,她一直在吃着。
小妹有点惊,转回了头,三个人待的屋很静。
这一整天母亲都没有现身。
又是小妹先告别,她说要上街,闷的慌,后来大妹说要不给姐先捎来那个,省得第三天带上这么多东西,孟梨都笑着送出门。
回来了,屋里香气还有,孟梨索性坐在地上,盘起腿,就让脑子想一年,母亲在老宅烧香,那是为她一人专门烧,驱蚊,一种老玩意,说是栗子蒿,是真栗芽子,串成麻绳,拿手里是个鞭子,不能冲人,只在微角点,有时她母亲放在柱墩,有时就夹在厨房木门缝,但是她在屋里,隔片铁门,也能从门缝里钻进来,越来越呛,越来越苍,烧麦秸杆,你一出门就是烟雾,雾腾腾的,她母亲都说她,再晚点进去洗,熏得慌,她看着她妈先进去,给她吸进去点,等她再进去,就和个小蚊香一样,平淡了。
棕的,麻萎萎,底座是个圈,勾门勾道的好用。
那道香就烧到了尾。孟梨再敬一支,坐到小的紫蒲团,就想不起来要干什么,再盯住母亲了看一回。她在镜片中,看到活的母亲,就在圣母像周围,转。一声罄敲响,母亲消失不见。
母亲就有一次给孟梨对上句,她在乘凉,第二天就又见大妹三妹,她得洗洗那块布。说是乘凉,哪有大院子,她还坐在母亲左边,一块高出来的青石板,母亲那边现在还是石头,没变。她把那块布找着了最后,就塞在个拉箱,她也找着个本子,孟梨母亲最后笔迹,上边还担着心,交代要问的局名,字都写得大,生着气,她半责怪着自己收到那个蓝箱子。
把布平铺,看不出是绸了,这么多年,早僵,她白天补上后句,直到如梁上燕,岁岁长相见,但只怎么看怎么不好,乱了。她就听到一轮风,不像盛夏,是秋天刮过来的,孟梨坐在外面,一开始的白绸字,压上个裙边,她母亲不会再坐对面,可听到了那年一些声音。
真好啊,啊!就和秋天一样了,是,秋天哎?说来就来了,啊?
一俩个拍掌手声,孟梨捂住左膝盖,骨头疼,刮骨的疼,她只能捂,但笑起来,击掌引来了雨汽,膝盖更揪着窜上来,蜻蜓,断头的,地上蚂蚁,组队,夜间黄鼠狼,朝你点头,天上青云,青石板上秋影,白白的母亲,我们打从阿拉巴马来,还带着五弦琴,我们到路易斯安纳州去探望朋友们,最后母亲也唱,一个碎掉的字,一串字,一句,母亲右边的大叶无花果,孟梨这边巨大冬青,出厦前边的一棵百年老石榴。
雨汽,蒲公英花露水味,香水瓶上9号字,啪啪揍着蚊子,两只一扎壁虎,掉下檐头,各分东西,刚吃掉的凉面,明天的雨。
她再想不起来什么,想不起来了。母亲就走了,孟梨但记着她就在这晚,出过声,但其实也没有。
也是这天她做梦,好歹又见得着母亲,她但是在以前屋的窗子里边,在叠东西,窗框高孟梨看不见,那时她也好歹下了火车,这种穿行在纯旱田地里的,她觉得身边有人,看不见是谁,就这么一路欢歌笑语的,她看着方方窗外边,离人很近。最喜欢这种车!嗯,就是啊。就是,就走在人脚前。孟梨在心里对着,那人也听见得了,往后她就老被听一种纤细金属,就像旧电影里,陋巷子卖杂货,两根铁条条,噌——噌——来回擦一下,轮子和铁轨摩擦声,压过地草,伴着就过去了——几个站野田里看车男人,一个小孩子找草,三两个妇女竟抄手——他们马上就逼将过来,孟梨就安全地刮开他们,把他们又留到苦日子里,她向着好的日子早走直了。
不值钱的安全感,她总在做这样梦,经常在和母亲住过的街巷子,突然辟了条铁道,以后再不用多走路,从家门口就可离开家,能到梦里远方,离得破日子远,真的,在家门口,不用犹豫就看自己,说着就上车了,还回回坐中间连接厢子。有回特别宽,她身子裂长,回头冲母亲笑,她母亲眉头都开了。
刚下了火车,就降到老窗,母亲被看了会,蒙醒过来,露出白牙齿,她隔窗子,就看起来了,也不知道进去。
妈你还在这里啊。
孟梨梦外听见这句,醒过来母亲还是阵烟,今天立秋,但是晚立,孟梨一试一身汗,看着呼呼转的风扇。
更有一年深秋,九月底了,她和母亲等一年夏天,票都买好,忽然住的老宅,清代道光年间的,前边防空洞塌了,得修。她在里屋床上,看古代书信选,外边她母亲指挥工人,她老能听见母亲声音。
母亲倒是没扫兴,说着说着就会开心,和他们是一家,她可在床上越听越闷,心算又多添上这几天,发狠起身,外边都是墨绿,香椿遮天蔽日,石榴快接上了,满院潮气,到处是人,不如回来,那天她正看到,一个古人忆当年,怎么撑船过河,几年就都没了,孟梨看着心烦,扔到一边。
但是这几年她一想,就觉得窗户外头,浓绿无比,衬得她看的白皮书珍贵,那内容又好,谶倒先有。这几年什么都有,可那年再想也便成好的不得了。
天明了,又是阴乎乎,三妹把孩子也带来,一个女孩,叫梦,姊妹三人坐到矮桌前,梦就窜屋玩,也没有人陪。
妈妈最喜欢的花是樱花。
不对!是梅花,妈就是不带这个梅字,她说她也非常喜欢,有一年买过。
孟梨却注意牌位,正下放着个贝壳,就是樱花的。
这一周都是,大妹你就别走,陪三妹再看看童年那些街道。
四句话后,屋子又安静下来,孟梨左腰有股窜疼,把两手弯着举到嘴边,正能看着外头小院,三妹削桃,完了一只递给二姐,大妹刚想送孟梨,也就收了手,看着外边檐下绿叶子,静静咬了口大桃子,汁水都喝完后,朝着伸进的那枝,说龙宋岳是不是该也回来了。三妹只顾削小桃。
他说他要调走了。
大妹很吃惊,回头那眼睁得老大,三妹接上了,孟梨拿着小托盘说我再盛上点,离开到走廊。
梦站着,笔直的,恭敬的,她不动,那边是个墙啊,孟梨在这边对角,讶异了回接着回神,一只手,很温柔,透明,打开了,从墙里边,一段胳膊,那手便想弯,和梦有一个手距,孟梨几步过来打断了,一把搂住了梦。
很长一段时间,孟梨其实在责怪自己,她怎会不知手的来历!?
梦也看到,她竟是能看到,但是她回到母亲身边,还是玩起了小皮鸭子,静静的,有时听二姨笑,有时就瞅走廊一忽,回来还是她母亲在笑,孟梨经常注意梦这边。
第三天是雨后晴天,不易得,厚的白云,扯来扯去没完,堆在天上好看,云间是风,蓝的天透底。姐妹四人,做了野餐盒,到了大海边,不是远海的海上公园,就是碌对岛。
大人的裙子先飘起来,接着是梦的布裙,细灯芯绒居然也动了,惹得孟梨想起老多事,梦跳着,叫着,喊小姨你的绿裙子好看着呢,大姨我不喜欢你的红裙子。谁是你小姨,啊?还小姨,哈哈哈哈哈哈——你追不上的!
浪花翩纤,勾人摄魄,最后竟是三妹这个喜鹊,先回忆起母亲,她说你们看,那里是不是妈站的地方……快看,快看!一杀就没了。你快看啊,姐,姐,没了没了!啊……!
三妹最后发出了虎嗓子,大妹眼里含了泪儿,可劲地叨叨,我是看着呢小妹,可看着呢小妹可是……可,浪忒大了,一盖就。
就都得给没了。孟梨说完这句。原先,可能是母亲站的地方,她终于站起来,捱海,浪心,现在是浪涛在笑。
这天回来,孟梨全记起来,10年前,她就是在那个地方,捡到一个贝壳,很怪,刷着粉边,和个花一样。
这叫樱贝。
母亲说的,但是她以前根本不太爱好花。
吃午餐前,孟梨光听三妹说母亲母亲,怕她还是那脾气,拾起这个丢那头,最后再看把花给妈忘了带,往盒里放火腿时回了头,她和大妹在相片后头,梦的小头在上边,孟梨看着发笑,又回过神,仔细整理贡物。
一根大肠,她切了腰花,火腿她买的,上等品,几块熏鱿鱼,鲅鱼,鳕鱼,最后是细长香米。
你们看,妈那时多高兴。
谁啊?哪有妈妈啊。
什么!?
孟梨不打算回头,三妹老在重复这句,她神态就有点多意,越过沙发,探近头,怎么!?看了这么多天的相片,她亲手打开,亲手装上的照片,里边压根就没有母亲!她,大妹,三妹,在海跟前笑。
那一整个白天,她们都在母亲墓地,哪也没去,守着,到晚上孟梨送走俩姊妹外甥女。到实在没可收拾的地儿,她也没上床,又坐下来,这时已是下两点钟。她还在责备。
她逼着自己想,10个年头,想来想去,都没有,不添算好的。她开始责备,原来,这十年间都是她一人,在想母亲该干的事。假的就是假的了,真的不真实,孟梨感到天实在是冷,冷啊,就是最后连妈生前说的,都也是她以后她想出来的?
我……妈妈我,一定,永远是我们四人活在这间屋子。
她不会走开,这是孟梨自己想出来?
母亲,模样端庄,模样典雅的母亲,她应该出现在10年前的那个海边,应该看见了孟梨找到那个樱贝,第一个就见着,她应该是站在了孟梨的左肩头上边。
但是那天,是秋十月,母亲却穿着她那件印黄花的,纱绸短袖,脸上被海风吹过还是有汗,大妹却穿上棕裤,三妹也是裤,那分明是秋天。
妈妈——从离世那天开始——就已经走掉
龙宋岳说他这就离开,要到分局,那时孟梨因为母亲常现身,从来没想到答应,每次他来他走,孟梨根本不迈多步,光在檐下目送。
她不怪一切。她有什么资格来怪起别人?亲生妈走时,她还为的自己,让母亲的魂留住,一会儿是一会儿,此刻脸红。那么,有时母亲在小木香花丛,是怎么回事?有时母亲当孟梨削果,她就在后边,是怎么回事?有时母亲就光着站在浴室,孟梨在镜中看到,是怎么回事?有时母亲还很好,突然悲凄,突然百病,突然消失,是怎么回事?有时母亲不好看,她就走得快,有时母亲回归娃娃脸,站孟梨好看的花间,怎么回事?有时,只是有时,孟梨稍一过龙宋岳身板,母亲罕见笑,她听到过,怎么回事?
甚至那个日本典故,也是母亲亲口说,孟梨记,这些年再想,就认为是自己从头掌握,是怎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
往前,很多苦日,都是孟梨的,谁也再不抢,都是孟梨。她只能回忆,溢出边角,也对。单就这典故,让她感觉妈,她经常说的句,也从不在现实听见:都赖我啊。怎么会呢?孟梨每次听到都问,有时是灰天花板,有时是台风扇,有时是半露台外边的雨。
小僧不走,不是傻,也傻,这么大个人,没必要去专门等旧鞋,何况无故夺鞋的人,这样无情,忘恩。见小僧前,见些景,不有小僧一段老桥底,能见因桥栏有的雨后虹?他不知道,或根本知道,但只走,往前,昏昏走,走过美景,小僧站过,望过,顾过,因小僧才能有的最终结局,完美不露丑,出极大丑,落桥亡,泡洪水,漫天骇浪。不是小僧,他伸条手,借你鞋,你就忘了回家路,压根记不住,起不来。然他一直在,他在等。你忘记,不是慢慢,根本从一开始就不想记,努力去忘,去掉,去扔。小僧他其实很怨,他一直给时间,去等,还能记个秋天,他为你做过的事?他也不走,换个方式,变老,腿腐,成天价烘在脏水滩子。
到这里孟梨发现,赖我啊,都赖我啊,是她说的。
现在庭院已进深秋,有棵石榴靠墙,都黄掉,但是缤纷,孟梨有时贪看,一上午干的活放下眼还是,外边榴根底圈金,洋洒,映她这深屋亮粉,她觉她脸也是金黄,像缕缕金。每年修砍的香椿,孟梨看着树顶子,回忆一年擦边就走的大鸟,湖鹭鸶,那么大的野翅子,喊过母亲她都不信,简直如天上。看石头缝里草,点头黄鼠狼也不来,蚂蚁早有记忆,她母亲好用各种清洁剂,有时就飘来异香。
有时有风。
还会有风,大的,小风,阵雨天,好的坏的,孟梨就把牌位——彼此让它们透个气,有时让姥姥在右边,有时发现母亲和姥姥忒近,就再挪,上边放的吊坠水晶,不是她送的,还记不记?孟梨好端详日号,11年前九月,天可好,美花凉风,一阵阵的,姥姥坐过一种紫花前头,13年前十月,天大好,凉透,孟梨母亲就单独说,在个大学校园,藏满树绿屋里,她说以后咱哪也不去,就上这,周围静悄悄,冬天的腊梅还没开。
以后还会有十月,九月,还会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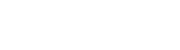
什么怪林伤痕文学
青春手摇饮?这是在干嘛?
看不下去
为了都海伊前男友看的,跪求电影里48-49分的歌曲是哪首?搜了好久没搜到
内容不能吸引我。那个被采访的珠熙漂亮却没留演员名字。看48分钟,跳了一下后面。宁愿跳也不用二倍速,看什么都从来这样,只有原速是享受,不喜欢就免谈。
既小清新,又有深度
片名很奇怪,内容也不太理解。
太无聊了,看不进去。
관계의 가나다에 있는 우리는
hancinema.net的简介:一直在用纪录片与不公正作斗争的敏奎,现在因财务问题试图退出。韩娜在放弃了她唯一的梦想花样滑冰后,正在为自己的身份而苦恼。朱熙在寻找亲生母亲的过程中即将面临痛苦。三人的旅程从寻找朱熙的母亲开始,变成了一个机会,结识了反对不公平裁员的吉他工厂工人,结识了在朝鲜有丈夫的老妇人,并获得了新的对韩国的看法。旅途中,三人互相照顾痛苦,各自寻找自己的身份。此外,敏奎和韩娜彼此产生了感情……呃,编排得略稀碎,就算两星半吧
中文译名 非常浪漫